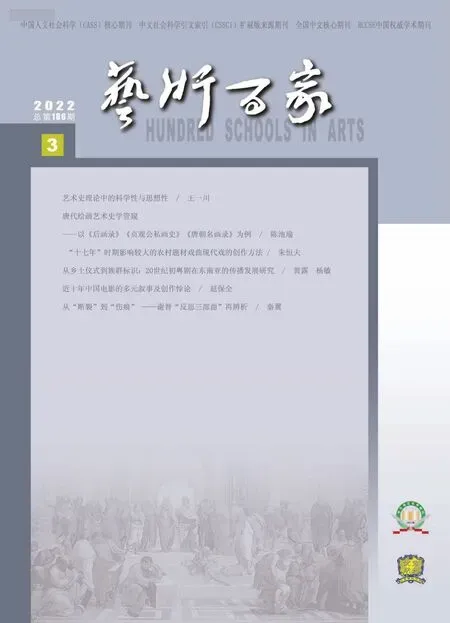紀(jì)錄片類型與風(fēng)格的歷史演進(jìn)與現(xiàn)實圖景
牛光夏
摘要:技術(shù)的發(fā)展和社會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的變遷,都可能催生出新的紀(jì)錄片形態(tài)。文章從早期紀(jì)實影片中以寫實主義為主流的最初探索、弗拉哈迪的人類學(xué)紀(jì)錄片對浪漫主義傳統(tǒng)的確立、前蘇聯(lián)和歐洲不同的現(xiàn)代主義詩意傳統(tǒng)、格里爾遜式紀(jì)錄片為時代鼓與呼的現(xiàn)實主義潮流、法國真實電影和美國直接電影兩大不同創(chuàng)作理念和美學(xué)風(fēng)格下的新寫實主義、西方新紀(jì)錄電影及其后紀(jì)錄片類型與風(fēng)格的多元與開放等幾個歷史時期,檢視一個世紀(jì)以來紀(jì)錄片發(fā)展與嬗變中類型與風(fēng)格的歷史演進(jìn)和興衰更迭,在此基礎(chǔ)上描述其多元共生的現(xiàn)實圖景和新的數(shù)字技術(shù)條件下紀(jì)錄片推陳出新的不同風(fēng)貌,以全球化視野梳理和構(gòu)建紀(jì)錄片類型學(xué)的譜系圖。
關(guān)鍵詞:當(dāng)代中國;電影創(chuàng)作;藝術(shù)形態(tài);紀(jì)錄片;類型與風(fēng)格;演進(jìn)
21世紀(jì)的第一個十年之后,我國紀(jì)錄片在生產(chǎn)創(chuàng)作平臺建設(shè)與國內(nèi)外的傳播推廣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jìn)展,引起社會各方的關(guān)注。在20世紀(jì)末開始拉開帷幕且日呈燎原之勢的數(shù)字媒體語境下,紀(jì)錄片的類型與風(fēng)格正在發(fā)生嬗變,涌現(xiàn)出了一些新的類型與表現(xiàn)風(fēng)格,折射了創(chuàng)作者新的美學(xué)追求,紀(jì)錄片領(lǐng)域呈現(xiàn)出一種生機(jī)勃勃的多元發(fā)展態(tài)勢。
紀(jì)錄片發(fā)展的歷史告訴我們,技術(shù)的發(fā)展和社會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的變遷,都可能催生出新的紀(jì)錄片形態(tài),自1898年盧米埃爾兄弟在巴黎卡普辛路大咖啡館地下室的放映活動之后,在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已達(dá)百年的歷史進(jìn)程中,不同時期不同國度有不同的居于主導(dǎo)地位的創(chuàng)作理念,這種流變貫穿于中外紀(jì)錄片的發(fā)展史,也孕育了不同的紀(jì)錄片類型。對每個當(dāng)代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者來說,歷史的眼光、比較的方法不可或缺。這就需要我們檢視一個世紀(jì)以來紀(jì)錄片發(fā)展與嬗變中類型與風(fēng)格的歷史演進(jìn)和興衰更迭,在此基礎(chǔ)上描述其多元共生的現(xiàn)實圖景和新的數(shù)字技術(shù)條件下紀(jì)錄片推陳出新的不同風(fēng)貌,以全球化視野梳理和構(gòu)建紀(jì)錄片類型學(xué)的譜系圖。
一、寫實主義為主流的最初探索:早期紀(jì)錄影片的稚嫩開拓
電影自誕生之初就以它稚嫩的面孔承擔(dān)起了記錄的使命,盧米埃爾兄弟的《火車進(jìn)站》《工廠大門》《代表登陸》等短片給觀眾帶來了最初的有著紀(jì)錄感的影片,建立起了非劇情片的傳統(tǒng)。他們的拍攝和放映活動使觀眾無論貧富尊卑,都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看世界的感覺。但盧米埃爾兄弟帶給這個世界的只是紀(jì)錄電影早期的較為原始的形態(tài),那些短片是對生活片段的簡單再現(xiàn)。“對兄弟倆而言,藝術(shù)并不是現(xiàn)實的模擬,而是對真人真事的直接的未經(jīng)修飾的紀(jì)錄”,相當(dāng)于今天安放于車站工廠大門口、街頭的監(jiān)控裝置所拍下的未經(jīng)剪輯的片斷,基本是一種寫實主義的紀(jì)錄。如巴薩姆所說:“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之前,非劇情片的寫實主義傳統(tǒng)已從拍攝日常生活戰(zhàn)爭及國外游景式實況電影報道中建立起來”。
盧米埃爾兄弟之后,19世紀(jì)和20世紀(jì)之交的紀(jì)實影像在“忠于題材中內(nèi)蘊(yùn)的本質(zhì)和結(jié)構(gòu)”的寫實主義風(fēng)格之外,還有一小股虛構(gòu)之風(fēng)與之相融共存。埃里克·巴爾諾在他的《世界紀(jì)錄電影史》中列舉了幾個實例,如曾擔(dān)任過盧米埃爾兄弟攝影師的杜勃利埃1898年所拍攝的發(fā)生在俄國南部猶太人地區(qū)的《德萊浮斯案件》,用的卻是與此案完全無關(guān)的攝于法國和尼羅河三角洲的鏡頭。美國長島和新澤西的雪景被用在了1904年比沃格拉夫公司攝制的《鴨綠江的戰(zhàn)斗》一片里,1905年《維蘇威火山》一片中火山爆發(fā)的場景不是在現(xiàn)場拍攝而是利用桌上景物模型采用特技攝影得來的,反映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的片子也是如此。英國制片人詹姆斯·威廉遜在他家的后院拍攝了發(fā)生在中國的教會被襲事件,在高爾夫球場拍攝了有關(guān)布爾戰(zhàn)爭的部分場面,1907年一部反映西奧多·羅斯福非洲狩獵旅行的片子,導(dǎo)演在攝影棚里拍攝了一位與羅斯福長相酷似的人擊斃一頭老獅子。這些例證說明“搬演”或日“真實再現(xiàn)”手法在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中早已有之,并不是20世紀(jì)后半葉才出現(xiàn)的現(xiàn)代人的新發(fā)明。
戰(zhàn)爭是人類矛盾沖突的最高形式,而戰(zhàn)爭使紀(jì)錄影片突顯了它的作用
隨著1898年2月15日美國停泊在古巴哈瓦那港的緬因號戰(zhàn)艦爆炸沉沒,美西戰(zhàn)爭爆發(fā)。“電影工作者第一次有機(jī)會去記錄真正的戰(zhàn)斗行為及為戰(zhàn)爭宣傳出力”。戰(zhàn)爭紀(jì)錄片滿足了人們戰(zhàn)時的信息饑渴,同時也展示了這類紀(jì)錄片強(qiáng)大的宣傳與鼓動力量。“這些早期的戰(zhàn)爭影片不僅首次使觀眾感受到觀看戰(zhàn)斗活動畫面的刺激,同時也喚起了輿論與支持戰(zhàn)事的情緒”。在此后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如埃里克·巴爾諾所言,電影攝制者成為戰(zhàn)爭宣傳員,他把此類影片稱為“軍號片”,把創(chuàng)作者稱作“喇叭手”。
二、浪漫主義傳統(tǒng)的確立:弗拉哈迪的人類學(xué)紀(jì)錄片
美西戰(zhàn)爭之后,在紀(jì)錄戰(zhàn)爭風(fēng)云之外,紀(jì)錄片還成為世界上一些族裔和部落的影像民族志。1922年美國探險家和勘探者弗拉哈迪所拍攝的《北方的納努克》作為早期探險電影的代表作品,被稱為影視人類學(xué)的開山之作。
與盧米埃爾兄弟及稍后時期歐洲寫實主義風(fēng)格的紀(jì)實影像不同,弗拉哈迪的紀(jì)錄片成為浪漫主義傳統(tǒng)的先驅(qū)。他選擇的拍攝對象都是偏遠(yuǎn)之地的少數(shù)族裔,盡管這些地方在他到達(dá)之前已經(jīng)或多或少地受到現(xiàn)代文明的浸染,苦難、腐敗或剝削也隨處可見,但他在片中成功地回避了這些社會問題。在后來拍攝的《摩阿拿》(1926)、《亞蘭島人》(1934)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1948)等片中,他均專注于人與自然之間的斗爭,而非著眼于人與人間的斗爭。他著力要表現(xiàn)的是這些地方自由的人們與他們簡單快樂、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活。他以浪漫主義的眼光和探險家的品性,以細(xì)膩的觀察力和豐富的想像力,把鏡頭瞄準(zhǔn)了在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逼壓和包圍下,行將被改變、滅亡或消失的另一種古老的遠(yuǎn)離繁華都市的文明。
當(dāng)他拍攝《摩阿拿》時,來到位于太平洋小島上一個只有百戶人家的波利尼西亞村莊,島上人已經(jīng)開始穿西裝。弗拉哈迪找到村里的酋長,要求他們穿上民族服裝,還特地讓一個男孩紋身——當(dāng)?shù)厝朔Q為“刺青”,而這種成人儀式幾十年前就已經(jīng)失傳了。儀式前的舞蹈慶典和化妝活動也都是弗拉哈迪按照當(dāng)?shù)孛褡骞爬系娘L(fēng)俗習(xí)慣搬演的。在拍攝《亞蘭島人》時,為了再現(xiàn)這個小島居民本來的生活面貌,弗拉哈迪專門從倫敦請來一位專家教居民用魚叉捕鯊魚。亞蘭島人的祖輩曾經(jīng)這樣捕魚,但弗拉哈迪拍片的時候早已改用蒸汽輪船了。所以有人稱弗拉哈迪的這種“重塑過去”的紀(jì)錄片是寓言式的、遁世主義的、浪漫主義的,但他在百年之前所做的這些嘗試和努力都是可貴的,由他發(fā)端的“搬演”和“情境再現(xiàn)”、交友拍攝、戲劇化敘事、較高的片比,對后世的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
他采取的與被拍攝者長期共處、實地跟蹤拍攝、藉以溝通了解并掌握其真實面貌的拍攝方式,成為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者沿用至今的一種工作方法。通過這種拍片方式,弗拉哈迪打開了通往人類學(xué)紀(jì)錄片的道路。今天,如何更好地與拍攝對象溝通相處以獲得更為真實自然的原生態(tài)現(xiàn)實,也仍是每個紀(jì)錄片工作者不得不面對的最基本的命題。但與早期那些“僅描寫被拍攝對象表面價值”的創(chuàng)作者不同,弗拉哈迪雖以一種直覺式的工作方法,如寫實主義影片一樣倚重大景深和長鏡頭來獲得空間與動作的完整性,但他的影片只是視覺上“看起來”像寫實主義,他善于通過細(xì)節(jié)的選擇與安排來進(jìn)行敘事,在細(xì)節(jié)的并置中使影片的浪漫主義風(fēng)格自然呈現(xiàn)。
三、現(xiàn)代主義詩意紀(jì)錄:前蘇聯(lián)和歐洲不同的詩意傳統(tǒng)
在20世紀(jì)二三十年代,蘇聯(lián)的維爾托夫和杜甫仁科都以自己富有詩意的紀(jì)錄開拓了紀(jì)錄片的表達(dá)形式與美學(xué)風(fēng)格,而且二者的紀(jì)錄影片都成功地兼顧了藝術(shù)和宣傳上的需求。而這一時期歐洲則出現(xiàn)了城市交響樂(city Symphony)電影,這種被薩杜爾稱之為“第三先鋒派”的紀(jì)錄電影流派,同樣是以非敘事的詩意紀(jì)錄為主要特征。
吉加·維爾托夫是電影史上較早探索紀(jì)錄片樣式并產(chǎn)生了較深遠(yuǎn)影響的一位紀(jì)錄片導(dǎo)演,他的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實踐具有濃厚的理論和實驗色彩。他反對敘事性電影,排斥故事片中的演員、化裝、布景。照明和攝影棚中的藝術(shù)加工,認(rèn)為攝制人員要“到生活中去”,成為“觀察的匠人——眼睛所看得到的生活的組織者”,攝影機(jī)就是“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的“電影眼睛”,主張通過蒙太奇技巧重新組織自然形態(tài)的實拍鏡頭,從而在意識形態(tài)的高度上表現(xiàn)“客觀世界的實質(zhì)”,他的《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1926)《帶攝影機(jī)的人》(1929)等影片在今天看來應(yīng)屬于詩意性質(zhì)的紀(jì)錄片,這些片子只提供相對較少的信息,而將更多的篇幅用于情緒的渲染,盡管已經(jīng)站在了紀(jì)錄片的“邊緣”,但還是因為其與現(xiàn)實密切相關(guān)的主題和情緒渲染受到了當(dāng)時觀眾和主流媒體的熱烈歡迎。
杜甫仁科在電影史上被稱為蘇聯(lián)默片時代諸位大師中的詩人,這位導(dǎo)演善于運(yùn)用象征與節(jié)奏,表達(dá)生存的艱辛與美麗、生命的延續(xù)與死亡的不可避免,以豐富的想象力來反映他所熱愛的烏克蘭農(nóng)民生活。在他的《土地》等富有濃郁抒情意味的片子中,貫穿了三個相互交織的主題:愛國主義、純真及熱愛大自然。導(dǎo)演精心經(jīng)營、刻意展現(xiàn)影片的抒情韻味和詩意風(fēng)格,包括豐沛的節(jié)奏感、如畫家般講究的構(gòu)圖、對時空的高度省略性跳接,這些視覺表現(xiàn)手法使片子敘事從容、富有韻律,呈現(xiàn)給觀眾的是詩意盎然的無聲電影,這種詩化風(fēng)格也深深影響了后世的許多杰出導(dǎo)演,如塔科夫斯基等。
維爾托夫和杜甫仁科都能把這種現(xiàn)代主義詩意和蘇聯(lián)共產(chǎn)主義的主題宣傳進(jìn)行完美結(jié)合,這種探索使他們的紀(jì)錄片獲得了強(qiáng)大的藝術(shù)感染力和生命力,使《持?jǐn)z影機(jī)的人》和《土地》得以在近百年之后仍被今人稱頌。
蘇聯(lián)維爾托夫和杜甫仁科的紀(jì)錄片是建立在寫實主義基礎(chǔ)上的現(xiàn)代主義詩意,而歐洲的第三先鋒派電影則是凸顯形式主義的現(xiàn)代主義詩意,它們同是詩意呈現(xiàn),但形式和內(nèi)容卻不盡相同。
19世紀(jì)20年代,處于無聲電影末期的歐洲出現(xiàn)了一個引人注目的電影派別,它是一個致力于對城市生活進(jìn)行萬花筒式描繪的紀(jì)錄電影流派,薩杜爾稱之為“第三先鋒派”。它極力抨擊故事片的創(chuàng)作法則,反對敘事,敵視情節(jié),主張“非戲劇化”,反對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認(rèn)為構(gòu)成電影的要素是“純粹的運(yùn)動”、“純粹的節(jié)奏”、“純粹的情緒”,著重于表現(xiàn)運(yùn)動、節(jié)奏和形狀。卡瓦爾康蒂的影片《時光流逝》(1926)是第三先鋒派的先聲之作,表現(xiàn)了一個大都市從清晨到黃昏一天的日常生活。德國的招貼畫設(shè)計師,同時又兼學(xué)建筑和音樂的華特。魯特曼1097年創(chuàng)作了《柏林——大都市交響曲》,建立了城市交響曲電影的基本規(guī)范,成為歐洲第三先鋒派電影的代表作品。“城市交響曲電影”未能完全脫離早期先鋒派電影的影響,在反對單純的敘事方面與之前的先鋒派電影相似,它放棄情節(jié)和演員。在表現(xiàn)內(nèi)容上則以城市生活的一天為線索,按照交響曲的樂章和節(jié)奏組織結(jié)構(gòu),展示萬花筒一般的城市面貌。在那樣一個機(jī)器崇拜的年代,火車、汽車、電車是最具城市特征的意象,通過紀(jì)錄這些象征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的城市物象來強(qiáng)調(diào)城市帶給人的速度、力量和節(jié)奏的新體驗,著力于表現(xiàn)運(yùn)動感、節(jié)奏感和形式感,這些影片涉及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交通、餐飲以及社會各個階層的日常活動等等)。
城市交響曲紀(jì)錄片的余韻一直延續(xù)至今,并獲得了新的發(fā)展:拍攝技巧更為先進(jìn),題材范疇逐漸擴(kuò)大——從城市擴(kuò)大到鄉(xiāng)村,甚至將整個地球乃至整個宇宙作為表現(xiàn)對象,主題思想更加深刻。最近這些年產(chǎn)生較大影響的交響曲式紀(jì)錄片有美國導(dǎo)演高夫瑞·雷吉奧的“生活三部曲”,即《失衡生活》(1983)、《變形生活》(1988)、《戰(zhàn)爭生活》(2002),以及羅恩·弗里克的《Baraka》(1992,中譯名為《天地玄黃》)。這類紀(jì)錄片還被廣泛運(yùn)用于城市形象宣傳,如我國的張以慶拍攝的廣東佛山市城市形象宣傳片《聽禪》(2011),就屬于這種類型的紀(jì)錄片。
四、為時代鼓與呼的現(xiàn)實主義潮流:格里爾遜式紀(jì)錄片
英國的約翰·格里爾遜熱衷于投身社會改革,認(rèn)識到在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里,電影和其他各種大眾傳播形式將在某種程度上取代教堂和學(xué)校,成為用作教育和有效影響公眾輿論的媒介手段。他將紀(jì)錄電影發(fā)展成為聲勢浩大且影響波及全世界的運(yùn)動,不僅創(chuàng)立了英國紀(jì)錄電影學(xué)派,而且領(lǐng)導(dǎo)了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的紀(jì)錄電影運(yùn)動,所以他被譽(yù)為“世界紀(jì)錄電影的教父”。
雖然格里爾遜把弗拉哈迪奉為自已的老師,但他并未遵循弗拉哈迪的紀(jì)錄片理念與創(chuàng)作模式,對弗拉哈迪迷戀那些偏遠(yuǎn)之隅未開化少數(shù)種族的生活頗不以為然。他力圖把紀(jì)錄片作為有力的教育手段和社會工具,以之來影響社會發(fā)展,他也毫不掩飾自己對于紀(jì)錄片的這種政治功利主義的主張,曾直言:“我把電影看作講壇,用作宣傳,而且對此并不感到慚愧”。格里爾遜提出紀(jì)錄片要關(guān)注現(xiàn)實,他認(rèn)為在攝影棚里攝制的故事片大大地忽略了銀幕敞向真實世界的可能性,只拍攝在華麗的人工背景前表演的故事,紀(jì)錄片拍攝的則是活生生的場景和活生生的故事。格里爾遜的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理念傾向于實用性有效性和理性。他對紀(jì)錄的興趣首先不是把它看作一種藝術(shù)形式,而是將它當(dāng)作一種影響公眾輿論的手段,他將電影比作“打造自然的錘子”,而不是“觀照自然的鏡子”,所以他把紀(jì)錄片定義為“對現(xiàn)實的創(chuàng)造性處理”。他認(rèn)為隱藏在紀(jì)錄電影運(yùn)動后面的基本動力是社會學(xué)的而不是美學(xué)的,希望紀(jì)錄片成為一種協(xié)助政府傳播主流價值觀念啟蒙民眾的工具。
英國紀(jì)錄電影學(xué)派涌現(xiàn)了一批優(yōu)秀作品,如格里爾遜的《漂網(wǎng)漁船》(1929)、阿貝爾托·卡瓦爾康蒂的《煤礦工人》(1935)、巴西爾·瑞特的《錫蘭之歌》(1935)等優(yōu)秀紀(jì)錄電影,贊美工人們的勞動,針對特定的全國性議題和公眾關(guān)心的問題,他們還拍攝了密切關(guān)照現(xiàn)實的紀(jì)錄片,如埃德加·安斯梯和阿瑟。埃爾頓的《住房問題》(1935)、哈萊·瓦特和巴錫爾·瑞特的《夜郵》(1936)等,把現(xiàn)實題材、詩意表達(dá)與社會教育結(jié)合在一起,以實現(xiàn)紀(jì)錄片的社會價值。
格里爾遜的紀(jì)錄電影理論在不同意識形態(tài)的國家里得到了運(yùn)用,如德國女導(dǎo)演萊尼·里芬斯塔爾應(yīng)希特勒之邀所作的《意志的勝利》一片,被后世譽(yù)為“史上最成功的宣傳片”。正如巴爾諾所說:“紀(jì)錄電影政治化,并非格里爾遜所創(chuàng)新,而是具有世界性的現(xiàn)象,是時代的產(chǎn)物”。舛他的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理念孕育了主題先行畫面加解說的紀(jì)錄片模式,被稱為“格里爾遜模式”,其典型特征是“上帝之聲”、證據(jù)剪輯和全知視點,借助于解說詞來表達(dá)思想和立場。
格里爾遜模式迅速影響到世界其他地方,并在此后近30年里成為世界紀(jì)錄電影的主要模式。在美國,導(dǎo)演帕爾·羅倫茲把格里爾遜模式演繹到了極致狀態(tài)。他拍攝的兩部在世界紀(jì)錄片史上極為經(jīng)典的紀(jì)錄電影——《開墾平原的犁》(1936年)和《大河》(1937年),分別反映美國中部平原濫墾導(dǎo)致的土壤沙化和密西西比河的洪水泛濫成災(zāi),這兩部探討生態(tài)保護(hù)問題的片子引起了羅斯福總統(tǒng)的密切關(guān)注和資金支持,也推動了羅斯福新政的進(jìn)行。
“二戰(zhàn)”期間,格里爾遜模式的紀(jì)錄片不僅被英美等反法西斯同盟國廣泛使用,用以揭示戰(zhàn)爭的威脅和本質(zhì),鼓動大家為國家和民族而戰(zhàn),如英國的《傾聽不列顛》美國的《我們?yōu)楹味鴳?zhàn)》,而且作為法西斯軸心國的德、日、意也都制作了很多這種模式的紀(jì)錄片用于戰(zhàn)爭宣傳。
這一創(chuàng)作模式在中國曾壟斷主流形態(tài)的紀(jì)錄片達(dá)40年之久,主題宏大、畫面配解說的專題片是主要的類型,當(dāng)20世紀(jì)90年代紀(jì)實美學(xué)受到中國電視人的熱情擁抱時,“格里爾遜式”一度成為一個頗具貶義色彩的概念。但這種模式的紀(jì)錄片由于表達(dá)上借重具有高度概括力的解說語言,能夠加快節(jié)奏、直抒胸臆,傳達(dá)傳播者的主觀意愿,更適于為時代鼓與呼,發(fā)揮輿論宣傳和鼓動功能,所以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現(xiàn)在還是將來,它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價值所在。
五、不同理念下的新寫實主義:法國真實電影和美國直接電影
出于對“二戰(zhàn)”后具有強(qiáng)烈教化意味且缺乏個性的“洗腦式”紀(jì)錄片的反感,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者利用新的攝制技術(shù)來發(fā)現(xiàn)與記錄生活原本的樣貌,達(dá)成他們理想中的真實紀(jì)錄。誕生于上世紀(jì)6n年代前后的法國真實電影和美國直接電影有一個20世紀(jì)共同的技術(shù)基礎(chǔ),即16mm小型便攜式攝影機(jī)和輕便的同步錄音設(shè)備,這使外景拍攝與同步拾音成為可能,使過去的紀(jì)錄影像中不曾有過的貼近式觀察成為可能,也使同步記錄人物訪談和現(xiàn)場其他聲音成為可能。同時由于當(dāng)時意大利新現(xiàn)實主義、英國自由電影及戰(zhàn)后的法國新浪潮電影等幾股力量的合力,共同催生了這兩種紀(jì)錄片史上新的美學(xué)范式和類型。
法國人類學(xué)家讓·魯什和社會學(xué)家艾德加·莫林合作拍攝的《夏日紀(jì)事》副標(biāo)題為“一次真實電影的實驗”,在片中創(chuàng)作者肩扛攝影機(jī)走上巴黎街頭和居民家中對他們進(jìn)行采訪,談?wù)撍麄儗ι畹母惺軐Ρ舜说挠∠螅捌袇⑴c者們還被邀請到放映室里觀看影片并發(fā)言討論,最后魯什和莫林在一座建筑物中面朝鏡頭走來,談?wù)撍麄兯M(jìn)行的這種無演員無布景無劇本的電影實驗?zāi)軌蜃C明什么。真實電影主張攝影機(jī)成為催化劑來激發(fā)人物內(nèi)心的真實,而不是僅僅記錄浮現(xiàn)于表面的真實。雖然強(qiáng)調(diào)真實必須是未經(jīng)排演過的,但有時電影創(chuàng)作者又是攝影機(jī)前的積極參與者,這也引領(lǐng)了后來出現(xiàn)的自我反射式表現(xiàn)風(fēng)格的紀(jì)錄片。
美國的直接電影則以“墻壁上的蒼蠅”式的冷靜觀察為典型特征,不介入不控制,努力將電影創(chuàng)作者對拍攝對象的干預(yù)或者闡釋縮小到最低限度,不靠旁白而依賴現(xiàn)場畫面和同步收音,追求給予觀眾一種身臨其境的自然之感。德魯小組成員及懷斯曼、彭尼貝克等稟持這種創(chuàng)作理念,攝制了諸如《初選》《椅子》《推銷員》《給我庇護(hù)》《提提卡蠢事》等一系列影片。
紀(jì)錄片的寫實主義傳統(tǒng)發(fā)端于盧米埃爾兄弟而后經(jīng)弗拉哈迪及維爾托夫加以發(fā)展,真實電影和直接電影既是對這種傳統(tǒng)的融合,也是對于傳統(tǒng)的決裂,二者分別以“真實”和“直接”標(biāo)榜自己,但都與維爾托夫的電影眼睛理論有著深厚的淵源,均投身于寫實的社會觀察,力圖更進(jìn)一步地靠近理想中的事物的本真狀態(tài),成為“不昂貴的更貼近現(xiàn)實,并且不被技術(shù)所奴役的電影”。
直接電影的這種創(chuàng)作理念和美學(xué)風(fēng)格在中國20世紀(jì)90年代的新紀(jì)錄運(yùn)動中得到了彰顯,被很多紀(jì)錄片人奉為圭臬。這種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方法由于顯得更為客觀真實,并且從攝制層面來看技術(shù)門檻較低宜于被個體操作,時至今日仍是許多獨(dú)立紀(jì)錄片人喜歡采用的拍攝方法,如法國導(dǎo)演托馬斯·巴爾姆斯《陽光寶貝》周浩的紀(jì)錄片《差館》《高三》查曉原的《虎虎》等,只是這些片子也用了人物采訪這種真實電影中的典型方法,以挖掘人物內(nèi)心深處的世界,增加片子的信息含量,實際上成為了把真實電影與直接電影揉合在一起的參與觀察式影片。
六、多元與開放:西方新紀(jì)錄電影及其后的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
20世紀(jì)60年代末期以后,美國處于激烈的社會文化動蕩期,后現(xiàn)代主義成為主宰人們的文化生活觀念,加之越南戰(zhàn)爭引發(fā)的反戰(zhàn)浪潮,社會問題紛繁復(fù)雜在當(dāng)時的政治文化語境下,時代要求紀(jì)錄片承擔(dān)起對當(dāng)時種種社會現(xiàn)象進(jìn)行理性分析和生動闡釋的責(zé)任,由于直接電影為追求客觀和不介入所帶來的含意模糊和表達(dá)曖昧,美國一些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者開始反判和對抗直接電影的教條,如利柯克等人制定的無解說、不用燈光、沒有互動和采訪等,打破曾經(jīng)被奉為準(zhǔn)則的戒律,在拍攝和剪輯制作時對其他可能的表達(dá)方式進(jìn)行了大膽的探索和嘗試,呈現(xiàn)出新的紀(jì)錄美學(xué)和豐富的樣態(tài),這導(dǎo)致了直接電影霸權(quán)的逐漸衰退,也使西方紀(jì)錄影片在20世紀(jì)80年代以后進(jìn)入了一個多元與開放的新時期,這一時期的紀(jì)錄片被冠以“新紀(jì)錄電影”之名。
所謂“新”,以示它與之前曾占主導(dǎo)地位的直接電影與格里爾遜式紀(jì)錄片的區(qū)別,以表明新與舊、當(dāng)代與傳統(tǒng)的差異。如保羅·亞瑟所言,新紀(jì)錄電影“作為一個創(chuàng)作群體,沒有像我們界定新政時期紀(jì)錄片運(yùn)動和直接電影運(yùn)動那樣,新紀(jì)錄電影既沒有具體的導(dǎo)演名單,也沒有連貫的論戰(zhàn)、明確服務(wù)的社會范圍,以及意識形態(tài)上的忠誠。只是在偶爾的采訪和文章中,新紀(jì)錄電影的制作者總是指責(zé)較早紀(jì)錄片的美學(xué)假定和風(fēng)格影響”。它并沒有明確的美學(xué)綱領(lǐng)和顯見的領(lǐng)導(dǎo)者,而且這些紀(jì)錄片在形式上也千差萬別,創(chuàng)作方法也不一而足,所以業(yè)界和學(xué)界或稱之為“后直接電影”,或稱之為“新紀(jì)錄電影”,也有人稱其為“后現(xiàn)代主義紀(jì)錄片”。
新紀(jì)錄電影之“新”,表現(xiàn)在它的創(chuàng)作方法、美學(xué)風(fēng)格、受眾人群、題材選擇等諸方面都與之前的紀(jì)錄片有了很大的不同,如埃羅爾·莫里斯的《細(xì)細(xì)的藍(lán)線》(The Thin Blue Line,1987)、邁克爾·摩爾的《羅杰和我》(Roger and Me,1989)、肯。波恩斯的《內(nèi)戰(zhàn)》(civil War,1990)、克勞德。朗茲曼《浩劫》(Shoah,1985)等代表作品。它與后現(xiàn)代社會沒有恒定主題反英雄的時代語境相契合,以巨大的包容性和融合性把畫外敘述、歷史影像、現(xiàn)時訪談、再現(xiàn)式搬演、字幕、特效等交織揉和在一起,這種雜揉有時甚至模糊了傳統(tǒng)的虛構(gòu)與紀(jì)實、故事片與紀(jì)錄片乃至MTV的界限劃分。新紀(jì)錄電影以一種更為開放和包容的姿態(tài)進(jìn)行創(chuàng)作實踐,它不再是直接電影式的超然物外的冷靜,也不復(fù)是格里爾遜傳統(tǒng)的空泛與缺乏個性,但它同時又積極吸納了格里爾遜式紀(jì)錄片的畫外解說,只是這種解說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上帝之聲,而是更具個性和平民化,有時甚至以導(dǎo)演本人第一人稱的旁白出現(xiàn)。它兼容了先鋒紀(jì)錄電影各種大膽奔放的形式實驗,如風(fēng)格化的音樂、戲劇化的搬演、自我反射手法的運(yùn)用。動畫段落的穿插,故事片的各種特效等。它并沒有放棄直接電影靈活的拍攝手法和技巧,但又常在畫面中顯現(xiàn)拍攝者的存在與干預(yù)。它把真實電影的人物訪談方式拿來主義地使用,但又進(jìn)行了更符合創(chuàng)作者意圖的改進(jìn),如埃羅爾。莫里斯發(fā)明了被稱為恐怖采訪機(jī)(interrotron)的裝置,“用一個由很多鏡子和視頻影像組成的系統(tǒng)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拍攝方式,這樣受訪對象既能直接看著我的眼睛,同時又能直接盯著攝影機(jī)”。把采訪者和攝影機(jī)合為一體,讓觀眾和受訪者有直接的眼神接觸,以更好地與觀眾互動。斯泰拉·布魯茲在論述歐美新紀(jì)錄片的時候?qū)懙剑骸靶录o(jì)錄片已經(jīng)在以多種不同的方式歸復(fù)到當(dāng)初沒有太多拘束的起點,戲劇化表演乃至其他形式的虛構(gòu)和故事化再一次占據(jù)了優(yōu)勢位置”,這兼容并蓄的手法使這些影片一改過去紀(jì)錄片的精英與小眾而成為大眾化的紀(jì)錄片,滿足了觀眾更深入地了解真相的渴望。
西方新紀(jì)錄電影打破了紀(jì)錄片的邊界,不同形式、風(fēng)格、方法和技巧的運(yùn)用,使得紀(jì)錄片成為日益開放的多元的領(lǐng)域,進(jìn)入21世紀(jì)以后,隨著數(shù)字技術(shù)和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的普及,傳媒生態(tài)的變遷,第一人稱自傳體紀(jì)錄片、紀(jì)錄劇情片、動畫紀(jì)錄片、未來時態(tài)的紀(jì)錄片、互動紀(jì)錄片、網(wǎng)絡(luò)眾籌紀(jì)錄片、沉浸式VR紀(jì)錄片等新的紀(jì)錄片理念或形態(tài)出現(xiàn)在人們的視野中,使過去人們對紀(jì)錄片的狹隘認(rèn)識不斷受到?jīng)_擊。如美國導(dǎo)演納撒尼爾·康的《我的建筑師》(My Architect:ASong Journey,2003)以第一人稱視點記錄他的尋父之旅,以色列導(dǎo)演阿里。福爾曼以動畫紀(jì)錄片《和巴什爾跳華爾茲》講述1982年黎巴嫩戰(zhàn)爭的慘象,兩片均獲得多項國際大獎。
自2000年以后,在中國紀(jì)錄片中才有了西方新紀(jì)錄電影的創(chuàng)作理念和創(chuàng)作方法的顯現(xiàn),從最早的《中華文明》(2010),到金鐵木的《圓明園》(2005)《大明宮》(2009)等,均采用了真實再現(xiàn)和三維動畫手法。同時,越來越多的第一人稱紀(jì)錄片出現(xiàn)在各種展映交流活動中,如舒浩倫的《鄉(xiāng)愁》(2006)、林鑫的《三里洞》(2006)、魏曉波的《生活而已》(2010)、吳文光的《治療》(2010)等,一批帶有實驗和先鋒色彩的創(chuàng)新之作如孫曾田的《康有為·變》(2011)、邱炯炯的《癡》(2015)等也引起了人們的關(guān)注,所有這些都昭示著中國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也邁入了多元而豐富的新世紀(jì)。
梳理紀(jì)錄片一百多年的發(fā)展歷史,我們看到它在創(chuàng)作者們不斷的探索和創(chuàng)新中前行,沒有停滯于某一形式或理念的固守,擺脫了僵化刻板的因循,以包容的姿態(tài)及與歷史、現(xiàn)實和將來展開自由對話,以真實為指向,去記錄人類社會及其周圍無限廣闊的宇宙萬物,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類型與風(fēng)格。
(責(zé)任編輯:陳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