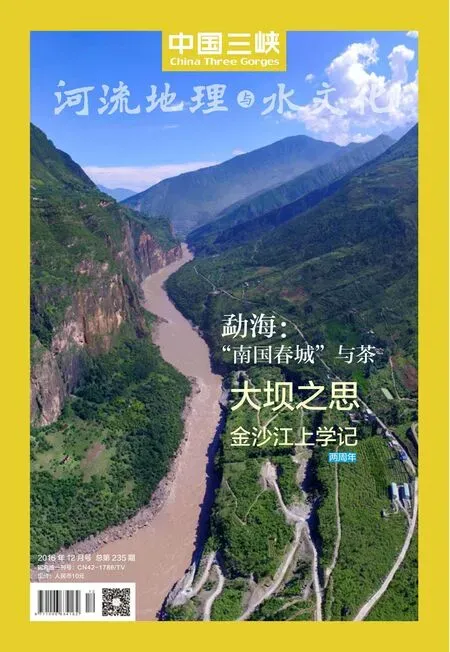康有為游荷蘭
文 / 張林杰 編輯 / 任紅
康有為游荷蘭
文 / 張林杰 編輯 / 任紅

荷蘭阿姆斯特丹街景 繪圖/李雨瀟
光緒三十年二月,即公歷1904年3月,康有為從香港再次去往歐洲。
此前不久,他離開養病的印度大吉嶺,經南亞回香港探望母親。他的身份雖還是個政治流亡者,但出亡之初那種奔命的緊張和組織保皇活動的熱鬧已經過去,他的政治生活隨著革命浪潮高漲而愈來愈無足輕重,他也因此有了更多時間精力來投身個人興趣。旅行看世界,就是他的興趣之一。
一百多年前,交通條件比古代已大大改善,但從中國去往歐洲,仍然是相當漫長的旅程。康有為乘法國輪船離開香港,經越南、泰國到達馬來亞的檳榔嶼,然后換乘一艘英國輪船,經錫蘭(今斯里蘭卡)、從亞丁灣進入埃及,又沿蘇伊士運河入地中海,終于在意大利登岸,踏上了歐洲大陸。這次航程總共耗時差不多三個月。
自流亡以來,康有為去過了不少國家,在日本、北美及英國治下的香港、馬來亞、新加坡和印度都有過生活經歷。對他而言,海外不再是《鏡花緣》中的秘境,歐洲也不再是《瀛環志略》中的陌生世界。因此,作為一個興致勃勃的旅游者,盡管歐洲各國的政治、文化和建設成果依然讓他稱道不已,但歐洲列強在他的眼中,已不再像過去那么光鮮亮麗了。他看到的倫敦與巴黎,繁盛宏偉卻污穢不堪;德國井井有條,但警察治國,禁錮言論,缺乏自由;意大利并不比中國富庶,意人也“至貧多詐”,騙子、竊賊猖獗,纏住游客討錢的乞兒一如印度;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如僻郡荒村一般,“道穢屋卑”,無可觀攬。只有北歐小國給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尤其是荷蘭,更讓他贊不絕口。
一百多年前的荷蘭,如人們今天所見,已是一個治理得井井有條的現代國家。在乘船去往北歐諸國的途中。經過荷蘭海岸時,康有為見到的是“道路整潔,田疇平直,嘉樹夾道,樹影遞天,牛羊被野,樓閣新靚”的景象,他興奮得借詩遣興,“嘆荷之小而能治國也”。

① 荷蘭阿姆斯特丹的運河 攝影/黃旭/ FOTOE ② 荷蘭阿姆斯特丹街景 繪圖/李雨瀟
不過,他真正踏上荷蘭土地,是在一個多月后。當他從布魯塞爾乘五小時汽車抵達阿姆斯特丹時,已是晚上十點半。這座城市的夜景讓他耳目一新:“海島穿錯,船火萬億,與樓臺相映,境界甚新,行歐界以來所無也。”
康有為對荷蘭的第一印象就是干凈整齊:“其屋極整齊,萬家一律”,百姓的居住環境也相當整潔,“玻窗明艷,前臨水木,極凈美”。在阿姆斯特丹,不僅“道路廣潔,百貨駢輳,人民繁盛,樓宇峻整”,而且橋河縱橫,“有橋三百余,島九十余,花樹菲菲繁盛,引溪開溝縱橫千百,穿貫全市,而處處以橋通之”。大城市如此,鄉村田疇也不遑多讓,大塊的田地,都呈長方形,田地四周河溝環繞,并用小橋連接起來,四通八達的水路,保證了灌溉,“故田野極綠,草樹彌望”,到處植被豐盛,“其夾道必植樹,樹距丈許,樹影相遞,堤道極直,遞百千里無際”。如此豐饒的田園景象,讓康有為不禁想起了中國古代治水治田的圣人,他穿鑿附會地稱,大禹治理溝洫和孔子井田溝澮之法在荷蘭得以“見實行之”。從荷蘭人的治水治田,康有為也看到了一種理想的治國方式,他說荷蘭人治國,就像有潔癖的人把自己的齋榻整理得精整無塵,像有花癖的盆景師將盆景收拾得纖悉不遺一般。這樣的境界,“大地萬國”中惟有荷蘭做到了。他認為,這正是荷蘭以蕞爾之邦成為強盛之國的原因。由此,他想起了自己所規劃的大同世界:“他日大地大同,不能不取法荷夫!”

不過,康有為以大為美的趣味,也讓他對荷蘭的建筑略感遺憾,他認為,荷蘭建筑多“甚卑小,不如英法德之宏大”。不久前,他才游覽過的瑞士、比利時、挪威等國,建筑也同樣顯得卑小。他認為,這種小與國土有關:“凡國土之偏小者,其國之宮室器物必卑小偏狹。”五年前,在日本居留期間,他也曾注意到,日本“屋室、園地、杯盤、花木無不尚小者,人民亦氣量偏狹”。用 “偏狹”“卑小”來形容小巧玲瓏的事物,是因為重“大氣”的康有為,把“小”視為一種氣度缺陷。在他看來,大國均有一種偉大的氣象,英、德、法、美等國皆如此,美國尤其如此,它“開闊豪爽,真有泱泱之大風”。這一發現,也讓他對自己的國家頗為自豪:“吾國雖今守舊衰弱,而人士的廣大豪爽,屋舍雖卑污,亦自軒昂廣大,與日本迥殊。”他相信:“國土之感人甚深,囿人甚迫,而生其地者不能出其風土之外也。”這種對風土人情的解釋,顯然得自中國傳統的“天人交感”理論,同時,這套理論也與當時歐洲盛行的從環境來解釋民族精神的理論很相似。在史達爾夫人《論德意志》和丹納的《藝術哲學》中,都有類似的闡釋。
康有為游覽歐洲,博物館是必去的地方。博物館不僅是他了解各國歷史文化的窗口,更滿足了他對藝術的獨特興趣。康有為自稱“性癖書畫”,早年曾收藏過不少國畫、碑帖和古玩,流亡海外后,又四處搜羅了數百件中西繪畫作品。在荷蘭他也十分留意博物館藏的繪畫。荷蘭繪畫在歐洲頗有影響,不少繪畫大師,如魯本斯、維米爾、哈爾斯、倫勃朗等都是荷蘭人。不過,康有為的繪畫趣味太受宮廷畫風影響,談到國畫時,他特別看重工致、講法度、風格華麗細膩的“院體畫”,而提到西畫,他所喜歡的畫家,更多是帶著文藝復興古典主義風格的意大利畫家,拉斐爾的繪畫更被他作為藝術的標桿。在這種趣味支配下,康有為對荷蘭繪畫顯然缺乏領悟。他說荷蘭繪畫“以黝黑為體,于黝中著光色取神以為勝”,這一描述雖然抓住了荷蘭繪畫注重光影的特征,但他對這種特征卻并無太大興趣,斷言荷蘭畫“黝然無味,神采去拉斐爾派遠矣”。按照他的標準,歐洲繪畫有三大派,西班牙派繪畫最次,荷蘭派繪畫居中,而意大利派繪畫最佳。這種充滿成見的審美趣味,讓康有為不僅對崇尚神似的中國文人畫有所排斥,而且對寫實繪畫的欣賞也僅僅停留在甜膩、圓潤、光潔的拉斐爾式風格中。
康有為的荷蘭游記也時時流露出“帝王師”的心態。當年在上呈光緒的條陳和書稿中,他曾用俄國彼得大帝“微服作隸”,立志“變政”的故事來激勵光緒變法,到荷蘭后,他也不忘去彼得當年學習造船的“彼得學船之屋”參觀。在阿姆斯特丹時,正好遇上荷蘭女王巡視,接受群眾的歡呼,這給康有為提供了一個直觀西方君主與民眾關系的窗口。他記述了女王出宮門時的儀式,并目睹了市民夾道歡呼及女王答禮的場景。他看到百姓不斷向女王表達敬意,而女王也不斷對百姓的歡呼回禮致意。認為這不只是禮尚往來,也是溝通君民之情的方式。由此,他想起中國古代禮制,都強調君臣之間的相互禮節。但元代之后,蒙古跪拜式軍禮變成了國禮,跪禮成為習俗,并被明朝延續下來,結果君主對臣子越來越簡慢,民眾對“喝殿出門”的官家也很少致意。
康有為的政敵往往把他視為“妄人”,他既有士大夫的固執和道貌岸然,也有名士的狂妄和落拓不羈,他常常即興發議論,不少議論在今天看來,都是缺乏“政治正確”,又頗為有趣的奇談怪論。一天,在一個公園里,他偶遇一位和他同船來的荷蘭女孩。這位豐滿漂亮的女孩熱情邀他去家中做客,把他引薦給家人,還用茶點招待他。康有為于是得出結論說,歐美女性都善交際,喜歡結交名流,“其好事、好名、好近貴介人,殆不可思議”。康有為也喜歡談論女人。他聽說荷蘭女王以容貌秀麗而著稱歐洲,但見到巡視的女王(康所見到應該是威廉明娜女王)后,他覺得不過是豐滿端莊而已。不過,他認為歐洲出美女的國家,一是瑞典,一是荷蘭。他用地理決定論去解釋這個問題:說生長于湖海邊的人都秀美,中國的杭州如此,歐洲的瑞典、荷蘭亦然;生長于平原者則多豐滿,如德國人;生長于山石之地的人多瘦癯,如廣東山民。他將這種籠統的結論,上升到對種族的概括,說“英人多長,德人多肥,法、意人矮與中國同”,而“歐人之白,一因地度之高寒,二因波羅的海、地中海之水汽,非洲、印度人之黑,則日蒸使然”。甚至斷言:“白人聰敏而黑人愚劣,則顏色與智慧竟相關,而顏色視所生之地。”這套地理決定種族的理論,也使康有為在白人面前有一種自卑感,他在一首詩中這樣寫道:“地中有海生人白,二者天驕我不如。”
康有為青年時代就喜歡旅行,這既讓他能將書中知識“一一案之經歷實驗”,也為他提供了從人世紛擾解脫出來的途徑。流亡海外后,他更是“三周大地,游遍四洲”,歐洲十一國之行,是他海外旅程的重要一章,而游荷蘭,則是這一章中一段輕松的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