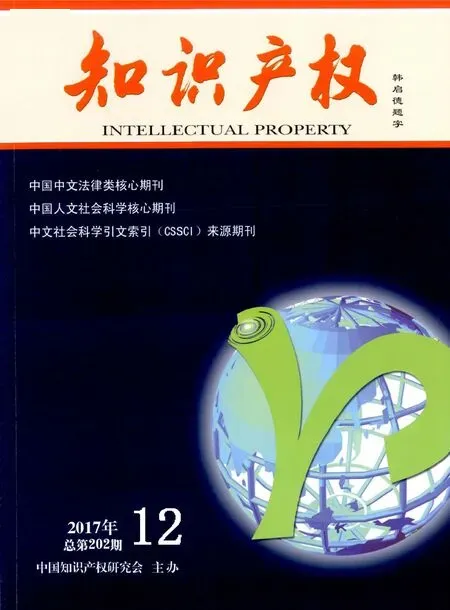“傾聽權(quán)利的聲音”: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警告的制度機(jī)理
謝曉堯
“傾聽權(quán)利的聲音”: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警告的制度機(jī)理
謝曉堯
知識產(chǎn)權(quán)具有相對性,權(quán)利與侵權(quán)之間存在較大的模糊區(qū),需要尋求產(chǎn)權(quán)的再界定。產(chǎn)權(quán)的私人磋商與有效配置源于信息的溝通,侵權(quán)本質(zhì)是權(quán)利的對抗,警告則是權(quán)利維護(hù)的呼吁機(jī)制。我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訴訟案件急劇增長,加大了司法成本。可行的做法是:將侵權(quán)警告作為訴訟的前置程序,過濾和分流案件;通過懲罰性賠償?shù)戎贫仍O(shè)計,對雙方形成“可信的威脅”,激勵當(dāng)事人之間的私人協(xié)商。
知識產(chǎn)權(quán) 侵權(quán)警告 警告先于訴訟
謝曉堯,中山大學(xué)法學(xué)院教授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e not absolute. There is large area of uncertainty between right and infringement, which entails the redefinition of property right. The private negotiation and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property right depends on the communication of information. The essence of infringement is the confrontation of rights, and the IP warning is a “voice” mechanism for right protection. The number of China’s IP cases rocket up dramatically, and the judicial cost increases accordingly. A feasible solution is to use the Infringement Warning as a prepositive procedure of litigation, in order to filter and redistribute cases. Meanwhile, private negotiation will be encouraged through the design of punitive compensation system that exerts “credible threats” to the two parti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warning; warning before litigation
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警告是一個偏冷的話題,長期來,國內(nèi)學(xué)界的研究寥寥無幾①筆者在中國知網(wǎng)(http://kns.cnki.net,2017年9月14日登錄)以“警告函”為主題詞檢索,錄得二十五篇論文;以“知識產(chǎn)權(quán)”和“警告函”為主題詞檢索,錄得十篇論文。。為數(shù)不多的理論文獻(xiàn),學(xué)者從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外在視角聚焦于警告行為的正當(dāng)性,企圖廓清侵權(quán)警告與商業(yè)詆毀、權(quán)利濫用的法律界限。②參見梁志文:《論專利權(quán)人之侵權(quán)警告函》,載《知識產(chǎn)權(quán)》2004年第3期;孫棟:《對向第三方發(fā)送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警告函的法律規(guī)制——以我國的訴訟文化為背景》,載《知識產(chǎn)權(quán)》2015年第12期;劉維:《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警告函的正當(dāng)性邊界》,載《比較法研究》2016年第2期;儲翔:《專利侵權(quán)警告行為的正當(dāng)性判斷標(biāo)準(zhǔn)》,載《學(xué)術(shù)月刊》2017年第3期;孔譯珞:《論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警告的法律屬性及其規(guī)制——兼評最高人民法院兩個典型案例》,載《知識產(chǎn)權(quán)》2017年第4期。這當(dāng)然是重要而有價值的。
“世界偏僻角落的事件可以說明有關(guān)社會生活組織的中心問題。”③[美]羅伯特?C?埃里克森著:《無需法律的秩序:相鄰者如何解決糾紛》,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16年版,第1頁。埃里克森提醒我們。權(quán)利乃是一種論爭文化,財產(chǎn)建立在利益的正當(dāng)性求證和論爭性交涉的基礎(chǔ)上,權(quán)利的獲得要達(dá)成起碼的社會共識,權(quán)利的維護(hù)取決于他人的認(rèn)同和尊重。法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將“談判理論”視為“財產(chǎn)經(jīng)濟(jì)理論的基礎(chǔ)”④[美]羅伯特?考特等著:《法和經(jīng)濟(jì)學(xué)》(第六版),史晉川等譯,格致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頁。。與有形物相比,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權(quán)利論爭機(jī)制尤為重要,無論法定產(chǎn)權(quán)的初始配置,還是權(quán)利事后討價還價的修正和再配置,都貫徹著論爭機(jī)制,前者如專利、商標(biāo)專用權(quán)“物權(quán)公示”規(guī)則下的異議制度,后者如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撤銷和宣告無效制度。“侵權(quán)—警告”是知識產(chǎn)權(quán)重要的論爭程式,權(quán)利的明晰和界定在高度對抗中得以實現(xiàn)。一些國家明確將知識產(chǎn)權(quán)警告作為法定程序,前置于訴訟,以發(fā)揮其功能。⑤以德國為例,《著作法》第97條規(guī)定:“被害人應(yīng)當(dāng)在提起不作為訴訟之前警告侵害人并賦予其機(jī)會,通過履行以適當(dāng)違約金保障的不作為義務(wù),調(diào)解訴訟。”其《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也有類似規(guī)定。晚近以來,我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訴訟案件不斷增加,侵權(quán)警告卻遭受冷遇,加劇了司法運(yùn)行成本。將侵權(quán)警告“內(nèi)置于”知識產(chǎn)權(quán)制度,引導(dǎo)更具效益的權(quán)利界定和維護(hù)模式,尤其具有現(xiàn)實意義。范長軍先生曾主張:“設(shè)立專利侵權(quán)警告制度的目標(biāo)是促使當(dāng)事人在進(jìn)入司法訴訟與行政處理這兩種國家程序之前自行解決糾紛,最大限度地節(jié)約當(dāng)事人的成本和社會資源。”⑥范長軍:《專利侵權(quán)警告制度探析——對專利法第四次修改的建議》,載《知識產(chǎn)權(quán)》2014年第3期。這一觀點極具建設(shè)性,可惜的是,在理論和立法中并未引起更多反響和重視。
秘魯學(xué)者德?索托在《資本的秘密》中,講述了“狗的叫聲”的故事:當(dāng)他在印度尼西亞的稻田里漫步時,并不知道每個人的地產(chǎn)邊界在哪里,但是,狗卻知道答案。當(dāng)他從一個農(nóng)場進(jìn)入另一個農(nóng)場時,都會有不同的狗沖著他吠叫,這些狗“掌握著”所有權(quán)的基本信息。要建立正規(guī)所有權(quán)制度,就得“傾聽狗的叫聲”。“傾聽狗的叫聲”無疑是隱喻性的。在知識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即使存在一套事先劃定的官方所有權(quán),其權(quán)利邊界通常也未必是確定無疑、清晰可辨的,完全交由司法程序代價高昂,鼓勵產(chǎn)權(quán)的私人磋商,“傾聽權(quán)利的聲音”,是可行的做法。
本文從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內(nèi)在視角審視侵權(quán)警告行為,揭示其在權(quán)利論爭中的地位和作用程式,以期未來能完善立法制度。
一、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不確定性與產(chǎn)權(quán)的再界定
(一)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相對性
與其他有形財產(chǎn)權(quán)相比,知識產(chǎn)權(quán)呈現(xiàn)出更大的不確定性⑦蘭德斯和波斯納認(rèn)為,交易成本越高,法律就越不可能通過設(shè)定寬泛的對世權(quán),而必須縮小其財產(chǎn)權(quán)的范圍,知識產(chǎn)權(quán)是趨向于成本高昂的保護(hù),交易成本遠(yuǎn)大于物質(zhì)成本,合理使用原則的適用要廣泛的多。參見[美]威廉?M?蘭德斯、理查德?A?波斯納著:《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的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金海軍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532頁。,這是理解侵權(quán)警告行為的關(guān)鍵⑧理邦公司與邁瑞公司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也是從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不確定性的內(nèi)在視角對待警告函的,指出:“由于專利權(quán)本身在效力上的相對不確定性及侵權(quán)判斷的專業(yè)性,尤其是不確定性必然伴隨無能為力,法律不能強(qiáng)人所難,因此不能苛求侵權(quán)警告內(nèi)容完全確定和毫無疑義,對其確定性程度的要求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案件具體情況進(jìn)行把握。”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91號民事裁定書。。
第一,形而上學(xué)的固有局限。知識產(chǎn)權(quán)建立在形而上學(xué)的法律組織技巧上,為了獲得法定產(chǎn)權(quán)的前瞻性和穩(wěn)定性,作品、發(fā)明和商標(biāo)的可保護(hù)性,被提煉出“獨(dú)創(chuàng)性”“創(chuàng)造性”“顯著性”等高度形式化的抽象命題,本身缺乏賴以觀察和度量的確切性。⑨戈斯汀指出著作權(quán)并非對諸如一片土地或者一條羊腿之類的有體物,而是人的思想成果,“對這種捉摸不定的‘財產(chǎn)’還真是難以確定其界限”,“著作權(quán)的形而上學(xué)(metaphysics)之所以是如此捉摸不定,原因在于,作為其形而下的對象(physics)是如此不穩(wěn)定”。參見[美]保羅?戈斯汀著:《著作權(quán)之道:從古登堡到數(shù)字點播機(jī)》,金海軍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第6、11頁。在有形物世界,權(quán)利設(shè)定得依其物理特征,難以超越其性能無限擴(kuò)大,田村善之稱為“物理性剎車器”,知識產(chǎn)權(quán)是“人們頭腦中虛構(gòu)出來的”,剎車器的缺失有可能引發(fā)沒有節(jié)制的權(quán)利。⑩[日]田村善之:《田村善之論知識產(chǎn)權(quán)》,李揚(yáng)等譯,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版,第28-49、94頁。莫杰斯教授認(rèn)為,知識產(chǎn)權(quán)并非如同排放的黑煙或者閑逛的牛群,存在“清晰的標(biāo)識”,侵權(quán)人甚至無法知道其獨(dú)立研發(fā)的技術(shù)本身就有可能構(gòu)成侵權(quán)。?See Robert P. Merges, Toward a Thir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aradigm: Of Property Rules, Coa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94 Colum. L. Rev.2655 (1994), pp.2655-2673.
第二,權(quán)利語言的模糊性。為了緩解上述問題,知識產(chǎn)權(quán)制度借助于語言將無形物的權(quán)利邊界“物化”,并通過注冊登記制度,將無形的“抽象物”轉(zhuǎn)變?yōu)榭梢杂^察和核實的“紙上所有權(quán)”,以簡化權(quán)利的管理成本。?詳細(xì)的分析參見謝曉堯、吳楚敏:《轉(zhuǎn)換的范式:反思知識產(chǎn)權(quán)理論》,載《知識產(chǎn)權(quán)》2016年第7期。然而,語言具有模糊性,比如,在專利申請中,即使通過職業(yè)化的專利代理人,使用高度標(biāo)準(zhǔn)化的科學(xué)語言,也難以構(gòu)筑權(quán)利“四至”的清晰藩籬。語言的模糊性導(dǎo)致了解釋無處不在,周邊限定主義、中心限定主義等解釋方法因案而異,陷于解釋循環(huán)的漩渦之中,法律與語言的解釋并不能廓清權(quán)利的邊界?在恩迪科特看來,模糊性與不確定性是法律的基本特征,可能不存在任何明晰的邊際情形,解釋不是解決所有不確定性問題的技巧。要到達(dá)法的明確性,就要求消除法的模糊性,這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參見[英]蒂莫西?A?O恩迪科特著:《法律中的模糊性》,程朝陽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127頁。。
第三,知識產(chǎn)權(quán)“安全閥”的調(diào)控范圍。知識產(chǎn)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公共物品屬性,過于嚴(yán)格的權(quán)利保護(hù)會加劇知識的傳播運(yùn)用成本,阻礙創(chuàng)新。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排他性設(shè)計從來都是有限的,法律預(yù)留了溝通私人產(chǎn)權(quán)與公共領(lǐng)域的過渡地帶,為潛在的使用者提供“安全閥”,比如:合理使用、在先使用、權(quán)利用盡、平行進(jìn)口、法定許可,等等。這些“安全閥”的調(diào)控界限是變化不居的,既取決于公共政策的調(diào)整,也因不同案件特定的情形而異。
第四,權(quán)利的不安定性。專利、商標(biāo)即使獲得授權(quán)和核準(zhǔn),也可以被宣告無效或撤銷,法定權(quán)利處于“事實上”不確定狀態(tài)。訴訟本質(zhì)是權(quán)利適格性的再界定,被控侵權(quán)人會竭盡全力主張“豁免”:公知性、顯而易見性、唯一表達(dá)、通用性、權(quán)利濫用等林林總總的抗辯事由,均有可能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構(gòu)成實質(zhì)性的威脅。權(quán)利是利益變化的時間函數(shù),權(quán)利拋棄、權(quán)利的懈怠、逆權(quán)占有,都會導(dǎo)致初始權(quán)利的再配置。同樣的,未注冊商標(biāo)、非核準(zhǔn)企業(yè)名稱(簡稱、別稱)、知名商品特有名稱、作品標(biāo)題、人物形象,等等,這些非法定權(quán)益的生成和演變,會導(dǎo)致權(quán)利的競爭和沖突,引發(fā)權(quán)利的再次配置。
第五,權(quán)利實施的不完全性。“不可占有性”是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物品屬性,權(quán)利專屬性并不強(qiáng)。?參見大衛(wèi)?蒂斯著:《技術(shù)秘密與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轉(zhuǎn)讓與許可》,王玉茂等譯,知識產(chǎn)權(quán)出版社2014年版,第57-60頁;[美]蒂莫西?泰勒著:《斯坦福極簡經(jīng)濟(jì)學(xué):如何果斷第權(quán)衡利益得失》,林隆全譯,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5-86頁。知識的開發(fā)成本高,傳播和復(fù)制的邊際成本卻接近于零,侵權(quán)的預(yù)防、核實、監(jiān)督和維護(hù)成本高,高昂的排他成本導(dǎo)致了法定產(chǎn)權(quán)實施上的不完備性。由于權(quán)利的界定和維護(hù)需要成本,當(dāng)成本過于昂貴時,權(quán)利人有可能放棄權(quán)利將其置于“公共領(lǐng)域”,成為可以自由取用的公共產(chǎn)品的一部分,各國專利、商標(biāo)維持率不高即為明證。
(二)“產(chǎn)權(quán)產(chǎn)生于解決爭論的過程中”
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相對性決定了,侵權(quán)與不侵權(quán)、真侵權(quán)與假侵權(quán)、惡意侵權(quán)與“無意踏入”等界限,并非一目了然,需要開啟權(quán)利的交涉程序,謀求權(quán)利的再界定。
知識產(chǎn)權(quán)權(quán)利邊界在許多情形中都非清晰,紙面上的法定產(chǎn)權(quán)和事實上的產(chǎn)權(quán)并不一致,“權(quán)利—侵權(quán)”絕非非此即彼的兩個極端,兩者之間有著廣闊的中間地帶是產(chǎn)權(quán)的模糊區(qū)。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明晰性是從核心區(qū)向模糊區(qū)漸次過渡,即使在核心區(qū),也有可能存在合理使用的“權(quán)利飛地”。同樣,“侵權(quán)”的外觀之下,其實有可能隱含著“權(quán)利”。權(quán)利與侵權(quán)呈現(xiàn)出的相互“嵌入”,需要引入多向度的權(quán)利思維。霍菲爾德將權(quán)利人與相對人的關(guān)系劃分四種標(biāo)準(zhǔn)類型:權(quán)利/義務(wù)、特權(quán)/無權(quán)利、權(quán)力/責(zé)任、豁免/無權(quán)力?參見[美]霍菲爾德著:《基本法律概念》,張書友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76-77頁。。在本文看來,權(quán)力/責(zé)任、權(quán)利/義務(wù)的類型,普遍性地表達(dá)了核心區(qū)權(quán)利人與侵權(quán)人之間的關(guān)系;特權(quán)/無權(quán)利、豁免/無權(quán)力則更容易落入權(quán)利的模糊區(qū),比如:合理使用就可理解為知識產(chǎn)權(quán)疆域中的一塊“飛地”,對于所有人而言是“無權(quán)利”,相反,對那些有可能被標(biāo)簽為“侵權(quán)”的侵害人來說,則構(gòu)成“特權(quán)”?有學(xué)者將版權(quán)法定位為“使用者權(quán)利的法”,賦予作者獨(dú)占權(quán)的前提是他人的合理使用。參見[美]萊曼?雷?帕特森等著:《版權(quán)的本質(zhì):保護(hù)使用者權(quán)利的法律》,鄭重譯,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53頁。。
知識產(chǎn)權(quán)是高信息成本產(chǎn)品,權(quán)利的核實和驗證困難。由于缺乏清晰而固定的權(quán)利“柵欄”,人們傾向于將模糊區(qū)視為“公地”,逾越、跨界實為常態(tài)。一概禁止他人踏足模糊區(qū),預(yù)防成本太高,會遏制周邊發(fā)明等創(chuàng)新活動;奉行“先勘定,再行走”,權(quán)利等待的機(jī)會成本高昂;可取的做法是:“先行走,再勘定,然后糾錯”。法定產(chǎn)權(quán)只是初始化的“紙面權(quán)利”,不是永久不變的,巴澤爾將產(chǎn)權(quán)視為“自己努力加以保護(hù)、他人企圖奪取和政府予以保護(hù)程度的函數(shù)”。?[美]Y?巴澤爾著:《產(chǎn)權(quán)的經(jīng)濟(jì)分析》,費(fèi)方域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9年版,第2頁。有人將專利權(quán)的設(shè)定視同黑暗中的燈塔,吸引著各方聚集起來形成燈塔效應(yīng),激發(fā)和幫助不同角色之間的互動、對話。?斯格特?凱夫:《關(guān)于專利法律與政策的經(jīng)濟(jì)學(xué)》,載竹中俊子主編:《專利法律與理論——當(dāng)代研究指南》,彭哲等譯,知識產(chǎn)權(quán)出版社2013年版。這當(dāng)然包括,不同利益方事后一對一談判,以“打補(bǔ)丁”的方式進(jìn)行權(quán)利修復(fù)和界定。布羅姆利教授強(qiáng)調(diào)了權(quán)利的“斗爭哲學(xué)”: “產(chǎn)權(quán)不是不證自明的東西,在特定的法律斗爭之前,它的本質(zhì)是無法通過直覺或內(nèi)省搞清楚的”,“產(chǎn)權(quán)產(chǎn)生于解決爭論的過程中”,產(chǎn)權(quán)是在解決互相排斥的權(quán)利主張中,在“爭斗中”“被創(chuàng)造”的,法庭提供了必要的論壇。?[美]丹尼爾?W?布羅姆利著:《充分理由:能動的實用主義和經(jīng)濟(jì)制度的含義》,簡練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0-222頁。
警告行為成為獨(dú)特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律問題,與其固有的不確定性相關(guān)?日本學(xué)者指出,知識產(chǎn)權(quán)警告函的依據(jù)是,“權(quán)利領(lǐng)域比較抽象、不明確,所以,相關(guān)各方相互負(fù)有使其明確的協(xié)助義務(wù)。”參見[日]田村善之編:《日本現(xiàn)代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理論》,李揚(yáng)等譯,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頁。。為克服權(quán)利的不確定性,必須引入低成本的權(quán)利交涉、對話、界定與協(xié)調(diào)機(jī)制,鼓勵事后的私人產(chǎn)權(quán)談判。考特等人認(rèn)為,法律的重要目標(biāo)就是“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促進(jìn)私人談判順利進(jìn)行”,他們給出了兩個財產(chǎn)法規(guī)則:(1)“規(guī)范的科斯定理”:構(gòu)建法律消除私人協(xié)商的障礙;(2)“規(guī)范的霍布斯定理”:構(gòu)建法律使私人協(xié)商失敗造成的損害最小化。?[美]羅伯特?考特等著:《法和經(jīng)濟(jì)學(xué)》(第六版),史晉川等譯,格致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頁。侵權(quán)警告很大程度上是權(quán)利交涉中回應(yīng)交易成本的產(chǎn)物。
二、“侵權(quán)”與“警告”:權(quán)利論爭的程式
作為權(quán)利的交涉方式,一個標(biāo)準(zhǔn)的警告行為包含內(nèi)容有:(1)侵權(quán)事實;(2)權(quán)利聲明;(3)呼吁與威懾。前兩者具有信息交流的功能,后者則是策略性的。信息溝通有利于緩解權(quán)利談判、評估和界定所必需的知識需求。
(一)“侵權(quán)”及其信號
侵權(quán)本質(zhì)上是權(quán)利的對抗。只要權(quán)利是不完備的,那些沒有清晰界定的模糊區(qū),就有可能引發(fā)“剩余權(quán)利”的再界定,“侵權(quán)”是侵害人權(quán)利的另類表達(dá)?萊斯格曾言,如果“盜版”意味著不經(jīng)允許而擅自使用他人的作品,“整個人類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盜版的歷史”。參見[美]勞倫斯?萊斯格著:《免費(fèi)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的未來》,王師譯,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頁。。侵權(quán)可能是惡意的,也可能是非惡意的,不加區(qū)分、簡單地貼道德標(biāo)簽,并不可取。可行的做法是,通過制度設(shè)計,激勵潛在的侵害人放棄侵權(quán)與權(quán)利人達(dá)成協(xié)議;通過甄別侵權(quán),懲罰惡意行為,激勵人們對財產(chǎn)權(quán)的尊重。侵權(quán)當(dāng)然增加了權(quán)利的防范、維護(hù)和管理成本,但是,侵權(quán)有著積極的信號功能。“侵權(quán)”也是一種“權(quán)利的聲音”,絕對禁止侵權(quán),既無可能,也并非總是有效益的選擇。
第一,市場發(fā)現(xiàn)。通常認(rèn)為,權(quán)利人通過財產(chǎn)的價值評估,來確定相應(yīng)的權(quán)利界定和保護(hù)水平?。當(dāng)動用產(chǎn)權(quán)的收益不足以彌補(bǔ)成本時,人們寧愿將權(quán)利置于公共領(lǐng)域,也不會去實現(xiàn)它;只有權(quán)利帶來的利益大于成本時,動用和維護(hù)產(chǎn)權(quán)才會被付諸現(xiàn)實。誰有能力發(fā)現(xiàn)知識的價值?所有人當(dāng)然擁有資產(chǎn)屬性的信息優(yōu)勢。知識資產(chǎn)具有異質(zhì)性,不同人的稟賦、經(jīng)歷和能力并不一致,比較優(yōu)勢不盡相同,一些情況下,“盜賊”有可能更具有發(fā)現(xiàn)市場價值的能力,進(jìn)而對資產(chǎn)屬性做出較高的評價。“盜賊”能喚醒權(quán)利人對資產(chǎn)屬性的新認(rèn)知和再評估,進(jìn)而決定權(quán)利的保護(hù)水平?關(guān)于“盜賊”對資產(chǎn)屬性的評估與權(quán)利的保護(hù),參見[美]約拉姆?巴澤爾著:《國家理論——經(jīng)濟(jì)權(quán)利、法律權(quán)利與國家范圍》,錢勇等譯,上海財政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227頁。。這種現(xiàn)象在知識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尤為突出,“搶注者”“炒標(biāo)者”“山寨企業(yè)”“跳槽者”“職業(yè)維權(quán)人”,等等,就具有發(fā)現(xiàn)市場價值的比較優(yōu)勢,其“越軌”行為具有喚醒“權(quán)利意識”的積極功能。權(quán)利人通過發(fā)現(xiàn)侵權(quán),能尋求互補(bǔ)性資源的高效配置。
第二,權(quán)利挑戰(zhàn)。知識產(chǎn)權(quán)在各國的保護(hù)水平日益提高,批判的觀點認(rèn)為,受特殊利益集團(tuán)俘獲過于嚴(yán)重,不太符合效益標(biāo)準(zhǔn),“過分保護(hù)知識產(chǎn)權(quán)和完全不保護(hù)知識產(chǎn)權(quán)是同樣有害的”?肯恩?奧凱:《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的賭注》,載戴維?凱瑞斯著:《法律中的政治——一個進(jìn)步性批評》,信春鷹譯,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頁。。理想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制度,不應(yīng)當(dāng)僅僅激勵壟斷,而要尋求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最佳均衡,“提供最優(yōu)的增量創(chuàng)新激勵”?[美]克里斯蒂娜?博翰楠等著:《創(chuàng)造羈限:促進(jìn)創(chuàng)新中的自由與競爭》,蘭磊譯,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70頁。。時間長、范圍寬、責(zé)任嚴(yán)的高水平保護(hù),會引發(fā)競爭性搶占知識產(chǎn)品的重復(fù)投入和過度投資,產(chǎn)生無謂浪費(fèi);各自畫地為牢使公共知識的增長利用受到限制,加大了知識的傳播和運(yùn)用成本,“周邊發(fā)明”等創(chuàng)新活動受阻。?參見[美]蘇珊娜?斯科奇姆著:《創(chuàng)新與激勵》,劉勇譯,格致出版社2010年版,第94-95頁;參見杰?P?克森:《專利局異議程序和法院專利無效程序:互補(bǔ)還是替代》,載竹中俊子主編:《專利法律與理論——當(dāng)代研究指南》,彭哲等譯,知識產(chǎn)權(quán)出版社2013年版。制度安排上宜允許、引導(dǎo)和激勵對權(quán)利的挑戰(zhàn)。作為權(quán)利擴(kuò)張的挑戰(zhàn)和制衡,試探法定權(quán)利的邊界與保護(hù)強(qiáng)度,最常見、最原初的方式不是訴訟和行政救濟(jì),因為其成本過于昂貴。權(quán)利質(zhì)疑與挑戰(zhàn)強(qiáng)勁的力量來自市場的逐利動因,侵權(quán)在挑戰(zhàn)權(quán)利的同時,開啟了權(quán)利有效性的驗證。這是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糾正機(jī)制,或者說權(quán)利過濾機(jī)制,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質(zhì)量和權(quán)利配置據(jù)此進(jìn)行競爭性檢驗。同時,在一些情形中,模仿、侵權(quán)的壓力甚至是激勵權(quán)利人不斷創(chuàng)新的動力。?勞斯迪亞(Kal Raustiala)等人的研究表明,在時尚、美食、金融、字體、橄欖球、喜劇等行業(yè)中,模仿往往會激發(fā)創(chuàng)新。參見[美]卡爾?勞斯迪亞、克里斯托夫?斯布里格曼著:《Copy Right!模仿如何激發(fā)創(chuàng)新》,老卡等譯,電子工業(yè)出版社2015年版。
第三,價值評價。侵權(quán)行為一概禁止嗎?科斯以交易成本為基礎(chǔ)提出了著名的相互性命題:“關(guān)鍵在于避免較嚴(yán)重的損害”?[美]羅哈德?哈里?科斯著:《企業(yè)、市場與法律》,三聯(lián)書店上海分店1990年版,第76頁。。法經(jīng)濟(jì)學(xué)認(rèn)為,當(dāng)交易成本足夠低時,無論產(chǎn)權(quán)如何進(jìn)行分配,有效的資源配置都會出現(xiàn);當(dāng)交易成本足夠高時,有效率的資源配置要求把產(chǎn)權(quán)分配給對其評價最高的一方。?[美]羅伯特?考特等著:《法和經(jīng)濟(jì)學(xué)》(第六版),史晉川等譯,格致出版社2012年版,第86頁。一些場合,侵權(quán)是資源高價值評價的信號顯示,比如:逆權(quán)占有(adverse possession,也稱反向占有),被視為是糾正紙上所有權(quán)、改進(jìn)知識產(chǎn)權(quán)財產(chǎn)制度的一種方法?[美]威廉?M?蘭德斯、理查德?A?波斯納著:《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金海軍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2頁。。侵權(quán)人不用經(jīng)過談判,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持續(xù)、公開和敵意的占有他人權(quán)利之后,就能導(dǎo)致所有權(quán)轉(zhuǎn)移。逆權(quán)占有的經(jīng)濟(jì)合理性在于:它消除了所有權(quán)瑕疵,阻止了有價值的資源被長期閑散留置,允許財產(chǎn)轉(zhuǎn)移到評價更高的使用者一方;通過所有權(quán)的再配置,消除未來發(fā)生爭議的風(fēng)險,降低了交易成本。?[美]羅伯特?考特等著:《法和經(jīng)濟(jì)學(xué)》(第六版),史晉川等譯,格致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頁。在功利主義看來,表明財產(chǎn)在他手中已經(jīng)沒有多少價值,就不應(yīng)再享有真正意義上的所有權(quán)。參見[美]詹姆斯?戈德雷著:《私法的基礎(chǔ):財產(chǎn)、侵權(quán)、合同和不當(dāng)?shù)美罚瑥埣矣伦g,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233頁。也有學(xué)者對逆權(quán)占有表示質(zhì)疑,財產(chǎn)的閑置狀態(tài)有可能比反向占有狀態(tài)更有價值。參見斯蒂文?沙維爾著:《法律經(jīng)濟(jì)分析的基礎(chǔ)理論》,趙海怡等譯,中國人民大學(xué)2103年版,第65-68頁。
(二)“警告”及其信號
訴訟、仲裁、第三方調(diào)解等都是權(quán)利的界定方式。警告行為是其中經(jīng)濟(jì)成本最為低廉的做法,其功能在于:
1.權(quán)利宣示
知識產(chǎn)權(quán)特異性強(qiáng),權(quán)利人具有信息優(yōu)勢,由權(quán)利人做出權(quán)利宣示,可以避免權(quán)利信息的搜尋、核實、驗證和度量等多重成本,克服和緩解信息不對稱,增進(jìn)他人的權(quán)利認(rèn)知。伯克等人認(rèn)為,“訴訟通常是雙方彼此誤解的產(chǎn)物。如果雙方能夠確知涉訴權(quán)利的實際價值,那么避開訴訟通過私下的解決方式對雙方都有利。”?[美]丹?L?伯克等著:《專利危機(jī)與應(yīng)對之道》,馬寧等譯,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7頁。考特等人也認(rèn)為,信息溝通能夠彼此糾正和降低各方所持有的錯誤的樂觀主義,在信息不對稱的環(huán)境中,“壞消息有助于和解”。?[美]羅伯特?考特等:《法和經(jīng)濟(jì)學(xué)》(第六版),史晉川等譯,格致出版社2012年版,第386-388頁。沙維爾也分析了信息披露有助于和解。([美]斯蒂文?沙維爾著:《法律經(jīng)濟(jì)分析的基礎(chǔ)理論》,趙海怡等譯,中國人民大學(xué)2103年版,第380頁。)
及時的權(quán)利宣示,能避免社會資源的無謂浪費(fèi)。侵權(quán)行為是資產(chǎn)專用性投資的過程,現(xiàn)金、實物和人力資源一經(jīng)“固化”到侵權(quán)產(chǎn)品,改作別的用途就會貶值。侵權(quán)被發(fā)現(xiàn)和制止越早,越有利于侵害人“退出”,減少資源的浪費(fèi)。權(quán)利人并非都有著及時宣示權(quán)利的動機(jī),這與談判策略有關(guān),侵權(quán)的專用性投資越大,承擔(dān)賠償?shù)呢?zé)任資產(chǎn)也越大——可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增加了權(quán)利人事后要價的籌碼。為此,制度必須約束權(quán)利的放任行為,激勵權(quán)利人及時宣示。
2.允諾與“質(zhì)押”
警告是對權(quán)利挑戰(zhàn)的積極回應(yīng)。赫希曼將行為滑向衰落的回應(yīng)模式分為“退出”和“呼吁”,在退出之前呼吁更為可取,是一種恢復(fù)機(jī)制,有利于經(jīng)濟(jì)績效。?[美]阿爾伯特?O?赫希曼著:《退出、呼吁與忠誠——對企業(yè)、組織和國家衰退的回應(yīng)》,盧昌崇譯,經(jīng)濟(jì)科學(xué)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頁以下。警告不僅僅是紙面權(quán)利的宣示,更具建設(shè)性、進(jìn)取性的在于,其開啟了產(chǎn)權(quán)界定的恢復(fù)性對話。在不確定性的困局中,警告行為緣何能開啟恢復(fù)性對話?原因在于,警告隱含著權(quán)利允諾,權(quán)利人“拉緊”法律的大門,斷了自己的退路,主動接受各種法律約束。權(quán)利人必須對沒有根據(jù)的警告行為承擔(dān)法律后果,面臨濫用權(quán)利、商業(yè)詆毀、干擾商業(yè)活動等諸多風(fēng)險。警告即承諾,禁止反悔,權(quán)利人如同將自己“捆綁”,向?qū)Ψ教峁叭速|(zhì)質(zhì)押”,擔(dān)保權(quán)利品質(zhì)的確切性,以換取他人的權(quán)利認(rèn)同和不侵權(quán)。
這種“捆綁”是權(quán)利正當(dāng)性的自我補(bǔ)強(qiáng),同時也有利于“相互捆綁”。警告一經(jīng)通知侵權(quán)人,權(quán)利人“對過錯的證明就基本被減輕了”?[德]魯?shù)婪?克拉瑟著:《專利法——德國專利和實用新型法、歐洲和國際專利法》,單曉光等譯,知識產(chǎn)權(quán)出版社2016年版,第1096頁。,它能固化被警告人的主觀意圖,促使其采取防范措施,否則,惡意侵權(quán)將承擔(dān)更大的法律責(zé)任。警告對侵害人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加深對他人權(quán)利的認(rèn)知,放棄侵權(quán);從樂觀主義轉(zhuǎn)向為悲觀主義,為未來的和解奠定基礎(chǔ);激活談判機(jī)制,謀求事后的許可授權(quán);促使使用者提供再擔(dān)保;在沒有共識時盡早解決糾紛。
3.侵權(quán)甄別
侵權(quán)警告也是一套甄別機(jī)制。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有四種類型:(1)不知道他人權(quán)利,無意中侵權(quán);(2)不確定他人權(quán)利范圍而侵權(quán);(3)知道他人權(quán)利,因疏忽而“無意踏入”;(4)明知他人權(quán)利,無正當(dāng)理由侵權(quán)。警告可以篩選和甄別不同的類型。第一種情形,只要權(quán)利人的信息披露充分,能產(chǎn)生他人的權(quán)利確信,通常會主動停止侵權(quán)。第二種情形比較復(fù)雜,有可能隨著信息不對稱的消除而停止侵權(quán)。也有可能產(chǎn)生“真”糾紛,即侵權(quán)人堅信沒有“闖入”他人邊界而要求權(quán)利勘定,并能顯示出界權(quán)的誠意,比如:提供侵權(quán)擔(dān)保,參與權(quán)利界定的談判,啟動行政確權(quán),提起不侵權(quán)訴訟。在第三種情形中,侵權(quán)人通常會主動停止侵權(quán),權(quán)利人會傾向于寬容,司法中也應(yīng)對“無意踏入”持寬容做法?在祥和泰公司與江蘇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案中,法院認(rèn)為:注冊商標(biāo)專用權(quán)是法定授權(quán)性權(quán)利,“實踐中極有可能出現(xiàn)被控侵權(quán)人無意踏入注冊商標(biāo)保護(hù)范圍的情形”,查處侵權(quán)行為時宜保持“謙抑與平衡”,行政執(zhí)法的重點是制止惡意侵權(quán)和重復(fù)侵權(quán)。參見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蘇知行終字第0004號行政判決書。。第四種情形實則為權(quán)利論爭的“假糾紛”,權(quán)利疆域確定而無實質(zhì)上的分歧,耗費(fèi)界權(quán)資源而無更多產(chǎn)出,必須加大對此類案件的威懾。
甄別侵權(quán),最終要落實到責(zé)任的不同配置上,寬容“無意踏入”,善待“真糾紛”,嚴(yán)格遏制“假糾紛”。通常認(rèn)為,權(quán)利越是確定和清晰的,交易成本也越低,越應(yīng)促成當(dāng)事人的事前談判,事后訴訟的權(quán)利運(yùn)行成本太高,并不可取;相反,權(quán)利越是不確定,事前談判成本會越高,通過事后權(quán)威機(jī)構(gòu)的集中估價,則具有經(jīng)濟(jì)上的合理性。法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將前者稱為“財產(chǎn)規(guī)則(Property Rules)”,后者稱為“責(zé)任規(guī)則(Liability Rules)”,財產(chǎn)規(guī)則通過禁令等責(zé)任方式激勵事前的談判,責(zé)任規(guī)則允許事后的賠償取代事前協(xié)商。?吉多?卡拉布雷西等著:《財產(chǎn)規(guī)則、責(zé)任規(guī)則與不可讓與性:一個權(quán)威的視角》,明輝譯,載《哈佛法律評論?侵權(quán)法學(xué)精粹》,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不確定性,使事前的談判成本高昂,侵權(quán)警告行為通過權(quán)利的“補(bǔ)強(qiáng)”,成就了財產(chǎn)規(guī)則的適用條件,為此,侵權(quán)警告作出之前,采取責(zé)任規(guī)則,適用損害賠償;警告行為做出之后,由于權(quán)利得到確切性保證,談判成本降低,采取財產(chǎn)規(guī)則,適用禁令、懲罰性賠償?shù)取?/p>
(三)“權(quán)利的聲音”緣何微弱
知識產(chǎn)權(quán)盡管是論爭文化,與其他糾紛類型相比,“權(quán)利的聲音”卻具有天生微弱的一面:權(quán)利人對待侵權(quán)呈現(xiàn)出固有的社會寬容心態(tài),屬于一種寬容文化。即使是在高保護(hù)水平的國家,公眾較之其他非法行為亦更為寬容?[美]安守廉著:《竊書為雅罪:中華文化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李琛譯,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9頁;平新喬:《“新經(jīng)濟(jì)”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從〈信息規(guī)則〉談起》,載《國際經(jīng)濟(jì)評論》2000年第4期。。蘭德斯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專利權(quán)利人通常會“容忍適度的侵權(quán)行為”?[美]威廉?M?蘭德斯、理查德?A?波斯納著:《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的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金海軍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頁。。
這種寬容并非就是利他主義,而是權(quán)利人的自我節(jié)制和約束。原因在于:權(quán)利的呼聲是有代價的,侵權(quán)警告、訴訟等是“雙刃劍”,有可能引火燒身。權(quán)利宣示會招致利益相關(guān)人的抵制,觸發(fā)專利、商標(biāo)無效等確權(quán)程序的啟動,面臨權(quán)利資格在行政、司法的“多重審查”。程序即懲罰,僅其漫長的確權(quán)過程,就會帶來商業(yè)交易的不確定性。而一旦被宣告無效和撤銷,知識產(chǎn)權(quán)資產(chǎn)專用性投資將化為泡影。蘭德斯等人對美國聯(lián)邦巡回法院1982–1992年專利案件的實證分析表明,法院支持有效專利的案件,最低僅為45%(1982年),最高為76%(1985-1986年)?[美]威廉?M?蘭德斯、理查德?A?波斯納著:《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的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金海軍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430頁。。在我國有研究表明,2001–2010年間,專利請求無效量共2萬件左右,在專利復(fù)審中,發(fā)明專利、實用新型被宣告全部無效或部分無效的分別占47.04%和46.37%。?董濤、賀慧:《中國專利質(zhì)量報告》,載《科技與法律》2015年第2期。
相比訴訟,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警告的“聲音”就更加孱弱,原因在于:
第一,正統(tǒng)性。侵權(quán)警告通常被歸為自力救濟(jì)的范疇,是權(quán)利人的自助行為,盡管也是“權(quán)利的實現(xiàn)方式”,卻沒有獲得正統(tǒng)地位。傳統(tǒng)理論認(rèn)為:“根據(jù)禁止自力救濟(jì)的原則,即使在權(quán)利受到實際侵害的情況下,權(quán)利人應(yīng)當(dāng)始終依靠司法程序。不那么做,如果通過審判外的告知、警告來行使權(quán)利造成損害,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賠償責(zé)任。”?[日]田村善之編:《日本現(xiàn)代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理論》,李揚(yáng)等譯,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頁。在雙環(huán)公司與本田株式會社案中,法院既將侵權(quán)警告作為“自力救助行為”“民事權(quán)利的應(yīng)有之義”,同時也顯示出勉強(qiáng):“法律對于在法院侵權(quán)判決之前專利權(quán)人自行維護(hù)其權(quán)益的行為,并無禁止性規(guī)定”。?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三終字第7號民事判決書。
第二,準(zhǔn)入門檻。侵權(quán)警告意在低成本啟動權(quán)利磋商程序。現(xiàn)有的制度卻對警告提出了不切實際的前提,比如,我國臺灣地區(qū)規(guī)定,警告函必須履行確認(rèn)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先行程序方視為正當(dāng),包括法院確權(quán)、第三方調(diào)解等,否則構(gòu)成違法。?我國臺灣地區(qū)“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于事業(yè)發(fā)侵害著作權(quán)、商標(biāo)權(quán)或?qū)@麢?quán)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第3條規(guī)定,“事業(yè)踐行下列確認(rèn)權(quán)利受侵害程序之一,始發(fā)警告函者”,包括:經(jīng)法院判決確權(quán);經(jīng)著作權(quán)審議及調(diào)解委員會調(diào)解認(rèn)定;請專業(yè)機(jī)構(gòu)鑒定取得鑒定報告等。這一做法大大限縮了侵權(quán)警告的范圍。同時,在不確定的條件下進(jìn)行權(quán)利宣示,侵權(quán)警告面臨極大的預(yù)防成本和風(fēng)險,一些法院要求“以警告內(nèi)容的充分性、確定侵權(quán)的明確性為重點”。?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三終字第7號民事判決書。 最高人民法院同時也指出:“不能過高要求權(quán)利人對其警告行為構(gòu)成侵權(quán)的確定性程度,否則會妨礙侵權(quán)警告制度的正常效用和有悖此類制度的初衷。”
第三,回旋余地。權(quán)利協(xié)商是迂回而漫長的過程,現(xiàn)有制度大有“開弓沒有回頭箭”之勢。比如,《關(guān)于審理侵犯專利權(quán)糾紛案件應(yīng)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guān)于權(quán)利人不撤回警告、不提起訴訟的限期分別為“一個月”和“二個月”,期限屆滿,被警告人有權(quán)提起不侵權(quán)之訴。該規(guī)定意在鼓勵當(dāng)事人即時訴訟,避免權(quán)利的不安定狀態(tài),卻人為地制造了司法界權(quán)的緊迫性、權(quán)利面臨的即時威脅性。實踐中,雙方不了了之、權(quán)利的拋棄等本身就是權(quán)利界定方式。再如,雙環(huán)公司與本田株式會社案中,法院以被警告人提起不侵權(quán)之訴為界限,區(qū)分了前后不同的兩階段,就此認(rèn)定進(jìn)入訴訟之后再行提出警告是不正當(dāng)?shù)摹T谠V訟之中限制侵權(quán)警告并無助于鼓勵私人磋商,頗需檢討。由于司法成本高昂,理論上,建立審判制度的重要原因在于,“給受害者以必要的威懾來誘使其進(jìn)行和解”?[美]斯蒂文?沙維爾著:《法律經(jīng)濟(jì)分析的基礎(chǔ)理論》,趙海怡等譯,中國人民大學(xué)2103年版,第373頁。,對待訴訟中的和解理應(yīng)給予“高度尊讓”?[美]克里斯蒂娜?博翰楠等著:《創(chuàng)造羈限:促進(jìn)創(chuàng)新中的自由與競爭》,蘭磊譯,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7、103頁。。
三、警告與訴訟:尋求權(quán)利界定成本的最小化
(一)知識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的訴訟膨脹
晚近十年,我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糾紛案件連創(chuàng)新高?我國一審知識產(chǎn)權(quán)案件受理量,2012年突破10萬件,2015、2016年都以達(dá)到13萬件以上。,北京等地設(shè)立了專門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院,但是,“案件數(shù)量增長遠(yuǎn)超預(yù)期,辦案壓力持續(xù)增大”?。訴訟膨脹其實充滿著悖論:我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事業(yè)僅僅走過三十余年,質(zhì)量整體偏低,“含金量”不足,權(quán)利人對他人本應(yīng)有更多的寬容,以避免觸發(fā)他人的反制行動。知識產(chǎn)權(quán) “好訴”現(xiàn)象的泛濫,有多方面的原因。
1.作為市場替代的訴訟
知識產(chǎn)權(quán)糾紛不只是法律現(xiàn)象,更是市場問題,當(dāng)市場交易成本過高時,當(dāng)事人會選擇侵權(quán)或放任侵權(quán),尋求訴訟解決。51謝曉堯、林良倩:《權(quán)利何以通約——華蓋公司作品維權(quán)的標(biāo)本意義》,載《學(xué)術(shù)研究》2012年第8期。(1)就侵權(quán)人而言,侵權(quán)和事前許可能夠相互替代,當(dāng)侵權(quán)更具成本優(yōu)勢時,就不會選擇事前的談判。知識產(chǎn)權(quán)具有無形性,排他成本異常高,容易滋長機(jī)會主義;模糊區(qū)的廣泛存在,權(quán)利核實和確證成本高昂;知識產(chǎn)品異質(zhì)性較強(qiáng),估價困難。市場交易成本過高會誘導(dǎo)使用者謀求事后“定損”,與其事前獲得授權(quán)不如靜候他人的“官司”。(2)就權(quán)利人而言,當(dāng)許可市場交易成本高時,也會“放水養(yǎng)魚”放任侵權(quán),尋求事后的補(bǔ)償,原因在于:用戶的市場需求心理,是內(nèi)斂的,發(fā)現(xiàn)成本高昂,但是侵權(quán)行為具有外顯性,發(fā)現(xiàn)成本低;事前的許可會受到預(yù)算的硬約束,消費(fèi)的范圍和程度受到抑制,放任侵權(quán)產(chǎn)生了權(quán)利失控的假象,為使用者無節(jié)制的消費(fèi)提供了激勵;當(dāng)知識產(chǎn)品的替代性強(qiáng),權(quán)利人并無事前的議價優(yōu)勢,侵權(quán)則如同向權(quán)利人提供了“人質(zhì)質(zhì)押”,有利于獲得談判優(yōu)勢。同時,訴訟具有某種組織優(yōu)勢:市場談判面臨“破局”的可能性,司法屬于管理型的交易,法院不能拒絕裁判,當(dāng)事人也不能抵制法院的“強(qiáng)制性”交易;法院處理糾紛有嚴(yán)格的程序,時間上可預(yù)期,不會無休止地討價還價;司法具有歷史價格(過往判決)的可參照性,是當(dāng)事人權(quán)利界定中權(quán)威的“定價中心”。
2.“稟賦效應(yīng)”
行為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提出了著名的“稟賦效應(yīng)(endowment effect)”:人類具有損失厭惡的心理趨勢,物品一旦擁有,對其價值評價要比未擁有之前大大提高,不愿意輕易放棄。52參見[美]丹尼爾?卡尼曼著:《思考,快與慢》,胡曉嬌等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52–273頁;[美]理查德?泰勒:《“錯誤”的行為:行為經(jīng)濟(jì)學(xué)關(guān)于世界的思考,從個人到商業(yè)和社會》,王晉譯,中信出版集團(tuán)2016年版,第165–173頁。稟賦效應(yīng)理論包括許多非理性怪癖:在實際擁有所有權(quán)之前就產(chǎn)生擁有的感覺;一旦成為所有者,會生活在“損失體驗”之中,強(qiáng)迫自己防止失去。53[美]丹?艾瑞里著:《怪誕行為學(xué):可預(yù)測的非理性》,趙德亮等譯,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99–107頁。知識產(chǎn)權(quán)是強(qiáng)稟賦效應(yīng)的一類財產(chǎn),由于缺乏實物世界的物理可控性,所有權(quán)邊界是“虛擬”的,這會產(chǎn)生無所節(jié)制的權(quán)利占有欲。比如:知識極具供給彈性,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在很大程度上侵害的是一種“許可價值”,即使用權(quán),權(quán)利人通常會放大“損失體驗”,主張對所有權(quán)的動搖。知識產(chǎn)權(quán)存在兩種相互背離的趨勢:權(quán)利的相對性滋養(yǎng)著寬容的文化心理,傾向于合作、減少紛爭;權(quán)利的稟賦效應(yīng),滋生非理性的樂觀主義,“敝帚自珍”,高估和夸大其價值,更多地主張權(quán)利、增加糾紛。
3.法定賠償
我國是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定賠償適用范圍最為廣泛的國家,現(xiàn)行《商標(biāo)法》《專利法》和《著作權(quán)法》均有規(guī)定,新修訂的《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也引入了該制度;法定賠償?shù)淖罡呦揞~也“輪番上漲”542001年《商標(biāo)法》、2001年《著作權(quán)法》規(guī)定的法定賠償為50萬以下;2008年《專利法》為100萬以下, 2013年《商標(biāo)法》為300萬以下,2014年的《著作權(quán)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為100萬以下,2015年的《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為10萬–500萬。。法定賠償并非各國立法通例,適用國家有限55美國和俄羅斯的商標(biāo)法規(guī)定了法定賠償(參見《十二國商標(biāo)法》,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版);美國的版權(quán)法規(guī)定了法定賠償(參見《十二國著作權(quán)法》,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專利法中鮮見該規(guī)定。,最高限額也不及我國56《美國版權(quán)法》第504條規(guī)定,不低于750美元或者不超過30000美元,系故意實施的,不超過15萬美元;《蘭哈姆法》規(guī)定,仿冒商標(biāo)的不少于500美元或不超過10萬美元,系惡意的不超過100萬美元。。法定賠償是一種訴訟激勵措施,其本質(zhì)是假定“法定損失”的存在,而無須當(dāng)事人證明。其目的在于鼓勵訴訟,即當(dāng)實際損害賠償很小或損害難以證明時,為避免侵權(quán)行為的檢舉概率偏低,鼓勵受害人起訴。57這方面更明顯地體現(xiàn)在美國有關(guān)消費(fèi)者保護(hù)的立法中,該領(lǐng)域大量立法規(guī)定了固定上、下額的法定賠償,法院在判決中明確闡明法定賠償旨在鼓勵私人訴訟,并指明特別適用于“實際賠償很小或難以證明的案件”。See Sheila B. Scheuerman, Due Process Forgotten: The Problem of Statutory Damages and Class Actions,74 Mo. L. Rev. 103 (2009), p107, p.110.美國在商標(biāo)假冒中適用法定賠償,一個考慮因素是假冒行為猖獗,假冒者通常銷毀財務(wù)證據(jù),難以取證,必須鼓勵權(quán)利人維權(quán)。Aaron L. Melville, New Cybersquatting Law Brings Mixed Reactions from Trademark Owners, 6 B. U. J. Sci. & Tech. L. 324 (2000), p.327.在我國,法定賠償可以為法官的司法定損確立簡便性的“標(biāo)準(zhǔn)”。但是,這一制度會激勵訴訟行為的過度投資,維權(quán)過度又會加劇司法的錯誤成本。訴訟是不確定狀態(tài)下博弈,當(dāng)訴訟的成本高于其收益時,潛在的權(quán)利人會放棄訴訟,這是“不確定性之美”58有時候,不確定性是不可缺少的,甚至“模糊比精確更可取”。參見[荷]基斯?范迪姆特著:《不確定之美:給模糊的贊歌》,胡焰林譯,時代出版?zhèn)髅焦煞萦邢薰荆?頁。。法定賠償保障了權(quán)利人“損失缺失”下的確定性收益,“好訴”現(xiàn)象自然會流行。
(二)“警告先于訴訟”:糾紛的過濾和分流
法律程序的目標(biāo)在于最小化糾紛解決的社會成本59[美]羅伯特?考特等著:《法和經(jīng)濟(jì)學(xué)》(第六版),史晉川等譯,格致出版社2012年版,第379頁。。為避免更大的司法運(yùn)行成本,可行的制度安排是:將侵權(quán)警告作為法定的前置程序,優(yōu)先于司法程序,權(quán)利人只有采取侵權(quán)警告之后方有權(quán)提起訴訟。德國的《著作法》和《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采取的就是這一做法60因為簡單、快捷、花費(fèi)低而且有效,在實踐中90%~95%的競爭糾紛通過這種訴訟外的警告程序得到了解決,以至于警告制度逐漸發(fā)展成為一種習(xí)慣法。而后迅速被其他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采納。轉(zhuǎn)引自范長軍:《專利侵權(quán)警告制度探析——對專利法第四次修改的建議》,載《知識產(chǎn)權(quán)》2014年第3期,注釋。。“警告先于訴訟”的功能在于,過濾和甄別不同性質(zhì)的侵權(quán)糾紛,引導(dǎo)案件的分流。將沒有社會收益、能低成本協(xié)商的案件,激勵其私人協(xié)商,避免“低私人收益,高社會成本”的不合理配置。私人調(diào)解是爭議解決的最主要方式,當(dāng)且僅當(dāng)警告之下調(diào)解比訴訟更具效率時,當(dāng)事人通常才會選擇達(dá)成協(xié)議。在我國,最近十年來,一審知識產(chǎn)權(quán)民事案件的調(diào)撤率均維持在60%以上,平均調(diào)解率超過65%。61參見歷年的《中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年鑒》《全國法院司法統(tǒng)計公報》和《中國法院知識產(chǎn)權(quán)司法保護(hù)狀況》。這表明大量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案件具有和解的基礎(chǔ),程序的設(shè)計與優(yōu)化,應(yīng)當(dāng)是激勵當(dāng)事人更愿意在訴前調(diào)解而不是訴訟中調(diào)解。那么,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警告如何過濾和分流?
1.引導(dǎo)訴訟案件追求社會收益
訴訟的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并不一致,私人收益在乎賠償?shù)臄?shù)量。何種案件值得耗費(fèi)社會成本通過訴訟解決?沙維爾認(rèn)為,訴訟的社會收益,包括威懾效應(yīng)和先例的開啟。62[美]斯蒂文?沙維爾著:《法律經(jīng)濟(jì)分析的基礎(chǔ)理論》,趙海怡等譯,中國人民大學(xué)2103年版,第357頁。前者使訴訟獲得了范圍經(jīng)濟(jì),間接地引導(dǎo)人們的行為,后者創(chuàng)造了增量知識。哈特認(rèn)為,法庭不僅解決爭端,而且基于爭端傳播規(guī)則,是否值得花費(fèi)公共補(bǔ)貼去解決私人爭端,取決于解決爭端之外能否還有“外在收益”,即創(chuàng)造司法知識(規(guī)則、先例)的可能性。“訴訟具有兩個獨(dú)立的功能——解決爭端和創(chuàng)造規(guī)則。訴訟的公共補(bǔ)貼歸因于訴訟的規(guī)則創(chuàng)造功能。”他同時指出,大量的判決是沒有作為規(guī)則使用的“未來價值”。63[美]奧利弗?哈特等著:《現(xiàn)代合約理論》,易憲容等譯,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154頁。巴澤爾也有同樣的觀點,在不完備的產(chǎn)權(quán)中,糾紛與權(quán)利的形成息息相關(guān),解決糾紛就是界定權(quán)利,法院的權(quán)利界定方式有兩種:一是直接的,法院實際處理糾紛;二是間接的,糾紛解決會帶來一種“公共物品”——先例的確切性對類似糾紛進(jìn)行了權(quán)利界定,會引導(dǎo)人們不以訴訟方式解決其糾紛。64[美]Y.巴澤爾著:《產(chǎn)權(quán)的經(jīng)濟(jì)分析》,費(fèi)方域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9年版,第95-96頁。在普通法國家,創(chuàng)造先例以提供資源配置的效率是理解其法律制度的關(guān)鍵。65[美]尼古拉斯?麥考羅等著:《經(jīng)濟(jì)學(xué)與法律——從波斯納到后現(xiàn)代主義》,吳曉露等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頁.
回到我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案件結(jié)構(gòu)和特征耐人尋味:60%以上的被告為中小微企業(yè)(銷售者)、個體工商戶,系列案、“批量訴訟”居多,“職業(yè)維權(quán)人”參與其中66在長沙,60%的案件以個體工商戶或個人為被告,84%的案件涉及與銷售行為類似的終端侵權(quán)行為。參見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chǎn)權(quán)民事案件損害賠償額判定狀況(2011—2015)》。上海、浙江、山東的情況大致相當(dāng)。參見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年上海法院知識產(chǎn)權(quán)審判白皮書》;《山東法院知識產(chǎn)權(quán)司法保護(hù)報告》(2013)。。權(quán)利人通常的訴訟策略是,被告面臨更大的信息不對稱,議價能力和反制能力弱,缺乏挑戰(zhàn)權(quán)利的要挾手段,因此案件解決的回旋余地大。這類案件,原告的權(quán)利通常較為確定,處于核心的“非爭議區(qū)”,案件多為“真侵權(quán),假糾紛”,法院也可以進(jìn)行標(biāo)準(zhǔn)化的處理。這些案件耗費(fèi)司法成本,卻無法產(chǎn)生外部收益,不具“未來價值”。訴訟不僅僅是解決個案,有效率的司法安排應(yīng)當(dāng)是,既能為權(quán)利界定生產(chǎn)出增量知識,也能發(fā)揮傳遞、引導(dǎo)和協(xié)調(diào)他人行為的間接功能。
2.引導(dǎo)和促進(jìn)知識產(chǎn)權(quán)糾紛的私人和解
我國目前的絕大部分案件,與其說是“維權(quán)”,不如說是“定損”,司法運(yùn)行(管理)成本和司法錯誤成本巨大。法院可以參照歷史上同類案件判決的賠償中位值,確定公允性的損失。法院畢竟不是市場,過分依賴司法定損,會模糊司法的功能和地位,挫敗市場的價格機(jī)制。司法實踐中,大量知識產(chǎn)權(quán)損害賠償不是建立在科學(xué)的評估和測定基礎(chǔ)上,而是法定賠償限額內(nèi)“瞎子摸象”的游戲67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chǎn)權(quán)民事案件損害賠償額判定狀況(2011—2015)》對770件案件的統(tǒng)計表明:法定賠償?shù)倪m用率高達(dá)98.2%。已有的研究報告,結(jié)論高度吻合。參見萬迪等:《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損害賠償制度實施效果分析及完善路徑——以北京法院判決書為考察對象(上)》,載《中華商標(biāo)》2016年第4期;詹映等:《我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司法判例實證研究——以維權(quán)成本和侵權(quán)代價為中心》,載《科研管理》2015年第7期;段蕓蕾、謝曉堯:《論商標(biāo)侵權(quán)案件中的損害賠償水平》,載《政法學(xué)刊》2014年第2期。,由此引發(fā)了“賠償?shù)汀薄氨Wo(hù)力度不夠”的社會觀感與反響68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執(zhí)法檢查組關(guān)于檢查〈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情況的報告》(2014年6月23日)。。賠償定損當(dāng)然也能輸出司法知識,產(chǎn)生未來價值。但是,法官本身并不具備發(fā)現(xiàn)和制定價格的能力,具有這種能力的是公平而科學(xué)地發(fā)現(xiàn)價格的司法程序。在知識產(chǎn)權(quán)案件中,訴訟程序通過有效引入開放性的對話協(xié)商機(jī)制,讓專家證人、專家輔助人、科學(xué)證據(jù)、市場調(diào)查報告、專家證言、“法庭之友”等都參與知識的競爭市場,在這種高度對抗性的知識論證中,由法官決定哪一種優(yōu)勢知識勝出。顯然,司法程序一旦開啟,運(yùn)行成本代價高昂,這是世界性的現(xiàn)象69許多研究發(fā)現(xiàn),侵權(quán)責(zé)任制度的運(yùn)行成本已經(jīng)接近甚至超過了受害者所得賠償?shù)臄?shù)量。參見斯蒂文?沙維爾著:《法律經(jīng)濟(jì)分析的基礎(chǔ)理論》,趙海怡等譯,中國人民大學(xué)2103年版,第256頁,我國也不能例外。
案件缺乏合理的分流,會模糊司法功能,直接影響法院組織體系的建設(shè):(1)如果司法的主要功能在于解決個案,基于案件法律問題簡單,多為“真侵權(quán),假糾紛”的現(xiàn)實,知識產(chǎn)權(quán)司法應(yīng)當(dāng)是審判力量的“下沉”和程序的簡化,比如,放開基層法院的案件管轄權(quán),推行簡易程序和獨(dú)任審判,重視和發(fā)揮基層調(diào)解能手的作用。忽略糾紛的真實類型與結(jié)構(gòu),一味強(qiáng)調(diào)知識產(chǎn)權(quán)技術(shù)性強(qiáng)、專業(yè)性高、法律復(fù)雜,有可能導(dǎo)致司法組織的“超標(biāo)配置”,制度成本過高。(2)如果司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增進(jìn)社會收益,訴訟案件就應(yīng)鎖定“真糾紛”,審判本質(zhì)是“二次界權(quán)”,既關(guān)乎提升知識產(chǎn)權(quán)質(zhì)量,也事關(guān)新制度知識(司法規(guī)則)的輸出,牽一發(fā)而動全身,裁判需要更大的膽略、正當(dāng)性和權(quán)威性,就應(yīng)當(dāng)由更高層級的審判組織來擔(dān)當(dāng)“守門人”,比如設(shè)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chǎn)權(quán)巡回法庭。現(xiàn)行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院的設(shè)置,既不能高效率地解決個案,也不能增進(jìn)社會收益。
(三)“可信的威脅”:侵權(quán)警告如何促成私人協(xié)商
與“訴訟熱”形成鮮明對比,我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警告的運(yùn)用相當(dāng)有限70筆者在北大法寶司法案例庫進(jìn)行檢索,在全部319, 078條知識產(chǎn)權(quán)案件中,涉及到權(quán)利人發(fā)警告函的僅為850條。http://www.pkulaw.cn/Case/,最后訪問日期:2017年9月14日。。“警告先于訴訟”旨在促使當(dāng)事人以協(xié)議的方式替代訴訟,為達(dá)此目的,就應(yīng)當(dāng)讓侵權(quán)警告對雙方都具有“威脅價值”,以消除各自的樂觀主義:(1)對于潛在的侵權(quán)人而言,權(quán)利人的權(quán)利越具確定性,越能使其認(rèn)識到侵權(quán)行為的嚴(yán)重性;(2)對權(quán)利人而言,可能遇到的權(quán)利挑戰(zhàn)和法律難題越多,越有可能從權(quán)利迷戀和虛妄損失中走出來。基于這一原理,可以對侵權(quán)警告及其配套制度進(jìn)行優(yōu)化設(shè)計71范長軍先生曾建議在專利法修改稿中明確規(guī)定警告函:“專利權(quán)人或利害關(guān)系人在向法院起訴或請求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處理之前,應(yīng)警告侵權(quán)嫌疑人。侵權(quán)嫌疑人應(yīng)作出以合理的違約金作保證的停止侵權(quán)的承諾(服從聲明)。只要警告是合法的,警告人可以請求賠償必要的費(fèi)用。侵權(quán)嫌疑人收到警告之后不予回應(yīng)、再實施同樣的行為且法院或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認(rèn)定侵權(quán)行為成立的,法院或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可以責(zé)令三倍的損失賠償。”其建議基本反映了上述機(jī)理。參見范長軍:《專利侵權(quán)警告制度探析——對專利法第四次修改的建議》,載《知識產(chǎn)權(quán)》2014年第3期。。
1.警告行為中的保證:“有保障的信任”
知識產(chǎn)權(quán)具有相對性,警告行為是一種威脅性的權(quán)利宣示。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被警告方當(dāng)然難以接受。要達(dá)到以威懾促合作的效果,權(quán)利人就必須獲取被警告人的信賴。獲取信任的方式有多種,威廉姆森認(rèn)為存在一種通過采取保障措施來處理雙方關(guān)系的“算計性信任”,比如使用債券、抵押、信息披露規(guī)則等,都是“精心安排各種可信的承諾”,“創(chuàng)造信任功能的替代品”。72[美]Oliver E?威廉姆森著:《治理機(jī)制》,王健等譯,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頁。顯然,警告人通過保證行為向潛在的侵害人提供“有保障的信任”,有利于獲取對方對權(quán)利的信任。同樣的道理適用于被警告人,如果其堅信沒有侵權(quán),在警告之后要繼續(xù)其經(jīng)營行為,合理的做法是提供相應(yīng)的擔(dān)保。
為此,制度可以設(shè)計為:權(quán)利人發(fā)出侵權(quán)警告,必須對其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權(quán)利有效性作出保證,對警告行為可能引發(fā)的權(quán)利瑕疵和行為瑕疵承擔(dān)法律責(zé)任;在糾紛解決前,被警告人可以向警告人提供擔(dān)保以繼續(xù)其生產(chǎn)經(jīng)營行為,生產(chǎn)商可以為經(jīng)銷商、代理商提供擔(dān)保,以繼續(xù)其銷售行為。
警告人和被警告人的相互保證,本質(zhì)上雙方“捆綁”為“人質(zhì)”,增強(qiáng)了各自的報復(fù)能力,警告行為威脅變得“可信”:如果警告沒有根據(jù),警告人面臨責(zé)任;如果警告有根據(jù),被警告人必須停止侵權(quán);被警告人有合理的依據(jù)不停止侵權(quán),就得提供反擔(dān)保。這既是一種“壓迫”機(jī)制,也是一種甄別機(jī)制,就前者而言,它有利于迫使雙方傾向于妥協(xié)和讓步;就后者而言,可以借此過濾案件,訴訟解決的糾紛是存在權(quán)利爭議的“真糾紛”。
2.侵權(quán)警告對侵權(quán)人“惡意”的固化
法律的實施具有不完備性,侵權(quán)的治理不在于消滅侵權(quán),而在于通過成本的施加,引導(dǎo)潛在侵害人采取事前的預(yù)防措施,減少未來侵害的發(fā)生量。侵權(quán)警告應(yīng)當(dāng)引導(dǎo)當(dāng)事人選擇成本更為低廉的預(yù)防措施,在發(fā)生侵權(quán)的場合,選擇私人之間的協(xié)商。為此,制度上可行的做法:被警告人收到警告函之后既不停止侵權(quán),也不提供有效保證的,視為惡意侵權(quán)。
其經(jīng)濟(jì)機(jī)理在于:法律責(zé)任的功能是補(bǔ)償與威懾,補(bǔ)償是面向過去的補(bǔ)救,威懾則指向未來的防范,在我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審判也明確了司法威懾功能73《關(guān)于當(dāng)前經(jīng)濟(jì)形勢下知識產(chǎn)權(quán)審判服務(wù)大局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fā)[2009]23號)指出:“增強(qiáng)損害賠償?shù)难a(bǔ)償、懲罰和威懾效果,降低維權(quán)成本,提高侵權(quán)代價。”。通常認(rèn)為,威懾功能的發(fā)揮既可以提高侵權(quán)行為的查處概率,也可以加大侵權(quán)行為的究責(zé)嚴(yán)厲性。從效率性出發(fā),最優(yōu)威懾力的組合是:“低的查處概率,高的懲處強(qiáng)度”74[美]斯蒂文?沙維爾著:《法律經(jīng)濟(jì)分析的基礎(chǔ)理論》,趙海怡等譯,中國人民大學(xué)2103年版,第430-431頁;[美]羅伯特?考特等:《法和經(jīng)濟(jì)學(xué)》(第五版),史晉川等譯,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第336頁;[美]理查德?A?波斯納著:《正義/司法的經(jīng)濟(jì)學(xué)》,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頁。。低查處概率節(jié)省了法律運(yùn)行成本,高的懲處強(qiáng)度能產(chǎn)生足夠的威懾力,而不會降低潛在加害人的防范水平。運(yùn)用侵權(quán)警告進(jìn)行過濾、分流,減少訴訟數(shù)量的同時,合理的做法是保持對侵權(quán)行為高嚴(yán)厲的究責(zé)。高懲處強(qiáng)度只能針對惡意侵權(quán)行為,全面實施有可能加大社會的防范成本,并不可取。以警告行為“物化”主觀惡意,也能節(jié)省司法管理成本,在我國司法實踐中,侵權(quán)警告行為成為判斷當(dāng)事人主觀過錯的證據(jù)75在孫俊義與鄭寧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認(rèn)為,銷售商已經(jīng)收到該警告函的情況下,原則上可以推定銷售商知道其銷售的是專利侵權(quán)產(chǎn)品。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036號民事裁定書。。
3.對惡意侵權(quán)實施“財產(chǎn)規(guī)則”
通常認(rèn)為,財產(chǎn)規(guī)則實則是以威懾為特征的強(qiáng)制手段,增強(qiáng)和鞏固權(quán)利人在討價還價中的地位76[美]羅伯特?庫特:《整合侵權(quán)、合同和財產(chǎn)法:防范模式》,載[美]唐納德?A.魏特曼編:《法律經(jīng)濟(jì)學(xué)文獻(xiàn)精選》,蘇力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頁。,以便在禁令陰影下,促成潛在的事前協(xié)商77Mark Schankerman and Suzanne Scotchmer, Damages and injunctions in 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32,No.1, Spring 2001. pp.199-220.。按照蘭德斯等人的說法,責(zé)任規(guī)則允許資源從受害人向侵害人轉(zhuǎn)移而不用經(jīng)過受害人的同意,而財產(chǎn)規(guī)則下任何占有行為都是被禁止的,當(dāng)市場成本較低時,財產(chǎn)制度比責(zé)任制度更具經(jīng)濟(jì)性;但當(dāng)市場交易的成本較高時,財產(chǎn)制度就略遜一籌了,因為它有礙于資源的最優(yōu)配置。78[美]威廉?M?蘭德斯等著:《侵權(quán)法的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王強(qiáng)等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頁。考特等人說得更加直接了:“賠償一般是合同法和侵權(quán)法的救濟(jì)方法,而禁令一般是財產(chǎn)法的救濟(jì)方法。”79[美]羅伯特?考特等著:《法和經(jīng)濟(jì)學(xué)》(第六版),史晉川等譯,格致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頁。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究竟適用財產(chǎn)規(guī)則還是責(zé)任規(guī)則?學(xué)界存在較大分歧,盡管也有人批評財產(chǎn)規(guī)則下的禁令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沒有效率80邁克爾?A?艾因霍恩著:《媒體、技術(shù)和版權(quán):經(jīng)濟(jì)與法律的融合》,趙啟衫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頁。,不過主流的觀點還是認(rèn)為,財產(chǎn)規(guī)則對于激勵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私人談判更為有效81[美]斯格特?凱夫:《關(guān)于專利法律與政策的經(jīng)濟(jì)學(xué)》,載竹中俊子主編:《專利法律與理論——當(dāng)代研究指南》,彭哲等譯,知識產(chǎn)權(quán)出版社2013年版。莫杰斯也認(rèn)為,財產(chǎn)規(guī)則在涉及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許多情況下都是效的。(Robert P. Merges. Toward a Third Intellectual Properly Paradigm: Of Property Rules, Coa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94 Colum. L. Rev. 2655,1994, pp.2655-2673.)。本文認(rèn)為,在侵權(quán)警告之前,知識產(chǎn)權(quán)并不具有有形財產(chǎn)的確定性和唯一性,事前的談判成本高,一概適用財產(chǎn)規(guī)則未必可取;但是,權(quán)利人發(fā)出侵權(quán)警告行為,尤其是通過保證進(jìn)行權(quán)利補(bǔ)強(qiáng)之后,適用財產(chǎn)規(guī)則,更有利于鼓勵當(dāng)事人選擇協(xié)商。財產(chǎn)規(guī)則的責(zé)任承擔(dān)方式多樣,包括:刑事制裁、行政處罰或者民事上的禁令、強(qiáng)制履行、返還原物、恢復(fù)原狀、排除妨害、懲罰性賠償。我國不同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立法已經(jīng)全面引入懲罰性賠償,適用條件如何把握?可行的做法是通過警告行為判斷惡意作為要件。
基于此,制度可以設(shè)計為:對惡意侵權(quán)行為,權(quán)利人有權(quán)請求人民法院采取禁令、恢復(fù)原狀、排除妨害和懲罰性賠償,侵權(quán)人得依法承擔(dān)行政和刑事責(zé)任。
4.侵權(quán)人得承擔(dān)警告費(fèi)用
侵權(quán)警告函通常以律師函的名義發(fā)出,律師在法律地位上是專家,負(fù)有更大注意義務(wù),對不恰當(dāng)?shù)木嬗兄斑^濾”的作用,有利于避免糾紛,預(yù)防更為高昂的司法運(yùn)行成本。這涉及到律師費(fèi)等警告開支費(fèi)用,如果警告行為合法,這筆費(fèi)用由侵權(quán)人承擔(dān),有利于激勵其采取事前的預(yù)防。82這筆費(fèi)用并不小,《德國著作權(quán)法》規(guī)定,警告函合法時,收件人應(yīng)支付必要的花費(fèi)(尤其是律師費(fèi))。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的興起,權(quán)利人和律師已經(jīng)把警告函作為一項額外收入的方式,出現(xiàn)了“警告函洪流”,以至于法院和政府部門要對簡單明了、非實質(zhì)性侵權(quán)的案件采取限制律師服務(wù)的費(fèi)用。參見[法]喬治?卡明等著:《荷蘭、英國、德國民事訴訟中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執(zhí)法》,商務(wù)印書館2014年版,第332-333頁。
5.警告人權(quán)利有效性和行為合法性之確保
在知識產(chǎn)權(quán)相對性的困局中,權(quán)利人面臨兩難:一方面,法律賦予了其紙面所有權(quán),對侵權(quán)行為不警告,則有可能身處權(quán)利松懈、逆權(quán)占有等不利境地;另一方面,一旦發(fā)出警告,除了引發(fā)撤銷和宣告無效的風(fēng)險之外,還面臨警告失當(dāng)?shù)木薮箦e誤成本,比如,禁止反悔、商業(yè)詆毀、權(quán)利濫用和干擾商業(yè)關(guān)系83侵權(quán)警告若不存在“散布”、也未侵犯對方聲譽(yù),可構(gòu)成對他人商業(yè)關(guān)系的干擾。《美國侵權(quán)法重述》中的干擾商業(yè)關(guān)系包括:故意干涉合同關(guān)系和干涉預(yù)期合同關(guān)系。我國司法實踐多作為不當(dāng)攫取商業(yè)機(jī)會。。
通常認(rèn)為,雙方談判范圍過于狹窄時,結(jié)果會不對等地偏向具有議價能力的一方,制約了調(diào)解的可能性;將談判事項擴(kuò)展,相互制衡的權(quán)利反而會促進(jìn)雙方尋求“下臺階”,增加合作的余地。在侵權(quán)警告中,權(quán)利的不確定性使得雙方都有制衡對方的“威脅價值”,反制對方的能力會使威脅變得可信。由于雙方都有規(guī)避風(fēng)險的需求,妥協(xié)也就成為可能性,所謂“合作是最佳的選擇”。按照沙維爾的說法:“一旦我們將風(fēng)險規(guī)避程度引入以上的基本模型,和解的幾率會變得更大。其理由很簡單:因為審判結(jié)果乃是未知數(shù),進(jìn)入審判程序本身就是一項冒險的行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任意一方的風(fēng)險規(guī)避程度越高,或標(biāo)的額度——也就是判決金額或者法律費(fèi)用——越高,和解就會變得愈發(fā)可能。”84[美]斯蒂文?沙維爾著:《法律經(jīng)濟(jì)分析的基礎(chǔ)理論》,趙海怡等譯,中國人民大學(xué)2103年版,第367頁。
結(jié) 語
知識產(chǎn)權(quán)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存在巨大的模糊區(qū),這使得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事后界定制度變得尤為重要。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權(quán)利界定和糾紛解決模式很多,諸如侵權(quán)警告、訴訟、第三方調(diào)解、行政解決,等等。法律應(yīng)當(dāng)激勵當(dāng)事人選擇最有成本優(yōu)勢的方式。侵權(quán)警告不僅具有宣示保護(hù)產(chǎn)權(quán)的策略功能,更是一種雙方威懾互動、互摸底牌、確定產(chǎn)權(quán)邊界的過程。“侵權(quán)—警告”是知識產(chǎn)權(quán)重要的論爭程式,權(quán)利的明晰、界定和維護(hù)在高度對抗中得以實現(xiàn),此乃其特殊的物品屬性決定的。在我國,晚近以來,知識產(chǎn)權(quán)訴訟案件不斷增加,侵權(quán)警告遭受冷遇,同時呈現(xiàn)出兩個看似矛盾的趨勢:維權(quán)過度和侵權(quán)泛濫,訴訟膨脹加劇了司法成本,暴露出現(xiàn)行制度無法有效激勵當(dāng)事人之間的私人協(xié)商。司法的運(yùn)行成本和錯誤成本都非常高昂,必須對不同的侵權(quán)糾紛進(jìn)行過濾和分流。一種可行的選擇是,將侵權(quán)警告作為前置性程序優(yōu)先于訴訟程序,權(quán)利人行使警告行為之后方能起訴。為加大警告行為的“可信性”,在制度設(shè)計上可以考慮權(quán)利人作出警告必須提供保證;被警告人收到警告不停止侵權(quán)的,視為惡意侵權(quán),須承擔(dān)禁令和懲罰性賠償。侵權(quán)警告制度的設(shè)計應(yīng)鼓勵權(quán)利人自愿性的產(chǎn)權(quán)再界定,降低司法成本,增加法律責(zé)任威懾的可信性,激勵當(dāng)事人采取預(yù)防行為,消除潛在的侵權(quán)行為。侵權(quán)警告當(dāng)然會產(chǎn)生一系列法律問題,制度的選擇從來是“兩害相權(quán)取其輕”。或許,我們較佳的安排是:最少的司法干預(yù),最大的市場博弈,“……必須去聽一聽那些狗的叫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