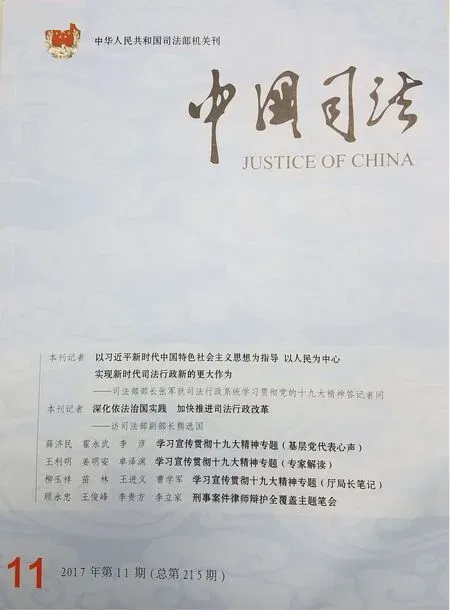律師調解:經由“試點=實驗”的制度構建
王亞新(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律師調解:經由“試點=實驗”的制度構建
王亞新(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最近共同發布《關于開展律師調解試點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味著十余年來一直有律師事務所在探索嘗試的律師調解工作正式走上了制度建構的軌道。律師調解作為一種法律服務的現象或者社會事實,只要有律師職業就始終存在。不過,律師在制度上站到中立的位置,充當調解人為當事人雙方提供處理解決糾紛的服務,則是給內容已經相當豐富的我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再增添一個新的“品種”。而且,與傳統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相區別,律師調解自有其特點,這種糾紛解決方式的制度化將會起到十分積極的作用,能夠在建設法治中國的進程中作出自身獨特的貢獻。
關于律師調解的特點,首先可以通過與在我國社會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中占據主要地位的人民調解制度相對比來加以考察。人民調解源遠流長,植根于我國傳統上與血緣地緣等人際關系網絡緊密相關的民間調解。這種調解注重道德倫理和地方性知識,往往適合處理解決日常生活中“磕磕碰碰”引起的矛盾糾紛。與此不同,律師調解則主要是運用法律專業知識,促使當事人各自認識理解已方立場在法律上是否有理的“強弱”態勢,再設法幫助雙方形成法律框架內利益相互兼容的解決方案。因此,如果屬于“注入”法律專業知識能夠使糾紛解決的方向得以明確、當事人雙方也易于理性地接受此類解決方案的糾紛類型,就可能更加適合由律師充任調解人來進行處理解決。在這個意義上,律師調解如果能夠得到廣泛的運用,往往可能帶來法律專業知識向社會生活中牽涉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各個領域持續“注入”或者“滲透”的效果,在法律知識的普及、法治意識的增強等方面發揮更為顯著的積極功能。
其次,與商事領域等行業的調解或者交警對于交通事故糾紛的行政調解等更具專業性的調解相比,律師調解的特點則在于其專業背景的一般性或泛用性。律師作為具備一般法律專門知識的專家,能夠單獨或者采取與其他行業或專業的調解相配合的方式為不同領域的糾紛提供調解的法律服務。在這一點上,律師調解與法院的審判就法律專門知識的同構性而言可能更加接近也更容易銜接。因此,在律師調解形成一定規模之后,法院將已起訴的案件分流給律師事務所或律師調解中心實行委托調解,或者律師調解的相關紀錄在訴訟程序中使用等程序性事項的推進,可以期待獲致更好的效果。
從理論上講,律師調解雖然具有上述的意義及種種優點,但以前部分律師事務所或律師嘗試開展的調解卻未能取得較明顯的成效。推究起來,阻礙律師調解充分發揮作用的原因恐怕主要還在于以下兩點:一是通過律師的調解當事人即便達成了協議,一旦有一方翻悔卻很少有什么補救的措施;另一則是律師作為遵循市場規律的服務行業,免費或者低價提供糾紛解決的服務不易廣泛推行或者往往難以為繼。不過,隨著《意見》的出臺和實施,這兩個難點都有望得到有效的緩解。
首先,該規范性文件規定了經律師調解達成的協議如合乎法定的條件,債權人可據此啟動督促程序,向法院提出支付令的申請,法院審查后應當依法發出支付令;經律師調解工作室或調解中心調解達成的協議,當事人可向當地的法院或人民法庭申請司法確認。無論支付令還是確認調解協議效力的裁定,都能夠作為申請強制執行的依據。此外,《意見》還規定,“調解程序終結時,當事人未達成調解協議的,律師調解員在征得各方當事人同意后,可以用書面形式記載調解過程中雙方沒有爭議的事實,并由當事人簽字確認。在訴訟程序中,除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的外,當事人無需對調解過程中已確認的無爭議事實舉證”。換言之,即使律師調解沒有成功,但在作為法律專家的律師見證之下,當事人雙方對無爭議事實的確認從學理上可被理解為一種訴訟契約,能夠發揮簡化后續訴訟程序的作用。由此看來,上列規定的內容可以提升律師調解的實際效果。其次,關于經費保障機制的建立,《意見》列舉了幾種籌資的方法,包括律師事務所設立的調解工作室按照“有償、低價”的原則向當事人收取一定的調解費、司法行政機關和律師協會通過政府采購服務的方式解決經費、利用法律援助經費以及法院通過專項預算解決經費等渠道。在試點過程中,如果這些方法或渠道都能夠真正被利用起來,關于如何解決律師調解的經費來源或者其可持續性的問題有望獲得積極的答案。
《意見》指定了若干地區開展試點,律師調解今后的制度建構與這些地區的試點工作能否取得實質性的進展息息相關。試點類似于一種實驗活動,保障的提供或者資源的投入等只是初始的實驗條件,而實驗本身能否成功則取決于實驗主體的努力和能動性。在試點過程中,律師事務所以及律師協會才是至關緊要的“實驗主體”。無論是獲得并保持調解的案源,還是達到良好的糾紛解決效果,既是律師這個專門職業開拓服務領域的寶貴機遇,同時也構成了一項并不輕松的任務乃至嚴峻的挑戰。期待著我國的律師調解試點工作能夠成功地應對這項挑戰,完成從“實驗”到構建起制度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