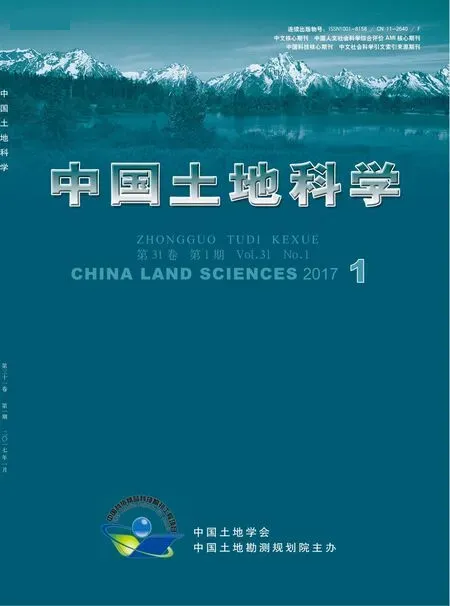農地“三權分置”實質探討
——尋求政策在法律上的妥適表達
陶鐘太朗,楊 環
(1.成都大學政治學院,四川 成都 610106;2.四川文化產業職業學院文化商學院,四川 成都 610213)
農地“三權分置”實質探討
——尋求政策在法律上的妥適表達
陶鐘太朗1,楊 環2
(1.成都大學政治學院,四川 成都 610106;2.四川文化產業職業學院文化商學院,四川 成都 610213)
研究目的:尋求并塑造對農地“三權分置”進行調整的妥適法律規范。研究方法:實證分析法、規范分析法、類比推理法、系統分析法。研究結果:從制度的妥適表達看,農地“三權分置”的實質并非三種具體權利的并立和對抗,而是三類主體之間享有的權利的并立和對抗。這三類主體即是農民集體、農民(農戶)和土地流入方。農民集體所享有的權利是集體土地所有權,農民(農戶)享有的權利則是一種集體成員權(可以“承包權”指稱)或者是土地承包經營權,土地流入方的權利則為土地經營權。研究結論:農民(農戶)集體成員權的調整可依據既存規范性文件,土地經營權必須進行物權塑造,農地“三權分置”才能得以在制度上實現。
土地法學;三權分置;主體權利;集體成員權;土地經營權;物權塑造
改革開放以來,多數時候的制度變遷,特別是在農地產權領域,總是因循著這樣的路徑:民眾首創、政策倡導、地方試點、制度變革。在這樣的制度變革路徑中,經濟學界是敏銳的,而法學界是穩健的。在決策層作政策倡導之時,經濟學界總是證成了制度變革的必要性。而當需進一步落實到制度變革時,法學界則貢獻自己的智識:厘清政策基本意蘊,結合既存的規范體系和社會事實,尋求政策在法律上的妥適表達,實現制度變遷。農地“三權分置”制度改革,采取了同樣的路徑依賴。當前,制度變遷正處于“地方試點”上升至“制度變革”的關鍵時期,法學界以體系性視野去尋求政策在法律中的科學表達,正當其時。
1 引論
作為討論的基本前提,首先要解決的是何謂“三權”以及“三權”之間的關系,這是“三權”得以在制度上實現的前置條件。從形式上看,各相關政策性文件對何謂“三權”,表述頗為一致,即“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和土地經營權”①從政策形成時間上排序,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2014年11月出臺的《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2015年11月出臺的《深化農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和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對何謂“三權”的表述幾乎一致,即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和土地經營權。。對“三權”之間的關系,各相關政策性文件亦有一致的表述,即“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②上述政策性文件對“三權”關系的表述,措辭上有些許差別,但基本意蘊無異,即“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而《深化農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更是對“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的內在意蘊進行了詳盡闡釋③其完整表述為:“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落實集體所有權,就是落實“農民集體所有的不動產和動產,屬于本集體成員集體所有”的法律規定,明確界定農民的集體成員權,明晰集體土地產權歸屬,實現集體產權主體清晰。穩定農戶承包權,就是要依法公正地將集體土地的承包經營權落實到本集體組織的每個農戶。放活土地經營權,就是允許承包農戶將土地經營權依法自愿配置給有經營意愿和經營能力的主體,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 參見《深化農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第二部分“關鍵領域和重大舉措”第一項“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第一點“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基于上述,似乎已經對何謂“三權”以及“三權”之間的關系作了清晰的解答,但事實并非如此。上述概念的界定以及相互關系的厘定,并非是在既有制度的概念體系下完成。更準確地講,上述概念更多地是在經濟學界話語體系下形成并被政策援用,而并不能在現有的法律概念體系中找到妥適的對應。
具體而言,首先,“農戶承包權”并非既有權利概念體系中的一員,其是否能夠直接與農戶享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用益物權的一種類型)劃等號,尚值商榷;其次,既存法解釋論下所形成的“土地經營權”,是債權非物權[1],債權型的“土地經營權”既不能實現“三權分置”,亦不能將其予以抵押進行貸款。對“土地經營權”權利性質進行重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尚需探討。當前階段,法學界對上述問題的認識各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農地“三權分置”在制度上的實現。因此,依托法學體系性語境厘清“三權”概念及其之間的關系,是農地“三權分置”制度實現的第一步,這需要對當前社會事實進行充分解讀并結合政策意蘊方能完成。
2 “三權分置”的實質厘定:三類主體權利的并立和對抗
當前階段的改革思路是“堅持家庭經營在農業中的基礎地位,并積極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其踐行,必需要對現有的農村土地兩權并立(即集體土地所有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模式進行變革,從之前的維護集體和農戶二元利益的產權設置轉變到維護集體、農戶和非該農戶的其他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三元利益的產權設置。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模式應運而生。
“三權分置”擬實現之制度功能,可分為三個維度。第一個維度是之于集體而言,以集體所有權繼續維護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確保農村集體的身份性權益不受外來資本的大規模沖擊,以此實現農村的持續性穩定;第二個維度是之于農民而言(農戶),以農戶承包權實現對集體土地所有權和土地經營權的權利制衡,一方面約束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權利擴張,一方面以回歸力保障農民不永久性失地,一方面以轉讓價金實現土地的財產性利益;第三個維度是之于土地流入方,以土地經營權確保其利益實現能夠有效對抗集體和農戶,甚至國家公權力機關,并能實現有效融資,以吸引外部資本進入農業領域,助推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蓬勃發展。
由是,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盡管在形式上“三權分置”應具體化為三種特定的權利類型的并立和對抗。但究其實質,卻應是農民集體、農民(農戶)、土地流入方三類主體之間的權利并立和對抗。即農民集體享有的權利、農民(農戶)享有的權利以及土地流入方享有的權利之間的分置。三類主體之間的權利存在形態是單一的,還是多樣的,則需要結合待規制對象的實然存在形式予以回答,方有正確結論。
當前階段的農村,三類主體之間的權利存在形態存在多樣性:一是作為基礎的“家庭經營模式”,是集體權利和農戶權利之間的對抗;一是在集體收回土地統一經營①這里的經營是廣義的經營,既包含農民集體自己運營該土地,也包含農民集體流轉該土地予第三方使用。的實踐或“確權確股不確地”的土地確權模式下,集體將土地使用權讓渡于第三方進行農業生產。在此情形下,每戶農民具體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已不存在,而以集體成員權保障其生存利益,此時的權利存在模式為:農戶以集體成員權與集體土地所有權形成制約與反制約的關系,集體土地所有權與土地經營權相互制衡。即“集體成員權→集體所有權← →土地經營權”的三權分置;還有一種即是農民(農戶)創設土地經營權讓渡給第三方,此時的農地權利結構為:農民集體的集體土地所有權、農民(農戶)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第三方的土地經營權三權之間的并立,即“集體土地所有權← →土地承包經營權← →土地經營權”的三權分置。上述三種農地權利結構形式,后兩種均可稱為“三權分置”,是“三權分置”在實踐中的具體實現形式。顯然,“三權分置”的實現形式具有二元性。可以發現,“三權分置”實現形式的二元性來源于農戶權利的二元性。在相關政策文件中,對農戶享有的權利的稱謂,是“農戶承包權”,故而,“農戶承包權”具有二元性。它在不同的三權分置模式下,或者表現為土地承包經營權(物權),或者表現為集體成員權(成員權)。事實上,決策層對農戶承包權的二元屬性,也有一定的認知,原中央農辦主任陳錫文就曾在不同場合對農戶承包權作出了二元認定②陳錫文在2013年12月5日接受人民日報記者采訪時,將承包權界定為物權。參見馮華,陳仁澤.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底線不能突破——專訪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 《人民日報》,2013-12-05(02);而在2014年1月22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新聞發布會中,陳錫文則將承包權界定為成員權。參見陳錫文. 《推進土地改革涉及三方面法律法規調整》,http://news.ifeng.com/mainland/ detail_2014_01/22/33243281_0.shtml.。而根據各地方實踐,也可以得出農戶承包權的二元性以及“三權分置”存在兩種模式的結論。曾被農業部部長韓長賦提名的“珠三角模式”和“上海松江模式”等“三權分置”的實現形式,以及黨國英教授推崇的“重慶巴南模式”,均是農民集體將集體的土地經營權作統一處理[2]。而“四川崇州模式”,則是通過農戶個體對土地經營權的處分以實現“三權分置”[3]。對相關政策性文件進行細致解讀,也能發現“三權分置”的二元性質。在《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中,可以發現土地經營權的出讓方,可以是農村承包經營戶,也可以是農村基層組織③參見《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第三部分規范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第六點嚴格規范土地流轉行為。。而在《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抵押貸款試點暫行辦法》中也明確了“沒有承包到戶的農村集體土地(指耕地)的經營權用于抵押的,可參照本辦法執行。”④參見《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抵押貸款試點暫行辦法》第27條。
顯然“三權分置”要尋求政策在法律上的妥適表達,需要以上述三種實然態的農地權利結構為規范對象。換言之,即是相關的制度設置,需要滿足“家庭承包經營”模式的二元農地權利結構模式,也要滿足兩種類型的三元農地權利結構模式。
3 “三權分置”立法表達的路徑依賴:立足于既有法律體系的適度創新
當前,學界對“三權分置”在制度上的實現有三類有代表性的觀點,部分學者認為,應當從現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中分置出“土地承包權”,并對“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去身份性改造和制度功能重塑,以此方式實現“三權分置”[4-5]。部分學者認為,在保留土地承包經營權制度的基礎上,在物權法框架下設置“農地經營權”制度,以此實現“三權分置”[6-7]。還有學者認為,所謂“土地經營權”,其實質也是土地承包經營權,只不過是較于“原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次一級土地承包經營權”。因此,無需新設“農地經營權”制度,而僅對土地承包經營權制度作細節性調整,即可實現“三權分置”[8]。上述觀點有其理論依據,并能實現各自在其概念體系中的邏輯自洽。但其共同的缺點在于:僅是依托于政策所提供的概念體系進行法律術語轉換工作,而忽略了對社會事實的充分認知以及對政策意蘊的深入解讀。因此,在進行“三權分置”政策法律表達的過程中,上述理論不可避免地落入進行三種具體的權利塑造的窠臼當中而無法自拔,其不合理性顯而易見。基于已經得出的結論,“三權分置”的實質并非是三種權利的并立和對抗,而是三類主體權利的并立和對抗,因此,制度設置不應是三種具體的權利塑造,而是三類主體權利的塑造。
三類主體的權利塑造,并不應是一個“破舊立新”的過程,而應是在既存法律體系下進行制度調適并適度創新的過程,采取這樣一種制度表達路徑依賴,是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從一般方法論角度考察,除非是制度的新創或者制度的整體移植,制度演進都存在慣性。特別是在農地產權制度改革領域,一直以來,其變遷過程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在充分汲取既存制度合理性的基礎上,作漸次性地突破。以最近的一次農村地權結構創新為例,即是以傳統的集體土地所有權為依憑,創設土地承包經營權,為家庭經營提供了權利保障,實現了“兩權并立”。而當前的“三權分置”倡設,其前提則是“兩權并立”,即需以集體土地所有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存在為依憑,“三權分置”脫胎于“兩權并立”。由是,制度演進的慣性決定了立法路徑依賴應是在既存制度體系下適度創新的過程。
其次,從調整對象上分析,“三權分置”的法律制度表達,既要能調整集體、農民(農戶)、土地流入第三方三類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同時,傳統家庭經營模式下的集體與農民(農戶)就土地而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也應屬其調整范圍之列。換言之,“三權分置”的法律表達必須具有兼容性,實然態的“兩權并立”和“三權分置”的權利結構,都應納入其規范框架內。當前,“兩權并立”的農村地權結構得到了妥適的法律調整,而“家庭承包經營”在未來的相當一段時間內,仍然是農業經營的主要形式。故而,“兩權并立”較“三權分置”而言,更是農村主流的地權結構。因此,“三權分置”的制度實現,應首先承襲既有的“兩權并立”的權利設置,在此基礎上,進行制度創新,實現“三權分置”法律表達。
再次,從既有制度可塑性方面來看,現有法律體系本就存在制度革新的變量。一方面,《物權法》實現了對農民集體成員權的立法確認,而且還規定了農民集體成員享有的具體成員權益,如參與管理權(第59條第2款)、知情權(第62條)、撤銷權(第63條第2款)等[9]。作為農民集體民主決策權的實現形式,《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也較為細致地規定了農民集體的議事規則。上述制度搭建了農民集體成員權的基本架構,依托于這一基本架構,是能夠實現農民(農戶)對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有效行使和制約的,但這需要對相關制度進行進一步的闡發和解釋;另一方面,土地承包經營權雖然在形式上被定義為派生于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用益物權,但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立法的基本趨勢是不斷強化這種權利。農民承包的法定期限不斷延長,甚至2008年“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農民享有的承包經營權長久不變[10]。而在對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頒證的過程中,很多地方國土行政機關對權利期限的表述已經不采用具體期限,而直接標明為“長期”。如果農民個人或者家庭享有的承包經營權長久不變,這種權利對土地的支配性已經接近于所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已經具有了準所有權性質,這為派生于其上“土地經營權”的權利塑造提供了多種可能性。
第四,從制度變革的必要性來看,既存法律尚不能滿足“三權分置”的制度需求,相關的制度創新具有現實必要性和緊迫性。具體而言,農民集體成員權尚不完善,集體成員身份的確定和變動規則,集體成員議事規則和權利行使規則、救濟機制,集體成員權與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相互轉化問題,尚需進行細致性探討。此外,在既有法解釋論下的土地經營權,尚不能滿足“三權分置”的政策要求。當前,《農村土地承包法》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對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問題進行了系統性規定。既存體系下,農民流轉土地所形成的權利變遷,或者是土地承包經營權本身的主體變更,或者是土地流入方形成債權型的“土地經營權”[11]。顯然,債權型的“土地經營權”并不足以與作為用益物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對抗,亦不能與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相抗衡。“三權分置”無從談起。要實現“三權分置”,需要對“土地經營權”進行權利性質重塑,以使其能夠與土地承包經營權和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并立,實現各方利益主體的平權保護。
基于上述,“三權分置”政策的制度實現,其重點在于兩項權利的適度創新,其一是集體成員權的細致化表達,其二是土地經營權的權利性質重塑。
4 集體成員權細致化表達:權利定位與規則建構
承接前言,關于集體成員權,既存的法律制度已有一般性規定,但需要進一步細化并進行相關規范性文件的銜接,方能形成妥適的集體成員權規則,以助推“三權分置”的實現。
4.1 集體成員權的權利定位:與集體所有權的異質性
合理的權利定位是合理規則設置的前提和基礎,而當前對集體成員權的權利定位,存在一定的誤區。從解釋論角度看,《物權法》在其第5章關于所有權(包括國家、集體和私人三類權利主體)的規定中,對集體成員權進行了概括性設置,故直觀地看,集體成員權應涵蓋于集體所有權權利內容之下,換言之,即集體所有權真包含集體成員權。上述認識并非筆者想當然,而是見諸于決策層的政策性文件。《深化農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明確表述,“落實集體所有權,就是落實‘農民集體所有的不動產和動產,屬于本集體成員集體所有’的法律規定,明確界定農民的集體成員權,明晰集體土地產權歸屬,實現集體產權主體清晰。”顯然,這一表述側重于闡釋集體所有權與集體成員權之間的關聯性,甚至于將集體成員權的實現等同于集體所有權的實現,而模糊掉了兩者之間的區別。無獨有偶,對集體所有權和集體成員權的認識,學界也有持類似態度者。“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來源于集體所有權,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因其成員身份所享有的權利,是集體所有權的實現方式之一。”[12]這種認識同樣將集體成員權的設定認為是集體所有權的權利表現形式,而同樣模糊掉了兩者的區別。當集體成員權和集體所有權混同時,集體成員權能對集體所有權產生制約機制也隨之模糊化,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對一類“三權分置”實現形式的忽略,進而影響了對“三權分置”的實質認知。
事實上,集體所有權和集體成員權之間具有很強的關聯性,但二者的區別卻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從權利主體看,集體成員權的權利主體是單個的農民或者農戶,而集體所有權的權利主體則是農民集體,盡管農民集體意志來源于農民(農戶)個體意志。但由于農民(農戶)個體意志的多樣性,在民主決策機制下,由此形成的農民集體意志必不同于少數派的農民意志。故而集體成員的意志不能等同于農民集體的意志,集體成員權的權利主體亦不同于集體所有權權利主體。
其次,從權利客體看,集體所有權的權利客體,可以是不動產,也可以是動產,但必須是物權法意義上的物①參見《物權法》第58條:集體所有的不動產和動產包括:(一)法律規定屬于集體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二)集體所有的建筑物、生產設施、農田水利設施;(三)集體所有的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等設施;(四)集體所有的其他不動產和動產。。集體成員權的客體是綜合性利益,可以抽象地稱為村社集體利益,以類型化的方式細分,具體包括村社利益、成員間的協作利益、村委會提供的公共服務、集體經濟組織利益份額等[13]。
再次,從具體的權利內容看,集體所有權是單純的財產權、所有權的一種,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積極權能,也有物權請求權的消極權能[14]。而集體成員權卻是一個權利組群,具有財產權和身份權的雙重屬性,包括作為財產權的集體資產的抽象持有份權(共有權),作為身份權的參與管理權、經濟監督權、分配請求權、知情權和撤銷權。
基于上述研究,集體所有權與集體成員權,兩者存在巨大差異而不存在真包含關系。從權利運行的角度考察,有了集體成員權的行使,方能形成集體所有權的主體意思,進而限制權利行使時的不當行為,以維護集體成員的正當利益。具體到“三權分置”的實現,如前文所言,當村、組將集體土地的經營權整體出讓給第三方時,農戶(農民)只能以集體成員權制約集體所有權,集體所有權與土地經營權之間形成相互制約。
而既有法制下的集體成員權規則尚需進一步完善,如何以集體成員權確保農民(農戶)在土地承包經營權缺失時基于土地而產生的利益,相關細則尚需細定。
4.2 集體成員權的規則建構:著眼于政策性規范的制度闡發
以類型化視角觀之,以集體成員權制約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三權分置”存在兩種具體的形式,一是農民集體(農村基層組織)收回土地進行統一經營模式,一是“確權確股不確地”的土地確權模式。這兩種具體形式的“三權分置”,在制度實現上存在差別,應分述之。
農民集體(農村基層組織)收回土地進行統一經營,是目前頗為流行的“三權分置”創新實踐模式。誠如前文所談到的“珠三角模式”、“上海松江模式”以及“重慶巴南模式”,盡管在具體操作形式以及稱謂上有所差別,但究其實質,均為農民集體(農村基層組織)收回土地進行統一經營。在該模式下,可將農民(農戶)與農民集體的關系分兩個階段觀察。第一個階段是農民集體收回農民(農戶)土地階段,其核心規則應當是農民集體在何種情形下能夠收回農民(農戶)的土地進行統一經營。現行政策更為側重農民(農戶)基本利益保障,故相關規范性文件作如是規定,“沒有農戶的書面委托,農村基層組織無權以任何方式決定流轉農戶的承包地,更不能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名義,將整村整組的農戶承包地集中對外招商引資。”①參見《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第三部分規范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第六點嚴格規范土地流轉行為。換言之,當且僅當農民(農戶)書面同意,農村基層組織才有權決定流轉農戶的承包地。顯然,在農民(農戶)未決定將土地流轉的權利讓渡于農民集體之前,集體成員權的相關議事規則將排除適用。而第二個階段,即農民(農戶)書面同意并將土地交回農村基層組織(農民集體)統一流轉時,其核心規則是農民(農戶)交回土地的行為是何種性質、土地流轉過程中農民(農戶)與農村基層組織(農民集體)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以及土地流轉結束后農民(農戶)對承包地的收回。首先,農民(農戶)交回土地(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土地使用權)所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筆者認為,此時應當認為是土地使用權與土地所有權的權利主體混同,土地使用權消滅②就此問題,需作進一步說明。農民(農戶)與農村基層組織(農民集體)之間形成的關系是就土地權利的委托關系,還是土地權利收回關系,筆者認為是后者。理由在于,首先,從形式上看,委托關系是受托人就委托人的事務與第三方發生的關系,而在土地流轉的過程中,農村基層組織(農民集體)是就自己享有所有權的土地與第三方達成流轉協議,這種處分權能本就蘊含在其土地所有權中,而并非單個農民(農戶)授予。其次,就權利保障以及權利結構穩定來看,以委托代理關系來表征農民(農戶)與農村基層組織(農民集體)的關系將不利于農民(農戶)以及土地流入方的權利保障,且農村基層組織(農民集體)以代理人身份出現在此類關系中,由此形成的權利結構并不穩定。再次,從政策旨趣來看,所謂“三權分置”,應為農民集體、農民(農戶)和土地流入方三方的土地權利而形成的制衡,但是,若形成的是委托代理關系,則農村基層組織(農民集體)并不是以集體土地所有權人的身份參與其中,而是以代理人(代理權)的身份參與其中,其所形成的關系就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委托代理關系,而不是政策上所倡導的“三權分置”關系。。農民(農戶)享有的權利從作為財產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演進為可享有財產收益的身份權——集體成員權,農村基層組織(農民集體)因其農民(農戶)集體成員權向其支付土地流轉的收益。其次,土地以農村基層組織(農民集體)名義自己經營③所作用的對象權利仍應為土地經營權而非土地所有權。或者向第三方流轉后,農民(農戶)以集體成員權制約農民集體所有權,其相關決策規則可參照《物權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而農民集體所有權與土地經營權之間形成相互制衡。第三,當土地經營權消滅,依農民(農戶)意愿,或者是繼續讓農村基層組織(農民集體)經營土地,或者是通過行使集體成員權將土地權利重新分配到戶,仍然實行各戶各自經營。
“確權確股不確地”模式,盡管在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明確表示要“從嚴掌握確權確股不確地”的范圍①“確權確股不確地”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方式是在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出,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則要求“從嚴掌握確權確股不確地”的范圍。,但“確權確股不確地”的土地確權模式在經濟發達地區還是頗為流行。在該模式下,單個農戶(農民)并不享有對特定土地的承包經營權,而是直接通過集體成員權對集體享有的資產以及相關事務進行制約。因此,相較于上一模式,其所牽涉的規范性內容較少,既無在前置的農民(農戶)同意集體統一流轉土地的程序,亦無土地經營權流轉完畢后的土地回收程序,而僅涉及土地流轉過程中農民(農戶)與農村基層組織(農民集體)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就該種關系的規范和調整,可參酌《物權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完成。
5 土地經營權的物權塑造:理論自洽及規則設置
在既存法制解釋論下,土地經營權為債權并非物權,但是,債權形式的“土地經營權”是無法與作為物權的“集體土地所有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對抗和并立的。因此,“三權分置”要實現,應對“土地經營權”予以物權塑造。
5.1 土地經營權物權塑造的理論自洽
對土地經營權進行物權塑造,存在一個理論自洽問題。從權源來看,在“集體成員權→集體所有權← →土地經營權”三權分置模式下,土地經營權直接來源于集體土地所有權,是在所有權之上設置用益物權,理論上并無障礙。而在“集體土地所有權← →土地承包經營權← →土地經營權”三權分置模式下,則有悖于“物權的排他效力”,無法實現制度理論上的自洽。具體來說,所謂物權的排他效力,是指在同一標的物上不允許有兩種以上不相容的物權同時存在。一種具體的表現形式就是,同一標的物上,不得有兩個以上同以占有為內容的定限物權存在[15]。設若將土地經營權進行物權塑造,則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土地經營權均為以占有為內容的用益物權,有違于“物權的排他效力”。
就此悖論,筆者認為,從事實層面分析,對特定物的占有,可分為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傳統民法理論,囿于認識和技術,對物的切割僅限于空間維度,而忽略了時間維度。近代民法發展,則突破這一限制,對物的占有實現了空間維度和時間維度的綜合性切割。《歐盟分時度假合同法》和德國《住宅所有權法》中的分時段居住權制度,即實現了對特定房屋的分時段所有或者使用。換言之,不同權利主體在不同的時間段分別享有對某一特定房屋的所有權或使用權,而該使用權可以是物權形態的權利[16]。上述權利,權利人在特定的時間段均能實現對客體的排他性占有,并不與“物權的排他效力”相悖。事實上,經營權設定后,其效果等同于土地承包經營權在時間維度上被分割,并予以部分轉讓[7]。其在特定物的占有屬性上,與上述分時段居住權別無二致,即不同權利主體對特定物的分時段享有,其并不有違“物權的排他效力”。
進一步論,從立法技術看,物權與債權的區分,并不是絕對的。物權的本質,就是把一個原來屬于甲和乙之間的關系(相對關系),通過了登記和公示,然后就被絕對化了[17]。土地經營權人與土地承包經營權人關于特定土地特定時間段的“占有使用協議”,完全可以通過登記和公示的方法被絕對化,成為絕對權。這首先需要《物權法》或者其他法律確定該權利為物權,其次是確定該權利的登記和公示方法,以使該法律關系絕對化[1]。
基于上述研究,土地經營權物權塑造并不有悖于“物權的排他效力”,而且在立法技術上亦不存在障礙,土地經營權物權塑造能夠實現理論自洽。
5.2 土地經營權物權塑造的規則設置
土地經營權的權利來源具有二元性,不同權源的土地經營權在具體制度設置上必然會有一定區別,但這并不意味著應當對兩種不同權源的土地經營權進行分別立法。現有立法技術下,可以在同一制度架構下實現兩類土地經營權細微差別的調和。
首先,土地經營權的定義。土地經營權應被塑造為用益物權,這種用益物權是以“農民集體所有的耕地”為對象①參見《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和《國務院關于開展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和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貸款的試點意見》。,并以從事種植業為其權利行使要求,故土地經營權應界定為“土地經營權人依法對農民集體所有的耕地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有權從事種植業等農業生產。”
其次,土地經營權的權源。需揭橥土地經營權權源的二元性。“土地經營權可由農民(農戶)在其承包經營的耕地上設立。也可由農民集體在其所有的耕地上設立。”
再次,土地經營權的設立方式。主要涉及土地經營權物權的形式要件要求,以區別農村土地債權型的流轉方式,包括期限和登記兩個要素。就期限要素論,有必要設立一個最短期限,以區別于短期的債權形式的土地流轉。物權型權利具有一定的穩定性要求,只有農地流轉達到一定的期限,方有必要以物權型權利予以保障。筆者認為以5年為最短期限。理由在于,農業投資回報期限一般較長,5年基本可認為是最短的投資回報周期。詳言之,流轉土地達5年以上者,應當認為其有一定的固定資產投入到土地之上,其所享有的權利,應為效力較高的物權。也有必要設立一個最長期限,析言之,在土地承包經營權上創設的土地經營權自不應超過其剩余的承包期限,而直接在集體土地所有權之上創設的土地經營權,其權利期限似能更長,不無疑問?筆者認為,未來農村土地制度領域仍充斥著變量,以較長期限設定土地經營權,并不意味著就能穩定農地產權結構,甚至反倒成為未來制度變革的絆腳石。故土地經營權的最長期限不易過長,統一以第二輪土地承包經營權剩余的承包期限為基礎,確定上限為15年為宜。就登記要素論,現行物權法解釋論下,不動產物權以登記為其生效要件,作為新創之物權種類,自應遵從。并且,以登記為生效要件,一方面能夠起到權利公示作用,另一方面也可與一般的債權型的土地流轉區別開來。故關于土地經營權的設立方式,應表述為“土地經營權由農民集體或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流轉土地達5年以上15年以下,并經登記成立。”
第四,土地經營權的權利主體。土地經營權的權利主體,首先應具有農業經營能力,這是前置性要件。其次,主體已經不限于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而可以是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自然人和公司,但應該賦予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在同等條件下對土地經營權的優先獲得權,故土地經營權權利主體的立法表達應為“土地經營權的權利主體應為具有農業經營能力的自然人或法人,同等條件下,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有優先獲得土地經營權的權利。”
第五,土地經營權的權利內容。作為用益物權,占有、使用、收益等基本權能無需贅述,這里所涉的是其處分權能的構建。土地經營權在權利存續期限內,可繼承、可轉讓、可抵押,并可將標的物出租。上述處分權能的具體表現形式,不應受土地承包經營權和集體土地所有權限制。故其權利內容應表述為“土地經營權在權利存續期間,可以繼承、轉讓、抵押,并能將耕地出租。”
第六,權利制衡方面。土地經營權的物權塑造,目的就是為了平衡集體土地所有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對債權性質的土地流轉權利的優越地位,以實現三類主體權利的并立與對抗。故具體化土地經營權與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關系性規則,是土地經營權物權塑造的立法旨趣使然。具體應表述為,“土地經營權存續期間,農民集體或土地承包經營權人不得妨害和干涉土地經營權的正當行使。因農民集體或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不當行為造成土地經營權人利益受損的,土地經營權人有權要求農民集體和土地承包經營權人賠償;土地經營權人不得濫用耕地,因濫用造成照成耕地受損的,農民集體或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有權要求賠償。濫用行為嚴重而可能造成耕地性質變更的,農民集體和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有權終止土地經營權。”
第七,土地經營權人的優先權。在土地經營權期限屆滿后,如果農民集體或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愿意繼續流轉土地經營權的,原土地經營權人在同等條件下有優先獲得土地經營權的權利。理由在于,土地經營權人的固定資產投入和長時間的經營行為,必然使耕地獲得價值增值,他是除原權利人外最有資格享有這部分利益的人。另一方面,從物盡其用的角度考慮,土地經營權人對耕地的各物理屬性最為熟悉,我們有理由相信耕地在其手中能夠實現效用最大化。故相關條款應設定為,“在土地承包經營權屆滿后,農民集體或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愿意繼續出讓土地經營權的,在同等條件下,原土地經營權人有優先獲取權。”
第八,權利的消滅。“土地經營權因期限屆滿、農民集體或土地承包經營權人因法定原因提前終止合同、客體滅失而消滅。”
6 結論與討論
“三權分置”的實質,是三類主體權利的并立和對抗。在三類主體權利中,農民(農戶)享有的權利是變量。它可以是身份權,也可是財產權。“三權分置”的制度實現,應以農民(農戶)權利的二元區分為基礎。“兩權并立”在未來仍是中國農地產權的主流結構且“三權分置”脫胎于“兩權并立”,故“三權分置”制度實現的路徑依賴,應是立足于既存法律體系進行制度調適并適度創新,而適度創新的內容,則是集體成員權的細致化表達和土地經營權的物權塑造。從立法論的角度看,本文雖然對集體成員權的細致化提出了立法方向上的構想,但就具體的制度設置上,還需進一步探討。而就土地經營權的物權塑造,雖然提供了具體的立法方案,但僅將視野限制于土地經營權本身,而欠缺對相關制度的關聯性考察,就此問題,還需做細致研究。
(References):
[1] 陶鐘太朗,楊遂全. 農村土地經營權認知與物權塑造——從既有法制到未來立法[J] .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2):73 - 79.
[2] 黨國英. 農地“三權分置”改革究竟是什么意思?[N] . 新京報,2016 - 06 - 09(A2).
[3] 韓長賦. 土地“三權分置”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創新[N] . 光明日報,2016 - 01 - 26(1).
[4] 鄭志峰. 當前我國農村土地承包權與經營權再分離的法制框架創新研究——以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為指導[J] . 求實,2014,(10):82 - 91.
[5] 丁文. 論土地承包權與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分離[J] . 中國法學,2015,(3):159 - 178.
[6] 孫憲忠. 推進農村土地“三權分置”需要解決的法律認識問題[J] . 行政管理改革,2016,(2):21 - 22.
[7] 蔡立東,姜楠. 承包權與經營權分置的法構造[J] . 法學研究,2015,(3):31 - 46.
[8] 朱廣新. 土地承包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政策意蘊與法制完善[J] . 法學,2015,(11):88 - 100.
[9] 管洪彥. 農民集體成員權:中國特色的民事權利制度創新[J] . 法學論壇,2016,(3):103 - 113.
[10] 孫憲忠. 中國農民“帶地入城”的理論思考和實踐調查[J] . 蘇州大學學報,2014,(3):63 - 69.
[11] 張毅,張紅,畢寶德. 農地的“三權分置”及改革問題:政策軌跡、文本分析與產權重構[J] . 中國軟科學,2016,(3):13 - 23.
[12] 李愛榮. 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中的身份問題探析[J] .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4):12 - 20.
[13] 童列春. 論中國農民成員權[J] . 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2):46 - 54.
[14] 崔建遠. 物權:規范與學說——以中國物權法的解釋論為中心(下冊)[M] .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395.
[15] 申衛星. 民法學[M] .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206.
[16] 陶鐘太朗. 居住權研究[M] . 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43 - 49.
[17] 蘇永欽. 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民法典[J] . 私法,2013,(1):1 - 17.
(本文責編:戴晴)
Discussion on the Essence of Tripartite Rural Land Entitlement System of Farmland Property Rights: Seeking the Appropriate Expression of Policy on Law
TAO Zhong-tailang1, YANG Huan2
(1. Law Department of Politics Faculty,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6, China; 2. Cultural Business School, Sichu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Chengdu 610213,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eek and enact the appropriate law to regulate the tripartite rural land entitlement system of farmland property rights. Methods used include empirical analysis, normative analysis, analogical reasoning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ssence of tripartite rural land entitlement system is not the coexistence and contradiction of three kinds of specific rights, but the coexistence and contradiction of three subjects’rights. The three subjects are farmers, farmers’ collective and the third party that transfer in the land. The farmers’collective has rural land ownership. The farmers have the collective member right or the land contractual right and the land management right. The third party has the management rights of land. The paper concludes the regulations for thecollective member rights can rely on the existing law system; the land management right should be modeled as the real right otherwise the tripartite rural land entitlement system of farmland property rights cannot be realized.
land law; tripartite rural land entitlement system; subject’s rights; collective member rights; land management right; real right enacting
D922.3
A
1001-8158(2017)01-0064-09
10.11994/zgtdkx.20170112.093314
2016-09-26;
2016-12-24
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農村房地產權城鄉間流轉與遺產繼承研究”(13AJY013);四川省社科規劃項目“民法典編纂與集體土地權利建構研究”(SC16B004);成都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新型城鎮化與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2016Z43);成都大學引進人才啟動項目“空間利用視域下的宅基地使用權設置”。
陶鐘太朗(1981-),男,四川簡陽人,博士,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物權法。E-mail: taozhongtailang@sin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