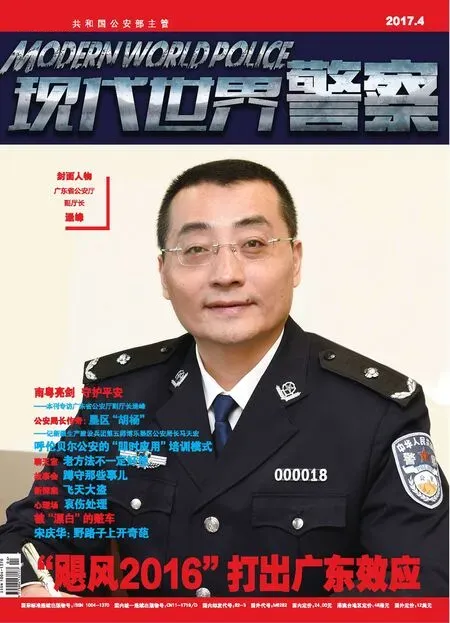韓非的末路
文/王志禎
韓非的末路
文/王志禎
公元前233年,秦國大軍攻打韓國。發動這場戰爭的目的絕無僅有,不是為了攻城略地,不是為了滅國破家,而僅僅是為了得到一個人。
這個人是誰?他究竟是何方神圣,有什么魅力,能讓秦王嬴政也就是后來的秦始皇為了他不惜興師動眾、大動干戈?
這個人可謂大有來頭。他就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法家理論的集大成者韓非,史稱韓非子。
韓非是韓國的貴族子弟,愛好刑名法術之學。他學說的理論基礎來源于黃帝和老子。他有口吃的毛病,不善言辭,卻擅長于著書立說。他和李斯都是儒學大師荀卿的學生,李斯自認為學識比不上韓非。
韓非看到韓國漸漸衰弱下去,心急如焚,屢次上書規勸韓王,但韓王沒有采納他的意見。韓非痛恨治理國家不致力于修明法制,不能憑借君王掌握的權勢來駕馭臣子,不能富國強兵,任用賢能之士,反而任用夸夸其談、對國家有害的文學游說之士,并且讓他們的地位高于講求功利實效的人。他雖師從荀子,卻認為儒家用經典文獻擾亂國家法度,游俠則憑借武力違犯國家禁令。國家太平時,君主就寵信那些徒有虛名假譽的人,形勢危急時,就使用那些披甲戴盔的武士。現在國家供養的人并不是有用的,而有用的人又不是所供養的。他悲嘆廉潔正直的人不被邪曲奸枉之臣所容。他考察了古往今來的得失變化,寫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十余萬字的著作。
韓非深深地明了游說的困難,并撰寫了《說難》一書,講得非常具體全面,但他最終還是死在秦國,不能逃脫游說的禍難。
《說難》中這樣寫道:大凡游說的困難,不是游說者的才智不足以說服君主,也不是游說者的口才不足以明確地表達出自己的思想,更不是游說者不敢毫無顧慮地把意見全部表達出來。游說的困難,在于如何了解游說對象的心理,然后用自己的說辭去打動他。
如果游說的對象想博取好名聲,而游說的人卻用重利去勸說他,他就會認為你品德低下,從而慢待并疏遠你。如果游說的對象貪圖重利,而游說的人卻用博取好名聲去勸說他,他就會認為你沒有頭腦、脫離實際,一定不會錄用你。游說的對象意在重利而公開裝作博取好名聲,而游說的人用博取好名聲去勸說他,他就會表面上錄用你而實際上疏遠你;假如游說的人用重利去勸說他,他就會暗中采納你的意見,而公開拋棄你本人。
行事保密就能成功,言談之中泄露了機密就會失敗。不一定是游說者本人有意去泄露機密,而往往是在言談之中無意地說到君主內心隱藏的秘密。像這樣,游說的人就會引火燒身。君主有過失,而游說的人卻引用一些美善之議推導出他過失的嚴重,那么游說的人就會有危險。君主對游說者的恩寵還不深厚,而游說的人傾盡肺腑,即使意見被采納實行并見到了功效,君主也會忘掉你的功勞;如果意見行不通而且遭到失敗,游說者就會被君主懷疑而身陷險境。君主自認為有了良策,而且打算歸功于自己,那么游說的人參與此事,也會有危險。君主公開做著一件事,而自己另有別的目的,如果游說者預先知道他的計策,也會有危險。君主堅決不愿做的事,卻極力要讓他去做,君主非做不可的事情,又阻止他去做,游說的人就危險了。所以說:“和君主議論在任的大臣,君主會認為你離間他們彼此的關系;和君主議論地位低下的人,君主會認為你賣弄權勢。說君主愛聽的話,君主會認為你是在利用他;議論君主所憎惡的事情,君主會認為你試探他的底線。如果游說者文辭簡略,君主就會認為你沒有才智而使你遭受屈辱;如果你鋪陳辭藻,夸夸其談,君主就會認為你語言放縱、大而無當。如果你順應君主的主張陳述事情,就會說你膽小,做事不盡如人意。如果你謀慮深遠,就會說你鄙陋粗俗,倨傲侮慢。”
大凡游說者最重要的,在于懂得美化君主所推崇的事情,掩蓋他認為丑陋的事情。他自認為高明的計策,就不要拿以往的過失使他難堪;他自認為是勇敢的決斷,就不要自以為是地去激怒他;他夸耀自己的力量強大,就不必用他為難的事來反駁他。游說的人謀劃另一件與君主相同的事,贊譽另一個與君主同樣品行的人,就要把那件事和那個人加以美化,不要壞其事傷其人。有與君主同樣過失的人,游說者就要明確地粉飾說他沒有過失。待到游說者的忠心君主不再抵觸,游說者的說辭君主不再排斥,游說者就可以施展自己的口才和智慧了。等到歷經很長的時間之后,君主對游說的人恩澤已經深厚了,游說者深遠的計謀也不被懷疑了,交相爭議也不被加罪了,便可以明白地計議利害關系,幫助君主建功立業,也可以直接評議君主的是非以正其身。用這樣的辦法扶持君主,就是游說成功了。
伊尹做廚師,百里奚當俘虜,他們都是這樣取得君主的信任重用的。這兩個人都是圣人,他們都不得不做這些低賤的事,經歷如此世事的卑污,那么智能之士就不會把這些看做是恥辱了。
宋國有個富人,因為天下雨毀壞了墻。他兒子說:“不修好將會被盜。”他的鄰居有位老人也這么說。晚上果然丟了很多財物,他全家的人都認為他兒子特別聰明,卻懷疑鄰居那位老人。從前鄭武公想要攻打胡國,反而把自己的女兒嫁給胡國的君主。他問大臣們說:“我要用兵,可以攻打誰?”關其思回答說:“可以攻打胡國。”鄭武公就把關其思殺了,并且說:“胡國是我們的兄弟之國,你說攻打它,居心何在?”胡國君主聽到這件事,就認為鄭國君主是自己的親人而不防備他,鄭國就趁機偷襲胡國,占領了它。這兩個說客,他們的預見都是正確的,然而言重的被殺死,言輕的被懷疑,所以說知道某些事情并不難,如何去處理已知的事就難了。
從前彌子瑕被衛國君主寵愛。按照衛國的法律,偷駕君車的人要判斷足的罪。不久,彌子瑕的母親病了,有人知道這件事,就連夜通知他,彌子瑕就詐稱有君主的命令駕著君主的車子出去了。君主聽到這件事反而贊美他說:“多孝順啊,為了母親的病竟不怕斷足的懲罰!”彌子瑕和衛國君主到果園去玩,彌子瑕吃到一個甜桃子,沒吃完就獻給衛國君主。衛國君主說:“真愛我啊,自己不吃卻想著我!”等到彌子瑕容色衰退,衛國君主對他的寵愛也疏淡了。后來他得罪了衛國君主,衛國君主說:“這個人曾經詐稱我的命令駕我的車,還曾經把咬剩下的桃子給我吃。”彌子瑕的德行和當初一樣沒有改變,以前所以被認為孝順而后來被治罪的原因,是由于衛國君主對他的愛憎有了極大的改變。所以說,被寵愛時君主就認為他聰明能干,愈加親近;被憎惡了,君主就認為他罪有應得,愈加疏遠。因此,勸諫游說的人,要搞清楚君主的愛憎態度之后再游說他。
龍屬于蟲類,可以馴養、游戲、騎乘。然而它喉嚨下端有一尺長的倒鱗,人要觸動它的倒鱗,一定會被它傷害。君主也有倒鱗,游說的人能不觸犯君主的倒鱗,就差不多算得上善于游說的了。
有人把韓非的著作傳到秦國。秦王見到《孤憤》《五蠹》這些書,說:“哎呀,我要見到這個人并且能和他交往,就是死也不遺憾了。”李斯說:“這是韓非寫的書。”秦王因此立即攻打韓國。起初韓王不重用韓非,等到情勢吃緊,才派遣韓非出使秦國。秦王很喜歡韓非,但沒有一開始就信任、重用他。李斯、姚賈嫉妒韓非,在秦王面前詆毀他說:“韓非是韓國貴族子弟。現在大王要吞并各國,韓非到頭來還是會幫韓國而不幫秦國,這是人之常情啊!如今大王不任用他,在秦國留的時間長了,再放他回去,這是給自己留下的禍根啊!不如給他加個罪名,依法處死他。”秦王認為他們說得對,就下令司法官吏給韓非定罪。李斯派人給韓非送去了毒藥,讓他自殺。韓非想要當面向秦王陳述是非,但又見不到秦王。后來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可惜韓非已經死了。
韓非的悲劇在于他生不逢時,空有滿腹學識而得不到重用,更在于他思想深邃但不善言辭,雖然透徹地知道游說的困難和危險,但最終也未能逃脫因游說不力丟掉性命的災禍。在這一點上,太史公司馬遷與韓非“心有戚戚焉”。司馬遷因為替李陵鳴不平而遭受宮刑,而韓非則因為未能充分地與秦王溝通遭到李斯等人的陷害。因此,才有太史公“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的悲嘆。
在中國法家代表人物中,韓非可算是登峰造極的人物。他的思想融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慎到的“勢”,并將其系統化,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法家思想理論體系。梁啟超認為中國兩千年的社會實際上是“外儒內法”的社會。毛澤東曾說:“中國古代有作為的政治家,基本都是法家。”可見韓非的思想對于中國歷史產生了怎樣深遠的影響。
作為一個思想家,韓非無疑是成功的。這是一種不死的精神,它超越生死,超越時空,永遠不會熄滅。但在現實世界里,他卻處處碰壁,受盡屈辱,最后還遭了同窗的毒手。他用自己短短47年的人生,詮釋了悲劇的內涵,著實令人扼腕、痛惜!
在秦國的幾個月時間,可算是韓非的末路。在這人生的最后一程,有大喜,有大悲;有座上賓的風光,亦有階下囚的凄慘;有同窗相見的寒暄,亦有幕后黑手的暗算。韓非的末路注定是一場跌宕起伏、驚心動魄的大戲,在大戲的幕后,深深隱藏著的,卻是法家思想與現實社會人生的激烈搏殺。韓非之死,既是法家思想的浩劫,亦是法家精神的涅槃與重生。從秦王開始的歷代帝王,開始前所未有地重視法家思想,并逐漸把它作為治國的精髓與良策。法家思想由此進入廟堂,被逐漸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