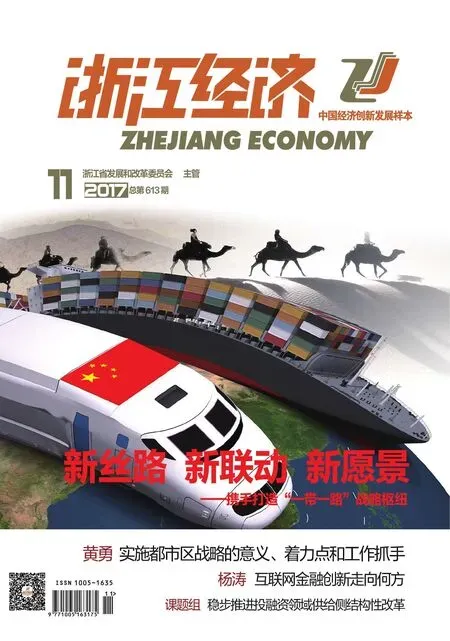互聯網金融創新走向何方
□楊濤
互聯網金融創新走向何方
□楊濤
互聯網金融整頓已經進入中期,行業正逐步回歸理性,變革應聚焦在行業未來發展方向上。事實上,互聯網金融的真正歸宿,還是應回到金融科技的主線上,即真正實現科技對于金融功能與產業鏈的全面重構
目前,互聯網金融整頓已經進入中期,“熱熱鬧鬧”的紛亂場景逐漸淡去,行業逐漸回歸理性。例如,據《網貸之家》統計,2017年3月P2P行業共有10家問題平臺,另有56家停業轉型平臺。由此來看,隨著更加嚴厲的整治措施出臺,各類“跑路劣幣”已經越來越少,更多的互金企業主動“離場”或轉型,說明了前期的“泡沫”和“非理性”在逐漸弱化。因此,當前除了短期應對監管約束,更需深入思考互聯網金融未來的發展方向,能否真正在我國金融創新與發展中找到自己的合理位置。
互聯網金融發展現狀
首先,要看到互聯網金融創新的源泉,在于推動實體部門“內生”的金融創新,加速傳統金融“脫媒”。隨著金融創新的演變和信息技術的騰飛,原有依靠銀行或資本市場的資金配置方式,實際上一直在被“脫媒”,只不過,近年來伴隨“虛擬一代”生活方式的演變,這種沖擊更加突出。對于實體部門,尤其是服務業部門來說,可以跳出對傳統金融體系的依賴,自發地推動相應的金融服務功能實現。當然,這有賴于監管部門的寬容,但是卻符合金融回歸實體的主流趨勢,應該說,與電子商務相聯系的供應鏈金融、產業鏈金融創新都是其中的代表。由此而言,未來真正有生命力的互聯網金融創新,還是要看如何與實體、產業更有效地融合。
其次,對于新興的互聯網金融企業來說,一是需要有效定位服務對象。對于傳統金融體系來說,被人詬病的問題之一,就是更注重資金需求者,尤其是大的資金需求者,而對中小需求者以及資金供給者的服務嚴重缺失。互聯網金融活動則走向不同的側面,一方面,無論從各類模式及產品設計,還是宣傳方面,現有各方焦點都過于注重服務資金供給者,尤其是為居民提供高回報的理財和財富管理產品等方面;另一方面,對于小微企業融資的真實作用,以及與包括小貸在內的線下非互聯網融資模式的實質性區別,在現實中的研究和關注還非常不足,而對于居民金融需求的支持也有所不足。由此來看,互聯網金融創新旨在強調避免傳統弊端的同時,也要有效實現服務資金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平衡,找出真正符合商業原則、可持續且能實現普惠金融目標的路徑。二是必須認清,現有的很多所謂互聯網金融模式,包括本土化的P2P網貸等,之所以前幾年能夠獲得巨大發展空間,除了政策寬容之外,更是因為利率市場化尚未真正完成,資金價格的“多軌制”仍存在。就此意義上講,現有許多互聯網金融模式所謂的“革傳統金融體系的命”,實際上也是在革自己的命,一旦利率市場化深入推進,金融要素流動壁壘不斷消除,結構性金融供求失衡的局面改變,則現有許多模式的可持續性也會大大弱化。正如在美國,新興互聯網金融企業發揮的作用仍然有限,資金需求者多數都能從現有體系中獲得滿足。因此,無論是互聯網金融的踐行者、投資者、受益者還是關注者,都需要從整體上、從長遠來認識其模式的可持續性所在,把握中長期發展軌跡。
再次,對于以商業銀行為代表的傳統金融業,其面臨的挑戰并非僅來自于互聯網金融,而是在產業結構變遷、市場化改革推進、國際化挑戰加劇、政府“父愛主義”弱化、消費者主權意識增強等多種因素影響下,所面臨的二次改革壓力的總體現。互聯網金融借助幾十年信息技術革命撲面而來的活力,只是為這些危機和壓力提供了一個令人感興趣的引領主題。人們喜歡談及的是,比爾·蓋茨在1994年接受《新聞周刊》采訪時將銀行比作恐龍,認為銀行客戶將在未來流失到其它高科技金融服務提供商。如果做另類解讀,我們會發現恐龍存活了2億年,且一直在食物鏈的頂端,而商業銀行已有歷史不過幾百年,由此來看似乎銀行的地位仍然長久。
值得強調的是,一方面是傳統金融機構沒有必要妄自菲薄,或者非要去趕時髦搞電商平臺或P2P網貸,或者以互聯網金融為名重啟表外的影子銀行業務,或者夸大其詞來繼續尋求政府父愛支持,而是應積極穩妥地推進互聯網技術創新策略。另一方面,透過互聯網金融的表象,要認清我國金融業面臨的真正危機與挑戰,包括:可能與全球同步的下一個經濟衰退周期;準備適應市場化和國際化帶來的競爭加劇;面對金融消費者主權時代的來臨,更強調客戶導向,而非神壇之上的“供給創造需求”;新的產融結合時代,金融與非金融部門的邊界進一步模糊,創新型合作模式不斷出現等。
互聯網金融的歸宿
技術對人類社會帶來的沖擊與影響,在歷史上從未如今天這樣,得到公眾熱烈的迷戀與追捧。筆者分析,一是由于無論政府、金融機構、企業和個人,都充分感受到了技術進步帶來的好處;二是因為技術進步也似乎逐漸脫離“摩爾定律”的束縛,從量變向質變進行飛躍;三是源于在高速信息化的社會中,眾多潛在的矛盾與頑疾都更加突出,人們期望技術能夠改變經濟社會中的諸多“百慕大三角”領域。
谷歌的首席經濟學家哈爾·范里安,也是一位研究微觀經濟學和信息經濟學的著名學者,近期指出計算機和新技術可以從五個方面影響經濟活動,包括:數據收集與分析、個性化與定制化、試驗與持續改善、合同管理創新、協調與溝通。
我們認為,金融作為經濟活動的“血液”,也同樣面臨這些技術帶來的新挑戰。例如,面對大數據和小數據,金融活動如何管理和發掘數據的價值,使之改善現實金融活動效率與經營業績;更加低成本、便捷、安全、智能地提供個性化金融服務,而不僅是“冷冰冰”的金融產品“流水線”;充分利用線上系統迭代與人工智能的深度學習,不斷優化金融運行的內在“升級”能力;通過大數據加區塊鏈的分布式技術演進,真正解決信息的互聯互通,以及信用合約的智能化,提升金融交易的效率;減少金融活動中的溝通、協調、交易成本,改變原有金融產業鏈的分工模式,使得“令人生畏”的金融巨頭不再那樣“難以觸及”。
在全球金融科技浪潮之中,中國也歷史罕見地成為領航者之一。據花旗銀行的2016年研究報告顯示,在2010年到2015年期間,全球在金融科技上的投資,從18億美元暴漲至190億美元,但截至2016年,在美國,有超過50%的小銀行或是信用社,尚未和任何金融科技企業接觸。英國金融科技公司協會InnovateFinance發布了報告,認為2016年全球金融科技領域投資總額超過170億美元,中國約77億美元。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日前也發表題為《金融科技,中國成為領導者》的文章點贊。
所有這些使我們得出幾個結論:一是金融科技的熱潮在全球涌現,而且近年快速增長,當然也有分析認為,近期有所放緩,因為全球也都再反思和“擠出泡沫”;二是由于種種原因,發達經濟體的金融科技應用并未如我們想象中那樣普及,我們仍處于同樣的起跑線;三是中國之所以成為“弄潮兒”,可能是資本驅動、電商經濟擴張、監管寬容等因素所致,其中不乏短期因素。
此時的中國金融科技創新,就面臨“向左走、向右走”的抉擇,也是為了避免“贏在起點、輸在終點”。我們不需要“風口的飛豬”,因為摔下來會很慘,而是需要矯健的獵豹;也不需要“彎道超車”,因為彎道失事的概率很高,而是需要在直道上提升“加速度”。簡單而言,我們的金融科技創新要真正成為全球金融變革中的“常青樹”,除了已有優勢,更需要激發兩方面驅動力。一是真正推動科技創新水平,提升技術對于金融活動的正效應;二是改善技術所伴隨的金融制度規則,使之更公開、透明、高效、安全、便捷、共贏。
由此來看,互聯網金融的真正歸宿,還是應回到金融科技的主線上,即真正實現科技對于金融功能與產業鏈的全面重構。我們認為,未來金融科技的影響方向有幾大方面:一是傳統金融業態在金融科技的支撐下,有可能出現全新的要素特點。例如類似于英國AtomBank這樣的一些完全基于手機APP的銀行,使得銀行發展已經脫離了PC互聯網,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當然,這也需要一個過程,國外監管部門也是經過不斷的考察才給予其全牌照。二是可能會產生許多利用金融科技做金融“小而美”的中前臺業務的機構,在金融產業鏈中擁有自己的分工定位。三是出現著眼于金融垂直生態、金融全產業鏈控制的新金融巨頭。四是作為小型金融科技企業,純粹為現有金融體系提供新技術外包,而不涉及金融業務自營。五是單純做金融科技而非金融業務,但不僅是從事簡單的技術外包,而是著眼于利用金融科技進行金融基礎設施改造,為金融活動提供開放型平臺的綜合技術解決方案。
雖然金融科技可能是一把“雙刃劍”,但在有效引導下,完全能為解決原有難題提供全新路徑。我們認為,一方面不管對金融科技的內涵有多少爭議,其確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考慮潛在不確定性與新風險來源;另一方面,也不要夸大其對于金融穩定與安全的負面沖擊,畢竟最大的風險來源還是在原有的金融部門“主干”上。整體上看,金融科技浪潮肯定會帶來更多的積極因素與進步效果。當然,最終衡量金融科技變革成功與否的標準,不是讓誰賺了多少錢、也不是無原則地降低門檻,而是能否彌補短板、改進社會福利、增加就業等現代化社會發展目標。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