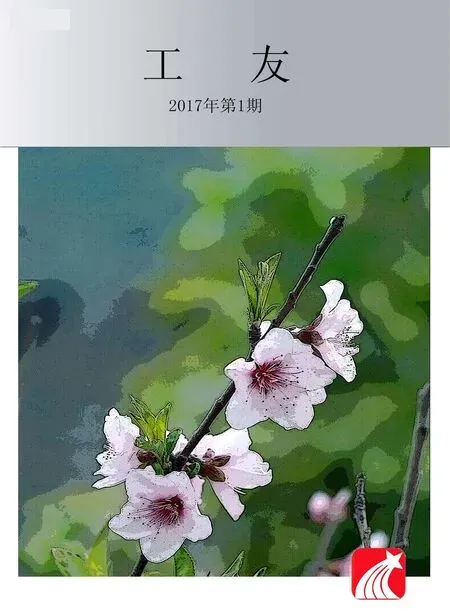新視點
新視點
“戲弄重癥病人”呼喚職業素養的回歸
北京和平里醫院兩名護士在聊天中自曝戲弄重癥病人,其中一人在重癥病房違規使用手機,拍攝發送了一段病人的視頻,并表示“我氣得她,有兩次都作出罵人的嘴型了。”(12月24日《京華時報》)
點評:
將護士戲弄重癥病人的個例上升到醫患矛盾的高度,的確有些牽強,但事實上,縱觀醫患沖突的事例,因醫護人員個人職業素養的缺失而引發的醫患矛盾并不少見。可見,醫護人員職業道德和素養在醫患關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提高醫護群體的職業素養,得從增強其對于工作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入手,當其對于醫護這一職業滿懷希望和認同,當他們能夠從醫院中找到其獨特的存在價值和意義,那么盡其所能為患者服務,也就自然而然成為了職業歸屬感的應有之義。
護士戲弄重癥病人的任性舉動,在根本上還是其職業道德缺失所造成的惡果。與其指責批評,倒不如以此為契機,呼喚職業素養的回歸,將職業素養作為考核職員的一項重要指標,在日常工作中培養其職業道德和素養,鏟除掉滋生工作中不良姿態的土壤。
給人“機會”,就是給企業機會
“新來的大學生,我們連探親假都不敢給,怕一回去就不回來了。”某國企一位管理者在接受采訪時,這樣訴苦。這樣的困擾,在國企中并不鮮見。記者調查發現,近年國有企業普遍存在“進新人走骨干”的現象,在與民營企業的同業競爭中,國企人才流失現象明顯加劇。(12月25日《瞭望》)
點評:
因為財富是人創造的,這才有了“人是企業的最大財富”一說。從這個意義上,人才的流失,實際上也就成了國有資產流失的一種形式。只不過,這種流失更隱蔽,更容易被忽略,尤其遇到從來不會“算大賬”的國企領導,真以為“走幾個人不算什么,想來國企的人一抓一大把”的時候,隱疾就會變成國企的惡疾。
現在有個詞叫做逆淘汰,逼走了有本事的,留下了平庸的,說的就是不少國企用人的現狀了。正常情況下,企業用人的激勵機制要達到“能者上不能者下”“有為者有位”的效果,至少也符合按勞分配,多勞多得才好。然而,在很多國企的制度環境中,有本事的人普遍有“被不公平對待”的感覺,拿不到與能力和付出相對應的報酬、尊重,長此以往,拋棄老東家就是不得已的事情了。而這樣的環境,對于那些求安穩,有關系背景,不好好干活也能活得馬馬虎虎的人,國企強大的“保障力”就顯示出吸引力了。久而久之,國企就成了“只適合練手,不適合久留”的人才中轉站,成了民企的“黃埔軍校”。
“機會”對于每一個職場中人都是剛需,那么,進行合理的“機會設計”,就成了人才流失嚴重的國企,必須潛心要做的功課。
法院拍賣贗品,輸掉的是情理
前不久,河南省宜陽縣人民法院“司法網拍”上掛出的拍賣物品——“扣押杜曉琴高仿LV包一個”,引發網友關注。明知該物品是“高仿”的假貨,法院可以進行拍賣嗎?(12月21日《北京青年報》)
點評:
不否認,高仿商品亦有其價值所在,但作為被執行物,且由法院這一“特殊主體”進行拍賣時,一切就顯得不合“常情”,有違“常理”。
現行法律對于法院拍賣贗品雖然沒有明確規定,但是法院作為國家司法公正的代表,以公開競價的形式來拍賣事實上的假貨,既不利于司法公正的正面導向,也存在置競拍者個人利益于不顧的嫌疑。依照《行政處罰法》等規定,假冒偽劣產品應被行政機關罰沒,而不應再流向市場。法院有無踩線,這個問題值得商榷。
公示高仿標識并不能成為“愿者上鉤”的籌碼。即便競拍者明知所拍物品是贗品而執意競拍,也不能改變法院將某種風險轉嫁給他人的本質。高仿名畫、高仿名包、未經檢驗的名酒等等,不但可能給競拍者造成經濟損失和健康風險,更是對名牌商標名譽的無形侵害。
干部“掛職”重在“掛事”
鄧比從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到云南省瀘西縣永寧村掛職第一書記兼駐村扶貧工作隊長第一天,遇上了一場暴雨之后的搶險救災,他來不及換衣服也趕到現場,與黨員干部群眾一起肩挑背扛,挖沙、扛袋、筑堤。“北京來的小伙子,你不用干活。”有鄉領導擔心鄧比干不了體力活。“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不要把我當掛職干部!”鄧比扛著沙袋回答。(12月21日《光明日報》)
點評:
掛職干部為了盡快融入掛職單位,卻不愿意當地人當自己是掛職干部,至少說明:第一,掛職單位對掛職干部普遍存有一種有限的期待;第二,很多掛職干部來掛職單位工作只是一種有限的投入。雙方會意,略有默契。在多方面的原因中,有一點需要特別注意,那就是許多掛職,是“掛人”為主,而“掛事”不足。
培養和使用干部的出發點決定了我們的方向感和價值追求。你把掛職簡單定位于干部個人的成長,雖不排除也能培養出具有民生情懷的干部,卻容易變成“為掛職而掛職”,讓基層干部群眾成為“陪太子讀書”的角色,降低大家對掛職干部的期待。重在“掛事”,就是以人民為本,讓群眾看得到實實在在的希望。為人民辦實事正是干部的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