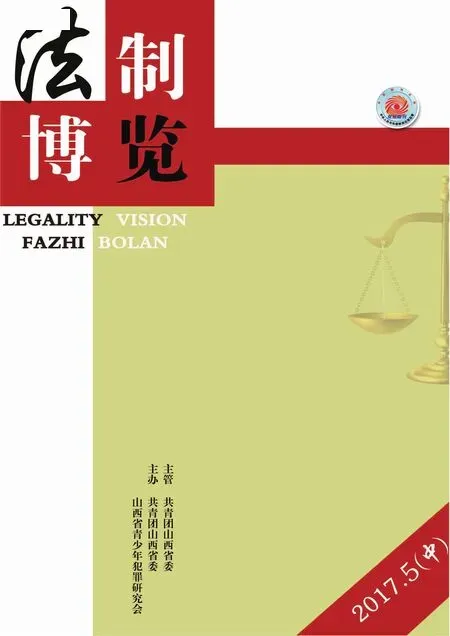中國古代法律規則下的同案同判障礙分析
章 燕
北方工業大學,北京 100144
?
中國古代法律規則下的同案同判障礙分析
章 燕
北方工業大學,北京 100144
中國古代對同案同判的追求,在司法實踐中最終為現實所消解。古代法律規則體系、法律語言模糊性與明晰性問題,賦予中國古代審判者較大的自由裁量權,成為同案同判的主要障礙因素。
同案同判;法律規則體系;法律語言
同案同判,因其背后關聯的平等、公正等價值,從通識角度而言是個應然的問題。“法前平等、司法公正,從東方文明到西方文明,從古至今,自有法以來就是司法的一個永恒主題,一個至高的價值追求。”①中國古代法制文明進程中亦是如此。統治者極為重視同案不同判的現象,“大理當其死坐,刑部處以流刑;一州斷以徒年,一縣將為杖罰”②,從立法、司法等多角度進行了持續不斷的多元改革措施,然而在司法實踐中最終為現實所消解。同案同判的消解或障礙,其本質與法官自由裁量權緊密相關。分析中國古代法律規則的特點,賦予中國古代審判人員何種自由裁量權,是研究中國古代同案同判障礙的關鍵路徑。
中國古代立法以法律應該整齊畫一、條文簡約、易于理解為宗旨,其立法技術經歷了許多個世紀的淬煉,逐漸成熟與精湛。然而其自身存在的諸多問題,并沒能真正實現統治者的理想司法效果,抑或產生出新的問題,賦予中國古代審判者較大的自由裁量權,進而成為同案同判的主要障礙因素。
一、法律規則體系化問題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評價申不害時,指其不擅法,并沒有統一法律規則體系。“不一其憲令,則奸多”,此弊為“奸臣”所利用,使裁判活動呈現出可以依據前法也可以依據后法判的不穩定色彩,“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③。漢朝立法也未能形成整齊劃一的法律體系,“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④,導致審判“罪同而論異”,同案同判難以實現,客觀上釀成了嚴重的司法腐敗后果。唐朝統治者意識到前朝法律體系不完善造成審判官員自由裁量權過大,影響同案同判公平判決的追求,審判結果“殊異”——大理裁判其為死罪,刑部判為流刑;州級審判官裁判為徒罪,縣級審判官僅決以杖刑。立法者強調法律體系整齊劃一,猶如權衡、規矩,后者可以知輕重、得方圓,前者能實現“邁彼三章,同符畫一”的效果。故唐自建國以來就開始繁重的立法工程,最終建立了一套比較完備的法律體系。如刪定格、令、式的立法者應統一以確保不同法律形式內容統一、體系完善,“《永徽式》十四卷,《垂拱》、《神龍》、《開元式》并二十卷,其刪定格令同。”⑤有少卿趙仁本撰寫《法例》,眾人稱贊“折衷”,以為有利于審判公正。唐高宗卻恐其影響整齊劃一的立法體系,“何為更須作例,致使觸緒多疑”⑥,給審判者同案同判增添障礙,遂下令廢而不用。
與唐朝高超的立法技術不同,清朝律、例同時存于《大清律例》中,且例文眾多、修訂并不統一,導致清朝法律體系的整齊劃一有所欠缺。當時精通律例者指出例文隨事纂定,并非由統一的立法機構或立法者所完成;對于五年小修一次,十年及數十年大修一次的條例修訂工作,也并沒能以整齊劃一為宗旨有序完成。“同治九年修例時,余亦濫厠其間,然不過遵照前次小修成法,于欽奉諭旨及內外臣工所奏準者,依類編入,其舊例仍存而弗論。自時厥后,不特未大修也,即小修亦迄未舉行。”⑦薛允升評價法律體系出現了“例之彼此牴牾,前后岐異”的缺點,勢必給同案同判的司法公正追求造成重重障礙。
二、法律語言模糊性與明晰性問題
法律語言具有模糊性特點,不僅表現在語言自身具有的模糊性屬性上,還表現在立法語言的概括性上。“語言的非精確性,即模糊性是語言的本質屬性之一。”⑧即法律語言的模糊性不僅是客觀上無法避免的,還是立法者主觀所為的。其目的是為了能使用概括性的法律語言以涵蓋復雜無法完全預見、羅列的現實,使法律規則充滿了生命力與靈活性。以《大清律例》“恐嚇取財”條文為例,“恐嚇,謂假借事端,張大聲勢,以恐嚇乎人,使之畏懼而取其財也。內蓄穿踰之心,外托公強之勢”。⑨恐嚇的定義具有極強的概括性,只要達到使他人畏懼或使他人相信的效果即可。但是,是否使他人畏懼或相信,會因被害人心理承受能力和認知能力的不同而不同,在具體的環境中亦會隨之變化,因此缺乏客觀的、具體的、有形的準確衡量標準,必然造成審判者在適用法律時擁有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從而為同案同判司法公正判決增添障礙。
司法判決欲以同案同判為目標,必然要求法律語言具有精確性、明晰性的特點,以引導審判者正確適用法律規則定罪量刑。中國古代立法者充分意識到法律語言精確明晰的重要性,經歷兩千年不斷的發展完善,其立法語言技術達到古代法律語體的高峰。以《唐律疏議·戶婚》義絕離婚規定為例。唐律規定,“諸犯義絕者離之,違者,徒一年。”何為義絕,前條律文疏議中注釋道:“毆妻之祖父母、父母及殺妻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殺及妻毆詈夫之祖父母、父母,殺傷夫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及與夫之緦麻以上親、若妻母奸及欲害夫者,雖會赦,皆為義絕。”立法者羅列義絕行為定義的方式,是中國古代立法的一個重大特點,即對法律語言精確明晰的追求,以減少法官同案不同判的風險。“立法者傾向于將犯罪行為作具體化規定的根本原因則在于,他們意欲將讓一體處罰的權力牢牢地控制在君主手中,并且盡可能地限制官員的處斷權。”⑩然而,中國古代立法者并沒能通過以上方式,徹底解決限制審判者裁量權的問題。具體性的條款面對無法列舉的現實案例,只能“以萬變不齊之情欲御以萬變不齊之例”?,即不斷增加例文,同治九年高達1892條。例文的增加不僅無法適應復雜、發展的社會現實,而且造成了法律規則龐雜、矛盾,使得審判者故意或過失適用法律不一,影響同案同判的司法效果。《小倉山房集·答金震方問律例書》載袁枚語:“千條萬端,藏諸故府。聰強之官,不能省記。一旦援引,惟例是循,或同一事也而輕重殊,或均一罪也而先后異。”
[ 注 釋 ]
①徐顯明.何謂司法公正[J].文史哲,1999(6).
②<唐律疏議·名例>.
③<韓非子·定法>.
④<漢書·刑法志>.
⑤<舊唐書·刑法志>.
⑥<舊唐書·刑法志>.
⑦<讀例存疑·自序>.
⑧伍鐵平.模糊語言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132.
⑨[清]沈之奇注,懷効鋒,李俊點校[M].大清律輯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611.
⑩[英]馬若斐,朱勇譯.傳統中國法的精神[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126.
? <清史稿·刑法志一>.
D
A
2095-4379-(2017)14-0190-02
章燕(1982-),女,漢族,江西人,北方工業大學,講師,研究方向:法制史、法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