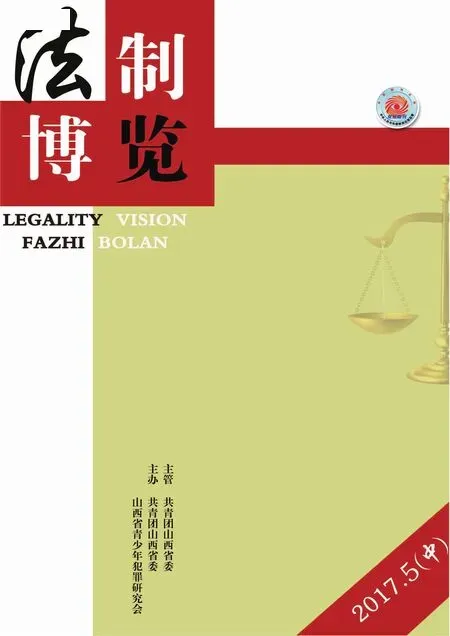論擴大“探望權”主體的必要性
謝如盼
江南大學法學院,江蘇 無錫 214122
?
論擴大“探望權”主體的必要性
謝如盼
江南大學法學院,江蘇 無錫 214122
有這樣一段描寫親情的話,“現在,終于讀懂了親情是有愛的地方,而且滿滿的都是愛。如果沒有你,我將會是多么可憐可悲的孩子。所以決定,好好愛你,像你愛我一樣不容易卻又必須好好愛著。”依筆者看來,探望權就應是一種與親情、血緣相關聯的權利,保障子女成長利益的最大化。
主體范圍;非絕對對等性;4+2+1;撫養權性質
一、探望權的主體范圍
我國《婚姻法》第38第1款規定道,“離婚后,不直接撫養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權利,另一方有協助的義務。”第27條第2款又規定道,“繼父或繼母和受其撫養教育的繼子女間的權利和義務,適用本法對父母子女關系的有關規定。”第26條第1款還規定到,“國家保護合法的收養關系。養父母和養子女間的權利和義務,適用本法對父母子女關系的有關規定。”因此,依據我國的現行法律,探望權僅被賦予以下主體:離婚后的父、母、繼父、繼母以及養父、養母。而依據立法原意,探望權是為了使父母離婚后子女仍然能夠身心健康地成長,實現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筆者認為,以上規定過度限制了探望權的主體,將“探望權”與“直接撫養權”相對,將不利于立法目的的實現。相反,應對“探望權”的主體作有限的擴大,在目前的立法下,及于祖父母、外祖父母和直接撫養人。
二、血緣,權利義務的非絕對對等性
權利義務對等性原則是指權利和義務是相對的,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權利的取得必然有義務的付出,義務的付出也對應權利的取得。我國《婚姻法》第28條的規定道,“有負擔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對于父母已經死亡或父母無力撫養的未成年的孫子女、外孫子女,有撫養的義務。有負擔能力的孫子女、外孫子女,對于子女已經死亡或子女無力贍養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贍養的義務。”第29條還規定道,“有負擔能力的兄、姐,對于父母已經死亡或父母無力撫養的未成年的弟、妹,有扶養的義務。由兄、姐扶養長大的有負擔能力的弟、妹,對于缺乏勞動能力又缺乏生活來源的兄、姐,有扶養的義務。”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祖父母、外祖父履行了對孫子女、外孫子女的撫養義務時,其便享有受贍養的權利;同理,履行了撫養義務的兄姐享有被撫養的權利。
依筆者看來,在血緣關系層面,權利義務是可以突破對等性原則的。當義務主體履行其義務時,其投入的除了可量化的義務履行成本外,更多的是無法量化的情感成本。此刻,我們刻意強調權利義務的對等性,其在數量上的等值關系,是在抹殺法律本該有的溫情。且《婚姻法》相對于其他法律而言,其本身帶有的“人”色彩會更為濃厚。因此,在此情況下,立法者在制度設計時著重于權利義務的關聯性,相應地淡化其對等性。
三、我國特殊的家庭人口結構——4+2+1
由于上世紀計劃生育政策的全面推行,在我國,典型的家庭人口結構為“4+2+1”,即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外加一個小孩。在目前的社會生活中,由于生父母工作的原因,孩子一般是由祖父母、外祖父撫養長大的。夸張一點說,祖父母、外祖父母在其身上影射的是血緣父母的情感;其承載了老人們近乎所有的情感付出。因此在現實生活中,相比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與祖父母、外祖父更為親近的情況也是比比皆是。但若按照我國《婚姻法》的現行規定,在其父母離異后,祖父母、外祖父母是不享有探望權的,當幼有所教時,老未必能有所養,有所依?且基于“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則,相伴其右的會更可能是其最大利益的捍衛者,而立法要做的便是賦予其更大的可能性。
四、自然權利
關于探望權的性質,我國采用的是狹義的探望權權利說,即是說探望權為單向性,僅為不直接撫養子女的父母一方享有,而子女不享有探望權。但筆者認為,探望權是一種自然權利,其是“天賦人權”,并不以法律授權而享有。“幸福權”是人本應有的自然權利,作為個體的人是有能力僅憑自我的努力便可達到享有“幸福”權利的狀態。這時,法律便不應該加以干預,而應任憑其發展。并且依筆者看來,“探望權”本質上是基于血緣與情感而構造起來的權利,是“幸福權”的重要內容。原因在于“探望權”在具有情感傾向性的——其傾向于與自己愿意親近的人,這是一種基于情感而作出的選擇;當其情感得到滿足時,此時“幸福權”已達到窮進行使狀態。所以此時法律的最優狀態便是讓作為理性人的子女獨立來行使自己的自然權利,并不受干預。
從我國的立法原意來看,設立“探望權”的目的是讓子女在父母離異后仍能健康成長,即用“探望權”來彌補愛的缺失。但此時除了子女自己,誰又能替其決定何為其所需要的保護與救濟?法律的觸角不能伸得過長,尤其在婚姻家庭關系領域,其本身固有的屬性便決定了其可由社會習慣、社會道德進行很好地約束。因此在“自然權利”領域,法律無禁止便是權利行使的最優狀態,而硬性“授權”、“規制”便是打破了這種平衡,成為一種權利行使的阻礙。
D
A
2095-4379-(2017)14-0271-01
謝如盼(1996-),女,漢族,廣東湛江人,江蘇省無錫市江南大學法學院,本科生,研究方向: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