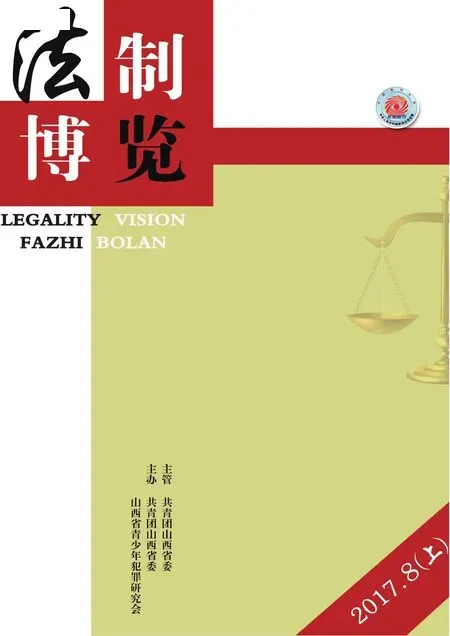騙取貸款罪初探
陳 萍
浙江鄭和陳律師事務所,浙江 臨海 317000
騙取貸款罪初探
陳 萍
浙江鄭和陳律師事務所,浙江 臨海 317000
騙取貸款罪作為以欺騙手段騙取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并給其造成重大損失或有其他嚴重情節的犯罪,司法實踐中似乎越來越傾向于懲罰借款人的欺騙行為,即只要借款人采取了欺騙手段,無論是否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的行為,都會被認定為犯罪。其他嚴重情節成為沒有重大損失之騙取貸款罪認定的模糊標準。這使騙取貸款罪有演化為行為犯之趨勢。
騙取貸款罪;重大損失;其他嚴重情節;騙取手段
案件一:陳某在明知系林某等人借用自己名義貸款且用于貸款申請的經營店面、營業信息等均系虛假的情況下,仍同意由自己出面作為申請人,以黃某、王某為擔保人,并利用上述虛假材料騙取銀行貸款40萬元。該筆貸款到期后一直沒有歸還。法院認為,被告人陳某祥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貸款,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其行為已構成騙取貸款罪。①
案件二:狄某、周某為從銀行貸款,偽造了張某的身份證、張某和狄某的結婚證(該身份證、結婚證上張某的個人信息為其本人信息,照片為被告人周某),并由被告人周某冒充張某,用張某的房屋所有權證、虛構的購銷合同和上述偽造的身份證、結婚證從某銀行貸款130萬元,后歸還了該筆貸款。狄某、周某又采用上述相同作案方法,從其他銀行貸款150萬元,貸款到期后已歸還。法院認為,被告人狄某、周某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貸款,有其他嚴重情節,其行為已構成騙取貸款罪。②
案件三:葉某的針織廠、俞某的制衣公司、黃某的服飾公司相互擔保向某銀行申請了網絡銀行電子商務聯貸聯保貸款。期間,葉某提供了包括其偽造的一份虛假土地使用證在內的申請資料。經銀行審核后,分別向三家企業發放了貸款。其中,被告人葉某獲得貸款134萬元(其中34萬元作為保證金)。后被告人葉某因經濟困難,在支付銀行8個月利息后,未按時向銀行支付利息,且在貸款期限屆滿后未能歸還貸款,最終由其他兩家擔保企業替被告人葉某歸還貸款100萬并支付了剩余利息。法院認為,被告人葉某提供虛假文件,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貸款,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騙取貸款罪。③
上述三個案件,行為人均采取了欺騙手段并取得了銀行的貸款,但是,只有案件一給銀行造成了損失,而案件二和案件三并未給銀行造成損失但卻因被認為情節嚴重一樣被認定為騙取貸款罪。這似乎表明只要騙取了銀行的貸款,無論是如期歸還亦或是逾期未予以歸還,無論是銀行有損失還是沒有損失,均會被認定為騙取貸款罪。那么,騙取貸款罪與非罪的界限是什么呢?
一、騙取貸款罪與非罪的界限
我國《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規定了騙取貸款罪這一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無論是自然人,還是單位,只要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以下均簡稱為銀行)貸款并給其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行為,均可構成騙取貸款罪。顯然,是否造成重大損失這一法定結果或者是否有其他嚴重情節是騙取貸款罪與非罪的界限。可見,騙取銀行貸款的行為,或者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二者必備其一,才可構成騙取貸款罪。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2012年5月7日)(以下均簡稱為《標準二》)明確指出: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貸款數額在一百萬元以上或者給銀行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二十萬元以上的,或者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貸款三次以上的,均屬于我國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即騙取貸款罪所稱的“重大損失或其他嚴重情節”。可見,重大損失的標準是明確的,但其他嚴重情節的標準則是模糊的,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貸款數額在一百萬元以上以及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貸款三次以上均應屬于其他嚴重情節的范疇。
犯罪作為一種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騙取貸款罪之其他嚴重情節應當嚴重到足以擾亂或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并且使貸款處于不能歸還之危險狀態。對于數額不大的,或者雖然數額較大但在案發前已經歸還了貸款或者在案發后立即歸還了貸款的,可以認為不屬于“其他嚴重情節”。④但是,上述案件二和案件三卻表明是否歸還貸款并不影響定罪。這顯然將騙取貸款罪視為行為犯而非結果犯或情節犯。
二、騙取貸款罪是結果犯還是情節犯
從我國刑法關于騙取貸款罪的規定看,騙取貸款罪是結果犯和情節犯并存的犯罪。但是,我國刑法規定的是“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犯罪行為。那么,“其他嚴重情節”是就情節而論,還是與“重大損失”并列的結果?雖然有“嚴重情節”但是未并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是否應當認定為犯罪?
如案件二和案件三就沒有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但是還是被認定為情節嚴重而構成犯罪。騙取貸款的行為在已經造成重大損失的情況下被認定為犯罪是沒有疑義的,但是,在沒有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的情況下,實際上銀行可能并不會對該行為主張追究借款人的刑事責任。在銀行并未報案的情況下,即使如刑法規定一樣的情節嚴重,一般而言,借款人是不會被追究刑事責任的,而銀行似乎也沒有理由這么做。銀行之所以追究借款人的刑事責任,是由于其貸款處于不能回收或有損失的危險狀態,即有相應的危害結果才是銀行追究借款人刑事責任的前提條件。因此,應當將“其他嚴重情節”中的“其他”理解為與“重大損失”相并列的“嚴重情節”,即處于造成“重大損失”的情節才應被視為“嚴重情節”而不應只要有所謂的“嚴重情節”就無一例外的追究借款人的刑事責任。畢竟銀行有自身的特點及行業規則,對于貸款的回收有其自身的程序與辦法、措施,不宜將尚未達到嚴重危害社會的一般危害行為納入犯罪的范疇,這似乎就是幫銀行“討債”。顯然這對銀行有利但對借款人卻十分不利。借款人固然采取了欺騙手段并取得了貸款,但顯然銀行亦有審核不嚴或流于形式之嫌,甚至不能排除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發放貸款之嫌疑。畢竟虛假的、偽造的貸款申請材料不可能輕易就通過審核,如果通過審核,那么這種審核的真正意義何在?如果銀行沒有損失而追究貸款人的刑事責任,那么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很可能就更不嚴格審核貸款申請材料。這亦不利于維護金融管理秩序。
三、騙取貸款罪之“欺騙手段”的認定
虛構抵押物或投資項目、編造虛假的購銷合同、偽造身份證件或產權證書……欺騙手段變化多端、不勝枚舉。但是,并非借款人采取的一切欺騙手段都是構成犯罪的前提條件,該欺騙手段首先必須是為騙取貸款的實行行為,而且該種欺騙手段必須達到一種嚴重程度,即這種欺騙手段必須足以使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陷入錯誤認識,且因錯誤認識而發放貸款并使貸款處于無法回收的高風險狀態。因為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有著完備的貸款審查制度和不良貸款清收、處理制度,對于一般的欺騙手段完全可以通過刑法以外的法律手段或其他手段予以解決,尚沒有必須納入刑法的調整范圍。而且,還必須認識到這種欺騙手段雖然是為了騙取貸款,但取得的貸款完全用于正當的、合理的、真實的以及如實陳述的用途,但最終因客觀原因而未能如期歸還則不宜一概而論的認定為構成騙取貸款罪的欺騙手段。畢竟不規范的貸款行為并不是借款人單方的行為,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對此通常是明知故犯。在這種情況下用刑法的手段懲罰一方當事人即借款人,可能亦是混淆了合同糾紛的性質。
綜述,騙取貸款罪應以銀行的重大損失為入罪的基本條件,同時以處于重大損失之危險的其他嚴重情節為補充,并對欺騙手段進行區分,只有致使銀行重大損失或處于重大損失之危險的欺騙手段才能被認定為騙取貸款罪之犯罪行為。
[ 注 釋 ]
①浙江省臺州市路橋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7)浙1004刑初102號.
②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5)溫瑞刑初字第472號.
③浙江省諸暨市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3)紹諸刑初字第1306號.
④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黃太云關于<刑法修正案(六)>的解讀[EB/OL].http://www.ccdi.gov.cn/djfg/fgsy/201308/t20130805_46333.html.
D
A
2095-4379-(2017)22-0133-02
陳萍,女,浙江鄭和陳律師事務所,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