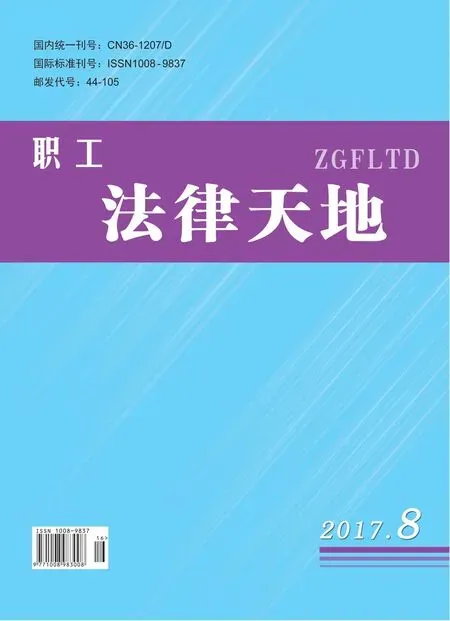刑事和解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建構和變通
——以涼山彝族自治州為例
張曉露
(610041 西南民族大學 四川 成都)
刑事和解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建構和變通
——以涼山彝族自治州為例
張曉露
(610041 西南民族大學 四川 成都)
我國民族地區的傳統糾紛解決方式長久處于一種萎縮狀態,但隨著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建立,傳統糾紛解決方式已被正視,并不斷融合于國家法。本文擬以刑事糾紛解決常采用刑事和解的涼山彝族自治州入手,對刑事和解在該地區的建構和變通展開研究,以期促進國家法和習慣法的融合,推進現代化法治建設進程。
刑事和解;民族自治地方;涼山彝族
在少數民族地區,傳統的糾紛解決方式并沒有隨著現代法治化進程的推進退出歷史舞臺,甚至仍在糾紛解決的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處理糾紛時,往往無法完全摒棄習慣法,甚至國家法有時候甚至會受制于習慣法。特選取近年來在國家法和習慣法的融合中頗具代表性的涼山彝族自治州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刑事和解制度在民族地區的運行,正視習慣法與國家法之間的沖突,找尋平衡點,尋求能夠使二者融合的路徑,更好的推行和貫徹刑事和解制度。
一、涼山彝族自治州刑事和解現狀分析
刑事和解重在修復關系、解決矛盾、實現安定有序,是我國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良好體現。對于少數民族地區,尤其是“小聚居”的民族自治地方而言,糾紛解決的前提是要維護原有的聯系緊密的“熟人社會”這一關系網不被破壞,要保持穩定團結的民族關系,因此在刑事案件中,比訴訟更容易讓人接受的是和解。
涼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區,這里絕大多數的彝族都以家支的生活形態存在,因此,為了維護“熟人社會”的穩定,為了保護家支的利益和家族的名聲,在發生糾紛時,相較于國家法嚴厲的處罰機制,人民更傾向于選擇習慣法中的糾紛解決方式。歷史上,涼山地區的彝族人民常常通過和解的方式來解決刑事案件,即通過“德古”、“畢摩”等民間權威人士作為中間人進行協商,賠禮道歉,彌補損失,達成和解協議,在此之后一般不再對加害人采取強制性的刑罰措施。筆者認為,這實際上是涼山彝族刑事習慣法體現的傳統意義上的“刑事和解”,雖不具國家法的強制性,卻能有效解決當事人雙方的矛盾沖突,在當地得到長久認可和遵從。
如今,國家法已深入各個地區、各個領域,刑事和解制度也已確立實行五年之久,越來越多的人會在刑事糾紛發生之后尋求司法救助,通過國家法解決糾紛。但涼山彝族自治州地處偏遠、經濟落后,刑事案件時有發生,實際上依然有很多人會選擇私下解決的方式解決糾紛,通過刑事和解來解決的刑事案件占據很大比例,即使受到國家法干預,最終的結果也往往是“坎下法庭”占優勢,他們更傾向于選擇民間權威的傳統糾紛解決方式。
但是,這樣的和解方式明是一種“刑民不分”的法文化的體現,有時候過于注重利益補償,而輕處罰,無法實現刑事和解所要達到的目的,甚至嚴重破壞國家法的權威性,維護了少數人的利益卻將危險擴大到更大的范圍甚至整個社會。目前,涼山彝族自治州除了對婚姻、資源保護等方面行使了變通權,作出明確的變通性規定外,并未對刑事案件及其和解作出相應的變通性規定和補充說明,這使得刑事和解在遭遇國家法和習慣法沖突時,適用混亂,無法作出有效的應對措施,無法快速解決問題,甚至會將矛盾激化,導致更嚴重的后果。
二、刑事和解在涼山彝族自治州的建構和變通
筆者認為,刑事和解在涼山彝族地區并非創設性的制度,“德古調解”等傳統的刑事糾紛解決方式完全契合法律對刑事和解制度設立的初衷,只是需要規范化來達到依法治國的要求以推進現代化法治建設進程。探究刑事和解在涼山彝族自治州等民族自治地方的建構和變通問題,實際上是融合國家法和習慣法,構建一種符合民族自治地方刑事和解制度地方模式。
在立法上,要充分行使刑法變通權,作出變通性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90條明確規定了“民族自治地方刑法適用的變通”,即賦予涼山彝族自治州等民族自治地方的省一級的立法機關權力,使其可以創設、制定適用于民族自治地方的關于刑事和解的變通性規定和補充性規定,但是目前涼山彝族自治州及其他民族自治地方均未作出關于刑事和解的變通性規定。因此,筆者認為應當作出符合當地實際且行之有效的變通性規定,通過法律規制使國家法和習慣法在涼山彝族地區的刑事和解當中發揮自身價值,既要以規定保證國家法的權威性,又要以規定保障習慣法的有效性,以實現二者的有機統一。
在司法中,應該加強對“德古”等民間調解人員的專業培訓,明確“德古”的法律地位,設立專門的刑事和解處理機構,并將“德古”等民間調解人員吸收納入其中,成為專職人員,使其在法律保護的范圍內參與甚至主持刑事和解工作,以便更好地將彝族習慣法和國家法連結起來,充分發揮民族地區刑事和解的作用。
此外,筆者認為除了在立法層面和司法層面明確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和解制度地方模式的建構外,在相關的制度上也應提供支持和保障。例如:為了避免被害人過度追求物質補償而排斥國家法的適用,避免加害人為逃避刑罰而過度補償被害人,為了更好地協調民事賠償和刑事處罰之間的關系,應當建立相對應的適用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被害人國家賠償制度;為了更好地修復被犯罪行為破壞的社會關系,應當將刑事和解和社區矯正連接起來,社區矯正的處理方式既貫徹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也符合以和為貴的民族傳統文化,能夠幫助刑事和解更好的實現司法價值,以達到刑事和解的最終目的——通過非刑罰化措施或輕緩化刑罰的修復性處理方式,化解、緩和當事人之間的矛盾以達成和解,維系社會和諧。
[1]宋英輝主編:刑事和解制度研究[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2]劉之雄:我國民族自治地方變通施行刑法之機制研究—以刑事和解為視角的考察[J].法商研究.2012年第3期(總第149期).
[3]楊雄:民族地區刑事和解實施的問題與對策[J].貴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11期(第36卷總第177期).
[4]王扎龍云等:涼山彝族習慣法探究—以刑事糾紛解決機制為視角[J].法制與社會,2015·4(下).
張曉露(1992~),女,云南劍川人,西南民族大學在讀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訴訟法學,少數民族糾紛解決機制。
西南民族大學2017年研究生“創新型科研項目”,項目名稱:《刑事和解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建構和變通——以涼山彝族自治州為例》,結題成果,項目編號:CX2017SP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