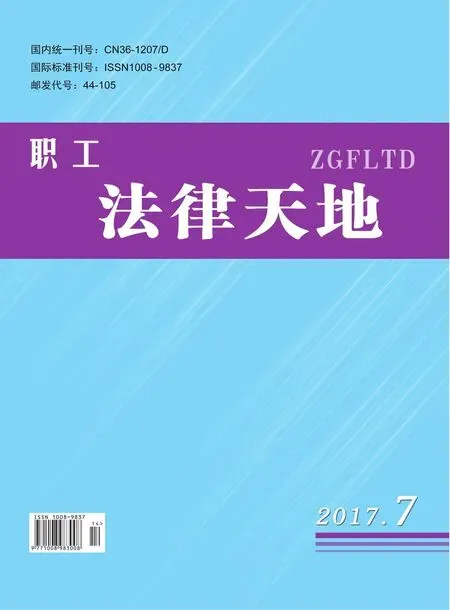網絡誹謗中的“網絡空間”與“公共場所”
白加寧
(053000 河北合明律師事務所 河北 衡水)
網絡誹謗中的“網絡空間”與“公共場所”
白加寧
(053000 河北合明律師事務所 河北 衡水)
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3年9月9日發布的《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事實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條第2款將傳統刑法中尋釁滋事行為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表述為“造成公共秩序混亂”,從而將某些網絡上造謠生非行為納入尋釁滋事的范疇。但網絡空間與現實生活中的實在的空間不同,應當在對網絡空間正確的理解基礎之上,實現網絡空間與現實空間的轉換。
網絡空間;公共場所;誹謗
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3年9月9日發布的《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事實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條第2款將傳統刑法中尋釁滋事行為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表述為“造成公共秩序混亂”,從而將某些網絡上造謠生非行為納入尋釁滋事的范疇。但網絡空間與現實生活中的實在的空間不同,應當在對網絡空間正確的理解基礎之上,實現網絡空間與現實空間的轉換。
一、“網絡空間”與“公共場所”之定義與爭議
網絡空間的出現是信息技術發展的必然產物,它不同于傳統的物理空間,是一種虛擬且無限擴大的空間。網絡空間的存在和發展,展現了計算機信息技術帶給人們的巨大改變。網絡空間通過數字與數字之間的關系,展現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它擁有自己的向度和規則。網絡空間是一種數字化空間,人們雖然不能實實在在進入這樣一個空間,但可以通過各種數字化界面的切換、數據化的支撐使虛擬的空間與真實空間相連接,從而完成各種活動。網絡空間兼具虛擬性、開放性以及更大范圍內的群眾參與性。這與哈貝馬斯對公共領域的定義相吻合。由此,網絡空間已經成為了人們生活、工作的又一基本場所,它與現實實社會構成“雙層社會”。
公共場所是“公眾可以任意逗留、集會、游覽或利用的場所”。在我國傳統刑法中,公共場所是一個運用較多的概念。2013年4月,“兩高”發布解釋,對尋釁滋事行為的刑罰適用做了更加明確的認定,也對公共場所做了列舉式規定。其中,公共場所的性質、活動是否重要、參與人數、時間及影響都成為考量因素。除此之外,我國刑法體系中,聚眾斗毆、強奸等犯罪都將公共場所納入客觀方面要件或法定刑的升格條件,這就要求公共場所必須實際存在。在網絡這樣一個虛擬的環境中無法實施“聚眾斗毆”或“強奸”行為。但就尋釁滋事行為來講,最高司法機關有若干個司法解釋中涉及公共場所。由此,無論是從公共場所本身含義,還是從我國現有刑法體系出發,公共場所實際存在于現實生活中似乎已經是約定俗成。
但《解釋》卻將“網絡空間”納入“公共場所”,引發討論。網絡空間本身的超凡性,似乎讓傳統刑法無法適從。而傳統刑法中嚴密的立法體系,似乎也無法將網絡空間很好地囊括進去。于是出現了在“四空間說”的基礎上的“第五空間”,甚至于出現了網絡是“沒有法律沒有邊界的新大陸”的說法。
一些學者認為,“網絡空間”不屬于“公共場所”。
從立法原意上,有論者認為,網絡上的虛假信息與現實生活中秩序的混亂沒有太大關系,以編造和散布公務人員違紀謠言為例,這樣的謠言可能會讓政府在公眾中的公信力下降,是對公眾思想的擾亂,但很難由此來判定該行為擾亂公眾生活。
從法律解釋體系上,有論者稱:將“公共場所”解釋為包括“網絡”,實質性地改變了立法原意,屬于類推解釋,應予以否認。從刑法體系協調性上,刑法中已經有諸多罪名涉及“公共場所”,且無一例外,均為實體空間,刑法應有自己的體系協調性和嚴肅性,同一法律術語應當在整個法律中含義一致。“公共場所”一旦有了不同含義,實施起來也會受到阻礙。刑法中的公共場所,應當是我們身體能夠進入的區域。
從公共場所本身來看,通常意義上的場所是可以表現出來的。通過長、寬、高的三維,能夠讓人感受到實際的物質存在。但網絡空間并不存在三維,也就不同于現實空間。網絡空間類似于一塊硬盤,當我們說硬盤“空間”大小時,指的是它的存儲量,而不是活動區域。同理,網絡空間無法形容大小,沒有三維,不符合公共場所本身的含義。
二、“網絡空間”應屬于“公共場所”
筆者認為,網絡空間確實是社會空間的一種,也是公共場所的一種。“網絡空間將人們的相遇、溝通、告別模式進行了改變。人們在網絡空間中不再是面對面的交流,而是改作互相發出的信息流相碰撞,讓信息的面對面取代現實中的面對面,但本質是沒有變化的。網絡空間與現實對接越來越緊密,也為我們的溝通交流提供了新的環境和形式。”“網絡空間根據鏈接的信息終端來確定信息傳播的速度與范圍”,當數量足夠多時,網絡空間的作用已經可以和現實中的公共場所“媲美”。公共場所的概念應當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的擴充,與現實社會逐步接軌。現在的網絡普及度,已經讓網絡成為新的溝通交流平臺。在網絡這個平臺中可以做很多現實中的事情,如交易、通信等等。網絡空間成為公共場所的一種,毋庸置疑。
從法律本身來講,最高法院給出了貼切的解釋:“編造虛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編造的虛假信息,在信息網絡上散布”,反映出信息網絡的工具特性、“公共屬性”及“社會屬性”,即網絡社會已經融入現實社會。將網絡空間納入公共場所的范疇,是合理的擴大解釋。將網絡社會類比現實社會,網絡社會中的辱罵、恐嚇以及散布虛假信息的行為,如果情節惡劣,將會引起網絡空間的公共秩序混亂。尋釁滋事行為在網絡社會已經被異化了,即利用網絡實施尋釁滋事或針對“網絡社會”這一公眾平臺的“網絡公共秩序”所實施的尋釁滋事行為都是應該處罰的行為。
在法律體系上講,我國司法解釋中已經出現了將網絡并軌至現實中的實例。如2005年以及2010年立法部門出臺的關于賭博的相關司法解釋已經將網絡中的賭博行為納入傳統意義中的賭博,將網上賭場并軌到現實賭場。再如對于淫穢物品的規定,已經不單單是現實中的淫穢光盤、圖片等,網絡中的淫穢視頻與圖片甚至文字都已經納入法律規制的范圍。刑法中個別語義的大小既要講求一致性,更要與所保護的法益相吻合。不同法法益,“詞語含義的不完全一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網絡中的種種不和諧因素也嚴重影響著我們的社會生活。現實生活中很多因為網絡輿論、網絡謠言導致引發的群體非理性事件出現,極大地干擾著公平公正。如藥家鑫案件中,網絡上“藥家鑫是富二代”等虛假信息激發了眾多網民憤懣,輿論幾乎一邊倒要求嚴懲藥家鑫。法院迫于壓力,也不得不做出相應判決。由此可見,網絡空間中的虛假信息,給現實中的社會帶來巨大的影響力。
當我們判斷一個行為在特定場域是否造成嚴重社會影響時,不應以特定場域的屬性為出發點,而應當以實際社會影響,造成的危害性為出發點。尋釁滋事行為在網絡空間蔓延,已經給現實生活造成了嚴重影響,因而我們不應當去否定現實,卻被公共場所的現實屬性所拘泥,甚至被傳統法律中一致性拴住手腳。法律是服務于現實的,也應當與現實與時俱進。將網絡空間納入公共場所,是一種完善,是一種兼顧法理與現實的進步。
當然,筆者雖認同將網絡空間納入公共場所,但并不贊同將全部的網絡空間均納入公共場所。可以被納入公共場所的網絡空間應當具有工具性和公開性,能夠為公眾輕易進入。一些涉密的個人空間,如僅能夠被自己看到的朋友圈,甚至一對一的聊天室,可以類比現實生活中的私密空間,如家庭等,是不包含在公共場所范圍之內的。
縱觀當今社會,很多國外相關判例也與時俱進,將網絡空間納入公共空間之中,給予公共空間更加廣泛的含義。如美國奧克芒公司訴奇才公司案中,法院判決將出現在電子公告、雜志等網絡頁面等同于公共場所,網絡中的虛假信息對奧克芒實際運營帶來了很大影響,從而判決奇才公司對奧克芒公司擔負責任。
綜上,尋釁滋事的網絡異化是在“三網融合”的大背景下應運而生,因而,不管“網絡空間”是否爭議四起、充滿質疑,它都肩負著維護網絡良好秩序,使網絡社會有法可依的重要責任。網絡空間應當納入公共空間的范疇,網絡謠言式尋釁滋事也應當受到應有的懲戒。
[1]參見齊愛民:《論網絡空間的特征及其對法律的影響》,《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02期
[2]參見孫鐵成:《計算機網絡的法律問題》,《法學前沿》1999年第3期
[3]參見宋占生主編:《中國公安百科全書》,吉林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40頁
[4]參見唐坤:《網絡謠言犯罪及其司法認定問題研究——以網絡謠言型尋釁滋事罪為視角》,新疆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
[5]參見李曉明:《刑法:“虛擬世界”與“現實社會”的博弈與抉擇——從兩高“網絡誹謗”司法解釋說開去》,《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
[6]參見劉廣三、楊厚瑞:《計算機網絡與犯罪》,《山東公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第2期
[7]參見侯帥:《論罪刑法定原則下網絡犯罪的刑法規制》,《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
[8]參見仝宗錦:《對曲新久教授<一個較為科學合理的刑法解釋>一文的評論》,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 article-151694-58814.shtml,訪問日期2015年12月11日
[9]參見蒙開熙:《網絡尋釁滋事犯罪概念要素解讀》,《湖北警官學院學報》2015年03期
[10]參見張明楷:《簡評近年來的刑事司法解釋》,《清華法學》2014年第1期
[11]參見張雪忠:《一個較為科學合理的刑法解釋?——與曲新久教授商榷》,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aeaff70102eg54.html,訪問日期2015年12月11日
[12]參見 A .R .stone, Will the real body please stand up? Boundary Srories about vitrua1 Culuture , In M.Benedikt(1991):Cyberspace: First steps, Cambridge, MA,Addison-wesley,p.85
[13]參見傅躍建:《論“網絡尋釁滋事”的刑法規制》,《江西警察學院學報》2014年11月第6期
[14]參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三庭:《<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試試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人民司法》2013年第21期
[15]參見趙秉志、彭新林:《尋釁滋事的罪與罰》,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95-97頁
[16]參見程陽強:《新司法解釋下尋釁滋事罪“口袋”的擴張與堅守》,《福建警察學院學報》2014年第5期
[17]參見Stratton——Oakmont v. Prodigy Svcs. Co. (N.Y. Sup. Ct. May 25, 1995)
[18]參見劉延婷:《美國法上的網絡誹謗侵權責任研究》,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07年碩士論文
白加寧,男,漢族,籍貫河北省衡水市,大學本科學歷,單位合明律師事務所,主任,研究方向:民事法律,刑事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