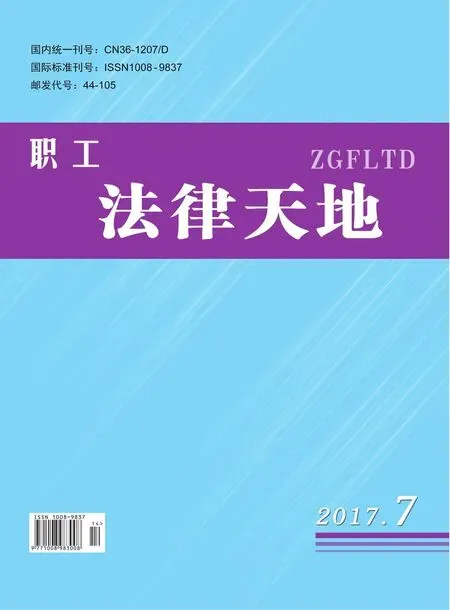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背景下解決行政爭議的思考
咸 慧
(100088 北京鑫萬佳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北京)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背景下解決行政爭議的思考
咸 慧
(100088 北京鑫萬佳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北京)
一、行政爭議的產生根源與解決途徑
(一)行政爭議的產生根源
行政爭議是指“行政機關與相對人之間因行政管理活動而產生的爭議”。[1]行政爭議具有不同于其他爭議的一些特點:產生條件的特定性、爭議主體的特殊性和利益沖突的復雜性等。正確處理行政爭議,就要找到產生爭議的不同根源:
1.經濟利益
行政爭議表面上是代表國家公共利益的行政機關和代表私人利益的公民法人組織,但在現實中行政機關往往不知不覺置身于經濟利益中,即是管理者,又是參與者。
2.地方或部門保護
行政主體從保護自身轄區利益出發而各自為政,從而損害相對人利益而產生行政爭議。
3.“官本位”思想
一些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缺乏服務意識,法律觀念淡薄,同時“大政府,小社會”的觀念,不敢或者不愿意放權于社會,導致各種爭議的產生。
4.法律意識淡薄
缺少依法行政意識,越權行政和濫用權力問題頻發。
(二)我國行政爭議的幾種解決途徑
1.調解制度
雙方當事人以外的第三者,進行疏導、勸說,促使自愿達成協議,解決糾紛。我國調解方式主要是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
2.行政申訴
根據《憲法》第41條的規定,行政相對人能夠申請行政監察機關、審計單位、黨的紀律檢查部門、人民檢察機關等提出申訴。
3.行政信訪
一項極具中國特色的制度,人民群眾通過信訪渠道來反映自己的要求和意見。
4.行政復議
行政相對人向上一級領導行政機關提出申請對行政爭議進行復查。
5.行政訴訟
行政相對人針對行政爭議向審判機關提起訴訟,由人民法院作出裁判的訴訟。
以上是解決行政爭議的不同方式,各具特點、各有側重。調解制度快捷靈活,便民高效;行政申訴與行政信訪在實踐中采用較廣,形式多樣;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的范圍則有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的限制,處理起來較為復雜和規范。
二、基于解決行政爭議的新《行政訴訟法》
(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略布局下修訂《行政訴訟法》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是首個關于加強法治建設的專門決定,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必須全面推進依法行政。
《行政訴訟法》自1990年10月1日正式施行以來,在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國家法治建設步伐的加快,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以及法律維權意識的增強,原有的《行政訴訟法》遠遠不能適應國家民主建設和法治建設的要求,出現了“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等問題,實踐中出現大量針對行政機關的信訪案件。
為此,新的《行政訴訟法》在第一條就增加了立法目的——“解決行政爭議”,這是非常重要的一處修改,強化了通過行政訴訟解決行政糾紛的作用,以法治的方式解決行政爭議。按照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精神,將解決行政爭議納入法條,作為《行政訴訟法》立法目的,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
(二)以解決行政爭議為立法目的的修改亮點
第一,針對“立案難”問題,由審查立案改為登記立案。“立案登記制”實際上降低了立案門檻。
第二,將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由“具體行政行為”擴大為“行政行為”。
第三,新法將原“人身權、財產權”擴大為“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
第四,重新定位復議機關在“解決行政爭議”時發揮的重要作用。過去復議機關為了避免成為被告,普遍做出維持原有決定。新法在第二十六條規定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行政行為的,復議機關和行政機關將成為共同被告。該規定能夠促進復議機關對案件進行大膽如實裁決。
縱觀新法全文,《行政訴訟法》的各項修改實際上均圍繞著“解決行政爭議”這一立法目的展開,不僅僅關注“案結”,更追求“事了”,是依法治國方略在行政領域的落地,真正惠及廣大民眾。
三、完善解決行政爭議機制的探討
(一)建立健全行政機關負責人參訴制度
新的《行政訴訟法》第三條規定了,“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相比于舊法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說明行政機關負責人有出庭應訴的法定義務。
強制行政機關出庭應訴只是推進依法行政邁出的第一步,履行出庭義務的同時更要認真做好答辯、舉證等準備工作,真正意義在于解決行政爭議,而不是為了“做秀”,需要各級政府切實建立健全參訴制度。
第一,將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制度納入領導干部學法內容,促使領導干部認真學習法律知識,深化依法行政意識,提高決策水平。
第二,當地政府要建立和完善依法行政考核體系。人民法院可以通過司法建議、白皮書等形式向行政機關做出評價,并以適當方式向社會公布,發揮考核指標的倒逼作用。
第三,加強政府法制機構和部門法規人員隊伍建設,積極探索行政應訴人員資格職業化和聘任新方式。
(二)擴大行政調解范圍、善用行政訴訟和解制度
在實踐中,行政糾紛多樣性的現實導致經常有“出判決但不解決糾紛”的兩難局面,因此法院有必要發展多樣性的行政案件解決機制。通過行政訴訟調解的方式來處理行政爭議,往往可以兼顧到情、理、法各個方面。
令人稍顯遺憾的是,新的《行政訴訟法》第六十條堅持了舊法的原則,并不主張調解,僅在但書條款規定了幾項例外[2]。筆者對此有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修訂一個專業性較強的調解法。現有涉及行政調解的法條分布散亂,有必要通過專門立法對調解制度進行規范和統一。
第二,擴大行政訴訟調解制度適用的范圍。雖然新的《行政訴訟法》定義了調解使用范圍,但實踐過程中仍有很多不屬于此范圍的案件以調解途徑結案。既然如此,何不針對客觀實際情況,研究擴大調解適用范圍。
第三,善用行政訴訟和解制度。過去理論認為,行政機關依法履行職責,只存在合法與違法的區別,不存在協調和解的法理基礎。但實際上協調和解制度對于穩妥化解行政糾紛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行政機關在法律框架內可選擇更柔性的方式。不過對于和解制度要會用善用,嚴禁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損害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1]齊樹潔.《程序正義與司法改革》,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25頁.
[2]新修訂的《行政訴訟法》第60條規定:“行政賠償、補償以及行政機關行使法律、法規規定的自由裁量權的案件可以調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