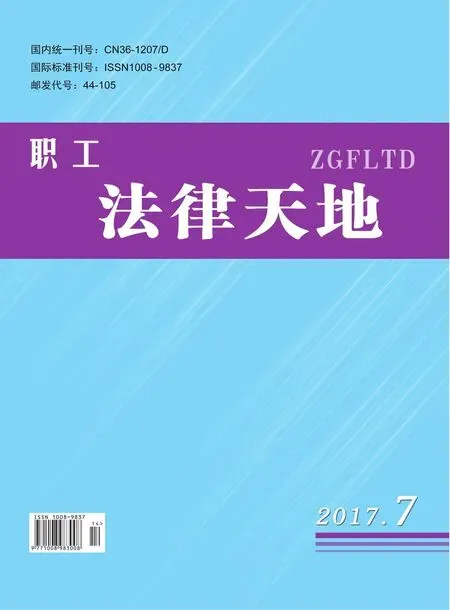胎兒利益民法保護初探
張進科 劉一梅 楊 蕾 劉南南
(071000 中央司法警官學院研究生教育部 河北 保定)
胎兒利益民法保護初探
張進科 劉一梅 楊 蕾 劉南南
(071000 中央司法警官學院研究生教育部 河北 保定)
根據“民事權利能力始于出生,終于死亡”的民法理論,胎兒在出生前并不具有權利能力,不能成為民事主體。但是,民法總則規定,胎兒在贈與、受遺贈等法律關系中作為受贈以及受遺贈的一方時,賦予胎兒民事主體資格。但是這樣的民法規定并不能滿足現條件下對胎兒利益的保護。胎兒作為生命的最初階段,如果其利益不能夠得到全面周到的保護,勢必影響出生后自然人的利益。
胎兒,民法,利益保護
一、賦予胎兒民事權利能力的生物學基礎
生命是人一切活動的基礎,如果沒有生命,人將不能稱其為人,也才有了生命,人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智力的增長,人在社會中才能為不同的行為,享有不同的權利,承擔不同的義務。但是,人的生命又是從何時才有的呢?這是一個值得探討問題,一般學說認為,胎兒不具有生命,人的生命始于出生,只有人出生呱呱墜地出生后,人才有生命,才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也有個別學說從生物學的角度闡述,胎兒具有生命的客觀形式,胎兒以及經過受孕的胚胎,是具有生命形式的,隨著在母體中不斷成長,通常在10個月后,經母體分娩生產,人們不能否認這一客觀事實。筆者認為,對于“人”的生命不能隨意、簡單、刻板、機械的認為以“出生”為起點,對于尚未出生的但具有生命形式的“胎兒”,不能單純的因為某種理論在解決某些問題時采用以出生為界點的暫時性、技術性手段而拒絕承認胎兒為“人”。我們必須明白這一事實,胎兒是嬰兒孕育生長的前提,沒有胎兒在母體中的孕育,就沒有出生后的胎兒,胎兒與嬰兒有生物上的必然聯系,只有保護好胎兒的利益才能保護好嬰兒的利益。
二、立法模式的選擇
在不同的國家,對胎兒利益的保護,有不同的立法例,筆者在搜集相關資料后,發現在大陸法系國家,主要還有一下三種不同的立法模式供我國參考借鑒。
(一)總括的保護主義
《瑞士民法典》第31條第2項規定:“子女,只要其出生時尚生存,出生前即具有權利能力。”總體保護主義在涉及胎兒利益的保護時,視為其已經出生,該學說賦予了胎兒在母體中遭受傷害時,待其出生后享有人身損害賠償請求權。
(二)個別的保護主義
《法國民法典》第725條規定:“尚未受胎者,不得為繼承人。”第906條第1項規定:“為有受生前贈與能力,以于贈與時已受胎為已足。”第1923條規定:“在繼承開始時尚未出生,但已懷孕的胎兒,視為在繼承開始前出生。”第2178條規定:“如果應得饋贈者在繼承開始之時尚未受孕或者其身份要通過在繼承開始之后方才發生的事件確定,則遺贈歸屬在前一情形隨出生、在后一情形隨事件的發生而發生。”該學說認為胎兒原則上無權利能力,但于若干例外情形視為有權利能力。
(三)絕對主義
即絕對否認胎兒具有權利能力。1964年《蘇俄民法典》(第418條)和我國《民法通則》即采用此種立法模式。
盡管我國民法通則中否定了胎兒的權利能力,但是《繼承法》第二十八條“遺產分割時,應當保留胎兒的繼承份額。胎兒出生時是死體的,保留的份額由胎兒的法定繼承人繼承。”該條規定例外的保護了胎兒的財產繼承權利。2017年3月1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其第十六條規定“涉及遺產繼承、接受贈與等胎兒利益保護的,胎兒視為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但是胎兒娩出時為死體的,其民事權利能力自始不存在。”民法總則對胎兒利益的保護依然沒有突破人身權利的保護,僅僅對胎兒純粹受益性的權利予以保護,沒有對胎兒的人身損害賠償請求權進行法律層面的規定。
三、胎兒利益保護面臨的社會問題
隨著對胎兒利益法律保護問題的研究,我國部分學者引出一個問題:胎兒生命權與我國的計劃生育、婦女生育自決權的沖突。對于該問題,筆者認為二者沒有必然聯系,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提倡優生優育,對尚未出生的胎兒進行檢查、篩選,如果發現存在有胎兒先天發育不良,可能產生畸形,會在充分尊重父母的意見下,實現墮胎的合法化,我們可以立法保護墮胎行為,但墮胎必須到合法機構、在合理時間。我們提倡保護胎兒的利益,是在胎兒遭受外部傷害,如父母非法墮胎,父母惡意傷害未出生胎兒,交通肇事,環境污染等等損害胎兒利益的行為或事件,不包含合法墮胎行為。
四、胎兒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行使的設想
侵害胎兒利益,造成損害的應承擔侵權責任。由于胎兒的權利具有特殊性,胎兒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行使,可根據胎兒在遭受傷害后是死體還是活體來區分。一、如果胎兒在遭受外部傷害后,出生后即為死體,我們可以不提倡胎兒的人身死亡賠償請求權,可以由其母親或其監護人以母親遭受身體傷害主張人身損害賠償請求。二、如果胎兒在遭受傷害后,出生后是活體。①胎兒出生后便能確定損害事實,可由胎兒作為原告,其監護人作為法定代理人,向法院主張人身損害賠償請求權。②胎兒出生后,經過長時間后才確定損害事實,并且該傷害直接導致胎兒成為無民事行為能力,可由胎兒作為原告,由他的監護人作為代理人參與訴訟行使原告的人身損害賠償請求權。③胎兒出生后未確定損害事實,待胎兒為成年人后,才確定損害結果,此時胎兒已成為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人,其可以作為獨立的訴訟主體參加訴訟。
在現時學說中,根本不主張胎兒具有人身損害賠償請求權,在實務中,處理方法多為以母親遭受人身傷害為由主張損害賠償請求權,出現的事實是母親權利嚴重擠兌胎兒權利,上述分類建議可以有限的突破現時學說的局限性,適度保護胎兒的人身損害賠償請求權。
[1]鄭玉波.民法總則[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
[2]楊顯濱.論胎兒利益的民事立法保護[J].法學雜志.2011(11)
[3]楊志祥.論胎兒利益的民法保護[J].法學雜志.2010(09)
[4]夏雨.論胎兒的民事主體地位[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02)
[5]何政泉,楊莉.關于胎兒權益保護的法律思考[J].經濟師.2008(03)
[6]覃怡.論胎兒利益的民法保護.法制與社會:旬刊
張進科(1993.11~),男,籍貫:河南省南陽市,單位:中央司法警官學院研究生教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