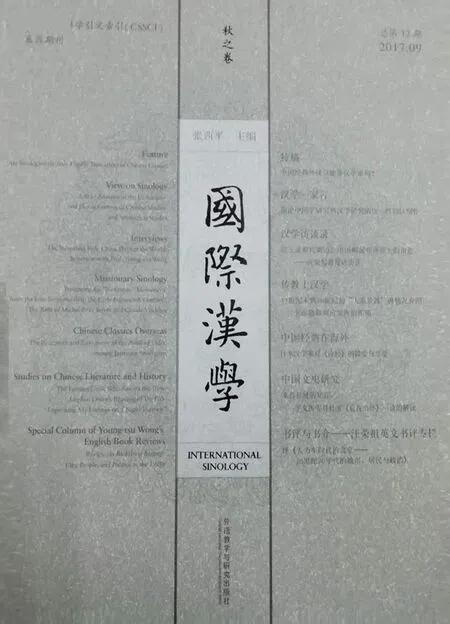編后記:不易初心念故人
□
審讀完《國際漢學》總第12期的稿子,恰逢學期末最后一周。在三年級研究生畢業典禮上,看到從事海外漢學研究的研究生在一個學院就有幾十人,讓人感到欣慰。回想20年前,海外漢學中心(如今更名中國文化研究院)成立之初,教師也不過三四人,更何論研究生。這些年海外漢學(中國學)研究的長足進步,是學術發展的一種內在需要。《國際漢學》能給海內外學術同仁提供一個發表成果的平臺,樂莫大焉,責莫重焉。
《國際漢學》不是一個孤立的雜志編輯部,而是以學術研究隊伍(研究院)、專業圖書館二者為依托。編輯部與研究院同屬一個學術機構,我們的編輯人員,也做翻譯與研究;我們的圖書館,也有極好的漢學資料文獻收藏,例如:倫敦亞非學院所藏的西方早期(1850年以前)出版的關于中國的圖書縮微膠片654種;全世界僅僅重印發行100部的《衛匡國中國新地圖集》(原書于1655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出版);梵蒂岡藏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高清復制件,等等。有這種研究型的編輯隊伍以及一流資料支撐,就形成一個編輯部、研究機構、圖書館三位一體的編輯部格局,這就更好地保證了我們稿件的編輯工作的內在品質。
“國際漢學”如今在人文社科領域已經成為一個“學科”,盡管她是一個“小學科”,她可能屬于歷史系、中文系,或者哲學系、外語系,也就是說,在現行學科體制下,我們可能還找不到她的確切學科定位,但她的研究對象是明確的,這就是外國人對中國歷史、文學、哲學、宗教、藝術等的研究,以及中國人對上述研究的“再研究”。就這兩個方面而言,內容都是極其豐富的。
在上述“漢學研究”的生產過程中,翻譯是一個關鍵所在。中國明代學者徐光啟早在380年前,在向崇禎皇帝的上書中,就提出了“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的觀念。直到今天,翻譯也仍然是漢學研究中的關鍵性環節。本期“特稿”欄目發表了翻譯界泰斗、96歲高齡的許淵沖先生的文章,專門討論翻譯問題,頗具啟發性,但是也可以爭鳴。
許老的文章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就是漢語的豐富表達能力,在這方面,本期文月娥對西方漢學家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的漢語語言觀及其當代價值的討論,頗有借鑒意義,而且更加具體。
當這篇“編后記”就將擱筆的時候,忽然從大洋彼岸傳來著名漢學家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 1919—2017)教授過世的噩耗。訃聞中寫道:“美國東亞思想研究的領導者狄百瑞,于2017年7月14日在紐約塔潘市霍托科多(Hotokudo)的家中平靜去世。當時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教授、教務長約翰·米切爾·梅森在他身邊。狄百瑞在1989年正式退休后繼續教書。雖然由于心臟病使他身體衰弱,但他仍完成了2017年5月的最后一門課程的評分。”①可參閱網站:http://www.legacy.com/obituaries/lohud/obituary.aspx?page=lifestory&pid=186099628,最后訪問時間:2017年7月22日。訃聞的第一段讀起來令人感動,特別是狄百瑞教授以98歲高齡仍然在教學第一線工作,正是中國古語中所說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狄百瑞本來有中文名—狄培理,但1982年香港新亞書院翻譯出版他的著作時,音譯為狄百瑞,當時狄百瑞沒有及時發現,也就沒能及時糾正。此后在中文界就沿用“狄百瑞”這個名字,成了“約定俗成”(這又是一個翻譯的問題)。直至2016年臺灣唐獎頒布時,才又使用“狄培理”一名。
我同狄百瑞教授初識于1981年,那一年秋天在杭州召開“全國宋明理學討論會”,在會議期間,我陪邱漢生先生拜訪他,那時他60多歲,邱先生70歲。邱先生與他討論了黃宗羲和《明儒學案》的問題。那次會議,馮友蘭先生與賀麟先生都參加了。事過20多年,2003年,《世界漢學》的主編劉夢溪先生,曾經通過王海龍先生約請狄百瑞教授寫過一篇大作,題為《中國研究何去何從?》,我當時作為副主編,做了一些具體工作。
現在重讀狄百瑞的那篇大作,有些話語仍然振聾發聵。例如文中說:“學界毫無限制地投注大量心力研究微不足道的題目,我們已見怪不怪。這一風氣每每以‘創新’或‘突破’等陳辭作為自我抬舉的借口。它聲稱眼前的發明或發現空前絕后,殊不知所作所述其實前有來者,甚至只是對前賢的曲解。所謂的‘新’竟可能來自對固有事物的‘新’破壞。”這樣的話,即使是對漢學以外的研究,也值得警醒。
美國漢學家梅維恒
梅維恒(Victor H.Mair),1943年生,著名美國漢學家,哈佛大學中國文學博士,賓夕法尼亞大學亞洲及中東研究系教授,賓大考古及人類學博物館顧問,還擔任京都大學、香港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等多所高校的兼任教職,精通中文、日文、藏文和梵文,被認為是當代西方漢學界最具開拓精神的學人,著述宏豐,研究領域包括:中國語言文學、中古史、敦煌學。他的《唐代變文:佛教對中國白話小說及戲曲產生的貢獻之研究》(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Contribution to the Rise of Vernacular Fiction and Drama in China,1989)、《繪畫與表演:中國的看圖講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Painting and Performance: 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 1988)、《敦煌通俗敘事文學作品》(Tun-huang Popular Narratives,1983)等諸多著作都在中西學界引起了強烈反響。梅維恒教授在中國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進行考古研究,發現了塔克拉瑪干沙漠迄今為止最早的文明遺跡,這個存在于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200年間的文明,為重新理解中國歷史、中西交通、歐亞文化交流史開啟了新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