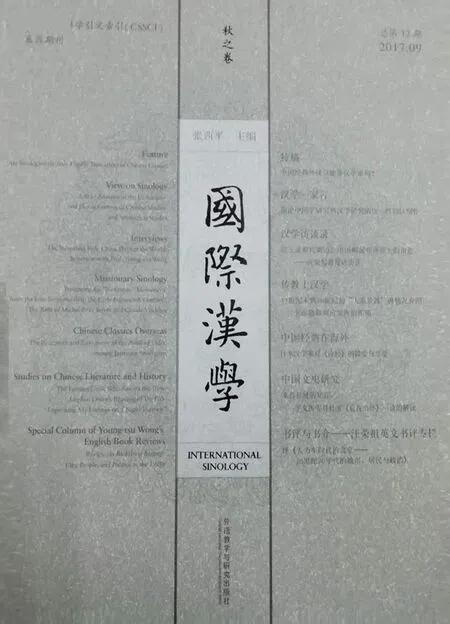18世紀中葉歐洲人構筑的北京印記—《北京志》初探*
□
從晚明開始中國與歐洲關系發展取得重大突破,作為明清帝都的北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中心地位。以耶穌會士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正是當時中西互動中的主體,他們寄回歐洲的信札、報告、日記等,刻畫了一個歷史悠久、文明先進、國家富庶的東方帝國形象,引發18世紀歐洲中國熱潮,奠定了歐洲漢學研究的基礎。傳教士在華生活多年,對中國的風土人情、社會政治、歷史文化等有著獨特而深刻的體認,留下了豐富的中西文文獻,為研究明清史提供了不少寶貴的史料,其中包括不少在京觀察、生活的文獻記錄,成為當時西方世界了解北京的珍貴材料,亦是研究明末清初北京與中西文化交流關系的重要歷史文獻。
16世紀開始,歐洲一些本土學者根據已出版或者未公布的耶穌會士的材料開始撰寫有關中國的作品,或為彌補完善傳教士傳遞的中國知識的不足,或為通過匯編整理來體現自己的學術興趣與認識。特別是隨著法國耶穌會士入華,他們忠實執行路易十四傳教與學術并重的指示,傳教之余也積極開展科學調查活動,越來越多地與歐洲知識界建立直接聯系。在當時通訊條件可能的情況下,歐洲學者與北京耶穌會士之間,在人文科學方面進行了廣泛的學術交流,推進了歐洲對中國的認知廣度與深度,豐富了歐洲的中國知識存量。歐洲本土學術界以各國科學院的介入為代表,不少科學家利用天文地理等學科的進展和來自傳教士的一手資料對中國展開了科學研究。這些本土作品雖然不像早期耶穌會士論著那樣對中華帝國進行全面的整體性描述,但在一些專題性研究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目前學界往往較為重視明清傳教士的中西文獻材料,忽略了同期歐洲學者編撰的一些有關中國的論著,本文遂將關注點轉向1765年在巴黎出版的一部著重介紹北京的著作:Description de laVille de Peking(中譯名:《北京志》)①該書譯名采用費賴之(Louis Pfister),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冊)中的譯名,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701頁。,對18世紀中葉歐洲人記錄的清代北京城市印象及地域文化進行總結和梳理。
一、全書概況
Description de la Ville de Peking(《北京志》)是一部以法文撰寫的專論北京的著作,由時任法國科學院院士約瑟夫—尼古拉·德·利爾(Joseph-Nicolas De l’Isle, 1688—1768)和天文地理學家潘格瑞(Alexandre Guy Pingré, 1711—1796)編撰成書,1765年在巴黎由吉迪(GVIDI)出版社付梓出版。
1.編者簡介
編者之一的德·利爾,法國天文學家。他出身于貴族家庭,父親克勞德·德·利爾(Claude De l’Isle)是一名歷史學家。由于家學淵源,家中兄弟11人日后大多成為了知名學者。德·利爾青少年時期師從著名天文學家J.卡西尼(Jacques Cassini, 1677—1756)②J.卡西尼,是著名天文學家G.D.卡西尼的次子。J.卡西尼接任了父親對巴黎天文臺的領導,繼承父親生前從事的子午線弧長勘測工作。卡西尼家族是天文學界最負盛名的祖孫四代在同一學科領域做出重大貢獻的家族。學習天文學。1714年進入法蘭西科學院,逐步晉升為科學院天文學會會員。1718年,德·利爾成為法蘭西大學教授及魯昂學院院士。1725年,應俄國彼得大帝之邀,遠赴圣彼得堡,主持俄羅斯科學院天文部。在這里他著手組建了圣彼得堡天文臺,開始享譽學界。1747年,德·利爾回到巴黎,獲得了天文學家頭銜,并被獲準建立專屬天文臺。1749年,被選為瑞典皇家學院外籍院士。1768年在巴黎去世。
另一位編者是天文學家與海洋地理學家潘格瑞神父,少時就讀于法國圣會傳教士學校(collège des pères génovéfains),16 歲 入 奧 古 斯 丁 會, 后成為常任議事司鐸。1735年被任命為神學教授。1749年在魯昂學院開始擔任天文學教授。盡管身患眼疾,但潘格瑞擁有驚人的數學運算能力,多次對天文現象進行精確計算,聲名鵲起。他擔任過圣·日內瓦圖書館館長及大學訓導長。多次隨法國海軍出海,進行天文觀測活動,收集了大量天文數據,并記錄了許多島嶼的自然地理狀況。1757年,潘格瑞開始對彗星產生了研究興趣,并于當年發表了關于彗星的觀測歷史和理論的關鍵性論文。1789年,在法國大革命浪潮影響下,思想進步的潘格瑞沖破阻力,將圣·日內瓦圖書館交予國家管理,成為該館最后一位教會任命的館長,以及第一位國家任命的館長。1796年在巴黎逝世。
2.素材來源
德·利爾在《北京志》的前言中明確提到撰寫該書的緣由:他與很多在華的耶穌會士保持了三十多年的書信往來,從中收集整理了大量關于天文學與地理學方面的一手數據,為寫作相關主題的論著積累了豐富的資料。此外,《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的第三任主編帕杜耶神父(P.Patouillet, 1699—1779)③帕杜耶神父,法國耶穌會士,18世紀歐洲漢學名著《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的四任主編之一。他繼第一任主編郭弼恩(Charles Le Gobin, 1653—1708)、第二任主編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之后,編著了《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27—34集。曾建議德·利爾寫一篇關于北京城導覽的文章,包括地圖和詳細說明,并且希望能放入《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Letter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I.recueil,1703—1776)第 29卷里。于是,德·利爾決定與他在海軍天文地理研究任務中的研究同道潘格瑞一起合作,利用現有材料來編寫這樣一部專題作品。
兩位編撰者匯集了當時他們在歐洲所能找到的絕大多數關于“北京”這一主題的西文資料,包括多位在京耶穌會士寄回的材料,以及其他做過類似研究的歐洲學者的著述,非常詳實地介紹和描述了當時的北京城。書中所使用的主要素材來源包括以下幾類:
(1)德·利爾與在中國和印度的耶穌會士的通信
(2)宋君榮神父(Antoine Gaubil, 1689—1759)1752年8月4日寫給德·利爾的信,特別介紹了北京的內城
(3)宋君榮神父1755年寫給英國皇家學會(La Sociéte Royale d’Angleterre)的信,有北京地圖及20多頁說明,翻譯成英文并于1758年在《哲學雜志》(Transaction Philosophique)第50卷發表,有所增補
(4)來自圣·日內瓦圖書館的相關資料
(5)德·利爾私人收藏的有關中國主題的資料
(6)德·利爾轉讓給國王圖書館的相關藏書
(7)海軍部檔案中的平面圖、地圖與航海日志
(8)德·利爾個人文集中的幾份手稿及天文觀測資料
其中,該書資料最主要的提供者是法國耶穌會士宋君榮(Antoine Gaubil, 1689—1759)。他自1722年入華,長期在北京生活,經歷了康雍乾三朝,深得幾代帝王的信任,在清廷擔任要職。宋君榮學識淵博,精通漢文、滿文,同時在物理、天文、地理、歷史、科學等方面皆有所成,著作等身。他與歐洲各國的著名學者都保持頻繁的通信,如巴黎天文臺的J.卡西尼、法國科學院院士德·利爾、德國學者巴耶(T.S.Bayer, 1694—1738)、英國皇家學會秘書摩爾底曼爾博士(Dr.Cromwell Mortimer, 1693—1752)等。由于在科學方面特別是天文學上的杰出成就,宋君榮后來被法國科學院、考古學會等接納為通訊院士,并成為彼得堡皇家學會、英國皇家學會的會員。德國著名的博物學家、自然科學家亞歷山大·洪堡(Alexandre von Humboldt, 1769—1859)稱贊他是“耶穌會傳教士中最杰出的學者”。①費賴之,梅乘騏、梅承駿譯:《明清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1997年,第806頁。法國第一位專業漢學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 1788—1832)也認為“宋君榮神父無疑是西歐人士中對中國文學之研究具有極深造詣者,至少他在運用方面是貢獻最大,涉及的領域最廣泛的一位”。②同上。
宋君榮利用了天文學方法和歐洲寄來的天文儀器對北京的經度緯度進行了測量,得到了較為精準的數據;由于他在京居住多年,交游甚廣,深得皇帝信任,享有出入宮廷的特權,因此觀察和記述當時北京城包括皇宮及周邊建筑的整體情況具有相當可靠性。據德·利爾在前言里所說,書中所依據的北京地圖及說明材料源自宋君榮神父于1752年8月4日寄給他的一封長信,但雷慕沙對此說有異議,他在《亞洲新雜纂》(Mélanges Asiatiques, 1825)第二卷(第288頁)撰文認為該書原稿是宋君榮寄給圣彼得堡科學院的,德·利爾不過是在僑居圣彼得堡期間謄抄了宋君榮的手稿而已,“此志原文及附圖,乃經君榮寄贈與圣彼得堡研究院者,里斯爾(即本文所言德·利爾)在俄京抄寫一本,得以刊行”。③《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冊),第701頁。同時參閱《明清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第824頁。由于還未有新的佐證,因此關于宋君榮《北京志》手稿之去向的兩種說法尚不能斷言。
3.主要內容
1765年出版的這本京城導覽圖解收錄了多幅由在華耶穌會士繪制的北京城圖,不僅提供了北京的地理位置、城市格局、重要建筑等具象信息,同時在解說部分也匯聚了不少與北京相關的人文歷史等知識,并充分利用了多名天文學家提供的天文數據來確定北京的經緯度,可以說是18世紀西方研究北京城市比較權威的作品,再現了當時中國首都的全景,推動了當時西方對北京的認識。該書于1765年在巴黎出版后又被譯為英文、俄文、德文在歐洲其他國家出版。
《北京志》共分為七章,包括(一)北京城的建立;(二)北京城概況;(三)北京內城詳情;(四)北京的外城及郊區;(五)某些地區的重點介紹;(六)對中國長度“里”的討論;(七)北京的經度與緯度。書后附了六幅地圖,包括北京內城、外城、帝王廟、國子監、天壇、地壇等,對我們了解當時北京城市布局和重要建筑具有很高的史料參考價值。
詳細目錄如下:
一、北京城的建立
二、北京城概況
三、北京內城詳情
(1) 紫禁城
(2) 皇城
(3) 京城
四、北京的外城與郊區
五、某些地區的重點介紹
(1)番經廠
(2)帝王廟
(3)國子監文廟
(4)天壇
(5)地壇
六、對中國長度“里”的討論
七、北京的經度與緯度
二、書中所錄北京概況
《北京志》利用當時的天文觀測數據,以及傳教士實地考察的記錄,對北京進行了多角度的介紹,圖文并茂,生動詳實,這些歷史記錄與科學論證真實再現了三百多年前北京城的地理、歷史等自然人文特征和城市建設等情況。下文擇其一二以饗讀者。
1.地理
文中開篇談了中國的首都北京位于帝國最北部的省份,距離著名的萬里長城僅有10到12法里。①法國古長度單位,一法里等于4.445公里。北京所在的行省被稱為“直隸”(Tche-Li)或者“北直隸”(Pe-che-li)。②從明朝開始,稱直接隸屬于京師的地區為直隸。明朝洪武初年建都南京(后改稱京師,永樂初年復改南京),以應天府等府為直隸。直隸于南京的地區被稱為南直隸,簡稱南直,相當于今天江蘇、安徽、上海兩省一市。清朝初年將南直隸改稱江南省。永樂初年移都北京后,又將隸屬于北京的地區稱為北直隸,順治二年(1645)改稱直隸,康熙八年(1669)稱直隸省,定省治保定府,相當于今天北京、天津兩市、河北省大部和河南、山東的小部地區。這一省份緊鄰北方韃靼聚居地,因此在軍事上具有戰略意義。為了抵御外族入侵,多個朝代均選址北京建都。北京由新城和老城兩個部分構成,其中老城是明朝嘉靖年間擴建出去的外城,即漢人聚居地,也叫漢城;新城即北邊滿人聚居地,也稱韃靼城,或京城。此外,城外還有12個近郊小鎮,它們與韃靼城和漢城一起構成了一座龐大的北京城。③Joseph-Nicolas De l’Isle , Alexandre Guy Pingré, Description de la Ville de Peking.Paris: Gdivi, 1765, p.2.
北京氣候溫和,人口眾多,經濟富庶。書中特別提到北京干旱少雨的氣候特征,一年中很少下雨,比較干燥。冬季河流有四個月左右的冰封期,但又不像歐洲那樣極端寒冷。土壤以沙質為主,不如南方地區肥沃。一條發源于北京城外西北部山區的小河,從北面流入京城,在城內又分為數條支流,環繞著宮城,形成數個人工湖泊,之后流入南面的漢城,匯聚為一條暗河,在北京城東的通州匯入白河。④Ibid..這一地理特征在侯仁之先生的《北平歷史地理》一書中也有類似的記載,他認為北平城區建于(1)向大平原的開口處,(2)渾河和白河兩河之間,其中“白河從北平灣的北端流入平原,并將北平灣中心地區一分為二。灣內西面所有的小河流匯成溫榆河,在通縣以北流入白河”。⑤侯仁之:《北平歷史地理》,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4年,第5頁。
除了地形、地貌、氣候等地理特征外,書中最后一章專門介紹了法國本土科學家如何利用各種數據反復測算、比對、確定北京經度與緯度的過程。⑥l’Isle, op.cit., pp.38—44.他們的考察首先基于中國古代天文資料記載的日晷的陰影長度來進行測算黃赤交角,特別是利用了宋君榮神父提供的元代著名天文學家郭守敬留下的六組日影觀測數據。由于中國古代測量儀器的局限,這些數據有一定的誤差,因此第二步就需要收集驗算多位傳教士在北京實地記錄的各類觀測數據,包括正南方太陽的高度、天狼星的高度、南北方星辰高度,以及木星的多個衛星出沒、日食與月食、水星凌日等天文現象。為了獲得更為精準的測量結果,法國科學院還專門給在京的傳教士寄去了比較先進的天文儀器象限儀襄助他們的天文研究工作。第三步,他們將這些在北京記錄的天文現象與歐洲取得的觀測結果逐一進行比較,包括比對同一日期在北京、巴黎、圣彼得堡和法屬昌德納戈爾四地的觀測數據;比對北京與巴黎相差兩到三天的階段性觀測數據;編訂各地關于木星一號衛星活動大事記的材料進行綜合測算勘誤等工作。①書中提到的所收集觀測木星衛星活動的地點有北京、巴黎、圣彼得堡、里斯本、萬斯泰德(英國英格蘭東南部埃塞克斯附近)、昌德納戈爾(法屬孟加拉)、英戈爾施塔特(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州南部城市)、烏普薩拉(瑞典中部城市)、斯德哥爾摩等地。這些看似繁瑣但卻具有高度科學責任感的細致工作對于歐洲科學界準確界定北京的實際地理位置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德·利爾和潘格瑞以位于北京城的法國耶穌會士住所為坐標,最后測算出該地的緯度是北緯39度55分15秒;如果以巴黎皇家天文臺為參照點,北京的經度與巴黎的子午線相差7小時36分23秒②書中只給出了北京與巴黎之間的經度差數值,沒有明確寫明北京的經度。。他們對這一結果具有相當的自信。如果我們去查閱同期其他歐洲人的材料,1693年11月來北京的俄羅斯使團成員也在自己的日記中記載了北京的地理位置為北緯39度59分,另一成員測定的是緯度40度,經度144度。③伊茲勃蘭特·伊臺斯,亞當·勃蘭特:《俄國使團使華筆記(1692—1695)》,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235頁—轉引自葉柏川《17—18世紀俄國來華使臣眼中的北京城》,《歷史檔案》2014年第4期,第81—88頁。現在,北京在世界上的位置是以天安門作為地理的標準坐標的,位于北緯39度54分27秒,東經116度23分17秒,與巴黎的時差為7小時。由此可見,基于大量觀測數據和嚴密的科學測算,1765年出版的《北京志》中所得出的北京經緯度已經比前人進步了許多,在同時代具有很高的科學性和權威性,與今天的數據也只有極小的誤差。
2.建城史
書中開篇回溯了從西周開始一直到清朝三千多年北京的建城史,并以此為主線對中國的歷朝歷代也展開介紹,為西方人展開了一幅遠長于基督教歷史的浩瀚的中國歷史長卷。
書中根據中國歷史的沿革對北京曾使用的主要名稱的演變進行了介紹,從燕城、燕京、順天府、大都、汗八里,到現今的名稱“北京”。
下表是依據《北京志》中的敘述所總結的北京歷史沿革④此表系筆者根據《北京志》第一章所述北京歷史整理而來,所輯的朝代更迭的重大事件及北京城市的名稱依據原書注音轉譯而來,與中國史書有一定出入,特此說明。:

王朝或時期 城市 重要政治事件周燕國國都 武王封召公燕秦燕國國都 秦始皇滅燕漢⑤ 燕⑥ 分封為諸侯國五胡十六國 鮮卑、匈奴、拓跋人先后占領燕地南北朝 中國分裂隋隋統一中國唐唐繼承大一統局面五代十國 契丹入侵北直隸,后晉割讓燕云十六州遼(契丹) 燕京 設為契丹陪都宋北宋與完顏阿骨打結盟滅遼金燕京 金占領北直隸與陜西,宋徽宗被俘,建都北京,后遷都開封

(續上表)
《北京志》中提到公元前1111年,周朝第一個君主周武王建國后,封其弟弟召公于北燕為燕王。召公在距離北京城西南二至三法里的地方建城。①l’Isle, op.cit., p.2.這段敘述中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其中有與中國史實不符的地方,也有能與當代考古成果印證的內容。第一是明顯有誤之處:召公奭并非周武王的兄弟,而是周初重臣三公(周公旦、召公奭、姜太公)之一,地位十分顯赫。第二是燕建國時間與中國史料不吻合:“公元前1111年武王封召公于燕” ,②Ibid..這個時間點在書中沒有任何注解,故不知其出處所在,但可以明確這一時間是不準確的。據《史記》記載,周武王十一年滅紂,同年封召公奭于北燕。武王十一年合公歷是哪一年?根據現在考古學的發現,1976年,陜西臨潼零口出土的利簋(一件青銅器)的銘文記載,武王克商時有天上哈雷彗星出現,這是一個重要的依據。天文學家依據銘中所記“甲子”日“歲星”(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參照《國語·周語下》記載的天象記錄,計算出這一時間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早晨。故“夏商周斷代工程”根據天文推算、文獻、金文歷的綜合研究,基本確定了公元前1046年為武王克商年,也就是西周封燕之年。第三,書中提到燕的始封地在北京城西南二三法里,也就是距離市區9到14公里左右,這個位置大致可與當代考古的成果遙相呼應。1962年夏,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的鄒衡先生在房山區劉李店、黃土坡、董家林村一帶進行調查并進行考古挖掘,初步認為燕國的始封地極有可能就在琉璃河。琉璃河遺址所在的房山區恰好就在北京西南,距離市區約22公里。后來在琉璃河遺址出土了兩件青銅器,兩件器物上發現了同為43字的銘文,而文字的內容也成為確定北京建城的直接依據。銘文的大意是—周王說:“太保,你用盟誓和清酒來供你的君王。我非常滿意你的供享,令你的兒子‘克’做燕國的君侯,管理和使用那里的人民。克到達燕地,接收了土地和管理機構,為了紀念此事做了這件寶貴的器物。”根據銘文,這兩件青銅器被命名為“克罍”和“克盉”。從銘文中可以肯定的是:琉璃河遺址是西周燕國的始封地,也就是文獻中的“燕”。
3.圖說北京城
1644年,清軍入關后攻占北京,將北京立為清朝都城。原來內城及皇城里面的眾多府邸,均為進京人數龐大的滿洲征服者所用。③王先謙:《東華錄》,順治元年(1644)六月、十月詔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四年后,清政府又頒布了新的法令,規定所有漢人,無論職業,一律遷至外城,內城專為滿洲人使用。④同上,順治五年(1648)八月詔書。內城劃為八旗駐地,并實行“滿漢分治”,滿人住內城,漢民住外城。因此,在同時代西方人關于北京的記錄和文獻中就出現了“韃靼城”和“漢城”的說法。
如《北京志》將北京城分為韃靼城和漢城兩個部分加以解說。書中提示說新城是韃靼人居住的地方,老城是原來的居民漢人居住的地方,新城在北,舊城在南。新城南面和舊城北邊相接。⑤l’Isle, op.cit., p.7.由于當時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均生活在韃靼城,對內城的了解最為翔實,提供給法國科學院的資料也更詳細,書中按紫禁城、皇城、京城從里到外的順序依次進行了詳細介紹。同時也提到在京的外國人沒有機會對漢城做詳細的調查和勘測,因此書中略過整體布局,只重點介紹了坐落其中的幾個大的建筑群。
中國皇帝曾命人繪制北京地圖,后來嚴嘉樂(Charles Slaviczek, 1678—1735)①嚴嘉樂,波西米亞人,1716年入華,精通算術和音樂,對機械技藝也頗有造詣。康熙曾說:“待一兼通歷算、音律之人久矣,今得汝,朕心甚歡。”曾作《北京內外城圖說》,德·利爾在《北京志》中使用其材料。參閱《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669—670頁。和宋君榮等幾位耶穌會士分別作了幾張摹本寄回法國。德·利爾和潘格瑞編撰《北京志》時參考了當時傳教士寄回科學院的三張地圖。書中附錄的第一張地圖:《北京兩城總覽圖》由天文學家梅西耶(M.Messier,1730—1817)②梅西耶,法國著名天文學家,被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稱為“彗星偵探”。成就主要集中在天文觀測領域。他一共發現了近10顆彗星和100多顆云霧狀天體。以宋君榮神父的地圖為底本進行繪制,除了原有編號外,還加入了重要地點。該圖把北京城內的一個坐標點:法國耶穌會士的住所北堂作為0°經線,即中央經線,以秒為單位,向東分列了16格經差,向西分列了10格經差;同時以北緯39度為緯度基點,向北分列了8格緯度差,向南分列了15格緯度差。在此基礎上,圖上標注了幾個重要的建筑坐標,韃靼城(即內城)里有法國耶穌會士住所(北堂)、圣約瑟夫堂(東堂)、葡萄牙耶穌會學校、皇家天文臺(古觀象臺)、鐘樓、鼓樓;漢城(即外城)有先農壇、天壇和一座佛塔。圖中還清晰標注了北京城的16道城門,九門在韃靼城,七門在漢城。如果去查閱17世紀在京的幾位耶穌會士如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 湯 若 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ens,1609—1677)等人的記載以及荷蘭訪華使團成員約翰·尼霍夫(John Nieuhoff,1618—1672)的《荷使初訪中國記》(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中也一致提及北京內城有九門,三座在南,其余諸邊各兩門。這些材料均對《北京志》的記述予以了證實。另據中國史料記載,明清北京內城共辟九門,東、西、北三面各二門,獨南面為三門。外城為七門,南面三門,東面一門,西面一門,另在東北隅和西北隅的“凸”字兩肩處開有二門。這和書中所言韃靼城九門、漢城七門,以及兩城總覽圖上的標識是完全吻合的。
《北京兩城總覽圖》對16道城門標注了中文名稱,清晰可見,文中對這16道門的名稱及釋義如下:

地圖標號 城門名稱 釋義前門(正陽門)直接對著太陽的門41 宣武門 戰功顯著的軍人之門42 崇文門 令人尊敬的文人之門43 朝陽門44 東直門 直通東方之門45韃靼城(新城)1韃靼城(新城)安定門 長久和平之門46 德勝門 勝利之門或尚武精神之門47 西直門 直通西方之門48 阜成門95永定門 永遠安定之門96 左安門 左邊的安定之門94 右安門 右邊的安定之門93 廣渠門 寬廣的水渠之門92 廣寧門 廣大安寧之門91 東便門 東邊的假門或東邊的彎曲之門90 西便門 西邊的假門或西邊的彎曲之門漢城(舊城)
據德·利爾介紹說書中附錄的第二幅地圖《北京韃靼城平面圖》主要參考了宋君榮神父寄回的地圖資料,以及他發表在《哲學會刊》(Transaction Philosophique)1758年第50卷的后續補充材料,此外還包括其他傳教士撰寫的有關北京主題的著作。這幅地圖也帶有經緯線和地圖的標尺。
書中提到了韃靼城(內城)從里到外由三部分構成:宮城(即紫禁城)、皇城和京城。紫禁城有高大堅固的城墻,長約六里,墻外有護城河。東南西北四面各有一座城門,城門上建有城樓,城墻四個角有精美的角樓。③l’Isle, op.cit., pp.12—13.
在法國編撰者的筆下,北京皇城以紫禁城中軸線為核心,分布的大小不一、錯落有致的門樓、殿閣、廣場和花園組群,既不斷變化,同時又和諧統一,氣勢雄偉,華麗壯觀,美倫美奐,不僅體現出中國古代建筑藝術的獨特傳統和風格,也是中國古代美學在建筑中深刻而完美的體現。書中以地圖為參照,向歐洲讀者逐一描述了中國皇城中軸線上從南往北排列的二十座重要的建筑:大清門、(天安門)①明朝時稱為“承天門”,順治八年改為天安門。《北京志》中只對天安門進行了描述,但沒有給出具體的名稱。、端門、午門、太和門②明朝時原名為奉天門,后在嘉靖年間改為大朝門,又改為皇極門,清代稱太和門。、太和殿、建極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門、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御花園、神武門、南上門、萬歲門、北上門③此門應當是景山外墻的北門“北中門”,正對著地安門內大街。(清)張廷玉等編《明史》卷68·志第44 /武英殿本:“皇城內宮城外,凡十有二門:曰東上門、東上北門、東上南門、東中門、西上門、西上北門、西上南門、西中門、北上門、北上東門、北上西門、北中門。”、壽皇殿、北安門。④此處沿用了明朝舊名,“北安門”是明朝時候的名字,清順治九年已改名為地安門。
在介紹北京皇城布局,特別是皇宮建筑的名稱時,筆者通過考證發現該書較多地參考了葡萄牙傳教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es, 1609—1677)的《中國新史》⑤該書是17世紀歐洲漢學名著,其重要特點是作者安文思對當時的北京城進行了非常翔實的介紹和描述,被稱為是第一部西文的北京地方志。(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 1688)中描述的材料,建筑大部分名稱可以跟現在紫禁城的宮殿名稱一一對應,但是其中也有幾處以訛傳訛的地方。現舉例一二予以說明。
其一,《北京志》中提及紫禁城外朝有幾個著名的宮殿,包括太和殿、建極殿、中和殿和保和殿。眾所周知,三大殿分別為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令人奇怪的是書中竟然多加了一個建極殿,原文名稱為“la sale très-élevée”,直譯為“極高的宮殿”。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筆者查閱相關資料發現,據明史記載,三大殿原名為奉天、華蓋和謹身,“奉天殿之后曰華蓋殿,又后曰謹身殿。四十一年更名奉天殿曰皇極,華蓋殿曰中極,謹身殿曰建極”。到了清代,這三殿更名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根據故宮博物院提供的資料可知,“中極殿”舊名華蓋,即后來的中和殿(順治二年改);保和殿位于中和殿后,建于永樂十八年(1420),初名為謹身殿,嘉靖時期遭遇火災焚毀,重修后更名為建極殿,清順治二年又改稱保和殿。在《日下舊聞考》中也說“(臣等謹按)明之華蓋殿即中極,今建為中和殿,謹身殿即建極殿,今建為保和殿。”⑥(清)于敏中撰:《欽定日下舊聞考》,卷34,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18頁。也就是說建極殿和保和殿實為同一殿在不同時期的名稱。如果說均采用舊名,那么這三殿的順序應是“皇極殿、中極殿、建極殿”;如果全用新名,那則應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筆者注意到葡萄牙耶穌會士安文思在其代表作《中國新志》中有同樣的記載順序:進入太和門后,有四個宮殿,分別是“皇極殿”“建極殿”“中極殿”“保和殿”。這顯然有誤。由于明清政權更替,殿名也經歷更改,安文思在寫作中有可能把外朝三大殿的新舊名稱和前后順序記混了,并且還平白多出了一個殿,其實《中國新志》中所說在“中極殿”前面的“建極殿”實際與第三殿:“保和殿”應是同一殿。從這一點來看,《北京志》編者在匯編材料時,明顯參考了安文思對皇城的介紹,甚至未經考證就直接沿用了這一錯誤的表述。
其二,書中提到的“南上門”這個建筑名稱也與安文思《中國新志》中的說法一致,如對照中國史料,可見又犯了一個錯誤。景山原來四周環繞著雙重圍墻。兩重圍墻間的道路為“御道”。現在外墻已拆除,御道擴建成了馬路。清代史料中說“神武門之北過橋為景山,山前為北上門,東門曰山左里門,西門曰山右里門,門內為景山門。入門為綺望樓,樓后即景山,有峰五。”⑦《欽定日下舊聞考》,卷19·國朝宮室,第259頁。故可知景山原有外墻的正門應叫做“北上門”,由于在此門的北面,已有“鎮山”之故,因風水原因,不能朝山開門,故雖曰“北上門”但依然南向開門。在《日下舊聞考》中還另有一處明確記載“萬歲門,再南曰北上門,左曰北上東門,右曰北上西門。西可望乾明門,東可望御馬監也。再南過北上門,則玄武門”。①《欽定日下舊聞考》,卷35·宮室明三,第549頁。安文思估計因景山此門位于南向,在外墻另有北門,便認為此門叫“南上門”,北門叫“北上門”,出現了名稱上的偏誤。《北京志》也照搬了這種錯誤的說法。
由此看來,雖然《北京志》綜合當時傳教士寄回的資料,對明清皇宮進行了相當詳盡的介紹,但是由于身處歐洲的兩位編者直接采信了傳教士的材料,缺乏實地考察知識,同時由于語言和條件所限無法與中國史料進行對比佐證,犯了一些常識性的錯誤,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結語
在華傳教士不受中國傳統史家的約束,無須隱晦自己的觀點;加之記載多以西方語言寫成,有些內容從向上級的報告轉化而來,因此比較忠實地記錄了在華的生活。以在京的耶穌會士為例,他們出入宮廷,結交權貴,不僅掌握了很多第一手的資料,親歷了所描述的史實,而且多為飽學之士,具有深厚的西方科學素養,從他們的視角看北京,多有中國史料不具備的內容和角度,頗有特色。因此他們所撰有關北京的著述,對北京的記錄與描摹還是較準確的,留下了當時西方人觀察北京的親歷經驗,對考察明末清初的北京形象提供了在中文文獻中不易見到的另一面,為研究北京史和北京地方志補充了重要的西文資料。
當他們的一手材料傳回歐洲之后,又被歐洲學術界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裁剪和利用,成為歐洲本土創作有關中國主題著作的素材來源。這些學者的作品在內容上除了借鑒歐洲當時新的人文科學研究成果對中國元素加以提煉和深化之外,從風格上看依然留存有傳教士漢學著作的一些特點,即“它們在提供許多新鮮事物的同時,表現得多少有點像游記一般”。②維吉爾·畢諾(Virgile Pinot)著,耿昇譯:《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163頁。這些歐洲本土編撰的作品保留了傳教士漢學作品那種“親眼所見事實”③同上,第179頁。的特征,避免使用晦澀的文筆和生硬的內容,喜歡轉述傳教區耶穌會士的直接記述,記述和評論都很樸實無華,這也是為了迎合18世紀上半葉特別喜歡游記的歐洲讀者的興趣。
通過對《北京志》這部作品中有關北京城的記錄所做的初步研究,可以發現該書主體內容簡明扼要,重點突出,描寫翔實,資料豐富;文中通過和前人及同輩類似作品的比較論證,同時借助傳教士實地調查的材料和天文觀測的科學數據,對某些定論進行了糾錯,得出了比較令人信服的結論,增強了作品的研究性和學術性。這些樸實無華但又涵蓋豐富信息的文字,試圖復原出當時泱泱天朝的帝都京城,將一個直觀、具體的北京城展示給歐洲,影響到了當時歐洲人的北京印象的形成。書中提供的相當完整和精確的北京城圖,采用了當時比較科學和先進的繪圖技術,留存了18世紀中期北京的自然地理、經濟地理、政治地理和人文地理方面的記載,承載了大量自然、社會和人文信息,對研究北京的歷史、地理、文化、民俗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作用,也是研究200多年前北京城市建筑布局與城市發展的珍貴西文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