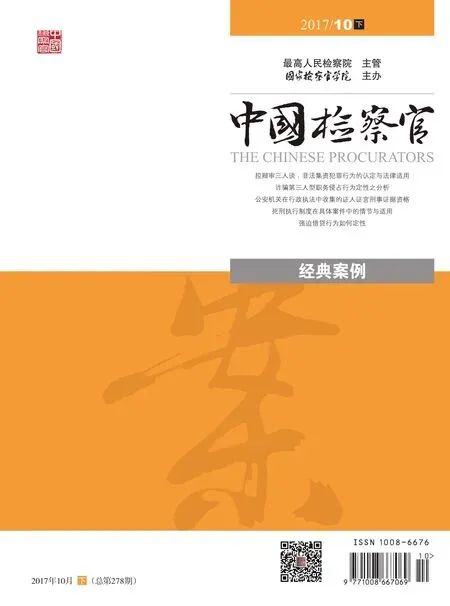特定情境下無過當(dāng)防衛(wèi)的司法認(rèn)定
——兼評(píng)田仁信故意殺人案
文◎韓 笑
特定情境下無過當(dāng)防衛(wèi)的司法認(rèn)定
——兼評(píng)田仁信故意殺人案
文◎韓 笑*
《刑法》第20條第3款是立法確認(rèn)無過當(dāng)防衛(wèi)權(quán)適用的一般規(guī)范性準(zhǔn)則,由于現(xiàn)實(shí)情況的復(fù)雜性使得司法認(rèn)定往往超出傳統(tǒng)的立法標(biāo)準(zhǔn),特殊情境下對(duì)無過當(dāng)防衛(wèi)行為的裁判時(shí)常陷入兩難:即使符合法律適用的經(jīng)驗(yàn)邏輯也不被公眾在情感上接受。在法理與情理的沖突下,嚴(yán)格遵循證據(jù)裁判規(guī)則與司法的理性邏輯,能動(dòng)地從當(dāng)事人角度判斷防衛(wèi)時(shí)的危險(xiǎn)程度是貫徹正當(dāng)防衛(wèi)權(quán)立法本意、鼓勵(lì)私人在危險(xiǎn)緊急時(shí)自衛(wèi)自救的應(yīng)有態(tài)度。
無過當(dāng)防衛(wèi) 司法認(rèn)定 法理與情理
[基本案情]2006年2月份開始,被告人田仁信與妻子羅某在浙江省瑞安市塘下鎮(zhèn)金太陽汽車裝修服務(wù)部上班,并被安排在塘下鎮(zhèn)天穎西路后的員工宿舍三樓,與同事張某(被害人)同居一室。同年3月18日凌晨,被告人田仁信從外面回到宿舍見房間未開燈,房門緊閉,便爬窗進(jìn)入,發(fā)現(xiàn)張某對(duì)羅某進(jìn)行性侵犯,遂與其發(fā)生扭打,后持菜刀砍擊張某頭部、頸部、上肢等部位20余刀致其當(dāng)場死亡。經(jīng)鑒定,張某因遭銳器多次砍擊,致使右頸總動(dòng)脈、頸內(nèi)靜脈斷裂,由此引起大出血而死亡。2014年2月20日,田仁信主動(dòng)到公安機(jī)關(guān)投案,并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實(shí)。2014年9月25日,溫州中院依法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田仁信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quán)利終身。
一、問題的提出
《溫州商報(bào)》刊登一則《目睹妻子遭人強(qiáng)暴丈夫砍死施暴者被判無期》的新聞報(bào)道[1]掀起一場輿論大波,引發(fā)學(xué)界熱議和社會(huì)的廣泛關(guān)注。針對(duì)該案判罰輕重的民意調(diào)查顯示,高達(dá)86%的網(wǎng)友認(rèn)為“判罰過重,丈夫保護(hù)被強(qiáng)奸妻子屬于正當(dāng)防衛(wèi)”,單從情感上表示理解丈夫行為的占12.2%,僅有1.2%的民眾支持法院判決認(rèn)為罪行當(dāng)罰。[2]該案判決之所以激起民眾的強(qiáng)烈不滿,網(wǎng)友為其高呼喊冤[3],緣于人們?cè)O(shè)想自己遇到類似情況緊急的突發(fā)狀況時(shí),對(duì)能否依靠自身力量盡快脫離危險(xiǎn)進(jìn)行防衛(wèi)產(chǎn)生懷疑,認(rèn)為有罪判罰會(huì)讓公民怯于正當(dāng)行使自衛(wèi)權(quán),變相限制甚至剝奪了公民充足的自我防衛(wèi)資格。公民對(duì)防衛(wèi)行為的正當(dāng)性擔(dān)憂和對(duì)司法裁判經(jīng)驗(yàn)邏輯的不理解,揭露出復(fù)雜事實(shí)與法律文本之間循回往溯的認(rèn)定過程,往往是不一致且難相符合的。根據(jù)規(guī)范法勾畫的防衛(wèi)行為認(rèn)定摹本,在一般情境下討論正當(dāng)防衛(wèi)與無過當(dāng)防衛(wèi)行為的法律適用,似乎依照傳統(tǒng)的防衛(wèi)節(jié)點(diǎn)、行為先后、手段輕重、損害結(jié)果與行為間的因果關(guān)系等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就可以盡善盡美地解決所有現(xiàn)實(shí)問題。然而,現(xiàn)實(shí)情景的復(fù)雜性決定了案件事實(shí)并非總是能夠恰如其分地套入規(guī)范法的“標(biāo)準(zhǔn)”之中,往往出現(xiàn)一般情境外的特殊狀況,需要法官在證據(jù)裁判規(guī)則的約束下根據(jù)現(xiàn)實(shí)證據(jù)材料謹(jǐn)慎判斷。解決特殊情境下無過當(dāng)防衛(wèi)行為的司法裁判難題需要從刑法理論與司法價(jià)值觀念上考量。
二、構(gòu)想:無過當(dāng)防衛(wèi)的特殊情境假設(shè)
正當(dāng)防衛(wèi)是刑法賦予公民對(duì)正在進(jìn)行的不法侵害予以制止,避免造成嚴(yán)重后果而作出一定防衛(wèi)行為的正當(dāng)權(quán)利。[4]一般而言,防衛(wèi)行為的正當(dāng)性與防衛(wèi)承擔(dān)的適當(dāng)性根據(jù)案發(fā)當(dāng)時(shí)的具體情況和證據(jù)材料能夠比較清晰地判斷,但特殊情境下存在防衛(wèi)主體、防衛(wèi)場景、防衛(wèi)時(shí)間以及主觀認(rèn)識(shí)與意圖方面的特殊性。結(jié)合田仁信故意殺人一案,可以從以下情境假設(shè)中探討無過當(dāng)防衛(wèi)行為的司法認(rèn)定問題。
(一)第三人防衛(wèi)
在第三人防衛(wèi)的語境下,由于防衛(wèi)行為的實(shí)施者是不法侵害之外的第三人,可能無法準(zhǔn)確判斷起因事件的緊急性和危險(xiǎn)性,甚至無法析分“不法侵害”外觀的真實(shí)性與客觀性,難免出現(xiàn)第三人因錯(cuò)誤認(rèn)識(shí)防衛(wèi)必要而錯(cuò)誤防衛(wèi)的情況。
本案中,田仁信與妻子羅某及被害人張某三人同住在員工宿舍,關(guān)系密切。根據(jù)被告人供述和羅某證實(shí)案發(fā)當(dāng)時(shí)的情形,或許存在被害人欲以強(qiáng)奸羅某的事實(shí)可能,但無法排除以下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羅某與張某二人具有不正當(dāng)關(guān)系,案發(fā)當(dāng)晚趁著田某外出之隙通奸,為避免田某撞破后羅某顏面盡失或遭受田某打罵,便制造張某強(qiáng)迫羅某與其發(fā)生性關(guān)系的畫面;另一種可能是:羅某與張某確實(shí)存有不正當(dāng)關(guān)系,但是在張某威逼利誘下無奈為之的。羅某與田某不甘忍受或心存報(bào)復(fù),便共同導(dǎo)演一出強(qiáng)奸戲碼。雖然從外觀上看羅某遭受了不法侵害,但實(shí)質(zhì)卻是給田某報(bào)復(fù)張某提供了合法外衣,借正當(dāng)防衛(wèi)規(guī)避刑事責(zé)任與刑罰懲罰。引起防衛(wèi)行為的危險(xiǎn)起因關(guān)系到防衛(wèi)的必要性與合理程度,如何界定防衛(wèi)起因的危險(xiǎn)程度和由誰判斷危險(xiǎn)狀況對(duì)于認(rèn)定無過當(dāng)防衛(wèi)尤為重要。
1.對(duì)作為防衛(wèi)起因犯罪侵害的理解。刑法條文雖將行兇與殺人、搶劫等暴力犯罪一道列入無過當(dāng)防衛(wèi)的適用范圍,卻缺少對(duì)該表述的權(quán)威解釋,事實(shí)上要求立法機(jī)關(guān)作出合理解釋的呼聲[5]自上一世紀(jì)起就存在,但解釋部門至今未予理睬。而在對(duì)“殺人、搶劫、強(qiáng)奸、綁架”表述的理解上,存在專指特定行為還是具體罪名的爭論,通說認(rèn)為應(yīng)作廣義理解,既可專指四種具體罪名的犯罪,又可認(rèn)定為四種形式的犯罪手段,是一種罪名與手段相結(jié)合的立法表述。[6]但也有學(xué)者主張應(yīng)將引起無過當(dāng)防衛(wèi)的犯罪侵害與防衛(wèi)行為看作兩個(gè)不同的裁判對(duì)象,不必事先確認(rèn)不法侵害構(gòu)成特定犯罪。[7]事實(shí)上,只要防衛(wèi)起因?qū)儆趪?yán)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符合暴力犯罪的危險(xiǎn)性和危害程度,即可認(rèn)為存在防衛(wèi)的事實(shí)前提,是一種概括性的表述。
2.關(guān)于緊急情況下危險(xiǎn)狀況的判斷主體問題。存在“客觀說”與“主觀說”兩種理論,前者以法庭事后認(rèn)定為標(biāo)準(zhǔn);后者則采信防衛(wèi)人的即時(shí)判斷和合理相信。[8]“主觀說”賦予防衛(wèi)人合理判斷的自由空間大,傾向于鼓勵(lì)私人的防衛(wèi)自助行為,但容易對(duì)“不法侵害人”造成不必要的損害;相對(duì)而言,“客觀說”的判斷主體中立,依據(jù)客觀,結(jié)論自然更為準(zhǔn)確,但要求防衛(wèi)者在緊急情況下立即作出如司法工作者同樣精準(zhǔn)的專業(yè)反應(yīng)未免有些強(qiáng)人所難。從刑法典及通行的刑法理論來看,我國采取由法庭事后依據(jù)事實(shí)和證據(jù)予以確定的客觀判斷標(biāo)準(zhǔn),同時(shí)設(shè)有無過當(dāng)防衛(wèi)的免責(zé)條款。
上述兩點(diǎn)同一般情境下認(rèn)定防衛(wèi)所要考慮的問題或無不同,但第三人防衛(wèi)要求司法認(rèn)定更具客觀性,應(yīng)當(dāng)嚴(yán)格按照證據(jù)裁判規(guī)則要求的確實(shí)充分程度進(jìn)行司法裁判。
(二)施害行為發(fā)生在與外界相對(duì)隔離的場所
通常情況下,不法侵害的現(xiàn)實(shí)危險(xiǎn)性與緊迫性在相對(duì)公開的外部環(huán)境中,會(huì)因施害行為的實(shí)施完畢而逐漸減弱或消亡,施害人在結(jié)束侵害后的短時(shí)間內(nèi)繼續(xù)進(jìn)行第二個(gè)不法侵害的可能性相對(duì)較小。但在絕大多數(shù)暴力犯罪案件中,施害行為往往在與外界相對(duì)隔離的物理空間中完成,被侵害人的人身安全在封閉場所內(nèi)的危險(xiǎn)狀態(tài)是持續(xù)且極不穩(wěn)定的,難以估測也無法排除施害人進(jìn)行下一步犯罪侵害的可能。也就是說,法秩序被隔絕在施害人依靠現(xiàn)實(shí)或潛在暴力威脅構(gòu)成的秩序規(guī)則外。[9]在這一特殊情境下,需要從期待可能性理論的層面上探討無正當(dāng)防衛(wèi)適用的時(shí)間界限問題。
期待可能性是指在實(shí)施行為當(dāng)時(shí)的情況下,能期待行為人作出合法行為的可能性。[10]該理論認(rèn)為,法律不期待防衛(wèi)人在人身安全極為不確定的狀態(tài)下,依然可以綜合判斷周遭環(huán)境的危險(xiǎn)指數(shù)繼而選擇是否采取防衛(wèi)行為。尤其當(dāng)不法侵害發(fā)生在與外界相對(duì)隔離的封閉場所內(nèi),無論是被侵害人的精神狀況還是人身安全,都處在十分高度緊張的狀態(tài)下,隨時(shí)有可能遭受施害人的二次侵害。在這種施害人憑借暴力建立起的可以對(duì)其生殺予奪的秩序空間內(nèi),無法以一般常理和邏輯要求被侵害人采取手段合理、力量等同且程度恰當(dāng)?shù)氖侄蚊撾x危險(xiǎn)或制止施害人。因此在司法裁判過程中,應(yīng)當(dāng)本著有利于被侵害人的角度進(jìn)行“場景化”分析,基于證據(jù)和事實(shí)努力還原被侵害人在緊急危險(xiǎn)時(shí)對(duì)當(dāng)下危險(xiǎn)系數(shù)的天然反應(yīng)和直觀判斷,而不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以一般理性人的邏輯思維認(rèn)定。
(三)非基于防衛(wèi)意圖的事后加害報(bào)復(fù)行為
各國刑法之所以普遍承認(rèn)正當(dāng)防衛(wèi)的合法性,得益于私人在不法侵害的緊迫威脅下進(jìn)行自救的一般理論,也是西方自然法學(xué)派認(rèn)為私人在法律無法干預(yù)以保障其生命時(shí)所享有的殺死侵犯者的自由。[11]法律在肯定私人自救的同時(shí),也在擔(dān)憂權(quán)利被濫用的危險(xiǎn),畢竟刑罰權(quán)是國家懲罰犯罪的專有權(quán)力,個(gè)人獨(dú)立對(duì)抗犯罪的防衛(wèi)權(quán)應(yīng)當(dāng)受制于國家刑罰權(quán)。因此,一旦發(fā)現(xiàn)防衛(wèi)人基于肆意泄憤或事后報(bào)復(fù)等不良動(dòng)機(jī),造成一定危害后果的,應(yīng)按照一般犯罪論處,追究其刑事責(zé)任。甄別行為人是基于防衛(wèi)主觀目的,還是惡意的加害報(bào)復(fù),需要對(duì)侵害行為“正在進(jìn)行”狀態(tài)及其危險(xiǎn)系數(shù)與緊迫程度綜合判斷。本案中,被告人田仁信供述:“……因?yàn)樽约捍虿贿^張某,就拿了一把菜刀朝張某亂砍,將他砍倒在地”,證人羅某證實(shí)田仁信見張某強(qiáng)迫其與之發(fā)生性關(guān)系,便與張某扭打、持酒瓶砸頭、持菜刀砍脖致其倒地。證人劉某聽到樓上田仁信說“太欺負(fù)人了”的話,后聽到張某呼喊救命,證人朱某還隱約聽見張某求饒。綜合全案證據(jù),無法排除對(duì)被告人田仁信出于泄憤目的而為的事后加害行為的合理懷疑。
三、反思:標(biāo)準(zhǔn)外的司法判斷與情理中的法律邏輯
關(guān)于是否賦予公民享有不受防衛(wèi)強(qiáng)度限制的 “無過當(dāng)防衛(wèi)權(quán)”的問題,在1997年《刑法》修訂之初就已爭論不休,令立法機(jī)關(guān)陷入兩難的境地:一方面試圖鼓勵(lì)公民積極利用正當(dāng)防衛(wèi)與違法犯罪行為進(jìn)行斗爭,另一方面又唯恐導(dǎo)致公民濫用防衛(wèi)權(quán),造成社會(huì)的混亂。雖然立法機(jī)關(guān)權(quán)衡后增設(shè)有關(guān)“無過當(dāng)防衛(wèi)權(quán)”的規(guī)定,但實(shí)際卻是將困窘轉(zhuǎn)嫁,換作由司法機(jī)關(guān)承擔(dān)認(rèn)定無過當(dāng)防衛(wèi)權(quán)適用的兩難。通過社會(huì)公眾對(duì)溫州中院關(guān)于田仁信故意殺人案裁判結(jié)論的不理解與情感上的不接受,得出以下兩點(diǎn)反思。
(一)現(xiàn)實(shí)復(fù)雜要求司法認(rèn)定能動(dòng)且富有人性
規(guī)范法層面限制的各項(xiàng)適用條件看似能夠應(yīng)對(duì)各種現(xiàn)實(shí)問題,但司法裁判絕不是簡單依照“大前提—小前提”三段論推理模式的量販?zhǔn)健拜斎搿敵觥被顒?dòng),刑事立法面對(duì)復(fù)雜現(xiàn)實(shí)難免會(huì)遇到解釋論的困窘,復(fù)雜現(xiàn)實(shí)需要裁判者發(fā)揮主觀能動(dòng)性并綜合各項(xiàng)因素考量。尤其當(dāng)出現(xiàn)特殊情形,如第三人防衛(wèi)時(shí)對(duì)暴力行為嚴(yán)重危及人身安全危險(xiǎn)性的把握、在與外界相對(duì)隔離的封閉空間內(nèi)期待被侵害人不過當(dāng)防衛(wèi)的可能,以及對(duì)防衛(wèi)人是出于防衛(wèi)意圖還是意欲報(bào)復(fù)主觀目的上的辨別都離不開司法的能動(dòng)裁判。這就需要裁判者從立法目的的角度出發(fā),從當(dāng)事人角度考慮,在兩者最佳交匯點(diǎn)去尋求合理的法律解釋,在客觀證據(jù)事實(shí)的約束下圍繞“人的利益”進(jìn)行司法裁判。[12]
(二)輿論感性要求司法裁判始終遵循經(jīng)驗(yàn)邏輯
雖然,裁判者在適用正當(dāng)防衛(wèi)與無過當(dāng)防衛(wèi)權(quán)法律準(zhǔn)則時(shí),基本都在證據(jù)裁判規(guī)則的約束下審慎為之,但會(huì)出現(xiàn)即便裁判結(jié)論符合司法準(zhǔn)則和法理要求,也難被公眾理解和接受。
客觀地說,溫州市中級(jí)人民法院的判決嚴(yán)格遵守證據(jù)裁判規(guī)則,符合法律的邏輯與經(jīng)驗(yàn)。公眾認(rèn)為以故意殺人罪判處砍死奸妻者的田某無期徒刑,刑罰過重,是出于倫理人性的考慮。田仁信故意殺人案所引發(fā)的法理與情理上的沖突[13]有以下三點(diǎn)需要反思:一是新聞媒體應(yīng)當(dāng)保證案件報(bào)道的客觀,確保向社會(huì)輸送信息的真實(shí)性,絕不允許為了搏人眼球而過分渲染、虛構(gòu)情節(jié)等不符合職業(yè)操守的傳播行為。監(jiān)管部門應(yīng)當(dāng)實(shí)時(shí)監(jiān)督,及時(shí)糾正傳媒機(jī)構(gòu)及新聞工作者欠缺合理性的播報(bào)。需要補(bǔ)充的是,加強(qiáng)對(duì)案件報(bào)道的監(jiān)督并不意味著限制討論,扼殺公民的言論自由,畢竟民主自由與真實(shí)正義并不矛盾,尤其是司法的權(quán)威應(yīng)當(dāng)?shù)玫阶鹬兀欢巧鐣?huì)公眾應(yīng)當(dāng)普遍認(rèn)同的是,正當(dāng)防衛(wèi)是法律賦予公民在緊急危險(xiǎn)中制止加害行為的合法權(quán)利,并非給予私人剝奪他人生命的正當(dāng)依據(jù)。原始社會(huì)對(duì)同態(tài)復(fù)仇的肯定固然能夠滿足民眾的報(bào)復(fù)情感與復(fù)仇心理,但這種做法極其野蠻又不符合現(xiàn)代法治社會(huì)的民主要求。公民應(yīng)當(dāng)尊重裁判者根據(jù)憲法和法律以證據(jù)裁判為規(guī)則形成的自由心證,不可盲目偏聽偏信,應(yīng)有自己獨(dú)立的判斷;三是站在裁判者的角度,當(dāng)裁判結(jié)果與民眾情感發(fā)生碰撞導(dǎo)致司法公信與接受程度不高,應(yīng)當(dāng)及時(shí)向公眾解釋并反思適用規(guī)則的合理性,始終遵循案件裁判的司法準(zhǔn)則與經(jīng)驗(yàn)邏輯。同時(shí),應(yīng)注重裁判文書的說理,充分闡述裁判結(jié)論形成的論證過程與認(rèn)定依據(jù),依此減輕或打消公眾疑慮,提升司法的公信力。面對(duì)報(bào)紙刊登的案件報(bào)道所引發(fā)的社會(huì)輿論,溫州市中級(jí)人民法院專門出具《關(guān)于被告人田仁信故意殺人案的情況說明》來回應(yīng)公眾的質(zhì)疑,對(duì)案件事實(shí)與量刑中被害人行為是否屬于強(qiáng)奸、被告人田仁信的量刑問題進(jìn)行解釋,并對(duì)裁判文書出現(xiàn)錯(cuò)訛予以補(bǔ)正說明,這是值得肯定的。
四、結(jié)語
在田仁信故意殺人案中,法院經(jīng)審查認(rèn)為,施害人張某對(duì)羅某的不法侵害停止后,田仁信為報(bào)復(fù)而持刀砍擊張某的行為,并不構(gòu)成刑法意義上的正當(dāng)防衛(wèi)或防衛(wèi)過當(dāng),故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田仁信無期徒刑。綜合全案證據(jù),雖然被告人在案發(fā)后能主動(dòng)投案自首,但其手段殘忍,且已潛逃8年,期間未作出任何民事賠償,基于刑法規(guī)范和裁判準(zhǔn)則,該判決在定罪與量刑方面都不存在明顯的不合理因素,符合司法的經(jīng)驗(yàn)邏輯。雖然公眾對(duì)“丈夫砍死奸妻者”敏感字眼的關(guān)注,使得故意殺人的無期判決在倫理情感上不被世人接受,甚至裁判文書上的錯(cuò)訛成為民眾對(duì)司法公正與司法權(quán)威產(chǎn)生“合理懷疑”的關(guān)鍵依據(jù)。但面對(duì)司法裁判中法理與情理的沖突,裁判者應(yīng)當(dāng)始終在規(guī)范刑法的框架下保持對(duì)案件事實(shí)的理性判斷,絕對(duì)不能破壞法律的基本原則來迎合民眾的報(bào)復(fù)情感與復(fù)仇心態(tài)。無論情境怎樣特殊,都需要裁判者本著事實(shí)和證據(jù)的客觀性,始終站在立法目的與當(dāng)事人角度的交匯處考量,獨(dú)立、公正且公開地作出裁判。
注釋:
[1]戚祥浩:《目睹妻子遭人強(qiáng)暴 丈夫砍死施暴者被判無期》,載《溫州商報(bào)》2015年6月15日。
[2]《砍死強(qiáng)奸犯丈夫被判無期 九成網(wǎng)友認(rèn)為判罰過重》,http://lady.163.com/15/0617/10/ASA9P7Q300264OFI.tml,訪問日期:2017年3月17日。
[3]陶舜:《丈夫砍死強(qiáng)奸妻子施暴者判無期冤不冤》,http://news.sina.com.cn/zl/zatan/2015-06-16/15233889.shtml,訪問日期:2017年3月16日。
[4]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xué)》,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頁。
[5]如趙秉志教授呼吁:為確保特殊防衛(wèi)權(quán)的正確適用,保證執(zhí)法的統(tǒng)一,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應(yīng)當(dāng)對(duì)“行兇”一詞作出明確的司法解釋,限于使用兇器的暴力行兇,即使用兇器對(duì)被害人進(jìn)行暴力襲擊,嚴(yán)重危及被害人人身安全的。
[6]王作富、阮方民:《關(guān)于新刑法中特別防衛(wèi)權(quán)規(guī)定的研究》,載《中國法學(xué)》1998年第5期;趙秉志:《特殊防衛(wèi)權(quán)問題研究》,載《法制與社會(huì)發(fā)展》1999年第6期。
[7]何萍:《論特殊防衛(wèi)中的犯罪侵害——兼評(píng)鄧玉嬌故意傷害案》,載《法學(xué)》2009年第8期。
[8]同[7]。
[9]陳洪杰:《特定情境下事后防衛(wèi)行為的可懲罰性問題探討》,載 《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7年第3期。
[10]龍立豪:《論期待可能性理論在我國刑法中的適用》,載《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0年第2期。
[11][英]洛克:《政府論(下)》,葉啟芳、瞿菊農(nóng)譯,商務(wù)印書館1996年版,第14頁。
[12]蔣惠嶺、王才亮:《強(qiáng)拆之痛:范木根防衛(wèi)過當(dāng)傷害致死案評(píng)析》,http://mt.sohu.com/20160506/n448005199.shtml,訪問日期:2017年3月26日。
[13]溫瓊:《丈夫砍死奸妻者審理的兩難》,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hina/gqmq/20150619125959_all.html,訪問日期:2017年3月19日。
*中央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法學(xué)院刑事訴訟法學(xué)碩士研究生[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