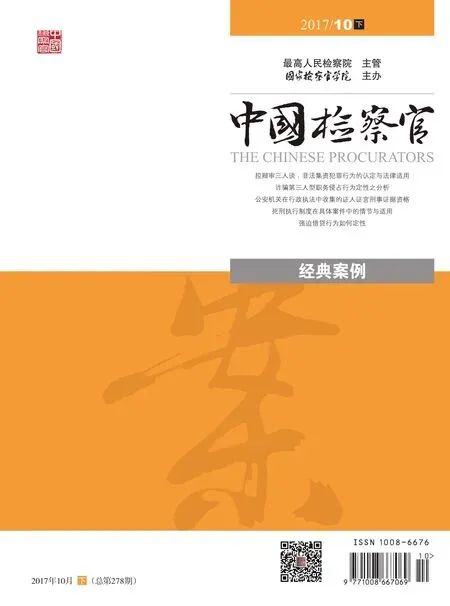公安機(jī)關(guān)在行政執(zhí)法中收集的證人證言刑事證據(jù)資格
——以馮某介紹、容留賣淫案為視角
文◎李 寧
公安機(jī)關(guān)在行政執(zhí)法中收集的證人證言刑事證據(jù)資格
——以馮某介紹、容留賣淫案為視角
文◎李 寧*
公安機(jī)關(guān)在行政執(zhí)法過程中收集的證人證言與刑事訴訟中的證人證言異形同質(zhì)。在辦理刑事案件時(shí),因路途遙遠(yuǎn)、死亡、失蹤或者喪失作證能力,無法重新收集的情況下,其證言來源、收集程序合法,并有其他證據(jù)相印證,經(jīng)審查符合刑事訴訟法要求的,應(yīng)當(dāng)賦予其刑事訴訟資格。
公安機(jī)關(guān) 行政執(zhí)法程序 證人證言 刑事證據(jù)資格
一、案情簡介
犯罪嫌疑人馮某,男,重慶市W區(qū)人,曾因犯容留、介紹賣淫罪被W區(qū)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8個(gè)月,緩刑1年。
2015年9月17日晚,犯罪嫌疑人馮某在其經(jīng)營的賓館內(nèi)容留陳某和張某,魏某和黃某進(jìn)行賣淫嫖娼活動(dòng),并非法獲利180元。案發(fā)后,偵查人員對陳某等四人進(jìn)行了治安處罰,并以行政程序制作了詢問筆錄。案件轉(zhuǎn)立刑事案件后,四人均已離開W區(qū),外出務(wù)工,偵查人員無法重新獲取其證人證言。認(rèn)定犯罪嫌疑人馮某涉嫌介紹、容留賣淫罪的其他證據(jù)有馮某的供述、辨認(rèn)筆錄、通話清單、視聽資料、扣押嫖資清單、行政處罰決定書。
馮某于2015年10月16日被批準(zhǔn)逮捕,同年11月19日被提起公訴,同年11月30日被重慶市W區(qū)人民法院以犯介紹、容留賣淫罪判處拘役5個(gè)月,并處罰金3000元。
二、審查批捕分歧
本案在審查批捕期間,關(guān)于偵查人員在行政程序中收集的證人證言是否可以作為刑事訴訟證據(jù),辦案檢察官之間產(chǎn)生了分歧,分歧觀點(diǎn)及理由如下:
(一)公安機(jī)關(guān)行政執(zhí)法程序中收集的證人證言不具有刑事訴訟資格
1.法律未明確賦予此類證人證言刑事訴訟資格。《刑事訴訟法》第52條第2款規(guī)定:“行政機(jī)關(guān)在行政執(zhí)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shù)據(jù)等證據(jù)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jù)使用”。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guī)則(試行)》、公安部《公安機(jī)關(guān)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guī)定》對應(yīng)該條款也作出了規(guī)定和解釋,內(nèi)容均為行政機(jī)關(guān)在行政執(zhí)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shù)據(jù)等客觀性較強(qiáng)的證據(jù)材料,可以作為證據(jù)使用,也就是說,在可以作為刑事證據(jù)使用的證據(jù)里面沒有包括言辭類證據(jù),行政機(jī)關(guān)在行政執(zhí)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言辭類證據(jù)材料應(yīng)當(dāng)由偵查機(jī)關(guān)重新收集、調(diào)取,不可直接作為證據(jù)使用。
同樣,2011年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出臺(tái)的《關(guān)于辦理侵犯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重申 “關(guān)于辦理侵犯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刑事案件中行政執(zhí)法部門收集、調(diào)取證據(jù)的效力問題:行政執(zhí)法部門依法收集、調(diào)取、制作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檢驗(yàn)報(bào)告、鑒定結(jié)論、勘驗(yàn)筆錄、現(xiàn)場筆錄,經(jīng)公安機(jī)關(guān)、人民檢察院審查,人民法院庭審質(zhì)證確認(rèn),可以作為刑事證據(jù)使用。行政執(zhí)法部門制作的證人證言、當(dāng)事人陳述等調(diào)查筆錄,公安機(jī)關(guān)認(rèn)為有必要作為刑事證據(jù)使用的,應(yīng)當(dāng)依法重新收集、制作。”
2.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導(dǎo)案例明確指出此類證人證言不具有刑事證據(jù)資格。刑事指導(dǎo)案例第972號(hào)王志余、秦群英容留賣淫案中闡述的觀點(diǎn)是未經(jīng)重新收集、制作的言詞證據(jù),不能作為刑事訴訟證據(jù)使用。理由是言詞證據(jù)具有較強(qiáng)的主觀性,變化性大,行政機(jī)關(guān)調(diào)查取證所依據(jù)的行政法律法規(guī)的程序要求明顯不如刑事訴訟嚴(yán)格。在刑事訴訟中重新收集證言,讓證人在更為嚴(yán)格的權(quán)利義務(wù)背景下敘述事實(shí),能夠保證其證言具有較強(qiáng)的可信性,也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實(shí),保障當(dāng)事人的權(quán)利。公安機(jī)關(guān)查辦賣淫嫖娼等行政違法案件時(shí),發(fā)現(xiàn)有犯罪線索的,在刑事立案后,對行政執(zhí)法中收集的言詞證據(jù),認(rèn)為確有必要作為刑事證據(jù)使用的應(yīng)當(dāng)由偵查人員依據(jù)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在告知權(quán)利義務(wù)、法律后果后,向證人、當(dāng)事人重新取證。不能因其職權(quán)的雙重性,混淆行政處罰與刑事訴訟程序,任意轉(zhuǎn)換不同程序進(jìn)行執(zhí)法。該案一審、二審法院均沒有將公安機(jī)關(guān)在查處賣淫嫖娼活動(dòng)中收集的言詞證據(jù)作為刑事證據(jù)使用,對檢察機(jī)關(guān)認(rèn)定的部分容留賣淫事實(shí)未予認(rèn)定。[1]
(二)公安機(jī)關(guān)在行政執(zhí)法中收集的證人證言具有刑事證據(jù)資格
1.刑事訴訟法未明確否定此類證據(jù)具有刑事訴訟資格。《刑事訴訟法》第52條第2款只是明確規(guī)定了實(shí)物類行政執(zhí)法證據(jù)具有刑事訴訟資格,并不能直接推導(dǎo)出言詞類證據(jù)不具備刑事訴訟資格。從邏輯上看,《刑事訴訟法》第52條第2款是一個(gè)特稱肯定命題(簡稱SIP),即有的S是P,其中S與P是一種包容關(guān)系,不能直接推導(dǎo)出非S不是P。
2.可以參照適用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guī)則(試行)》第64條第3款。該款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辦理直接受理立案偵查的案件,對于有關(guān)機(jī)關(guān)在行政執(zhí)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涉案人員供述或者相關(guān)人員的證言、陳述,應(yīng)當(dāng)重新收集;確有證據(jù)證實(shí)涉案人員或者相關(guān)人員因路途遙遠(yuǎn)、死亡、失蹤或者喪失作證能力,無法重新收集,但供述、證言或者陳述的來源、收集程序合法,并有其他證據(jù)相印證,經(jīng)人民檢察院審查符合法定要求的,可以作為證據(jù)使用”。雖然該條款的適用對象是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的案件,但刑事訴訟法針對其他類型案件的規(guī)定是空白的,根據(jù)漏洞填補(bǔ)規(guī)則,[2]可以類推適用。
3.此類證人證言具有刑事證據(jù)的特征。公安機(jī)關(guān)是兼具行政執(zhí)法權(quán)和司法權(quán)的機(jī)關(guān),其在行政程序中制作的詢問筆錄可以視為初查證據(jù)。公安機(jī)關(guān)在查辦賣淫嫖娼活動(dòng)中,既是行政機(jī)關(guān)又是初查涉嫌容留賣淫罪的偵查機(jī)關(guān),任何案件均需要一定的初查才能進(jìn)一步立案偵查,而初查的證據(jù)并不是刑事訴訟中應(yīng)當(dāng)排除的證據(jù)類型,只要不屬于非法證據(jù)排除的情形,符合證據(jù)的合法性、關(guān)聯(lián)性、真實(shí)性,就可以作為刑事證據(jù)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導(dǎo)案例有一定瑕疵。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辨認(rèn)筆錄、通話清單、視聽資料、證據(jù)保全的現(xiàn)金、行政處罰決定書與兩名賣淫女、兩名嫖娼人員的陳述能相互印證,能形成證據(jù)鎖鏈,賣淫女和嫖娼人員之前的陳述可以作為刑事證據(jù)使用。
三、分歧背后的法理探析
(一)行政執(zhí)法證據(jù)與刑事訴訟證據(jù)的比較
1.行政執(zhí)法證據(jù)與刑事訴訟證據(jù)的區(qū)別。行政執(zhí)法證據(jù)是指行政主體在行政執(zhí)法程序中為了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根據(jù)行政法律規(guī)范所設(shè)置的事實(shí)要素,而收集、運(yùn)用證明特定相對人法律行為或者事實(shí)的材料。刑事訴訟證據(jù)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用于證明案件事實(shí)的材料。行政執(zhí)法證據(jù)與刑事訴訟證據(jù)存在的差異主要體現(xiàn)在三方面:第一,證據(jù)收集的主體不同。行政執(zhí)法證據(jù)的收集主體是國家行政機(jī)關(guān)、被授權(quán)或者委托的組織,如工商、稅務(wù)等。刑事訴訟證據(jù)則主要是由偵查機(jī)關(guān)依職權(quán)收集,少數(shù)情況由當(dāng)事人、證人或者辯護(hù)人收集。第二,證據(jù)收集的方法不同。行政執(zhí)法活動(dòng)中常見的有詢問、勘驗(yàn)、檢查、鑒定等,刑事訴訟中的取證手段還包括采取強(qiáng)制措施。第三,證據(jù)的審查方式不同。行政執(zhí)法證據(jù)的審查人是執(zhí)法機(jī)關(guān)自身,而刑事訴訟證據(jù)則需要通過法院進(jìn)行當(dāng)庭舉證、質(zhì)證。
2.行政執(zhí)法證據(jù)與刑事訴訟證據(jù)的聯(lián)系。根據(jù)行政執(zhí)法證據(jù)是否可以運(yùn)用于刑事訴訟程序,行政執(zhí)法證據(jù)可以分為可直接轉(zhuǎn)化的證據(jù)、不可直接轉(zhuǎn)化的證據(jù)以及經(jīng)法定程序轉(zhuǎn)化的證據(jù)。
(1)可直接適用的證據(jù)。行政機(jī)關(guān)在行政執(zhí)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shù)據(jù)等證據(jù)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jù)使用。
(2)經(jīng)法定程序轉(zhuǎn)化的證據(jù)。符合經(jīng)法定程序轉(zhuǎn)化的證據(jù)有兩種類型,即符合條件的言辭證據(jù)及瑕疵實(shí)物證據(jù)。言辭證據(jù)不可轉(zhuǎn)化是一般原則,但存在經(jīng)法定程序轉(zhuǎn)化的例外,即符合客觀性、關(guān)聯(lián)性、合法性的言辭證據(jù),在出現(xiàn)特殊情況或緊急情況時(shí)可轉(zhuǎn)化。在現(xiàn)行法律框架體系內(nèi),主要指的是《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guī)則(試行)》第64條第3款規(guī)定,即人民檢察院辦理直接受理立案偵查的案件。瑕疵證據(jù)一般指行政執(zhí)法主體在收集相關(guān)證據(jù)時(shí)存在技術(shù)性缺陷的證據(jù),如缺少簽名、遺漏內(nèi)容等。瑕疵言辭證據(jù)不符合轉(zhuǎn)化標(biāo)準(zhǔn),《刑事訴訟法》第54條亦作出相應(yīng)規(guī)定。而瑕疵實(shí)物證據(jù)進(jìn)行補(bǔ)正或合理解釋后,可以轉(zhuǎn)化為刑事證據(jù)。
(3)不可轉(zhuǎn)化的證據(jù)。非法證據(jù)和言辭證據(jù)不可轉(zhuǎn)化,確有需要的,應(yīng)由公安司法機(jī)關(guān)重新收集。2011年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guān)于辦理侵犯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規(guī)定:“行政執(zhí)法部門制作的證人證言、當(dāng)事人陳述等調(diào)查筆錄,公安機(jī)關(guān)認(rèn)為有必要作為刑事證據(jù)使用的,應(yīng)當(dāng)依法重新收集、制作”。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內(nèi),絕大多數(shù)人認(rèn)為公安機(jī)關(guān)在行政程序中收集的證人證言是不能轉(zhuǎn)化為刑事證據(jù)的。但筆者認(rèn)為,這樣的理解有失偏頗,不適應(yīng)客觀辦案需要的,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法律應(yīng)當(dāng)賦予這些證人證言刑事證據(jù)資格,將這些證人證言作為刑事證據(jù)使用。
(二)公安機(jī)關(guān)為主體的行政執(zhí)法程序、刑事訴訟程序中的證人證言異形同質(zhì)
公安機(jī)關(guān)在行政程序收集的證人證言與其在刑事程序中收集的證人證言并不存在實(shí)質(zhì)上的差異,具體理由如下:
首先,取證主體同一。公安機(jī)關(guān)無論對行政違法行為還是刑事犯罪行為都有查處權(quán),不存在取證主體的不同。
其次,取證程序嚴(yán)格。公安機(jī)關(guān)的行政取證程序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機(jī)關(guān),其取證程序的復(fù)雜性及嚴(yán)苛性并不亞于刑事訴訟程序。公安機(jī)關(guān)辦理行政案件的程序依據(jù)主要是《公安機(jī)關(guān)辦理行政案件的程序規(guī)定》,其第2條規(guī)定了合法、公正、公開、及時(shí)的原則,并與《刑事訴訟法》一樣,同樣確立了保障人權(quán)原則。在落實(shí)該原則的具體制度上,有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回避制度等等。依照該規(guī)定,公安機(jī)關(guān)在行政程序中收集證人證言需要遵守以下規(guī)定:應(yīng)當(dāng)告知權(quán)利義務(wù);由兩名以上民警依法進(jìn)行詢問;辦理未成年人案件需要有合適成年人在場;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明辨是非、不能正確表達(dá)的人,不能作為證人等等。因此,二者在取證方式上也并沒有實(shí)質(zhì)性的差異。在權(quán)利義務(wù)告知方面,二者雖在字面上有所差異,但因《公安機(jī)關(guān)辦理行政案件的程序規(guī)定》第7條、第61條已經(jīng)對應(yīng)了證人權(quán)利義務(wù)第1條、第5條,因此其在實(shí)質(zhì)上并不存在差異(具體內(nèi)容見下表)。
最后,證據(jù)的最終審查主體是司法機(jī)關(guān)。公安機(jī)關(guān)按照行政執(zhí)法程序所收集的證據(jù)的證明效力、證明標(biāo)準(zhǔn)、證明對象等最后都是由司法機(jī)關(guān)嚴(yán)格按照刑事訴訟法進(jìn)行終局審查,既足以保證證據(jù)的可采性又能夠保障當(dāng)事人的合法權(quán)益。
因此,公安機(jī)關(guān)在行政程序中收集的證人證言不同于一般行政機(jī)關(guān)收集的言詞證據(jù),在實(shí)質(zhì)上與刑事案件中的證人證言并不存在差異。
(三)最高人民法院指導(dǎo)性案例已經(jīng)時(shí)過境遷
上述指導(dǎo)性案例中認(rèn)為行政程序中的證人證言必須經(jīng)過重新收集的依據(jù)是行政機(jī)關(guān)取證所依據(jù)行政法律法規(guī)的程序要求不如刑事訴訟嚴(yán)格。刑事訴訟法關(guān)于證人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罪證的法律責(zé)任;非法證據(jù)排除;證人保護(hù)等制度比行政程序更為完善,由此可能導(dǎo)致證人在不同的程序中敘述事實(shí)時(shí)可能會(huì)有所取舍。[3]筆者認(rèn)為這種擔(dān)憂是不必要的。該案例中的案件是2012年5月立案偵查的,當(dāng)時(shí)尚未出臺(tái)《公安機(jī)關(guān)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guī)定》。2013年1月1日開始,公安機(jī)關(guān)辦理行政案件須嚴(yán)格遵守該規(guī)定。隨著該規(guī)定的出臺(tái),公安機(jī)關(guān)在辦理行政案件時(shí)亦嚴(yán)格遵循了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權(quán)利義務(wù)告知等制度,足以保證證言的可信性,也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實(shí)。同時(shí),公安部于2016年7月1日施行了 《公安機(jī)關(guān)現(xiàn)場執(zhí)法視音頻記錄工作規(guī)定》,該規(guī)定第2條要求公安機(jī)關(guān)在現(xiàn)場盤問、檢查;違反治安管理、出入境管理、消防管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違法犯罪行為和道路交通事故等進(jìn)行現(xiàn)場處置、當(dāng)場處罰;辦理行政、刑事案件進(jìn)行現(xiàn)場勘驗(yàn)、檢查、搜查、扣押、辨認(rèn)、扣留等場合應(yīng)當(dāng)進(jìn)行現(xiàn)場執(zhí)法視音頻記錄。由此更進(jìn)一步保證了執(zhí)法過程的合法性和收集證據(jù)的客觀性。
(四)公安機(jī)關(guān)在行政執(zhí)法中的證人證言一定條件下具有刑事證據(jù)資格
行政執(zhí)法證據(jù)最終能否適用于刑事訴訟,關(guān)鍵在于是否滿足刑事訴訟的三個(gè)實(shí)質(zhì)性要件:客觀性、關(guān)聯(lián)性、合法性。這三個(gè)要素是判斷刑事訴訟證據(jù)能力的基本標(biāo)準(zhǔn),只有三者同時(shí)具備才能在刑事訴訟中使用。客觀性要求進(jìn)入刑事訴訟的證據(jù)能夠客觀反映待證事實(shí);關(guān)聯(lián)性要求行政執(zhí)法證據(jù)與刑事訴訟的待證事實(shí)具有一定的關(guān)聯(lián)性;合法性包含取證主體合法、證據(jù)形式合法、取證方式合法等要求。作為行政執(zhí)法與刑事案件交叉的證據(jù),二者的待證事實(shí)是同一的,因此其關(guān)聯(lián)性不言自明。因此決定行政執(zhí)法證據(jù)能夠進(jìn)入刑事訴訟的關(guān)鍵是要通過法律手段,保證證據(jù)的客觀性和合法性。
對此,筆者認(rèn)為,針對公安機(jī)關(guān)辦理的行政案件轉(zhuǎn)化為刑事案件的證人證言,可以比照《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guī)則(試行)》第64條第3款規(guī)定,對于在行政程序中收集的涉案人員供述或者相關(guān)人員的證言、陳述,一般應(yīng)重新收集;確有證據(jù)證實(shí)涉案人員或者相關(guān)人員因路途遙遠(yuǎn)、死亡、失蹤或者喪失作證能力,無法重新收集,但供述、證言或者陳述的來源、收集程序合法,并有其他證據(jù)相印證,經(jīng)審查符合法定要求的,可以作為證據(jù)使用。
但在審查過程中應(yīng)把握兩個(gè)原則:一是合法性原則。首先初查證據(jù)在內(nèi)容和形式上必須符合刑事訴訟法的法定要求,例如,初查中的詢問筆錄,要作為刑事案件的證人證言使用,必須完全符合刑事訴訟法關(guān)于詢問證人的程序要求;其次,初查證據(jù)的取證程序和手段必須合法,例如,在協(xié)助調(diào)查期間制作的調(diào)查筆錄,還必須審查協(xié)查期間是否存在非法取證尤其是疲勞審訊的問題。二是客觀性原則。相關(guān)證人證言應(yīng)當(dāng)是客觀證實(shí)的,并與全案其他證據(jù)相印證,足以排除合理懷疑。
四、司法建議
雖然案件最終被順利處理,但由此導(dǎo)致的認(rèn)識(shí)分歧并沒有因此而終結(jié)。由此筆者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出臺(tái)相應(yīng)的司法解釋,對于公安機(jī)關(guān)在行政程序中收集的涉案人員供述或者相關(guān)人員的證言、陳述,一般應(yīng)重新收集;確有證據(jù)證實(shí)涉案人員或者相關(guān)人員因路途遙遠(yuǎn)、死亡、失蹤或者喪失作證能力,無法重新收集,但供述、證言或者陳述的來源、收集程序合法,并有其他證據(jù)相印證,經(jīng)符合法定要求的,可以作為證據(jù)使用。
另外,筆者還建議公安機(jī)關(guān)在辦理行政刑事交叉案件時(shí),不僅應(yīng)當(dāng)告知當(dāng)事人行政案件的權(quán)利義務(wù),還應(yīng)當(dāng)全面告知當(dāng)事人可能面臨的刑事方面的權(quán)利義務(wù)。同時(shí)在收集言辭證據(jù)時(shí),還應(yīng)當(dāng)同步錄音錄像,以避免案件產(chǎn)生訴訟風(fēng)險(xiǎn)。
注釋:
[1]參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總第97集,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頁。
[2]漏洞填補(bǔ)規(guī)則是指當(dāng)刑事訴訟法出現(xiàn)漏洞時(shí),法官不得因此而拒絕裁判,而應(yīng)推過類推等方式進(jìn)行彌補(bǔ)。漏洞填補(bǔ)必須遵循合憲性、不得損害當(dāng)事人利益、司法克制等原則。參見縱博:《刑事訴訟法漏洞填補(bǔ)中的目的性限縮與擴(kuò)張》,載 《國家檢察官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1年第4期。
[3]同[1],第 100 頁。
*重慶市萬州區(qū)人民檢察院檢察官[404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