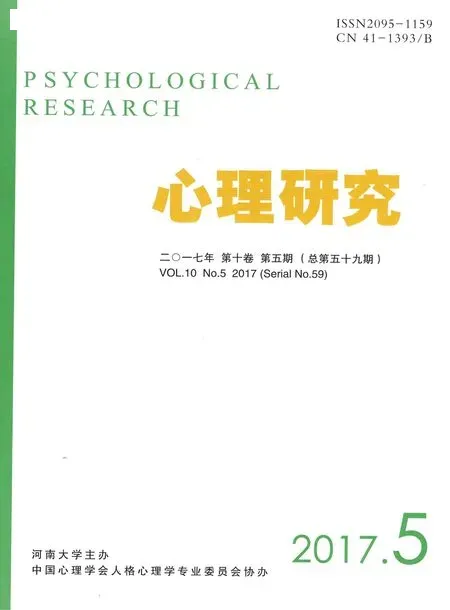分析性與整體性認知的跨文化研究述要
竇雪婷 鐘建軍
(內蒙古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呼和浩特 010022)
分析性與整體性認知的跨文化研究述要
竇雪婷 鐘建軍
(內蒙古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呼和浩特 010022)
分析性與整體性認知加工的跨文化研究一直是國外的研究熱點。本文結合國內外相關研究,對分析性與整體性認知在注意、分類與歸因、辯證思維、時間信息及情境信息等方面的文化差異進行詳細闡述,進一步從遠端環境、近端環境及個人等三方面分析導致該差異形成的文化因素。雖然國外研究成果頗豐,但國內還尚待深入,未來可從研究本土化、拓展分析性與整體性認知范圍、開展分析性與整體性認知神經科學相關研究、探討非文化因素及文化融合對分析性與整體性認知的影響作用等方面進行。
認知加工;文化差異;分析性與整體性認知
1 引言
1962年美國心理學家Witkin提出的心理分化理論推動了認知方式的相關研究,此后便引發了跨文化研究熱潮。眾多研究表明,認知處理方式存在文化差異,如給被試呈現一幅狼站立森林中的圖片,一些被試忽略環境信息森林只關注焦點物體狼,而另一些卻關注焦點物體狼與環境信息森林之間的關系。前者注重對環境中客體的認知被稱為分析性認知,后者注重環境與客體關系的認知則被稱為整體性認知[1]。該現象同樣可見于社會行為的歸因認知,有的文化下被試傾向將其歸因于行為個體的內部特性(如,競爭人格),有的文化則傾向將其歸因于行為個體的周圍環境(如,失業率)[2]。本文就現有的分析性與整體性認知的跨文化研究進行梳理,進一步分析文化對分析性與整體性認知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指出未來研究的幾個方向。
2 分析性與整體性認知的跨文化研究
2.1 注意
考察分析性與整體性認知的主要方式為視覺范圍內注意的是焦點物體還是環境信息。
2.1.1 有意義場景
2001年,Masuda和Nisbett呈現若干生動的自然水下場景片段,包含焦點物體及其背景,要求被試描述場景。日本被試較美國被試更喜歡描述背景及其與焦點物體間的關系(如,一條大魚游向綠色的海草)[1]。該文化差異在眼動研究中也得到了驗證,觀察若干包含焦點物體及其背景的自然場景圖片(如,叢林中的老虎),美國被試較中國被試時間開始更早且持續更長地注視焦點物體,而中國被試更多用眼睛快速掃視背景[3]。以上研究表明東西方個體對自然場景的注意確實存在差異。
既然自然場景環境已獲得證實,那社會環境情況又如何?2008年,Masuda、Ellsworth及 Mesquita等人開展了面部表情識別的跨文化研究,呈現給被試若干由五個卡通人物構成的圖片,焦點目標人物或高興,或悲傷,或生氣,或中性,其周圍的其他人與焦點人物表情或一樣,或不一樣,要求評定焦點人物高興、悲傷及生氣的程度[4]。結果表明,日本被試比西方被試評定焦點人物表情更易受周圍人的影響。隨后進行的眼動軌跡追蹤也進一步驗證了其結果,即日本被試比西方被試更多將注意集中于周圍人。該研究表明,西方個體關注自身,日本個體關注群體與自身的關系。東西方個體對社會場景的注意同樣存在差異。
2.1.2 無意義刺激
雖然研究已經證實確實存在注意的文化差異,但也僅局限在對動物、水下或面部表情等有意義場景描述的差異上。若對無意義刺激也存在同樣差異,就能更進一步證實其差異性。之后眾多研究者相繼使用簡單幾何圖形考察注意的文化差異,也確實得到了驗證[5-8]。 如,用框線任務(the Framed-Line Task,FLT)測量注意或忽視環境信息的能力。首先呈現一個正方形,其包含一條垂直線段;然后呈現大小不同的另一個正方形,要求被試畫線段,或者與之前呈現的長度一樣(絕對任務),或者與之前的相對(考慮框與線的比例)一樣(相對任務)。絕對任務僅需要注意線段長度,而不考慮框的大小,而相對任務需要注意線段與框的大小關系。日本被試較美國被試在絕對任務中犯更多錯誤,而美國被試在相對任務中犯更多錯誤[6]。隨后,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表明,相較于相容任務(如,美國被試做絕對任務,中國被試做相對任務),進行不相容任務(如,美國被試做相對任務,中國被試做絕對任務)更多激活了大腦有關注意控制的區域,表明不相容任務更具挑戰性[9]。
2.1.3 面孔構形
以上跨文化研究結果說明,感知包含焦點物體及其環境的刺激,東亞被試比美國被試更偏好注意環境信息。那對兩物體間的構形關系會不會也表現同樣的文化差異?由于物體構形關系提供了每個物體的位置信息,即除物體本身特性外的其它環境信息,故推斷東亞被試比美國被試更注意其關系。通過面孔識別任務(典型的構形加工處理)檢驗該假設,即東亞被試較美國被試對面部特征構形關系的變化更敏感。對面孔進行兩種不同的加工:一是空間變化,即改變面部各結構間的空間位置 (如眼睛與鼻子);二是面貌變化,即替換面部的某些結構(如眼睛與鼻子)[10]。實驗中既用到高加索人和日本人面孔,同時也都包含男女兩種類型。要求被試完成一致匹配任務,即對屏幕上依次呈現的兩張面孔又快又準確地判斷出是一樣的還是不同的。最后分別計算空間變化與面貌變化兩種條件下的正確率。
與預期一致,面孔的兩種變化與文化交互作用顯著。美國被試與日本被試在面貌變化條件下的成績差異不顯著,但空間變化條件下,日本被試比美國被試判斷更準確。且相較于日本被試,無論哪種變化條件美國被試反應都更慢,表明以上文化差異不是速度準確性權衡的結果。此外,完成判斷任務后,被試需要報告他關注面孔各個部分的程度。與一致匹配任務的結果一致,日本被試比美國被試報告更多注意構形方面,如外形和印象。為進一步探索認知的文化效應,選取了生活在美國的亞洲人。由于處在美國文化背景下,該部分亞洲人可能較少注意構形關系。結果如預期,生活在美國的亞洲被試在空間變化條件下的準確性與對面部各部分注意程度的自我報告中表現出居于日本被試與美國被試之間的成績。不少研究都表明文化環境影響個體注意面孔的構形關系,更進一步證實文化對認知的影響。
2.2 分類與歸因
注意方式的文化差異說明,呈現同樣的刺激,不同文化環境的個體產生不同認識。那么基于注意信息的其它認知加工也應同樣受到影響,如分類與歸因。西方個體注意焦點物體及其特性可能會依據物體特性對物體進行分類,而東亞個體注意物體間關系及其環境背景可能會依據物體間關系對物體進行分類。
已有研究證實,確實存在物體分類的文化差異,一些偏好使用分類學方式(taxonomic ways),另一些偏好使用主題相關方式(thematic ways)。所謂分類學分類,是基于物體的共同特征(如,是否物體間有共同的性質、外觀與功能);而主題相關分類是基于物體間空間、因果或暫時的聯系(如,是否物體間涉及一個主題或環境)。如,選擇三個物體中的兩個為一組(如,胡蘿卜、茄子和兔子)。依據分類學分類,選擇胡蘿卜和茄子,因為它們都是蔬菜;依據主題相關分類,則選擇胡蘿卜和兔子,因為兔子吃胡蘿卜。與預期相一致,美國被試更喜歡使用分類學方式,而中國被試更喜歡使用主題相關方式[11]。
注意不僅影響分類還影響歸因。引導西方被試注意行為者本身(如,燈光照亮行為者)較未引導的被試,其更傾向將行為者行為歸因于內在因素而非環境因素[13]。類似研究也表明,西方個體存在基本歸因錯誤,即過度內歸因(如,焦點物體的特性)及低度外歸因(如環境因素)傾向。另一方面,亞洲個體趨于感知焦點物體與環境間關系,可推斷其傾向將行為歸因于環境因素,且表現較弱或無基本歸因錯誤。相關研究已證實了該推論[12-17]。
其中較早表明因果歸因的跨文化差異的是,要求美國和印度被試敘述日常生活中較了解的某個人的行為,并且解釋為什么產生該行為。相較于印度被試,美國被試解釋行為(如,欺詐行為)更多涉及內在方面(如,競爭性人格),較少涉及環境(如,社會失業狀況)[2]。在中美被試間也發現了類似的文化差異,當權衡引發當下眾多謀殺事件的各因素時,美國被試認為內在因素(如長期心理問題)更主要,中國被試則認為環境因素(社會變革)更主要[16]。
由于西方個體更注重內在因素,假設西方個體較亞洲個體更易推斷行為者的性格。檢驗其可能性的方法之一是考察對詞匯的選擇,個體選擇描述行為詞匯的類型反映其潛在推斷[18]。形容詞(如,樂于助人的)傳達個體性格方面的信息,而動詞(如,幫助)提供個體周圍環境或個體與事物間關系的信息。西方個體比亞洲個體更偏好內在歸因,推斷其使用更多形容詞。相關研究表明,印度被試在描述他人時比日本被試使用更多形容詞、更少動詞[19];歐裔美國被試自發的從觀察到的暗指某些特性的行為推斷其性格,而亞裔美國人不會[20]。
2.3 辯證思維
若東亞個體關注物體間聯系,或許也能感知對立物間的關系且接受其矛盾的存在。之前所做的研究確實已證實以上猜想[21]。1999年Peng和Nisbett發現中國被試比美國被試更偏好包含矛盾關系的諺語(如,過于謙虛就是驕傲),其表明中國個體比美國個體更易接受甚至更偏好矛盾關系。接受矛盾關系的傾向被稱為“辯證思維”[22]。
辯證思維的另一個特征是認為現實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而非固定不變。Ji、Nisbett和Su于2001年在其研究中向被試呈現描述不同個體及其當前所處情境的情節,并要求估量未來事情變化的可能性。如,說一個高中生連續3年獲得國際象棋比賽冠軍,要求被試判斷該學生下一場與實力強勁對手比拼獲勝的可能性。相較于美國被試,中國被試認為結果變化的可能性更大,說明中國個體比美國個體傾向預期更大的變化[23]。
2.4 時間信息
以上探討的諸研究涉及的都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個體注意的是焦點物體還是環境信息。隨后研究進一步拓展到時間背景的注意問題,即發生在近期的事件被認為是焦點事件,而發生在較遠的未來或已經過去很久的事件被認為是環境事件。由于東亞個體較西方個體更注意環境信息,故其可能也更注意時間久遠的事件。Maddux和Yuki發現,西方被試注重對事件的鄰近影響,東亞被試則關注間接的、遠距離影響。如,判斷游戲中之前射擊對之后射擊的影響,歐裔美國被試認為前一次射擊對后一次射擊有更大影響,而亞裔美國被試認為前一次射擊對接下來的第六次射擊有更大影響。其結果表明注意近端事件還是遠端事件是由文化導致而非個體差異[24]。
以上對近端或遠端事件關注的文化差異可能是估量近端或遠端效益多少的文化差異。Shechter、Durik、Miyamoto及 Harackiewicz要求被試通過閱讀教學筆記及聽錄音磁帶學習一項新的數學技能(如,不使用紙筆如何解決兩位數的乘法運算),同時近端和遠端效益的處理也包含于教學筆記中。遠端效益條件下的被試被告知該技能用于未來 (如,事業打拼、畢業),而告知近端效益條件下的被試該技能適用于當前日常生活(如,計算技巧、管理個人資金)。學習過后,被試進行乘法運算。最后報告為解決問題所付出的努力及對該數學技能的感興趣程度。結果與預期一致。相較于近端效益條件,遠端效益條件下,東亞被試報告對技能更感興趣、學習更努力,而歐美被試結果剛好相反。該結果不僅表明對遠端和近端事件關注的差異,也體現了二者內在動機的差異,即東亞個體認為為遠端目標完成當前任務的收益更大;而西方個體則認為為近端目標完成當前任務的收益更大[25]。
遠端和近端背景關注的文化差異也體現在關注遠端和近端的過去事件上。在判斷發生于過去和現在的各因素對解決偷盜事件的關聯程度上,中國被試比毆裔加拿大被試評價與過去信息的關聯性更高,而兩組被試對與現在信息關聯性的評價無差異。以上發現都表明東亞個體比西方個體更喜歡關注過去和未來的遠端事件,而西方個體比東亞個體更喜歡關注現在和短期的近端事件,其文化差異是動機不同的結果[26]。
2.5 情境信息
提到分析性(analytic)與整體性(holistic)認知,就想到局部(local)與整體(global)加工。很多學者認為二者表述的是同一內容,只是表述方式不同。實際上,其為兩對不同的概念。整體(global)加工表示復合結構中高層次(如,運動)的某一內容(如,騎車),局部(local)加工則是低層次水平的內容(如,腳踏板)[27],其探討知覺層面問題。然而,二者又存在聯系。相較于西方個體,東亞個體有時更偏好局部加工,有時更偏好整體加工,其與情境信息于復合結構的層次水平分布有關。
若情境信息是復合結構的低層次內容,即存在于局部特性,整體(holistic)認知加工與局部加工相聯系,東亞個體傾向表現局部加工。如,動詞比形容詞表達更多的情境信息[18]。相比較而言,動詞位于復合結構的更低層次,日本個體比美國個體更喜歡使用動詞描述他人[19]。故該任務中,日本個體比美國個體表現更多局部加工。
若情境信息是復合結構的高層次內容,即存在于整體特性,整體(holistic)認知加工與整體(global)加工相聯系,東亞個體傾向表現整體(global)加工。實際上,眾多視覺注意任務中,情境信息往往提供高層次內容,其比構成圖像的某一特定部分更具有整體性。如,FLT任務中,關注線與正方形框架間的關系比只關注線需要更多注意信息的整體水平[6]。正如以上所介紹,東亞個體尤其在該種視覺注意任務中表現更多整體加工。此外,在Navon的整體局部任務中,整體特性的識別(如,由小字母組成的大字母復合結構中識別大字母)比局部特性的識別(如,由小字母組成的大字母復合結構中識別小字母)需要更多關注小字母間關系的結構[28]。進一步的研究在實驗過程中增加了啟動,獨立啟動組被試促進局部加工,相互依存啟動組促進整體加工[29],其表明:若情境信息(如,結構關系)存在于整體特性,那相互依存文化的個體更偏好整體加工[7]。
但二者似乎存在另外一種聯系。Brockmole、Castelhano與 Henderson在視覺搜索任務中,選取部分密歇根州立大學本科生,要求其在自然場景(如,客廳、書房)內搜尋字母模型T或L,按鍵反應并記錄時間。被試學習目標字母所在位置(字母置于桌子上)后,變換情境信息,或局部(近環境)(桌子類型的變化,如:圓桌換為方桌),或整體(遠環境)(場景的變化,如:客廳換為書房),完成搜尋任務。結果表明,改變整體(遠環境)信息比局部(近環境)信息讓被試反應時間受影響更大,即被試關注整體信息,更偏好整體加工。該研究中,自然場景可視為復合結構,字母所在位置桌子為自然場景的低水平內容,同時可作為場景的焦點物體 (或提供目標字母的近環境信息);而具體的客廳、書房為自然場景的高水平內容,同時可作為場景的環境(或提供目標字母的遠環境信息)[30]。由此,情境信息既存在于整體,也存在于局部,個體更偏好整體加工。要說明的是,該研究被試信息不明確,不能進行跨文化的差異比較。
通過以上分析,進一步推斷對情境信息的不同處理(整體或分析性的認知加工)表現在獨立或依存的認知文化差異中,整體或局部信息加工的文化差異取決于情境信息于復合結構的層次分布,證實獨立和依存的文化環境因素通過分析或整體性認知加工直接影響局部或整體加工。
3 文化對分析性與整體性認知影響的分析
之前的闡述已經說明確實存在跨文化的認知差異,同時該種差異也表明文化作用的重要性。那文化是如何起作用的?具體講,該種認知的文化差異是如何形成的?以下內容從遠端環境、近端環境及個人等三方面影響因素探討。
3.1 遠端環境因素
眾多研究者提出認知的文化差異根源于遠端社會環境的性質[31-34]。社會環境的跨文化差異之一便是個體從出生就接觸和融入社會關系,或獨立于社會關系,即依存或獨立的社會結構[31,35]。
首先,不同文化經過歷史的洗禮(如,生態結構、政治制度等)形成不同社會結構。如,Nisbett等人提出認知的東西方差異可追溯到古希臘及中國的生態結構差異,中國古代社會以大規模農業為基礎,涉及大量個體間的合作與協調,故社會關系相互依存,其可能促進了個體對關系與環境的關注,而古希臘社會基于放牧、捕魚和小型農業,未涉及大量的個體間合作與協調,故社會關系相互獨立,其可能有助于注意焦點物體[33]。不同國家其生態結構的差異形成不同的社會結構,相比非洲西部的滕內人(從事水稻種植且強調一致性),加拿大的愛斯基摩人(從事狩獵且擁有靈活的社會關系)表現出更多的分析性認知。以上差異可能包含種族或語言等方面,是否同一國家的不同區域也可以發現生態和認知間的相類似關系呢?通過比較土耳其個體,研究者發現居住牧區(強調自主性)比生活在農業及漁業區域(強調合作)表現出更多的分析性認知[36]。政治制度在結構的性質上也起一定作用,西方文化中,意大利南部(封建制度)及中歐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相較于意大利北部、西歐及美國,其社會關系長久以來更相互依賴。與該種社會結構差異一致,意大利南部被試比北部的進行更多的主題分類,顯示更多整體性認知[37]。俄羅斯、克羅地亞被試在視覺任務中比美國被試注意更多環境信息[38,39]。
再者,宗教信仰塑造社會關系模式,其反過來又影響認知加工。如,基督教徒(其關注個體內在狀態和信仰)比天主教徒在行為歸因上更可能認可內部歸因[40];荷蘭加爾文主義者(強調個人責任)比荷蘭無神論者表現出更多目標關注;相較于意大利羅馬天主教徒及以色列東正教猶太人 (強調社會責任),臺灣佛教徒(強調同情及社會關系)表現更多關系關注[41]。
最后,即使來自同一社會的不同社會階級,其接觸生活的社會環境也存在差異。中產階級的環境涉及更高的控制感和更多的影響環境,而工薪階層的環境涉及較低的控制感和更多的適應環境[42-44]。故中產階級的個體比工薪階層更傾向于情境解釋、專題分類、注意環境信息并認可辯證觀[38,45,46]。
3.2 近端環境因素
遠端環境塑造核心的社會結構及思想,反過來其又形成并反映于個人日常生活中 (即近端環境)。長期參與、反復接觸該種近端環境(如,社會實踐、文化產品等)可能會影響個體的認知處理。
一方面,可直接通過引導個體注意焦點或環境信息調節和引導認知。首先,認知風格反映在日常生活所從事的各種社會實踐中,如父母的作為與語言文化。美國母親與嬰兒玩玩具比日本的更可能給孩子標注玩具,從而突出物體[47,48];非語言交流中,美國被試的報告主要靠面部和身體線索(相對突出、明確的非語言線索),而日本被試的報告除了面部和身體線索,還主要包括情境線索(如:天氣、氣氛,不突出的情境線索)[49-51]。其次,認知風格也體現在日常生活所接觸的文化產品中。如,美國報紙報道體育事件比香港的更多提及人格因素[16,52],美國媒體報道奧運會比賽比日本的更多關注運動員自身,較少關注背景特征[53];文化產品不局限于敘述,也體現于產品和環境的視覺特性。如,東方傳統繪畫(包括肖像、風景)通常比西方的包含更多環境信息[54]。最后,認知風格也體現于感知的環境性質,如城市風貌。Miyamoto,Nisbett和 Masuda隨機選取日本和美國的公立小學、郵局及旅店,從三種不同文化的城市街道的前面、后面及公共設施進行拍照,結果表明被試認為日本的環境比美國的更復雜和模糊[55];進一步研究顯示,日本被試比美國被試在情境信息中發現更多變化,而對焦點物體的變化辨別中沒有文化差異,其表明接觸日本環境的個體更可能注意環境信息[56]。
另一方面,可通過間接的社會關系模式(依存或獨立)影響認知。首先,社會實踐與交往中,日本個體比美國的更多出席相關職能會議,更注意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維護[57]。其次,文化產品上,美國教科書傾向強調獨立主題(如:自我的方向、成就),而日本的則強調相互依存的主題(如:從眾、群體和諧)[58];美國雜志廣告與韓國的相比往往更強調獨特性,而韓國雜志廣告與美國的相比往往更強調和諧[59]。
3.3 個人因素
遠端環境與個體間存在相互作用。大量的跨文化研究已經表明相互依存或相互獨立的社會結構會影響和形成對應的個體心理傾向[31],而該個體心理傾向可能與個體認知方式相關,故研究者要考察二者間的關系。
方法之一便是啟動個體內部相互獨立或相互依存的心理傾向,考察是否會引發對應的認知處理。如,相較于第一人稱單數代詞(如:“I”“me”)啟動的相互獨立組被試,第一人稱復數代詞(如:“we”“us”)啟動的相互依存組被試在Navon的整體局部任務中更快地識別整體結構且更多地回憶目標位置[29];方法之二即為考察心理傾向與認知方式間的個體差異及其相關。然而,大規模的研究表明,二者間為弱相關[60,61]。 與大量跨文化研究所表明的相一致,心理傾向與認知方式一致是以群組特點出現的,并不存在于個體差異。
近端環境與個體間存在相互作用,即群體與個體的聯系。遠端社會結構塑造近端環境,其反過來影響置于其中的個體認知。事實上,同一文化的每一個體接觸的環境只是其中一部分且存在差異,故心理傾向與認知方式在個體水平上的相關較弱,但有較強的群體相關。
4 總結與展望
上文從眾多方面闡述了認知的文化差異。西方個體傾向關注焦點物體及其特性,基于特性進行分類,行為歸因于內在特性(即內歸因),且圍繞焦點物體與近端因素分析事件;而東亞個體傾向關注焦點物體與情境間的關系,基于該關系進行分類,行為歸因于環境因素(即外歸因),且以情境與遠端因素為中心分析事件。認知加工的差異受文化的調節影響,遠端環境如生態和社會政治環境等塑造一個社會的核心結構,該社會結構影響并反映于近端環境中(即個體的日常生活),通過參與和接觸該環境,根據其反映的文化模式調節個體的認知。
盡管國外相關研究已取得驕人成績,但仍有些許尚未解決的問題以及有待進一步探索發現的研究,綜合考慮國內有關研究較少的現狀,未來研究方向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第一,內容本土化。縱觀已有研究,不難發現有關東亞群體的調查研究多選取日本人作為被試,較少取樣中國被試。可將對中國個體的該種認知方式的檢驗作為研究開端,進一步明確中國個體是否確實是整體性認知。中華民族博大精深,56個民族匯聚成一個大家庭,但56個民族各自居住環境、生活習性以及風俗習慣等都存在較大差異,具有不同文化特色。陳中永、鄭雪進行了中國多民族認知活動方式的跨文化研究,其對國內粗耕農業、漁業、游牧、狩獵、林業、城市工業、城市商業等八個被試組的多民族認知方式進行了跨文化比較研究,結果表明一定的生態環境和生存策略要求其社會群體發展出與之相適應的認知操作和認知方式類型[62]。56種文化的56個社會群體是都傾向于整體性認知加工,還是有的進行分析性認知加工,這個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研究發現。
第二,拓展分析性與整體性認知范圍。現階段文化差異研究主要涉及注意、分類與歸因、時間信息以及辯證思維等方面,研究范圍較局限,其差異也可能表現在認知的其它過程。整體性和分析性認知屬于認知加工方式之一,眾多研究表明認知方式影響其它認知過程。創造性是個體復雜的認知功能之一,已有研究表明認知方式影響創造力水平[63]。另外,認知方式與問題解決可能也存在關聯,采用眼動追蹤技術進行的相關研究表明,不同認知方式個體在語篇閱讀中抑制外部干擾的能力存在差異[64]。鄧鑄與曾小尤提出認知方式對問題表征及其轉化有影響,而抗干擾能力及問題表征方式是解決問題的重要因素[65]。由此看來,整體性和分析性認知的差異還可能表現在創造性、問題解決等方面。
第三,借助認知神經科學技術探索分析性與整體性認知的腦機制。目前對分析性與整體性認知內容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行為測量法,較少采用眼動軌跡分析法及功能磁共振成像技術等。隨著認知神經科學的迅猛發展,事件相關電位技術、神經圖像分析、多導腦電圖和腦磁圖等技術被廣泛熟知與應用,為研究意識與腦的關系提供了有力手段,而認知又是意識活動的基礎,可以運用這些技術探索有關整體性和分析性認知相關內容以奠定其生理學基礎。已有研究顯示,進行有關任務會激活注意相關區域,至于兩種認知方式具體激活哪一區域,是否激活不同區域還尚未知曉。在生理與行為實驗中使用共同的操作方法對建立其生理機制十分重要。
第四,深入探討影響分析性與整體性認知的非文化因素。認知加工的差異不單單由文化一個因素導致,這其中還受多種因素的調節影響。國內對有關影響認知方式的因素做了深入探究。Riding等根據研究結果提出認知方式具有先天性,有先天遺傳的基礎[66];對藏、回、漢族小學三年級、五年級、初二、高二共1032名兒童認知方式的特點進行的研究顯示認知方式的年齡差異顯著[67];對軍校學員認知方式的相關研究得出以下結論:不同學科傾向、專業訓練因素對認知方式形成有重要影響。故需要進一步研究文化認知加工差異的其它調節因素[68]。
第五,文化融合對分析性與整體性認知的影響。就現代社會發展狀況而言,居民城鎮化、出國留學訪學、移居國外等成為趨勢與熱潮。文化交流形式多種多樣,也越發頻繁發生,文化發展不再單一化,相繼而來的是多元文化融合發展。已有研究顯示,生活在美國的亞洲人其認知方式處于日本人與美國人之間的狀態[10]。但該方面相關研究并未引起足夠的關注,對于未來的研究發展方向,多元文化的認知研究將成為必然趨勢。
第六,探究分析性與整體性認知與其他認知方式的關系。國內有關認知方式的相關研究眾多,提到認知方式,最先想到的定是場依存—場獨立。自威特金及其同事(1954)首次提出場依存—場獨立認知方式概念后,經過不斷完善修正,威特金(1979)最終把場依存—場獨立性確定為人在認知活動中主要依靠外在參照,還是依靠內在自我的兩種對立的認知傾向。處于社會情境中的個體,相對而言自我本身是焦點目標,而其他構成自我與環境的聯系。場依存認知以外部為參照,即自我以外的其他,更注重關系;場獨立認知以內在為參照,即自我,更注重焦點目標。由此看來,其與整體性與分析性認知存在某種聯系。探究二者的關系及其他認知方式間的聯系,有助于更進一步理解其內涵與本質,揭示認知加工的作用機制。
1 Masuda T, Nisbett R E.Attending holistically versus analytically: Comparing the contexts sensitivity of Japanese and American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1, 81(5): 922-934.
2 Miller J G.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veryday social explana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4, 46(5): 961-978.
3 Chua H F, Boland J E, Nisbett R E.Cultural variation in eye movements during scene perceptio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5, 102 (35): 12629-12633.
4 Masuda T, Ellsworth P C, Mesquita B, et al.Placing the face in context: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perception of facial erno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8, 94(3): 365-381.
5 Doherty M J, Tsuji H, Phillips W A.The context sensitivity of visual size perception varies across cultures.Perception, 2008, 37(9): 1426-1433.
6 Kitayama S, Duffy S, Kawamura T, et al.Perceivingan object and its context in different cultures:A cultural look at New Look.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3,14(3): 201-206.
7 McKone E, Davies A, Fernando D, Asia has the global advantage: Race and visual attention.Vision Research, 2010, 50(16): 1540-1549.
8 Savani K, Markus H R.A processing advantage associated with analytic perceptual tendencies:European Americans outperform Asians on multiple object tracking.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12,48(3): 766-769.
9 Hedden T, Ketay S, Aron A, et al.Cultural influences on neural substrates of attentional control.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8, 19(1): 12-17.
10 Mondloch C J, Le G R, Maurer D.Configural face processing developsmore slowly than featuralface processing.Perception, 2002, 31(5): 553-566.
11 Ji L J, Zhang Z, Nisbett R E.Is it culture or is it language? Examination of language effect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 categoriza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4, 87(1): 57-65.
12 McArthur L Z, Post D L.Figural emphasis and person percep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977, 13(6): 520-535.
13 Choi I, Nisbett R E.Situational salienc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correspondence bias and actor-observer bia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1998, 24(9): 949-960.
14 Masuda T, Kitayama S.Perceiver-induced constraint and attitude attribution in Japan and the US:A case for the cultural dependence of the correspondence bia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4, 40(3): 409-416.
15 Miyamoto Y, Kitayama S.Cultural variation in correspondence bias:The critical role of attitude diagnosticity of socially constrained behavior.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3 (5): 1239-1248.
16 Morris M W, Peng K.Culture and cause: American and Chinese attributions for social and physical event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4,67(6): 949-971.
17 Norenzayan A, Choi I, Nisbett R E.Cultur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social inference:Evidence from behavioralpredictionsand lay theoriesofbehavior.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2, 28:109-120.
18 Semin G R, Fiedler K.The cognitive functions of linguistic categories in describing persons:Social cognition and language.Journalof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88, 54(4): 558-568.
19 Maass A, Karasawa M, Politi F, et al.Do verbs and adjectives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different cultures? A cross-linguistic analysis of person representa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6, 90(5): 734-750.
20 Na J, Kitayama S.Spontaneous trait inference is culture-specific behavioral and neural evidence.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1, 22(8): 1025-1032.
21 Spencer-Rodgers J, Williams M J, Peng K.Cultural differences in expectations of change and tolerance for contradiction: A decade of empirical research.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10, 14 (3):296-312.
22 Peng K, Nisbett R E.Culture, dialectics, and reasoning about contradiction.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1999, 54(9): 741-754.
23 Ji L, Nisbett R, Su Y.Culture, change, and prediction.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 12(6): 450-456.
24 Maddux W W, Yuki M.The “ripple effect”: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s ofthe consequences of events.Personality and SocialPsychology Bulletin,2006, 32(5): 669-683.
25 Shechter O, Durik A M, Miyamoto Y, et al.The role of utility value in achievement behavior:The importance ofculture.Personality and SocialPsychology Bulletin, 2011, 37(3): 303-317.
26 Ji L J, Guo T, Zhang Z, et al.Looking into the past:Cultural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past informa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9, 96(4): 761-769.
27 Forster J, Dannenberg L.GLOMOsys: Specifications of a global model on processing styles.Psychological Inquiry, 2010, 21(3): 257-269.
28 Navon D.Forest before trees: The precedence of global features in visual perception.Cognitive Psychology,1977, 9(3): 353-383.
29 Kuhnen U, Oyserman D.Thinking about the self influences thinking in general: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salient self-concept.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2, 38(5): 492-499.
30 Brockmole J R, Castelhano M S, Henderson J M.Contextual cueing in naturalistic scenes:Global and localcontexts.JournalofExperimentalPsychology,2006, 32(4): 699-706.
31 Fiske A P, Kitayama S, Markus H R, et al.Thecultural matrix of social psychology.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8.
32 Nisbett R E.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 and why.New York:Free Press, 2003.
33 Nisbett R E, Peng K, Choi I, et al.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Psychological Review, 2001, 108(2): 291-310.
34 Varnum M W, Grossmann I, Kitayama S, et al.The origin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ognition:The social orientation hypothesis.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 19(1): 9-13.
35 Markus H R, Kitayama S.Cultural variation in the self-concept.Springer New York.1991: 18-48.
36 Uskul A K, Kitayama S, Nisbett R E.Ecocultural basis of cognition:Farmers and fishermen are more holistic than herder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8, 105(25): 8552-8556.
37 Knight N, Nisbett R E.Culture, class and cognition:Evidence from Italy.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Culture,2007, 7(3): 283-291.
38 Grossmann I, Varnum M W.Social class, culture,and cognition.SocialPsychological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011, 1(3): 81-89.
39 Varnum M E W, Grossmann I, Katunar D, et al.Holism in a European cultural context: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style between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s and Westerners.JournalofCognition and Culture,2008, 8(3): 321-333.
40 Li Y J, Johnson K A, Cohen A B, et al.Fundamental (ist) attribution error: Protestants are dispositionally focused.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12, 102(2): 281-90.
41 Colzato L S, van Beest I, van den Wildenberg W M,et al.God: Do I have your attention? Cognition,2010, 117(1): 87-94.
42 Lachman M E, Weaver S L.Sociodemographic variations in the sense of control by domain:Findings from the MacArthur studies of midlife.Psychology & Aging,1998, 13(4): 553.
43 Snibbe A C, Markus H R.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gency, and choice.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Psychology,2005, 88(4): 703-720.
44 Stephens N M,Markus H,Townsend S M.Choice as an act of meaning: The case of social clas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7, 93(5):814-830.
45 Kraus M W, Piff P K, Keltner D.Social class, sense of control, and social explana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09, 97(6): 992-1004.
46 Miyamoto Y, Ji L J.Power fosters context-independent, analytic cognition.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11, 37(11): 1449-58.
47 Fernald A, Morikawa H.Common themes and cultural variations in Japanese and American mothers’speech to infants.Child Development, 1993, 64 (3): 637-656.
48 Tardif T, Gelman S A, Xu F.Putting the “noun bias” in context: A comparison of English and Mandarin.Child Development, 1999, 70(3): 620-635.
49 Eggen A, Miyamoto Y, Uchida Y.Cultural differences in nonverbal communication.Unpublished manuscript.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Madison, WI, 2012.50 Ishii K, Reyes J A, Kitayama S.Spontaneous attention to word content versus emotional tone:Differences among three cultures.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3, 14(1): 39-46.
51 Tanaka A, Koizumi A, Imai H, et al.I feel your voice: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multisensory perception of emotion.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 21(9):1259-1262.
52 Lee F, Hallahan M, Herzog T.Explaining real-life events: How culture and domain shape attribution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6, 22(7): 732-741.
53 Markus H R, Uchida Y, Omoregie H, et al.Going forthe gold: Models ofagency in Japanese and American contexts.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6, 17(2): 103-112.
54 Masuda T, Gonzalez R, Kwan L, et al.Culture and aesthetic preference:Comparing the attention to context of East Asians and American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8, 34(9): 1260-1275.55 Miyamoto Y, Nisbett R E, Masuda T.Culture and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perceptual affordances.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6, 17(2):113-119.
56 Masuda T, Nisbett R E.Culture and change blindness.Cognitive Science, 2010, 30(2): 381-399.
57 Miyamoto Y, Schwarz N.When conveying a message may hurt the relationship: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difficulty of using an answering machin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6, 42 (4): 540-547.
58 Imada T.Cultural narrative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A content analysis of textbook sto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Journalof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12, 43(4): 576-591.
59 Kim H, Markus H R.Deviance or uniqueness, harmony or conformity? A cultural analysi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Psychology, 1999, 77 (4):785-800.
60 Kitayama S, Park H, Sevincer A T, et al.A cultural task analysis ofimplicitindependence: Comparing North America, Western Europe, and East Asia.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9, 97(2), 236-255.
61 Na J, Grossman I, Varnum M E W, et al.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not always reducible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0, 107(14): 6192-6197.
62 陳中永,鄭雪.中國多民族認知活動方式的跨文化研究.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5.
63 李壽欣,李濤.大學生認知方式與人際交往及創造力之間關系的研究.心理科學,2000,23(1):119-120.
64 李壽欣,徐增杰,陳慧媛.不同認知方式個體在語篇閱讀中抑制外部干擾的眼動研究.心理學報,2010,42(5): 539-546.
65 鄧鑄,曾曉尤.場依存性認知方式對問題表征及表征轉換的影響.心理科學,2008,31(4):814-817.
66 Riding R J.Cognitive style: A review.In: Riding R J, Rayner S G (Ed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1: Cognitive Style.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0, 315-344.
67 陳妹娟,周愛保.認知方式、視錯覺及其關系的跨文化研究.心理學探新, 2006, 26(4): 42-44.
68 屈強.軍校學員認知方式與人格特質分析及其相關研究.山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
Abstract:Cross-cultural studies of analytic and holistic cognitive processing have been the focus of foreign research.After studying a large number of related foreign researches, authors discusse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analytic and holistic cognition on attention, classification and attribution, dialectical thinking, time and situation information and further analyzed the cultural factors which lead to the difference.Although the foreign countries have made some great achievements,we also have much space to develop it.The focus of research in the future is on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expanding the scope, cognitive neuroscience,and the influences of non-cultural factors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on analytic and holistic cognition.
Key words:cognitive process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analytic and holistic cognition
The 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 Analytic and Holistic Cognition
Dou Xueting,Zhong Jianjun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Hohhot 010022)
鐘建軍,男,副教授,博士。 Email:zhongjj70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