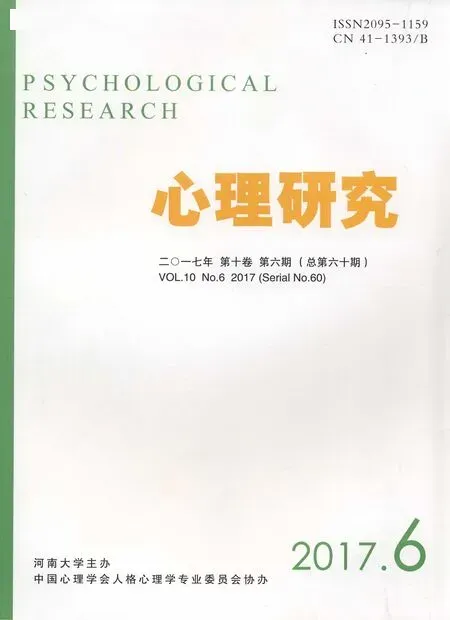情緒概念與垂直空間知覺的相互影響
張恩濤,李淑敏
(1河南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開封 475004;2河南大學國際教育學院,開封 475001)
情緒概念與垂直空間知覺的相互影響
張恩濤1,李淑敏2
(1河南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開封 475004;2河南大學國際教育學院,開封 475001)
情緒概念與垂直空間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是具身認知研究的熱點問題。大量研究從不同角度證實了情緒概念與垂直空間存在雙向交互效應,即情緒概念加工影響垂直空間知覺,垂直空間加工亦影響情緒概念加工。當前的主要爭議是,二者之間的聯系是基于身體經驗的直接聯系還是基于結構的間接聯系。未來研究應該從情緒概念與垂直身體姿態的相關性角度,建構更加整合的具身認知觀,采用多種技術系統地探討該效應的認知神經機制,并將這種研究拓展到應用領域。
情緒概念;垂直空間;具身認知
1 引言
概念(concept)是人類對客觀事物本質屬性的認識,是思維的基本單元[1]。概念如何表征是認知科學的核心問題。傳統的符號認知理論(symbolic cognition)認為,概念以獨立于感知經驗的抽象符號來表征。根據這種觀點,概念加工是符號之間相互鏈接的過程,并與感知覺加工相互分離[2]。與傳統的符號表征理論不同,具身認知(embodied cognition)理論認為,概念表征以感知運動經驗為基礎,概念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依賴先前感知經驗的激活[3,4]。當前,越來越多證據表明,概念理解與感覺運動加工之間存在緊密關系,其中情緒概念(emotional concepts)與垂直空間(vertical space)知覺的相互作用效應尤為令人關注[5-11]。
人類不僅要體驗事件帶來的情緒變化,而且要對各種復雜的情緒狀態進行概括和描述。在日常生活中,當我們描述自己的快樂情緒時,經常說自己好像活在天上,而當描述自己悲傷時,又常說自己仿佛跌入谷底;同樣當我們褒獎一個人時,總是向上豎起大拇指,而貶低一個人時,又會將拇指向下。這些日常現象預示著情緒表征與垂直空間之間存在緊密關聯。當前,大量研究證據表明,情緒概念加工與空間知覺加工之間存在相互作用的現象。一方面,情緒概念加工能夠影響空間知覺。比如,個體加工情緒詞“快樂”促進了對隨后屏幕上方目標的反應,加工情緒詞“悲傷”促進了對屏幕下方目標的反應[12]。另一方面,空間信息加工同樣能夠影響情緒概念加工和情緒體驗。比如當個體身體處于直立狀態或者知覺到向上運動的刺激時能夠促進對積極情緒概念的判斷[13],亦可以誘發更積極的情緒體驗[14,15]。 這種情緒概念表征與垂直空間知覺的相互作用效應被視作情緒概念具身性的關鍵證據之一,并成為研究情緒和認知具身性的有效途徑。
盡管大量研究表明情緒概念與垂直空間之間存在雙向聯系,但是研究者并不清楚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由于二者之間相互作用的相關證據并不一致,因此為了深入分析相關證據之間的分歧,研究者提出了許多理論觀點去解釋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這些理論觀點不僅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具身認知的理解,并且為未來研究提供了可以檢驗的理論框架。基于此,本文首先對情緒概念與垂直空間相互作用的基本理論觀點進行介紹,然后在總結相關重要研究證據的基礎上,重點對相關的理論解釋進行分析,最后展望未來研究應該關注的問題。
2 情緒概念與垂直空間之間相互作用的基本理論觀點
早期,關于情緒概念與垂直空間知覺相互作用的發生機制,存在兩種主要的觀點。一種觀點是 “先前感知經驗重新激活”[3,4]。 該觀點源自 Barsalou 提出的知覺符號理論(perceptual symbols theory)[3]。他認為,由于人們在情緒表達時伴隨了一定的身體活動(人們高興時經常身體直立、抬頭,人們悲傷時收縮身體、低頭),這種情緒發生時的身體姿態使垂直的空間表征成為了情緒概念表征的一部分[16,17]。按照這種觀點,情緒與垂直空間之間的聯系是以具體身體經驗為基礎的直接聯系,情緒概念的加工能夠自動激活其對應的空間表征。
另一種觀點是隱喻結構隱射觀點[18,19],該觀點源自Lakoff和Johnson的隱喻理論(metaphor theory)[17]。 該觀點認為,由于情緒本身較為復雜、難以概括,因此需要通過更加具體的維度(空間位置、大小、亮度)來表征[20],其中“上—下”圖式是表征情緒概念的基本方式之一,即存在“積極=上”和“消極=下”的隱喻關系。按照這種觀點,情緒與垂直空間之間的聯系是情緒的效價意義(積極和消極)與空間(上下或大小)之間的一般性聯系,而不必基于直接的、具體的身體經驗。
一般來講,兩種觀點都承認了概念加工以感知覺經驗為基礎,因此在一般的具身層面上,二者是一致的。但是二者的不一致之處體現在感知覺經驗與概念表征之間是直接關聯還是間接關聯上。具體來講,第一種觀點認為,情緒概念與空間的聯系是直接的、自動化的,情緒概念的理解能自動激活其對應的垂直空間知覺[21]。按照這種觀點,情緒概念理解中情緒—空間效應的產生并不依賴于情緒刺激和空間維度的任務要求。相反,第二種觀點認為,“上下”圖式為情緒概念提供了結構基礎,情緒與空間之間的聯系源自“積極對應上”“消極對應下”的隱喻映射,因此情緒概念與空間之間的聯系是間接的[18,19]。按照這種觀點,情緒與空間效應的產生依賴于情緒刺激的效價判斷和空間維度的任務要求,即需要通過效價判斷和空間判斷才能建立“積極=上”和“消極=下”的隱喻關系。
檢驗理論觀點正確與否,最好的方法就是通過實驗證據來講話,下面將總結相關研究證據發現的結果。讓人鼓舞的是,這些研究證據不僅深化了我們對上述兩種觀點的認識,并且催生了新的理論觀點。
3 概念與垂直空間之間的相互作用證據
3.1 情緒概念與垂直空間相互作用的產生是否依賴情緒刺激的效價判斷
當前,獲得情緒—空間效應的大部分研究采用了效價判斷任務[8,12,13],而在非效價判斷任務中該效應經常消失[22,23]。 比如,Brookshire, Ivry 和 Casasanto的研究要求被試采用手或腳的反應方式對呈現的具有情緒意義的詞匯進行歸類判斷[22]。結果發現,只有被試關注詞匯的效價意義時才能誘發情緒—空間效應,而當被試關注詞的顏色時,該效應消失。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情緒—空間效應的產生依賴于情緒概念的效價判斷。與之相反,Gozli等人的研究卻發現在非積極和消極的判斷任務中 (情緒和中性判斷任務),個體理解情緒刺激仍然對空間知覺和眼動反應產生影響[9,10]。需要指出的是,在這種情況下,情緒對空間的影響往往只出現在積極情緒刺激下,而負性情緒刺激并未誘發類似的情緒—空間一致性效應。
對比上述不同的研究證據,我們發現,大多支持情緒—空間效應具有效價判斷依賴性的研究使用的實驗材料是具有情緒效價意義的一般詞 (英雄),而反對性證據使用的情緒刺激是與垂直身體姿態直接關聯的情緒詞(比如快樂和悲傷)。這些發現預示著不同情緒刺激條件下情緒—空間效應可能并不相同。
3.2 情緒概念與垂直空間相互作用的產生是否依賴空間維度的任務相關性
當前,研究者采用空間 Stroop任務[12]、空間線索化任務[10]、Simon 任務[8]、啟動任務[13]均發現了情緒與空間的一致性效應[12,23]。由于在這些實驗任務中,空間維度信息并非是反應目標,所以起初大多數研究者均認為,情緒—空間任務效應的產生并不依賴空間維度的任務相關性。但是隨后的研究指出,空間維度的刺激凸顯性可能影響了該效應的產生。比如,Meier和Robinson將情感詞(英雄或者騙子)隨機呈現在屏幕上方或下方,詞出現前,會出現“+++”的注意線索,提示詞的出現位置[12]。研究發現了空間位置與詞的意義之間的交互效應,即盡管詞的位置信息與當前任務無關,但是被試對呈現在屏幕上方的積極詞反應更快,對呈現在屏幕下方的消極詞反應更快。但是,Santiago等人的研究發現,當注意線索“+++”消失時,該效應也消失[23]。 這說明空間維度的刺激凸顯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情緒—空間效應的產生。
另外,我們發現,在空間維度的刺激凸顯性較低的空間Stroop任務、空間線索化任務中情緒—空間效應并不穩定,表現為效應缺失或只出現在積極情 緒刺激下[10,23],而在空間維度較為凸顯的啟動范式和Simon范式下情緒—空間效應則更加穩定和對稱[8,13]。
我們認為,空間Stroop范式和空間線索化任務下,由于屏幕下方的刺激的空間信息并不凸顯,因此導致了消極刺激與空間刺激交互效應缺失。而在啟動范式中,之前研究使用了空間方位詞“上下”或上下箭頭等空間意義凸顯的空間刺激,所以才產生了更加穩健的情緒—空間效應。總之,情緒概念與垂直空間相互作用的產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依賴空間維度信息的任務設定。
4 概念與垂直空間之間的相互作用的理論解釋
4.1 注意偏轉假設(attention-shifting hypothesis)
該觀點認為,由于人們在情緒表達時伴隨了一定的身體活動(人們高興時經常身體直立、抬頭,人們悲傷時收縮身體、低頭),這種情緒發生時的身體姿態使垂直的空間表征成為了情緒表征的一部分,因此情緒概念能夠與空間信息形成直接、穩定的聯系,情緒概念理解將自動激活其空間信息[16,17]。 根據這種觀點,加工“快樂”將自動導致空間注意向上偏轉,加工“悲傷”將導致空間注意向下偏轉。Gozli等的研究采用眼動技術發現,當個體加工“快樂”后,促進了快速掃描軌跡朝空間上方偏轉,慢速掃描朝空間下方偏轉[10],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空間注意偏轉假設。但是遺憾的是,該研究并未發現消極詞的空間偏轉效應。
4.2 隱喻結構隱射觀(metaphoric structuring view)
該理論認為,情緒—空間效應的產生源自效價與空間維度的隱射關系[18,19]。 概念隱喻理論認為,存在“積極=上”和“消極=下”的效價—空間隱喻方式,因此積極詞對應一個“上”的空間信息,比對應一個“下”的空間信息時,被試反應更快。按照這種理論解釋,情緒概念與空間的一致性效應依賴于個體對情緒概念的效價判斷,并且這種一致性效應普遍發生于一般的具有效價意義的刺激中,而不局限于一般的快樂和悲傷等情緒刺激。
這個理論解釋了一般概念的空間鏈接基礎。比如,我們將從現實世界中獲得的空間認知方式應用到認知的各個方面。比如,“上”“下”可以表示時間,如“上周”和“下周”;可以表示道德評價,如“高尚”和“下流”;可以表示權力大小,如“高官”和“平民”;可以表示情緒狀態,如“高興”和“低迷”。而大量研究也表明,表示抽象意義的詞匯,諸如權力詞、道德詞、宗教詞、情感詞都能產生類似的概念—空間交互效應[25-28]。這些研究證據似乎表明概念與空間之間通過隱喻結構可以產生間接的聯系。但是情緒概念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空間表征很可能直接成為情緒概念的一部分,而不需要借助于隱喻結構。
4.3 語言的共同發生理論(linguistic co-occurrenc theory)
該理論認為,語言的組織本身就反映了具身關系,即知覺關系被編碼在語言中(即詞序反映了空間知覺關系),個體能夠有效地利用語言線索進行概念理解,主張用語言頻率來解釋概念與空間之間的交互效應。該理論認為,情緒—空間效應源自情緒詞與空間詞之間同時出現的頻率[29,30]。 由于“高”經常與積極詞出現在同一語言情境中(”高興“即反映了這種聯系),“低”與消極詞經常出現在同一語言情境中(“低迷”即反映了這種聯系),因此情緒—空間效應反映的是語言聯系而非概念聯系。由于大部分研究都采用詞匯刺激,因此很難區分情緒—空間效應中的概念聯系成分和語言聯系成分。而事實上,有研究者認為,這兩種成分都應該存在,并且語言聯系本身可能就強化了概念層次的聯系[31]。
4.4 極性對應原理(polarity correspondence principle)
Lakens認為,一致性效應產生的原因并不是知覺或概念信息的相互干擾,而是刺激極性、反應極性以及刺激反應對應綜合作用的結果[24,32]。其基本假設為,個體對正極的項目反應更快。概念一致性效應發生在正性刺激與其知覺維度之間,而負性刺激與知覺維度效應并不明顯。如果消除正性刺激的凸顯性,將消除整個概念知覺一致性效應。Lakens將表示道德或不道德的詞(如慈善、貪污)或表示積極或消極意義的詞(如快樂、失敗)隨機呈現在屏幕的上方或者下方,讓被試進行相應的意義判斷任務[24]。在執行該任務前,被試首先接受一個類似的歸類任務其中一個條件下正性詞占75%,另一條件下負性詞占75%。在被試接受負性詞占優的練習處理后,一致性效應消失。在接受正性詞占優的練習處理后,正性詞出現一致性效應,負性詞一致性效應消失Lakens認為正性為顯著的極性,負性為非顯著的極性,但是兩者之間的對立才是產生一致性效應的基礎。
我們認為極性對應原理是一般的原則,但是并不能以此否定詞匯空間效應中存在的知覺信息的激活。另外,極性對立原則可以預測促進效應,但是并不能預測干擾。此外,Ansorge等人的研究使用啟動效應來研究情緒效價—空間效應[13],發現即使空間詞(上、下,高、低)閾下呈現,仍然能夠促進情緒的加工,并且不管“上”與“積極詞”還是“下”與“消極詞”都能產生意義啟動,這與Lakens的理論預測并不一致[24]。因此,單純的極性對立并不能很好解釋詞匯空間效應。
5 小結與展望
當前,情緒概念與垂直空間之間的交互效應被作為一種重要的平臺來探索概念如何表征的問題。研究者根據不同研究范式下得到的結果提出了各自的理論觀點。注意偏轉假設強調情緒概念加工中空間信息的自動激活,但其研究證據可能局限于快樂、悲傷等特殊意義的情緒概念,而不能推廣到其它更為一般層次的情緒概念;源自概念隱喻理論的隱喻結構觀強調概念的二元結構與空間的二元結構產生的一般性鏈接,其鏈接過程可能依賴于實驗任務。而語言共同發生理論和極性對應理論則否認詞匯空間效應產生的空間信息激活的基礎,轉而從詞匯的語言學特點(詞頻、詞序)和極性對應的角度來解釋詞概念—空間效應產生的基礎。
根據已有的研究,我們認為當前的理論都不能很好地解釋當前的研究結果。此外,回顧文獻我們發現,當前研究一方面大多基于行為范式,另一方面這些研究在應用層次上少有建樹。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們對情緒概念—空間效應的探討。基于此,我們認為,未來研究應該從理論建構、神經機制和應用研究三個方面進一步深入拓展。
5.1 理論構建
情緒概念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具體和抽象概念[33,34]。 首先,由于情緒本身較為復雜、難以概括[17,35],因此情緒概念具有抽象概念的特點,需要更加具體的維度。其次,情緒概念本身又不像一般的抽象概念一樣,缺少直接的身體感知經驗,由于人們在情緒表達時伴隨了一定的身體活動 (人們高興時經常身體直立、抬頭,人們悲傷時收縮身體、低頭),這種情緒發生時的身體姿態使垂直的空間表征成為了情緒表征的一部分[36]。
我們認為在情緒概念理解中,情緒空間效應的產生可能基于雙重機制:即空間表征的自動激活和隱喻映射關聯。具體而言,如果在某種情緒概念獲得的過程中,伴隨著典型直立向上的身體活動(比如,快樂),那么在該情緒概念的理解中,情緒概念與空間的交互效應可能源于自動激活的空間表征與空間維度的交互影響;如果在某種情緒概念獲得的過程中,并沒有伴隨典型向上的身體活動(比如憤怒),那么該情緒概念與空間交互效應的發生可能源自隱喻映射。
5.2 神經基礎
具身認知理論的核心觀點認為,概念知識表征存在于感知運動系統中。根據這種觀點,情緒概念的理解需要情緒表達時涉及到的感知運動系統的重新激活。Quadflieg等人采用腦成像技術(fMRI)比較了被試在對情緒意義詞(生日、音樂和死亡、災難)進行效價判斷(積極或消極)、對物體詞(閣樓和地下室)進行空間位置判斷 (在現實中出現在視野的下方或上方)和對幾何圖形進行位置判斷(圓圈出現在水平線的上方或下方)時的大腦活動[37]。研究發現,在幾何圖形位置判斷中激活的頂下小葉區域(inferior parietal lobe)同樣在對物體詞和效價詞的判斷中被激活。需要指出的是,物體詞調節頂葉激活的程度與其視覺任務成績相關,而情緒詞與視覺任務成績沒有相關性。這說明物體詞加工可能激活了真實的空間體驗,而情緒詞可能只是激活了抽象的空間圖式表征。
另外,Xie等人采用一般意義上的具有情緒意義的效價詞作為實驗材料,發現了情緒概念理解影響了隨后空間目標的P200的加工[38]。類似的研究,Zhang等人的研究使用上下箭頭作為啟動刺激,情緒標簽詞作為目標刺激,發現空間啟動影響了隨后情緒詞的P200、N400以及LPC的加工[39]。綜上所述,由于fMRI和ERP技術的本身問題,我們并不知道空間信息的激活是否為情緒概念理解的必要階段,未來研究應該結合TMS技術對該問題進行探討。
5.3 應用研究
當前的大多數研究主要聚焦于情緒概念與垂直空間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并未將其拓展到情緒本身和垂直空間在現實中的實際聯系上來。盡管Seno等人的研究發現個體知覺向上運動的刺激能夠產生更多的積極情緒體驗[15],但是我們并不知道這些結果是否可以解釋一些情緒調節策略。比如,當人心情低落時,希望站在高處。如果提高一個個體的身體位置可以改善一個人的情緒狀態,那么未來研究應展開一些針對抑郁癥患者的病理性研究,將有助于這些問題的解決。此外,將具身認知的觀點在應用層次上展開,也將促進一般研究者對具身認知問題的理解。
1 Tulving E.Organization of memor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2.
2 Fodor J A.The modularity of mind:An essay on faculty psychology.London: MIT Press, 1983.
3 Barsalou L W.Perceptual symbol systems.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999, 22(4): 577-660.
4 Barsalou L W.Grounded cognition.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8, 59: 617-645.
5 Amer T, Gozli D G, Pratt J.Biasing spatial attention with semantic information:An event coding approach.Psychological Research, 2017: 1-19.
6 Dudschig C,Lachmair M,de la Vega I.From top to bottom:Spatial shifts of attention caused by linguistic stimuli.Cognitive Processing, 2012, 13: S151-S154.
7 Dudschig C, Souman J, Lachmair M, et al.Reading“sun” and looking up: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on saccadic eye movements in the verticaldimension.PLoS One, 2013, 8(2): e56872.
8 Dudschig C, Vega, Kaup B.What’s up? Emotionspecific activation of vertical space during language processing.Acta Psychologica, 2015, 156:143-155.
9 Gozli D G, Chasteen A L, Pratt J.The cost and benefitofimplicitspatialcuesforvisualatten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2013,142:1028-1046.
10 Gozli D G, Chow A, Chasteen A L.Valence and verticalspace: Saccade trajectory deviations reveal metaphorical spatial activation. Visual Cognition,2013:1-19.
11 Gozli D G, Jay P, Zo? M K, et al.Implied spatial meaning and visuospatial bias:Conceptual processing influences processing of visual targets and distractors.Plos One, 2016, 11(3): e0150928.
12 Meier B P,Robinson M D.Why the sunny side is up:Associations between affect and vertical position.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4, 15: 243-247.
13 Ansorge U, Khalid S, K?nig P.Space-valence priming with subliminal and supraliminal words.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3, 4(2): 81.
14 Larson C L, Aronoff J, Steuer E L.Simple geometric shapes are implicitly associated with affective value.Motivation & Emotion, 2012, 36(3): 404-413.
15 Seno T, Kawabe T, Ito H, et al.Vection modulates emotional valence of autobiographical episodic memories.Cognition, 2013, 126(1):115-120.
16 Barsalou L,Niedenthal P M,Barbey A K,et al.Social embodiment.In B H Ross (Ed.), The psychology oflearning and motiv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003: 43-92.
17 Lakoff G,Johnson M.Philosophy in the flesh.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18 Boroditsky L.Metaphoric structuring: Understanding time through spatial metaphors.Cognition, 2000, 75:1-28.
19 Gentner D, Bowdle B, Wolff P, et al.Metaphor is like analogy.In D Gentner, K J Holyoak, & B N Kokinov (Eds.), The analogical mind: Perspectives from cognitive science.Cambridge, MA: MIT Press,2001:199-253.
20 Crawford L E.Conceptual metaphors of affect.Emotion Review, 2009, 1(2): 129-139.
21 Gallese V, Lakoff G.The brain’s concepts: The role of the sensory-motor system in conceptual knowledge.Cognitive Neuropsychology, 2005, 22: 455-479.
22 Brookshire G, Ivry R, Casasanto D.Modulation of motor-meaning congruity effects for valenced words.In S.Ohlsson & R Catrambone (Eds.), Proceedings of the 32n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Austin: TX,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 2010.
23 Santiago J, Ouellet M, Román A, et al.Attentional factors in conceptual congruency.Cog nitive Science,2012, 36(6): 1051-1077.
24 Lakens D.Polarity correspondence in metaphor congruency effects:Structural overlap predicts categorization times for bipolar concepts presented in vertical spac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012, 38: 726-736.
25 Chasteen A L, Burdzy D C, Pratt J.Thinking of God moves attention. Neuropsychologia, 2010, 48 (2):627-30.
26 Lu A, Zhang H, He G, et al.Looking up to others:Social status, Chinese honorifics, and spatial attention.Canadia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2014,68(2): 77-83.
27 Schubert T W.Your highness:Vertical positions as perceptual symbols of power.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5, 89: 1-21.
28 Meier B P, Hauser D J, Robinson M D, et al.What’s “up” with God? Vertical space a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divine.Journal of Personality&Social Psychology, 2007, 93(5): 699-710.
29 Louwerse M M.Embodied relations are encoded in language.Psychonomic Bulletin& Review,2008,15(4): 838-844.
30 Louwerse M M.Stormy seas and cloudy skies: Conceptual processing is (still) linguistic and perceptual.Front Psychol, 2010, 2(6): 105.
31 Slepian M L, Ambady N.Simulating sensorimotor metaphors:Novel metaphors influence sensory judgments.Cognition, 2014, 130(3): 309.
32 Lakens D.High skies and oceans deep: Polarity benefits or mental simula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11, 2(6): 21.
33 Altarriba J, Bauer L M.The distinctiveness of emotion concepts: A comparison between emotion, abstract,and concrete word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4: 389-410.
34 Altarriba J, Bauer L M, Benvenuto C.Concreteness,context availability,and imageability ratings and word associations for abstract, concrete, and emotion words.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Instruments, &Computers, 1999, 31(4): 578-602.
35 Wierzbicka A.Defining emotion concepts.Cognitive Science, 1992, 16(4): 539-581.
36 Niedenthal P M.Embodying emotion.Science, 2007,316(5827): 1002-1005.
37 Quadflieg S, Etzel J A, Gazzola V, et al.Puddles,parties, and professors: Linking word categorization to neural patterns of visuospatial coding.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011, 23(10): 2636-2649.
38 Xie J, Wang R, Chang S.The mechanism of valence-space metaphors: ERP evidence foraffective word processing.PloS One, 2014, 9(6): e99479.
39 Zhang Y, Hu J, Zhang E, et al.The influence of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n valence judgements: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2015, 27: 218-226.
Interactions between Emotional Concepts and Vertical Space
Zhang Entao1,Li Shumin2
(1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2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The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emotional concepts and vertical space is a central topic of study in embodied cognition.Previous work has shown that bidirectional associations of emotion concepts and vertical space, the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concepts influence perception of vertical space, this is true for the opposite.The core controversy is that whethe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motion concepts and vertical space is direct or indirect.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posture-specific of emotions 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spatial experiences (up or down) , the future study will integrate theories of embodied cognition,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cognitive mechanisms of this effect by using multiple techniques,and extend this effect into application area.
emotional concepts; vertical space; embodied cognition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 (31700952)、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 (2015-QN-365)、河南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青年基金(2014-JKJJ-04)
張恩濤,男,博士,碩士生導師。 Email:zhanget201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