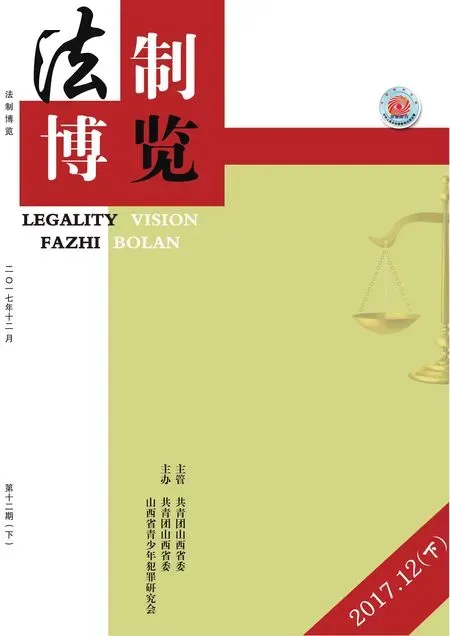民事訴訟中律師訴訟技巧的邊界
曹 力
北京市高朋(南京)律師事務所,江蘇 南京 210003
民事訴訟中律師訴訟技巧的邊界
曹 力
北京市高朋(南京)律師事務所,江蘇 南京 210003
民事訴訟法確定了訴訟誠信原則,該原則不僅約束訴訟參與人也約束法官。律師作為民事訴訟的重要參與人,由于其熟悉訴訟規則,更善于利用訴訟技巧而為當事人獲得訴訟利益。但律師訴訟技巧應當在訴訟誠信原則的邊界范圍之內進行,應當充分注意訴訟誠信原則對其行為之規制,避免不當的訴訟技巧行為而遭受民事制裁和紀律處分。
民事訴訟;誠信原則;律師;職業道德
民事訴訟法確立了當事人主義的抗辯式庭審模式,客觀上需要訴訟參與人尤其是律師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訴訟技能來實現委托人的訴訟目標。但與抗辯式庭審相配套,民事訴訟法確立了民事訴訟的誠實信用原則,并規定了對妨礙民事訴訟行為的制裁措施。近來,司法部和全國律師協會針對律師執業中不遵守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行為也加大了處罰力度。律師作為民事訴訟參與人如何恰當行使權利、最大限度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同時避免因不當執業行為而受到人民法院的民事制裁、司法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和行業協會的紀律處分,這應當成為執業律師關注的課題。筆者根據執業經驗,通過對法條的解讀、案例的分析試圖勾勒出民事訴訟中律師訴訟技巧的邊界。
一、律師應正確解讀民事訴訟誠信原則
民事訴訟法第13條規定了“民事訴訟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第56條規定了“第三人撤銷之訴”,第65條規定了“證據失權制度”,民事訴訟法第十章用9個條文(第109條至117條)規定了“對妨礙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四章用2個條文(第101條、102條)細化了逾期提供證據的民事責任;第113條規定了持有書證的當事人以妨礙對方當事人使用為目的,毀滅有關書證或者實施其他使書證不能使用行為的的民事制裁措施;第八章用19個條文(第174條至193條)對妨礙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進行了細化。對上述法條,司法實踐中一般按照如下原則進行適用:民事訴訟法有明確的法條規范的行為直接適用該等規定,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法條規范之民事訴訟不誠信行為則可以補充適用誠信原則。上述規定及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對于保障民事訴訟的有序進行、有利于法官發現案件事實起到了積極作用。
但是,訴訟誠信原則相對于辯論原則和處分原則,它只是一個起到平衡作用的原則,其適用要與具體案件掛鉤,離開了具體案件的具體情形,訴訟誠信就成為一宣誓性、內容空洞的模糊原則。反之,如果城市信用原則被濫用及泛化運用的話,就可能撼動辯論原則和處分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支柱性地位,無助于民事司法的良性發展,甚至會有重返職權主義老路上去的危險。①所以,在民事訴訟中,訴訟參與人仍有訴訟技巧可以施展的空間和使用的必要。民事訴訟實質上是一種對抗關系,訴訟法是爭斗的程序法。②而律師作為專業的法律人,其熟悉法律和民事訴訟規則,可以充分利用訴訟規則和自身專業技能從趨利避害的角度最大限度地維護和實現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但在這一過程,律師也最容易發生濫用程序的行為。針對這種現象,律師在訴訟中的活動不僅成為人民法院關注的對象,司法部和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也先后出臺通過了《律師執業管理辦法》、《律師執業行為規范》、《律師協會會員違規行為處分規定(試行)》等規范性文件,從律師執業紀律和律師執業道德的角度規范律師參與民事訴訟的行為。
所以,筆者認為:律師應當正確解讀民事訴訟誠信原則,了解其適用的規則,即不能因噎廢食、忽視律師訴訟技巧的使用,更不能肆無忌憚,濫用訴訟程序,應當找出訴訟技巧的合法邊界!
二、律師應正視真實義務責任
真實義務是要求當事人在訴訟中,不能主張已知的不真實事實或自己認為不真實的事實,并且不能在明知相對方提出的主張與事實相符或者認為與事實相符時,仍進行爭執。③如若當事人應負有真實義務,律師也應負有真實陳述義務。如果律師不負真實義務,律師的代理行為不僅無助于事實的查明,還會遮蔽法官的視線,這與民事訴訟的目的也是相違背的。④
德國《聯邦律師法》第四十三條a第三項規定:“律師不得于執業時有不客觀公正之行為。”日本《律師道德》第三條規定:“律師應精通法令和法律事務,誠實公正地履行職務;”第七條規定:“律師不得作偽證教唆、授意提交虛假證據或實施受懷疑之言行;”第二十五條規定:“律師鑒定不應囿于委托人的利害關系,而應根據事實作出公正判斷,并予率直的陳述。”美國《律師協會職業行為標準準則》第三節第三條A項一款規定:“律師應坦誠面對法庭,律師在明知的情況下,不得對法庭就有關事實或法律作虛假陳述”;第四款規定:“律師不得提供本人已知道是虛假的證據。如果律師在提交證據時并不了解其虛假性,到后來才知道,那么律師應該采取適當的救濟措施。⑤
然而,中國律師對于律師應負有真實義務的觀念認識卻欠缺一些,在訴訟代理中,要么無視所知悉的事實,要么將虛假陳述的責任推脫給當事人。筆者認為:律師只有充分認識到其應負有的真實義務責任,才能正確地運用訴訟技巧,將其控制在邊界之內。
在對訴訟誠信原則做了解讀、對律師真實義務責任進行明確的前提下,筆者將律師在民事訴訟中律師容易違反民事訴訟誠信原則的行為進行分析,以進一步說明律師技巧使用的行為邊界。
三、律師自認行為的法律后果
自認一般被界定為民事訴訟中的一方當事人對于另一方當事人主張的對其不利的案件事實,承認其為真實的訴訟行為。⑥我國民事訴訟法第51條規定,“原告可以放棄或者變更訴訟請求。被告可以承認或者反駁訴訟請求,有權提起反訴”。該規定將自認對象限定在對訴訟請求的確認,但是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中,將對事實的承認也確定為自認的對象。
律師在從事民事訴訟代理過程中,本應當遵從上述規定。然而,律師有時候會疏忽做虛假自認,或者為了達到自己的訴訟目的有意進行虛假自認。
(一)律師疏忽導致虛假自認
在一起房租租賃糾紛中,一審法院法官向被告(承租方)代理律師詢問承租的房屋是否均由被告(承租方)自用,被告代理律師未做詳細核實便承認了該事實。續而法官又詢問原告(出租方)代理律師,原告代理律師也予以了確認。基于上述事實,一審法院法官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間的租賃合同,并要求被告承擔違約責任。被告不服上訴至二審法院,并提出了被告所承租的部分面積已經轉租給了第三人使用的上訴事由。二審法院查明該事實后,將案件發回重審。在該案中,被告代理律師對事實的自認沒有認真與當事人核對、過于草率,一審法院在案件發回重審后,認為被告方對案件事實進行了虛假陳述,違反了訴訟誠信原則,擬對被告方進行處罰,被告方認為是律師當庭做的答復并沒有征得被告方認可,不應當處罰被告方,應當處罰律師本人。由此可見,律師在對案件事實做當庭陳述時應當做到知之為知之,不能隨意回答法庭提問,否則,產生了虛假陳述的后果并影響了訴訟程序的進行,律師就會成為民事制裁的主體。
(二)律師故意做虛假自認
律師故意做虛假自認大都是為了實現當事人的訴訟目標。比如商標侵權案件中,作為被告的侵權人為了不承擔侵權責任,聲稱其涉嫌侵權的商品自第三人處購得,申請追加第三人參加訴訟,第三人的代理律師自認涉嫌侵權的產品是自其處購得。后經法院查實,第三人之所以愿意承擔侵權責任,是因為第三人已經負債累累即將破產,被告與第三人之間從未發生過涉案侵權產品的買賣行為,第三人代理律師存在虛假自認行為,法院可以對其給予民事制裁。這里律師特別需要注意,如果虛假自認或者虛假陳述的行為最終導致了虛假訴訟的法律后果,律師及當事人還可能被追究虛假訴訟的刑事責任。
四、律師舉證行為的法律后果
民事訴訟活動就像一個斗獸場,各方訴訟參與人都在竭盡全力爭取打敗對方,而致勝的關鍵則是證據。舉證責任是民事證據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舉證責任的作用遠遠超出證據制度本身,對整個民事訴訟都有重大影響,素有“民事訴訟的脊椎”之稱。⑦因此,律師能否指導當事人搜集到充足的證據并通過舉證、質證活動來達到自己的訴訟目標就成為律師在民事訴訟活動中最為重要的工作。
(一)誘導(騙)取證
有時候律師發現某一對己方有利證據掌握在對方手中,需要通過誘導或者誘騙的方式取得。誘導的方式如通過電話錄音、短信聊天、郵件往來、微信等方式,在對方不易覺察時獲得該證據,或者獲得該證據在對方控制之下的證據。誘騙的方式比如假冒對方律師事務所助理人員或其他人員的身份騙取對方信任,從而獲得該證據或者該證據再對方控制之下的證據。
誘導取證可以作為律師技巧的運用,畢竟如實向法庭出示證據也是對方的舉證義務,并且誘導本身并未侵害對方合法權益。但是誘騙方式雖然取得的證據可能也是對方需要向法庭提交的證據,但誘騙行為屬于欺詐行為,所以,律師使用誘騙方式取得的證據不僅不應作為合法證據使用,同時,也違反了律師執業紀律和職業道德,應當受到紀律處分。
(二)釣魚式求證(Fishing Expedition)
釣魚式求證是英美法系為適應抗辯式庭審改良而采取的訴訟制度,其核心在于庭前公開證據,通過證據交換過程使得抗辯雙方獲得對方的證據信息,負有證明責任的一方往往在此過程通過提交混淆性的證據來誘導或者迫使對方提供出對己有利的證據。由于這一方式會將雙方的抗辯信息提前告知對方,為對方攻擊提供準備機會,所以,美國在9138年Federal Discovery Rules法案實施前,釣魚式求證是被嚴格禁止的。Stephen N.Subrin 在FISHING EXPEDITIONS ALLOWED: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1938 FEDERAL DISCOVERY RULES一文中寫到:Prior to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Federal Rules),discovery in civil cases in federal court was severely limited.The Federal Rules discovery provisions dramatically increased the potential for discovery.Authorized by the Rules Enabling Act of 1934(“Rules Enabling Act” or “Enabling Act”),the Federal Rules became law in 1938.The Rules Enabling Act was preceded by twenty-three year battle,spearheaded primarily by a 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ABA).⑧“釣魚式求證”在大陸法系稱為“摸索性證明”,它與傳統的證明方式相比具有三個比較明顯的特征,分別是探索性證明為一種試探性的證明方式、以啟動法院調查為手段、目的在于從對方處搜集事實和證據。⑨在我國目前的民事訴訟中,法官經常會安排庭前證據交換或者專門召開聽證挺,律師在上述活動中通過證據提交的先后、探索對方舉證目的和抗辯思路,然后取得對自己的有利的信息;在此過程中,律師還可以趁機申請法院調查令,從對方或者對方的相關方取得對己有利的證據。
所以,民事訴訟中舉證環節需要律師的技巧,該技巧的使用有利于人民法院發現真實做出公正判決,但該技巧的邊界同樣不得有違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并遵循訴訟誠信原則,律師提交虛假證據或者偽造證據、毀滅證據等行為應當嚴格杜絕。
五、律師拖延訴訟的法律后果
被告出于遲延履行債務之目的,或者為了等待更好的訴訟時機,律師常使用拖延訴訟的方法,比如:利用公告送達程序、管轄異議程序、質疑出庭人的身份、對證據進行真偽鑒定等。上述方式雖然都是法律所賦予給當事人的合法權利,但律師在使用上述技巧時并非沒有界限,如使用不當,被認定為故意拖延訴訟,仍可能會受到法院制裁。下面有幾個拖延訴訟的技巧應當予以小心注意:
(一)利用鑒定程序拖延訴訟
被告張某為拖延訴訟,對原告所提交的由其本人簽署的連帶責任保證函上的簽名的真實性提出了異議,認為“非本人簽署”,故申請人民法院對其簽名的真實性進行鑒定,人民法院接受了被告張某的申請,委托鑒定機構進行了鑒定,鑒定結論為被告張某的簽名屬實。
被告張某申請司法鑒定是其民事訴訟法賦予給其的合法權益,無可厚非。但從鑒定結論來看,被告張某向法庭所做出的“非本人簽署”的陳述,顯然是虛假陳述。法院可以根據民事訴訟的規定對其虛假陳述給予民事制裁。如果是律師提出的該訴訟技巧,則律師亦可能受到相應的民事制裁。
(二)利用文書公告送達程序拖延訴訟
被告張某和被告李某為同一案件的共同被告,張某系李某的姑媽,被告張某接受了人民法院送達的訴訟文書,被告李某不接受人民法院送達文書,導致文書不能送達,故人民法院對被告李某采取了公告方式送達文書。公告送達答辯期屆滿前一天,被告李某提出了管轄權異議,一審法院經審理駁回被告李某管轄權異議后,被告李某對管轄權異議裁定提起上訴。
從該案可以看出,被告李某在答辯期屆滿前一天提出管轄權異議是民事訴訟法賦予其的合法權利,無可厚非。但是,如果能有證據證明被告李某在公告送達的答辯期屆滿前就已經通過其姑媽被告張某獲悉了本案訴訟的有關文書,被告李某的行為有可能會被人民法院給予民事制裁,如果是律師提出的該訴訟技巧,則律師亦可能受到相應的民事制裁。
由此可見,濫用民事訴訟中的有關程序性規定,如被證實是惡意拖延訴訟的,仍有可能被人民法院給予民事制裁。
綜上所闡述,筆者認為:律師作為專業的法律工作者,其應當嫻熟地運用法律知識和法律技巧為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努力工作,同時,律師還應當恪守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誠信原則,遵守執業紀律和職業道德。律師的執業技能并不等同于律師的執業技巧,如果一味地追求執業技巧而不考慮其行為邊界,不僅不能實現民事訴訟目標,而且還可能受到民事制裁和紀律處分,尤其是本文特別指出的“自認”、“舉證”、“拖延訴訟”等訴訟環節,律師更應行為謹慎!
[注釋]
①王福華.民事訴訟誠信原則的可適用性[J].中國法學,2013(5):158.
②王福華.民事訴訟誠信原則的可適用性[J].中國法學,2013(5):154.
③吳英旗.律師真實義務研究—以民事訴訟為視角[J].行政與法,2015(11):87.
④吳英旗.律師真實義務研究—以民事訴訟為視角[J].行政與法,2015(11):88.
⑤吳英旗.律師真實義務研究—以民事訴訟為視角[J].行政與法,2015(11):88.
⑥全亮.被告人自認事實免證研究[J].西華大學學報,2013(11):75.
⑦李浩.<民事訴訟法>修訂中的舉證責任問題[J].清華法學,2011(3):7.
⑧See:Stephen N.Subrin,FISHING EXPEDITIONS ALLOWED: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1938 FEDERAL DISCOVERY RULES,page 691,Volume 39,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⑨丁朋超.論民事訴訟中的摸索證明[J].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15,11,28(6):56.
D925.1
A
2095-4379-(2017)36-0023-03
曹力(1970-),男,漢族,江蘇南京人,碩士,任職于北京市高朋(南京)律師事務所,研究方向:公司法、合同法、投資與并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