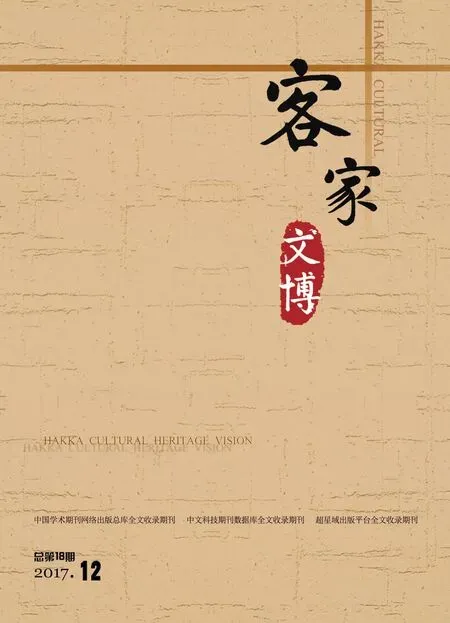梅州圍龍屋與福建土樓之比較研究
謝小康
2017年初春,筆者對福建初溪土樓群進行了考察,從而對土樓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關于梅州客家建筑的介紹,自上世紀80年代已頻見于各報章雜志,但真正稱得上“民居志”著作的當屬2011年出版的《客都家園》。該書較為系統地介紹了梅州境內8種類型的客家民居建筑,其中列舉了27個圍龍屋單體和4個村落(村中的民居不完全是圍龍屋)。圍龍屋和土樓分別為梅州(粵東北)和閩西客家民居的典型代表,它們二者在數量、類型、結構、文化價值和開發利用上有何不同?以下是筆者的分析。
一、數量與類型
廣東省梅州市客家建筑在中國民居建筑中占有一席之地,因為客家大遷徙的歷史源遠流長,從晉代(265-420年)開始至19世紀末和20世紀,由中原地區經福建、江西和廣東遷移到香港及南洋,甚至更遠的地方,遷途路徑與定居地的文化交流,再加上客家民風和習俗,形成了其建筑形式。實際上,關于梅州圍龍屋數量的說法至今仍有多個版本。如果按“據2009年普查,興寧現存較好的圍龍屋共有3041座,按照相關學術資料的統計口徑,興寧圍龍屋占梅州境內總數的60%以上”1這句話來推算,梅州圍龍屋的數量當在5000座上下;目前梅州官方媒體的表述是“據不完全統計,我市現存客家圍龍屋兩萬余座,遍布于各縣(市、區),一般都有二三百年乃至五六百年歷史”;應該承認,相較于福建土樓,梅州圍龍屋的普查覆蓋度、分類詳盡程度、代表性單體和群落的確認和宣傳力度都是遠遠不夠的。當然,因2009年申報(2012年獲批)“中國圍龍屋之鄉”工作需要,興寧市是梅州市下轄8個縣(市、區)中普查力度最大的,且首次對該市域內的圍龍屋劃分出七大類型:1、標準的半月形橫堂式圍龍屋,以寧新的東升圍、長興圍,福興的黃畿塘大王屋等為代表;2、棋盤式走馬廊的圍樓式圍龍屋,以坭陂的進士第、福公屋等為代表;3、四角帶碉樓的城堡式圍龍屋,以刁坊的棣華圍、黃宏昌,新陂的李振球故居、馨梓圍,興田的鳳翔圍等為代表;4、“八牡憬”鴇式圍龍屋,以羅崗的善述圍、翼寧圍、鴻吉圍等為代表;5、杠式圍龍屋,以福興的瑞征圍、寧中的寶慶圍等為代表;6、橢圓形圍龍屋,以羅崗的恒豐圍、黃陂的石氏中山公祠等為代表;7、并蒂蓮式圍龍屋,以永和大成村張屋為代表。筆者尚未對以上代表性單體做全面考察,無法對其劃分的科學性和完整性進行定論,但基本的原則是這些“屋”必須有“圍龍”(花胎)。興寧圍龍屋的分布以神光山前寧江平原較為密集,在24.08平方公里的區域內就有圍龍屋342座;而梅縣區南口鎮僑鄉村則是梅州圍龍屋最密集的行政村,在1.5平方公里范圍內分布著31座清末民初興建的客家圍龍屋。
福建土樓集中見于福建永定、南靖和華安3縣(區)。有資料顯示,福建土樓數量有30000多座,其中永定就有23000余座2。所以,福建土樓個體數量永定最多,這與明萬歷年(1573-1620年)以后,永定廣種煙草(條絲煙被譽為“煙魁”)有關。這種情況大致與梅縣清末民初因華僑多而建造的圍龍屋(包括中西合璧)數量較多相類似。從外形看,除了大家熟知的圓形和方形外(其實方樓的數量遠比圓樓多),福建土樓還有半圓形、橢圓形、四角形、五角形、八角形、日字形、回字形、交椅形、畚箕形、曲尺形、吊腳樓等十幾種類型,而從橫向結構看又分殿堂式、三合式、紗帽樓、走馬樓等多種建筑形式。
由此可見,無論數量還是類型上,福建土樓均多于梅州的圍龍屋。這一結果可能反映了以下幾個層面的涵義:一是福建土樓的普查力度遠大于梅州圍龍屋(不排除梅州圍龍屋多于5000座的可能);二是福建土樓的整體建筑質量好于梅州圍龍屋(已倒塌破敗的未列入統計的梅州圍龍屋數量不少);三是得益于“申遺”,福建土樓的科研成果比梅州圍龍屋豐富得多(目前出版的關于圍龍屋研究的專著不多)。顯然,普查、保護和科研都需要梅州政府和相關部門花費更多的精力。
二、結構與特點
不管是土樓或圍龍屋,其結構都有歷史演替進程。如土樓多圈層結構演變為單圈層(中空),或在底層開窗等;圍龍屋則從標準的前月池后圍龍演變為無月池、前圍龍或中西合璧等。圍龍屋的橫和圍與土樓的圈層是類似的概念,但如果從“屋”的嚴格意義來說,福建土樓是全圍,而圍龍屋是半圍,因為前面的半月形水池并非真正的“屋”。
土樓有圓、方之別(永定還表現為明顯的南北差異)。其中圓形土樓無疑是最為美觀的,其建筑結構一般以一個圓心出發,依照不同的半徑,一層層向外展開。其中心處為家族祠院,向外依次為祖堂、圍廊,最外一環住人。圍龍屋則因地形限制導致空間結構稍有不同,如屋后因地形所限不足以做標準的化胎和圍龍,也會用平直型圍屋代替;而屋前實在無法建半月型水池的則往往以墊腳屋形式代替。此外,在梅州與潮汕、福建、江西交界處,圍龍屋在內部結構和屋面裝飾上會略有不同。圍龍屋在結構上顯得稍為松散,其防御性明顯遜于土樓,所以門窗較土樓多,整體上是半開放性。這種前開敞后封閉的建筑空間形態,固然流露出客家人忠于傳統的固守與樂于新事物的接納;實際上也是因為梅州地區屬于純客家人聚居的中心地帶,沒有與外界沖突的緣故。
圍龍屋的禾坪與半月池之間有無墻、矮墻(花窗)和高墻(照壁)三種類型,后兩者往往在兩端各開一個小門,叫“斗門”。相對而言,圍龍屋的功能分區是橫向的,而土樓是豎向的,因此后者每戶便是自下而上成整體的“單元”,與鄰居“界線”分明;而圍龍屋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顯得更為協調和緊密。土樓的圈層內低外高,圍龍屋則由前而后(月池、禾坪、堂屋與花胎)逐次升高,且下、中、上堂高度也略有遞進。但圍龍屋前后高差不會很大,所以平面上很難認識其真面目。
在空間分布上,兩者稍有不同。就單體而言,土樓往往近河而建,因而內部往往不設水井;圍龍屋則依山而筑,這主要因其構筑圍龍(花胎)的需要,屋內必有水井。就群體而言,圍龍屋的密集程度之所以比不上土樓,蓋因為土樓不受方位限制,而圍龍屋則不然。當然,觀賞性的不同主要緣于其單體的高大程度,也正因為這個原因,圍龍屋前通常難以找到可以正面俯瞰全貌的觀景點(除非專門搭建平臺);而土樓群則曾被美國衛星誤以為是“核反應堆”。
就建筑與環境關系的處理而言,圍龍屋與自然山體結合更為緊密而合理,選址上依山就勢,建筑軸線順應山脈走向,建筑形態和空間也較為豐富。這種形態既不同于閩西圓形或方形的土樓的封閉獨立的形態,也不同于贛南、粵北圍子的需要大面積用地的需求,無疑是梅州客家人對環境適應和生活實踐積累的寶貴財富。
三、文化內涵與風水信仰
對于土樓的文化內涵,林基亮的概括可能最為全面:歷史悠久,具有文物性;高大雄偉,具有景觀性;功能奇特,具有研究性;裝飾考究,具有欣賞性;古俗新風,具有感召性;興詩立禮,具有文明性;輻射全球,具有效應性。就以上七“性”而言,圍龍屋與之是大體相當的,但比較之下,土樓在景觀性和效應性方面似乎更甚一籌,景觀性因為其高大,效應性則因其2008年“申遺”成功。
無論在閩西還是粵東北,客家人崇文重教都蔚然成風,所以在文化載體上,規模相當的土樓內往往設有書齋,圍龍屋則有私塾。相較于土樓,圍龍屋里走出的文人可能更多,類似“一門三進士”“一腹三翰林”“兄弟元魁”的佳話不勝枚舉。由于明代以來梅州文教興盛,使很多人獲得了功名,進而外出為官,成為品官之家,于是建起了相應規格的府第式圍龍屋,故“大夫第”“進士第”“太史第”等屋名比比皆是,留下的楹聯也琳瑯滿目。
宗教方面,兩地的客家人都是多神崇拜。不同的是,在每一座土樓乃至土樓里的每戶人家都供奉觀世音造像;梅州圍龍屋則除了講究對花胎以外的風水林保護外,對花胎前的“五方龍神”格外敬畏。“五方龍神”通常由在圍龍屋上堂的神龕之后、龍臺之下排列的五塊富有寓意的神秘石塊組成。這五塊石頭以不同的形狀相區別,分別代表“五行”,即:水、火、木、金、土。它們是構成宇宙的五種元素,圍龍屋擁有了這“五行”,也就擁有了與大千世界相一致的結構要素和結構秩序3。
客家人都十分信奉風水。土樓的建造主要依據八卦,非方即圓,線條一致,中間一般為實,也有空者,圓土樓采光更為科學。圍龍屋整體像是太極,前陰(月池)后陽(花胎),一律是橢圓,因為中間有堂屋,故而只能是實體。有學者指出,圍龍屋整體渾如雞蛋的橢圓形,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觀的反映。因為雞蛋形是天地未分時的宇宙混沌意象,蘊含著宇宙、天地、陰陽、道、本源等基本概念,同時還蘊含著從無到有、天地創生的宇宙起源論;前后半圓加之中間堂橫屋,形成天圓地方和“天、地、人”的結構。與土樓內部的平地不同,圍龍屋的花胎造型十分講究,要求隆起圓通(蘊意婦女十月懷胎的肚子),不得“硬底化”,需保持生機以化育胎息,故其上多鋪鵝卵石,象征百子千孫。也有人認為卵石是龍身鱗片。其實,無論圍龍屋還是土樓,古代陰陽思想在其中的投射都是顯而易見的。如“承啟樓”八邊各為一單元,并且每層每單元八間合為八八六十四間,則更明顯地體現了八卦變象化興的道理;另外,從它的住宿安排來看,上房正中供祖牌,則又順應了中為坤、坤為方、坤為陰的陰陽思想……
四、保護現狀與開發利用
圍龍屋和土樓都是客家民居的典型代表。其不僅是洞察客家民系意識的窗口,而且也是關照客家生活方式、經濟景觀、社會結構、風情習俗的具體途徑。通過幾次特別是最近一次福建土樓的考察不難發現,其最成功的保護利用方式無疑是通過“申遺”帶動文化旅游事業的發展,從而進一步促進土樓的保護利用。當然,樹立文化自信是至關重要的,而恰恰在這一方面成了梅州目前的短板。筆者沒有在土樓里對這一命題進行太多的民意調查,但是福建土樓能夠“申遺”成功,就已經足以說明問題。
據知情人士透露,早在福建土樓“申遺”之前就有專家建言梅州應抓住機遇開展圍龍屋“申遺”工作。按照世界文化遺產的評定標準,只要具備6項條件之一即可獲得批準,而梅州的客家圍龍屋,經比對符合其中4項,完全具備條件。但由于諸多原因,直到福建土樓成功“申遺”后的2009年,梅州政府才開始啟動“申遺”工程,而這時我們已經落后福建土樓11年。另外,江西贛南圍屋“申遺”工作也早在我們之前已悄然行動,并于2012年已成功入列國家文物局正式公布更新的45項《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上,這標志著贛南圍屋獲得了通向世界文化遺產的“準入證”。而梅州給出的時間表是“2017至2018年爭取完成客家圍龍屋列入《中國文化遺產預備名單》工作”,也就是說,我們落后贛南圍屋的“申遺”步伐至少5年時間,其難度可想而知。筆者以為,“申遺”的最大紅利并非使申報主體戴上“世遺”的帽子,而是整個“申遺”過程的反復宣傳讓其早已名揚天下。
那么,目前圍龍屋的問題在哪里呢?經過多年的調研發現,其主要表現在:一是產權復雜,政府與業主之間的權責和利益分配關系難以梳理;二是因為普查和宣傳力度不夠,從而缺乏有效的傳播觀念和手段。有一項調查顯示3,梅州當地人對圍龍屋完全不了解的占了23.6%,只了解一點點的占了58.8%,而很了解的幾乎全是老一輩的人。如此狀況的“文化自覺”顯然與福建土樓不可同日而語。誠然,大部分客家人只知道圍龍屋是梅州的特色民居,但對圍龍屋的結構特征及其蘊含的文化事象知之甚少,以致于在保護方面顯得麻木,甚至有隨意破拆改建的傾向。因此,無論政府還是宗族層面都必須引導人們樹立對傳統民居、傳統村落、重點文物的敬畏之心,并自覺加入到保護隊伍中來。除此之外,政府層面應對擬選“申遺”單體建筑和群落進行全方位包裝和宣傳,對三類村落(中國古村落、中國傳統村落和廣東省古村落)進行分類利用,并著重處理好民居保護、村民生活和游客體驗之間的關系。
五、結語
綜上所述,福建土樓和梅州圍龍屋,是客家先民在遷徙過程中為了適應當時的地理環境,基于生存和生活需要而形成的兩種代表性建筑類型,它們在建筑特色和文化價值上難分伯仲,各有千秋。就保護利用而言,福建土樓通過“申遺”使其綜合價值最大化的做法無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對于梅州圍龍屋而言,“申遺”顯然不是唯一辦法,與其一味步人后塵,不如在科學研究、旅游開發和村民生活三者之間尋找利益平衡點,這或許才是最佳選擇。
注釋:
1 引自http://www.meizhou.cn;
2 引自http://baike.baidu.com;
3 引自http://www.151313.com;
[1] 余志主編. 客都家園[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2] 龍炳頤. 中國梅州客家建筑之價值價值意義[A]. 余志主編. 客都家園[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3] 鄭煒梅.我市啟動客家圍龍屋申遺[N].梅州日報,2016-02-20(1).
[4] 梅州市城鄉規劃局主編.梅州古民居[M].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12.
[5] 肖文評. 梅州古民居概述[A]. 梅州市城鄉規劃局主編. 梅州古民居[M].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12.
[6] 程建軍. 客屬圍屋 唯我僑鄉[A]. 梅州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等編. 梅州嶺南近現代建筑圖集(1840-194 9): 236-243.
[7] 胡大新. 永定土樓:客家文化的象征[A]. 胡大新主編. 土樓與客家[C].永定縣博物館編,1998:5.
[8] 吳福文. 客家土樓的文化內涵[A]. 胡大新主編. 土樓與客家[C]. 永定縣博物館編,1998:20,29.
[9] 鐘德彪. 客家人的精神長城土樓[A]. 胡大新主編.土樓與客家[C].永定縣博物館編,1998:78.236-243.
[10] 譚元亨主編. 廣東客家史[M].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634.
[11] 林基亮. 文化內涵豐蘊的永定土樓[A]. 胡大新主編.土樓與客家[C]. 永定縣博物館編,1998:83.
[12] 廣東客家博物館編. 涯客家[M]. 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075.
[13] 房學嘉等. 客家文化導論[M]. 廣州:花城出版社,2002:24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