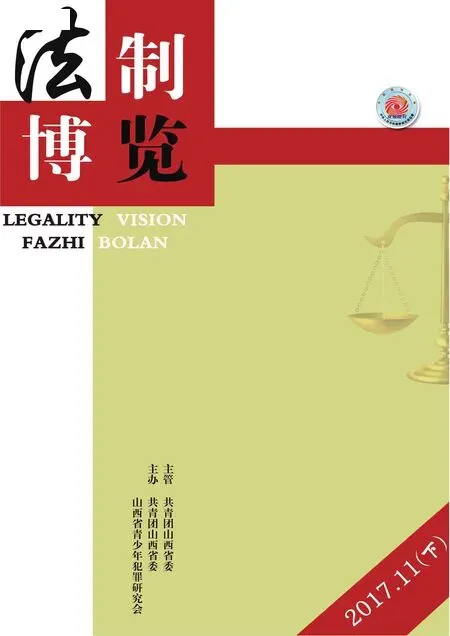政府環境信息公開的困境及對策
熊若蘭
江西師范大學,江西 南昌 330022
政府環境信息公開的困境及對策
熊若蘭
江西師范大學,江西 南昌 330022
當代環境問題層出不窮,如何處理人與環境的問題迫在眉睫,落實公民環境知情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中,政府環境信息公開作為實現公民環境知情權的重要途徑,得到了社會各界愈來愈多的關注。本文將從我國政府環境信息公開的概念及現狀入手,結合我國國情,淺析政府環境信息公開陷入的困境,并提出相應的對策。
政府環境信息公開;環境知情權;公眾參與;救濟制度
一、政府環境信息公開的現狀
首先,明確政府環境信息的概念。依我國《環境信息公開辦法》(以下簡稱《辦法》)第二條第二款規定:“政府環境信息,是指環保部門在履行環保職責中制作或者獲取的,以一定形式記錄、保存的信息。”明確了政府信息公開的主體及對象。所謂政府環境信息公開,即指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保部門及其他負有環保監督、管理職責的相關部門組織在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過程中,依職權主動或依申請被動公開環境統計調查、環境監測、主要污染物排放實際情況、污染防治、行政情況等內容。
(一)理論現狀
縱觀現有的相關立法,政府環境信息公開方面總體有進步,但仍存在缺陷。2015年1月新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新增了“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的內容。此章節賦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獲取、介入、監督政府環境信息的權利,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及其他相關部門應當如實公開環境信息,是綜合性環境制度的一大突破。此外,政府環境信息公開制度也體現在分散的部門規章之中,如《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環境行政處罰聽證程序規定》等法律法規,闡明了共享環境信息的意義,規范了環境信息公開程序等事項,為政府環境部門履行職責起到一定的規范指導作用。但目前我國關于政府信息公開的理論制度,仍停留在《辦法》這樣低層次、低位階的立法中,未形成完整體系,不利于環保部門發揮效力。
(二)實踐現狀
2017年4月20日,由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所頒布的《新<環境保護法>實施效果評估報告》引發了社會熱議。報告顯示,過去一年內我國的主要污染源監督性監測信息公開情況、各級行政部門對環保行政處罰信息及環保行政許可信息的公開情況仍然不樂觀。就不依法公開重點排污單位這一事項來說,在全國31個省級環保部門和70個地市級環保部門(共計101個調查對象)中,不依法公開重點排污單位名錄的地市級環保部門(包含不公開和不限時公開)共計56個,占到統計總數的76%,①此項數據揭示了環保部門對于信息公開的消極態度。此外,政府環境信息公開更新緩慢,公布的數據不完全、不真實等現象在實踐中仍普遍存在。綜上所述,現行制度下政府環境信息公開依然面臨的嚴峻挑戰。
二、政府環境信息公開的困境
(一)環境知情權的立法不明
從概念看,環境知情權是指公民與非政府組織收集、知悉本國甚至世界范圍內,與環境問題、政策有關信息的權利。《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奧斯胡公約》等國際公約對該概念做出深刻闡釋,我國的環境信息公開在立法層面上也借鑒了上述國際公約。然而當前我國對“環境知情權”的立法不明,僅在《環境保護法》的第五章中提出了類似“環境知情權”的概念,未制定出與該概念相對應的對策、救濟制度,在其他相關的法律法規中也未得到明確體現。導致該問題的原因主要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于“知情權”的立法不明,有關規定呈分散、列舉式的狀態,如《憲法》第四十一條,賦予了公民監督權,包括批評建議權、控告檢舉權及申訴權。雖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對公民“知情權”的保護,但并未直接對“知情權”給出規定,使得這一概念很難在高層次的環境法中得到體現,不利于公民對政府公開環境信息進行監督。
(二)公眾參與不足
公眾介入、監督政府環境信息的公開,對促進政府行政部門積極承擔責任有一定的作用。《環境保護部政府信息公開工作年度報告》近四年的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環境保護部共收到政府信息公開申請1076件,②之后呈逐年遞減的趨勢,直至2016年環保部僅收到政府信息公開申請499件③。在環境問題日益惡化的今天,為何公眾申請政府環境信息公開的數量反而會逐年遞減?筆者認為主要是由于當前政府信息公開中的公眾參與不足,其中兩大主體即民眾和非政府環保組織未完全發揮參與、監督的作用。首先,就民眾而言,大多法律監督意識淺薄,且由于民眾參與程序大多以事后為主,參與對象具有局限性等原因,通常難以獲取第一手信息,甚至出現民眾向政府申請環境信息公開“被忽略”的現象。其次,非政府環保組織開展的監督工作,大多集中在預防政府主體在環境保護領域的行為失靈上,而對政府信息公開的監督作用有限,使得政府環保部門與公眾之間的互動陷入惡性循環。
(三)缺乏專門救濟制度
完善并落實政府信息公開救濟制度,是保障公民環境知情權的關鍵。當前對政府環境信息公開的救濟主要通過行政救濟的途徑進行。依據《辦法》第26,27條的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認為環保部門不作為或侵犯其正當權益的具體行政行為,可以向上級環保部門舉報或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提起行政訴訟。此項規定是體現了政府環境信息公開不利的行政、司法救濟,但環保部門內部系統自我決策自我監督,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不利于公眾實現知情權的救濟。理論層面中,除《行政訴訟法》、《行政復議法》及其相關司法解釋之外,無與政府環境信息公開相關的專門立法,可見救濟制度的薄弱。同時在實踐中,環保部門不及時公布信息,或公布環境信息不完全不真實的現象常有發生,司法救濟權的缺失使得公眾在此種情況下處于絕對弱勢地位。
三、政府環境信息公開的對策
(一)規范“環境知情權”的立法制度
首先,確認“知情權”及“環境知情權”在《憲法》中的地位。知情權作為基本人權之一,與政府信息公開息息相關,然而當前相關立法中對以上概念的立法不明,不利于公眾知悉與環境相關的信息。因此要結合國情,學習借鑒相關國際宣言和其他國家地區對于“知情權”的規定。如《俄羅斯憲法》第29條第4款,“每個人都有以合法的方式自由探求、獲得、傳遞生產和傳播信息的權利”,直接規定了公民知情權,在立法中值得借鑒。且出于維護憲法體系的穩定性,降低立法成本的目的,可通過《憲法修正案》的形式來確立“知情權”的概念,形成強制力,引導地方各級環保部門積極履行義務,全面真實公布環境信息。其次,促進高階層信息公開法律法規關于“環境知情權”的立法發展,增加政府環境信息公開的透明度。在明確了憲法根據之后,分散的部門規章有章可循,逐漸形成規模效應,以進一步規范行政法體系中政府環境信息公開的程序事項。
(二)強化政府環境信息公開與公眾參與制度的銜接
公眾參與和輿論監督在政府環境信息公開起著綱舉目張的作用,加強二者之間的銜接尤為重要。首先,強化公眾參與的深度。地方各級政府環保部門和其他負有環境監督、管理職責的部門組織應重視與民眾、非政府環保組織的互動。通過降低公眾參與成本,來激勵公眾申請政府環境信息公開;創設考評機制,監督部門可定期收集公眾對環保部門及其行政人員做出的績效評價,或是搭建政府環境信息公開的信息反饋平臺④,通過良性互動,敦促政府信息公開監督體系的完善,以增強政府環境信息透明度和真實性。其次,優化公眾參與的程序。現階段公眾大多是事后參與,即政府部門往往是在環境問題產生后才希望公眾介入的,顯然不利于環境保護。因此要落實公眾的事前參與,健全環境立法聽證制度。在重大的環境信息決策前,可利用輿論宣傳等方式,引導公眾加入事前聽證的隊伍。最后,強化公眾的參與意識。如前文所提到的,近年來公眾申請政府環境信息公開的數量逐年減少,反映了公眾法律意識薄弱的困境。大力推動法律教育,推廣主流媒體輿論,從根本上提高公眾參與的積極性。
(三)落實政府環境信息公開的救濟制度
無救濟則無權利,完善政府環境信息公開的救濟制度,才能切實落實對公民環境知情權的保障。第一,完善環境公益訴訟體系。針對破壞環境、污染生態,侵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環境保護法》的第五十八條賦予了符合主體資格的社會組織提起公益訴訟的權利。然而當前理論層面上僅有這一條,無法支撐實踐中的具體訴訟問題。為了解決實踐中社會組織水平低、訴訟取證立案難等問題,建立相應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第二,規范普通環境行政訴訟制度。擴大行政問責的主體范圍,賦予公民更全面的追責對象來提出申訴,將本級或上級環保部門擴大至上一級人民政府;拓寬信息公開中可訴行政行為的范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政府信息公開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一條規定了五種可訴的具體行政行為,顯然不足以應對實踐中公眾的需求,因此筆者認為應拓寬可訴的具體行政訴訟范圍,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其中。第三,建立政府環境信息公開的國家賠償申請制度。國際社會中對于環境行政訴訟的救濟一般包括行政訴訟、行政復議和國家賠償,結合我國國情,完善國家賠償制度。然而當前公眾申請國家賠償仍以存在實際的具體的損害為前提,重構這一制度,任重道遠。
四、結語
當前社會的環境問題尤為凸出,政府積極履行環境信息公開職責的意義重大,同時以公民環境知情權為核心的政府環境信息公開制度也在不斷地改革完善。本文試圖回答三個問題:第一,什么是政府環境信息公開?第二,當前它存在了哪些問題?第三,如何有效解決上述問題?盡管本文的觀念仍有許多不成熟之處,仍然期待政府環境信息公開能置身于陽光時代中。
[注釋]
①2017年<新<環境保護法>實施效果評估報告>.
②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環境保護部政府信息公開工作2013年度報告[EB/OL].http://www.zhb.gov.cn/gkml/hbb/bgg/201403/t20140328_269812.htm,2017-9-28.
③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環境保護部2016年度政府信息公開工作報告[EB/OL].http://www.zhb.gov.cn/gkml/hbb/bgg/201703/t20170327_408849.htm,2017-9-28.
④沈霖.論政府環境信息公開——以環保主體互動理論為進路[D].寧波大學,2015.
[1]汪民霞.政府環境信息公開問題研究[D].西南政法大學,2015.
[2]沈霖.論政府環境信息公開——以環保主體互動理論為進路[D].寧波大學,2015.
[3]李廣宇.政府環境信息公開司法解釋讀本[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4]劉萍,陳雅芝.公眾環境知情權的保障與政府環境信息公開[J].青海社會科學,2010(2).
[5]范海玉.論我國政府環境信息公開問責制度——基于公眾參與外部問責模式的視角[J].法學雜志,2013(10).
X321;D63
A
2095-4379-(2017)33-0082-02
熊若蘭(1997-),女,浙江寧波人,江西師范大學,法學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