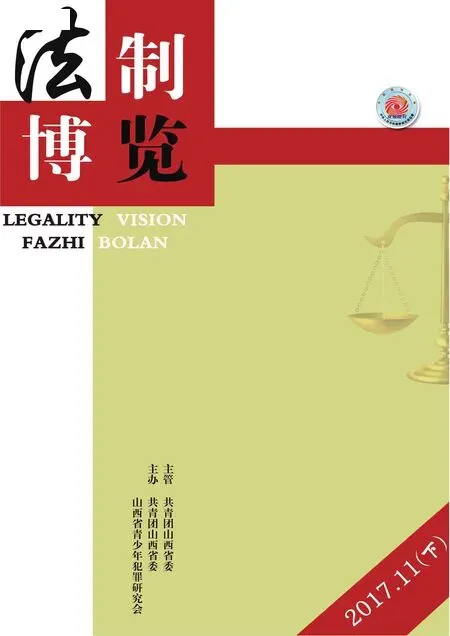毒品犯罪案件的若干問題研究
姚文忠 程鳳玲
湖北省鄂州市人民檢察院,湖北 鄂州 436000
毒品犯罪案件的若干問題研究
姚文忠 程鳳玲
湖北省鄂州市人民檢察院,湖北 鄂州 436000
通過實證分析并參閱最高法、最高檢指導案例,學習借鑒理論界專家學者的學術觀點,厘清司法實踐中一些模糊認識,總結經驗、統一思想,有效地打擊毒品犯罪。
半成品;運輸;明知;代購;容留他人;證據;審查
毒品已成為威脅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一大公害,毒品犯罪造成的嚴重危害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高度重視,成為當今世界共同關注的問題。①為研究和探討毒品犯罪,正確把握毒品犯罪案件的辦理,依法懲處毒品犯罪,維護社會穩定,本文從制造、運輸、販賣毒品罪及容留他人吸毒罪的相關法律適用出發,指出半成品應認定為毒品,但在量刑時可酌情考慮;對運輸毒品罪中“運輸”、“明知”等客觀行為進行準確界定;將牟取利益作為“代購型”販賣毒品罪的構成要件;將容留多人多次吸毒或造成嚴重后果作為容留他人吸毒罪的入罪門檻;同時指出販賣毒品罪不僅僅以毒品數量作為死刑適用的唯一標準等觀點,談談拙見,以期在司法實踐中形成共識。
一、制造、運輸、販賣毒品罪的相關法律適用問題
(一)制造的半成品毒品如何認定
制造的半成品毒品應認定為毒品。所謂半成品應是經過一定生產過程并已檢驗合格交付半成品倉庫保管,但尚未制造完工成為成品,其能再加工出成品,而不是無法再加工的廢液、廢料等。因此,在制造毒品犯罪中,對已經制成的半成品或粗制品毒品的,以犯罪既遂論。半成品毒品也視為成品毒品,一般不考慮純度,只按查獲的數量計算,但在量刑時根據毒品的含量不同予以酌情從輕處罰。如袁某、王某、左某制造毒品案。2015年3月至11月間,袁某、王某二人先后購買制毒原料、輔料、器具等物品,并到城郊某住宅小區內租房準備制造毒品,因二人不懂制毒技術,遂通過互聯網同左某聯系,三人共同制造毒品。制毒數日后被公安機關查獲,在制毒現場,查獲膏狀白色晶體和白色粉末四袋,共計25.129千克。經鑒定,甲基苯丙胺平均含量均在65.88%以上。后法院以制造毒品罪,分別判處袁某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王某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左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10萬元。
(二)運輸毒品罪中對“運輸”、“明知”如何準確認定
1.對運輸毒品罪中的“運輸”范圍,應以跨地區為運輸的標準,從同一區域的A地到B地,不應認定為“運輸”。運輸一詞的含義,現代漢語詞典中表述為“用交通工具把人員或物資從一個地方運往另外一個地方”。其內涵就是起到了中介的作用,運輸并不是行為的目的,而是一種手段,通過運輸行為使得人或物之間跨地域活動。②運輸毒品是指行為人明知是毒品而為他人運送,包括利用飛機、火車、汽車、船只等交通工具或采取隨身攜帶的方法將毒品從甲地區送到乙地區的運輸行為。轉移運送毒品的區域,應以國內的領域為限。運輸的形式一般為在境內自身攜帶、托人或者雇人攜帶,以及經偽裝后以合法的形式交給郵政郵寄、運輸部門或物流公司快遞托運等。
2.對運輸毒品中的犯罪嫌疑人不供認是“明知”毒品的,應以犯罪嫌疑人的客觀行為來推斷其主觀上的“明知”。“明知”應為知道或應當知道。就本罪而言,行為人要認識到自己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必須首先認識到自己運輸的對象是毒品。司法實踐中,犯罪嫌疑人常以不明知運輸的物品是毒品為由進行無罪辯解,對此審查認定往往成為定案關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2007年聯合發布的《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列舉了7種具體情形,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印發《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列舉了9種具體情形,對上述16種情形,犯罪嫌疑人不能作出合理解釋,且沒有證據證實確屬被蒙騙的,可以認定犯罪嫌疑人主觀上明知是毒品。如果有其他證據足以認定犯罪嫌疑人應當知道的,可以認定其主觀上明知。如被告人王某運輸毒品一案。被告人王某于2015年4月12日受付某的指使,攜帶付某給的三千元人民幣和手機(帶號)一部從湖北仙桃乘車到云南景洪,等待電話指令駕車回湖北仙桃。同月16日,王某接到素不相識的鄧某電話指令,到景洪某醫院與不認識的李某見面(約定暗號),在李某的帶領下,駕駛一輛大眾轎車至一木材廠附近后離開。次日凌晨,李某將8萬顆“麻果”(甲基苯丙胺片劑,重約8498.854克)藏入該車。當日上午,王某按鄧某的電話指令,檢查車內有無異味并清洗車輛,隨后駕車返回湖北仙桃。途中,王某經常接到鄧某詢問車輛行駛情況的電話,王某回仙桃后,按電話指令將車停放在某停車場后離開。王某到案后,辯稱其不知道車內裝有毒品。法院經審理后認為,王某從接受付某指使從湖北仙桃到景洪再從景洪駕車返回仙桃的整個過程,均呈現出異于正常活動的隱秘性,且眾所周知,云南景洪是全國毒品主要交易地之一,王某對其參與的整個異常活動應當有認識,其應當明知參與的是毒品犯罪活動。后以王某犯運輸毒品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并處沒收財產人民幣四萬元。
(三)代購毒品的行為能否認定為販賣毒品罪
代購毒品的行為應以行為人是否有牟取利益的犯罪目的作為認定其是否構成販賣毒品罪的前提條件。從“代購者”的主觀方面來看,一個具有完全民事、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他的每一種行為,都會具有較明確的目的。行為人受毒品吸食者的委托去代購毒品,其對毒品賣方的販賣行為系犯罪行為是明知的,明知賣方出售毒品的行為是犯罪,仍出于牟取利益的犯罪目的幫他人前去代購,在主觀上與賣方已構成販賣毒品“片面共同犯罪”之故意。所謂片面共同犯罪,亦稱為片面共犯,是指參與犯罪的人中一方有同他人實施犯罪的共同故意,暗中配合他人實行犯罪,而另一方卻不知道有人配合自己實施犯罪,因缺乏共同犯罪故意的情況。這種情況的處理方式在司法實踐中一般是對沒有共同犯罪故意的一方以單個犯罪定罪處罰;對有共同犯罪故意的一方,以他方的共同犯罪人論處。因此,代購毒品的行為在主觀上已具備構成販賣毒品罪所要求的條件。
(四)販賣毒品罪中對未查獲毒品實物的數量如何認定
販賣毒品案中對未查獲毒品實物的數量,應根據販毒者和購毒者的供述,結合本地區同類毒品數量的一般標準來綜合認定。販賣毒品罪的量刑最重要的標準就是毒品數量,毒品數量的多少決定量刑檔。未查獲的毒品證據已滅失,要從數量結果接近客觀事實、有利于被告人、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的角度,認定折算販賣毒品數量,實現刑法的公平正義。在販賣毒品犯罪中,作為重要證據的毒品未能查獲,毒品數量無法查實,被告人的供述與證人證言不一致等情況給販賣毒品犯罪的事實認定帶來困難,如果存疑就不予認定,勢必會放縱犯罪分子;如果全部予以認定,又恐會加重對被告人的處罰。所以在遇到此類情況要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本著“存疑時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對存疑事實不予認定或從輕認定。
根據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紀要》第二點指出“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資等證據已不存在,導致審查證據和認定事實困難,在處理這類案件時,只有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其他被告人的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誘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為定案的證據,僅有被告人口供與同案被告人供述作為證據的,對被告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要特別慎重。”由此可知,毒品犯罪案件中沒有查獲毒品實物的,毒品數量一般根據被告人一致的供述并結合相關證人證言、鑒定意見、書證等證據來認定,若被告人供述不一致或被告人供述與其他證據不一致的,則按照“就低不就高”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來確定。
二、容留他人吸毒罪的相關法律適用問題
容留他人吸毒罪的入罪標準問題,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三)》第十一條規定,將入罪標準歸納為五種情形:即兩次以上容留、一次容留三人以上的、曾因容留他人被行政處罰而再次容留的、容留未成年人的、造成其他嚴重后果或其他情節嚴重。但在司法實踐中,存在入罪門檻過低、打擊面過寬,且沒有區分情節,相關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定刑較輕,罪行不相適應等情形,不能適應現階段打擊該類犯罪的需要。從理論上說,只要容留他人吸毒,不論人數、次數、后果等均應構成犯罪,不符合刑法的謙抑精神。為有效遏制吸毒人員的滋生,最大限度地打擊毒品犯罪,應適時提高其入罪門檻。而人數及次數的判斷不僅關乎罪與非罪的問題,也是量刑的重要情節,因此,容留他人吸毒罪應提高入罪門檻,將容留多人多次吸毒或造成嚴重后果的作為入罪條件。
三、毒品犯罪死刑適用的相關問題
(一)毒品數量能否作為死刑適用的唯一標準
毒品數量是死刑適用的必要條件,但不能作為死刑適用的唯一標準,應結合毒品數量造成的嚴重后果以及是否為累犯、毒品再犯等各種情節進行綜合評判。一般來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判處被告人死刑:(1)具有毒品犯罪集團首要分子、武裝掩護毒品犯罪、暴力抗拒檢查、拘留或者逮捕、參與有組織的國際販毒活動等嚴重情節的;(2)毒品數量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并具有A:毒品再犯、累犯,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等,法定從重處罰情節的;B:多次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向多人販毒,在毒品犯罪中誘使、容留多人吸毒,在戒毒監管場所販毒,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實施毒品犯罪,或者職業犯、慣犯、主犯等情節的;C:其他從重處罰情節的;(3)毒品數量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且沒有法定、酌定從輕處罰情節的。
(二)毒品被及時收繳未流入社會能否作為從輕處罰的依據
在司法實踐中,販賣毒品罪的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往往以毒品被及時收繳未流入社會作為從輕處罰的依據請求法院對其從輕處罰。那么,毒品未流入社會能否作為從輕處罰的依據呢?筆者認為,販賣毒品的行為人為牟利高額非法利潤,公然藐視國家法律,無視社會公德,其主觀惡性極大,其為了販賣而先行買進毒品,再聯系購毒者進行販賣,一般數量較大,下家購毒者一般也是為了販賣而先買進,形成一張販毒網,涉案人員較長,涉案范圍較廣,社會危害性極大。根據法律規定,只要其實施了以販賣為目的的購毒行為即為販賣毒品罪的犯罪既遂。毒品被及時收繳未流入社會,只能說明偵查機關破案神速,有效防止其再次危害社會。因此,毒品被及時收繳未流入社會不能作為從輕處罰的依據。
[注釋]
①王艷平,周磊.跨境毒品犯罪的現狀、原因及趨勢分析[J].云南警官學院學報,2017(2).
②陳麗君.運輸毒品罪研究[D].云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D924.3
A
2095-4379-(2017)33-0107-02
姚文忠,男,湖北省鄂州市人民檢察院,刑事審判監督部負責人;程鳳玲,女,湖北省鄂州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