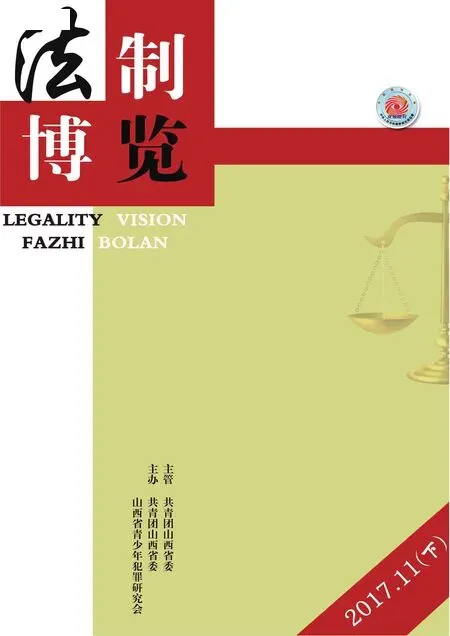村委會出租本村土地使用權村委會主任是否構成犯罪
趙穎莉
阜新市太平區(qū)人民檢察院,遼寧 阜新 123000
村委會出租本村土地使用權村委會主任是否構成犯罪
趙穎莉
阜新市太平區(qū)人民檢察院,遼寧 阜新 123000
隨著我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不斷加速和房地產(chǎn)市場的升溫,市場對建設用地的需求量也不斷加大,國有土地的供應量和價格已不能滿足建設單位的用地需求。很多用地單位將目光投向了農(nóng)村集體土地,特別是近郊農(nóng)村集體的土地。而近郊農(nóng)村青壯年大多進城務工,自己的土地大多租給別人耕種或閑置,如果用地單位能給出一個合理的價格,農(nóng)民肯定是樂享其成,認為這樣是一種最直接、最實惠的方式,而地方政府為發(fā)展本地經(jīng)濟,增加稅收,往往也倡導和鼓勵村集體出租土地,甚至在村集體和用地企業(yè)之間充當媒介,牽線搭橋。據(jù)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不完全統(tǒng)計,近年來因出租土地,村委會主任涉嫌非法轉(zhuǎn)讓土地使用權罪而被立案偵查的案件逐年增長,而理論界和司法實踐中卻對涉案的村委會主任是否構成犯罪有很大爭議,本文將結合真實案例,對于普遍性的村集體出租土地引發(fā)的法律問題、村干部涉嫌犯罪問題展開討論,以此引發(fā)專家學者對農(nóng)村土地制度的思考和對村干部命運的關注。
村委會;土地使用權;犯罪
案例:2008年5月1日,某市某村村委會主任馬某代表本村村委會,與某礦業(yè)有限公司簽訂了土地租用協(xié)議,協(xié)議內(nèi)容為:將該村集體農(nóng)用地共計28畝以30年的租期租賃給該礦業(yè)公司用于排放煤矸石,該礦業(yè)公司付給該村村委會租金人民幣118萬元。該款項由馬某家親屬及其他村民按土地份額分得。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后,檢察機關經(jīng)依法審查后認為,馬某違反土地管理法規(guī),未經(jīng)批準,以牟利為目的,將28畝農(nóng)用地租賃給他人使用,情節(jié)特別嚴重,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條之規(guī)定,構成非法轉(zhuǎn)讓土地使用權罪,并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訴。
法院經(jīng)審理后認為,土地使用權轉(zhuǎn)讓是指土地使用者將土地使用權再轉(zhuǎn)移的行為,包括出售、交換和贈送;倒賣土地使用權是指將土地使用權非法出賣給他人,或者為了出賣而向他人收買、租借土地使用權。土地使用權的轉(zhuǎn)讓、倒賣中均不包括出租土地的行為。該案中被告人馬某作為該村村主任,代表村委會與某礦業(yè)有限公司簽訂土地租用協(xié)議,并非轉(zhuǎn)讓也非倒賣,因此其行為不符合非法轉(zhuǎn)讓、倒賣土地使用權罪的構成要件,根據(jù)罪刑法定原則,馬某的行為不構成非法轉(zhuǎn)讓、倒賣土地使用權罪,一審宣告被告人無罪。
檢察機關經(jīng)過審查后認為,對土地的非法轉(zhuǎn)讓,應做廣義理解,應包括非法出租、非法抵押等,土地的非法出租是包含于非法轉(zhuǎn)讓中的一種形式,應涵蓋所有違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規(guī),將土地使用權永久或在一定期限內(nèi)轉(zhuǎn)移給他人的行為,將土地租期定為30年,實際是采取了“以租代賣”的方式將農(nóng)村集體土地出租給某礦業(yè)公司用于非農(nóng)建設(排放煤矸石)進而規(guī)避法律的行為,且達到情節(jié)特別嚴重,應構成非法轉(zhuǎn)讓土地使用權罪,法院一審判決在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應依法提請抗訴。
本案爭議的焦點是被告人馬某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
有一種觀點認為,構不構成犯罪是個嚴肅的法律問題,必須以有效的現(xiàn)行法為基礎和出發(fā)點,而不能拋開法律去談司法問題,無論是從法律規(guī)定的形式上,還是從被告人“違法”的情節(jié)上,都存在著諸多問題,按照疑罪從無的原則,應認為無罪,具體理由如下:
一、本案中,被告人馬某不是非法轉(zhuǎn)讓土地使用權罪的主體
刑法第228條規(guī)定:“以牟利為目的,違反土地管理法規(guī),非法轉(zhuǎn)讓、倒賣土地使用權,情節(jié)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非法轉(zhuǎn)讓、倒賣土地使用權價額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罰金;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非法轉(zhuǎn)讓、倒賣土地使用權價額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罰金。”刑法第231條規(guī)定:“單位犯本節(jié)第221條至第230條規(guī)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本節(jié)各該條的規(guī)定處罰。”
從上述法律規(guī)定可以看出,此罪是一般主體,單位可以成為犯罪主體,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可以構成該罪。很多人可能很自然地就認為村委會構成單位犯罪,村委會主任也構成本罪。但筆者認為,無論村委會還是村委會主任,能否成為本罪的主體都值得商榷。
(一)單位犯罪中的單位并沒有明確包括村委會
刑法第30條規(guī)定:“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guī)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一條:刑法第30條規(guī)定的“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既包括國有、集體所有的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也包括依法設立的合資經(jīng)營、合作經(jīng)營企業(yè)和具有法人資格的獨資、私營等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可見,村委會是不是單位,法律和司法解釋并不明確。而公安部2007年3月公布的《關于村民委員會可否構成單位犯罪主體問題的批復》中倒是有“對以村民委員會名義實施犯罪的,不應以單位犯罪論,可以依法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負責人員的刑事責任”的規(guī)定。當然,這一批復是否有法律上的效力,還值得探討。同時,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的規(guī)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更明確地說,村委會的領導機制是民主議定制,而不是領導負責制,換句話說,就是在這種決策機制下,不存在“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所以村委會是否是刑法意義上的單位并無法律依據(jù),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為罪。退一步講,本案中的村委會如果構成單位犯罪的話,由于本案中出租土地的決策都是通過村委會的集體討論,以村委會的名義作出的,根據(jù)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犯罪的罪責主要應由村委會承擔,起訴作為村委會成員的主任是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
本案中,作為村委會主任,被告人馬某也是農(nóng)民,應該說也不完全懂法。以為有鎮(zhèn)里領導支持、某礦業(yè)公司承諾辦手續(xù)、村委會集體討論、沒有謀取個人私利,租金該給誰給誰,自己只是代表村委會簽訂土地租用協(xié)議,所以,從主觀上,他根本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是犯罪,特別是出租土地的協(xié)議簽訂后,上級領導高興、老百姓高興,他有的可能只是使命感和成就感。但案發(fā)后他卻要對犯罪收入的總額負責而被處以高額的罰金,這違背了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
(二)被告人出租土地的行為并非必然出現(xiàn)違法的后果
按照馬某的供述,在與某礦業(yè)有限公司簽訂租用土地協(xié)議之前,該公司曾承諾所有手續(xù)都由其公司辦理。那么用地單位辦理用地手續(xù)的程序復雜,周期長,如果在用地手續(xù)辦理中被查處,可能就被認為是違法,如果辦妥了用地手續(xù),那就是合法的了。至于后期某礦業(yè)公司是否補辦了建設用地規(guī)劃許可證等相關用地手續(xù)則無相關證據(jù),也就是說,這些所謂的非法用地最后完全可能被合法化。
(三)出租土地的法律后果不應由村委會主任來承擔
按照《土地管理法》、《城市規(guī)劃法》和《建筑法》的規(guī)定,建設單位應取得建設用地規(guī)劃許可證、土地使用證后,再取得建設工程規(guī)劃許可證、施工許可證等一系列手續(xù),方可開工建設。也就是說,村委會雖然把土地出租給了用地單位,但用地單位只有在取得了一系列手續(xù)之后才能開工建設。用地單位在未取得這一系列手續(xù)的情況下就開工建設,其后果自然應由建設單位承擔,而不能轉(zhuǎn)嫁給出租土地的村委會及村委會主任。另外,國土和規(guī)劃監(jiān)察部門監(jiān)察不力,往往不能及時發(fā)現(xiàn)和查處用地單位的違法建設行為,對耕地的破壞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此檢察機關應在辦理案件的同時對相關單位下發(fā)檢察建議予以整改。
二、農(nóng)村集體組織出租土地在法律上存在合法因素
不得不承認,本案涉及的土地屬于被告人馬某所在的村集體所有,即被告人所在的村集體對本案土地享有所有權。而從法律上說,所有權屬物權范疇,是絕對權,是權利人對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民法通則》第71條規(guī)定:財產(chǎn)所有權是指所有人依法對自己的財產(chǎn)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物權法》第二條第三款規(guī)定:“本法所稱物權,是指權利人依法對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權利,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既然我們認可村集體對土地的所有權,就應該承認村集體對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村集體對土地的出租本身就是行使收益和處分(使用權)的權能。從這個意義上說,村集體出租土地的行為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近年來,甚至還有不少專家學者提出農(nóng)用地直接入市的建議。
當然,保護耕地的意義和必要性也不容質(zhì)疑,因此,保護耕地已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和法律制度,憲法和相關法律、法規(guī)中都有保護耕地的規(guī)定。正是基于此,有人認為被告人構成犯罪,村集體將耕地出租用于非農(nóng)建設侵害了國家利益,違反了刑法第228條(上文已詳述),土地管理法第31條:“國家保護耕地,嚴格控制耕地轉(zhuǎn)為非耕地”。第44條:“建設占用土地,涉及農(nóng)用地轉(zhuǎn)為建設用地的,應當辦理農(nóng)用地轉(zhuǎn)用審批手續(xù)。”
很顯然,同樣依據(jù)憲法和法律,我們對村集體出租土地的行為的合法性卻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不可否認,我國的土地法律制度存在著矛盾和缺陷,也體現(xiàn)出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于是,有觀點認為,當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發(fā)生矛盾和沖突的時候,應以國家利益為重,但物權法第4條規(guī)定:“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到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這一條被法律專家表述為物權的“平等保護原則”,即無論是國家的,還是集體的、私人的物權都應得到平等的保護,無所謂輕重。
該觀點中,被告人馬某的行為性質(zhì)同樣是依據(jù)法律卻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這種情況是由法律本身的矛盾和缺陷造成的,我們不能把這種矛盾和缺陷的不利后果強加在被告人身上。按照有利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刑訴理論,在我們的認識既可以得出有利于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結論,又可以得出不利于嫌疑人和被告人結論的時候,我們應該做出有利于嫌疑人和被告人的選擇,認定其不構成犯罪。
綜上,被告人馬某代表村委會出租土地,從犯罪的主體、動機和目的、犯罪后果等方面分析,馬某是否構成犯罪都值得探討。同時,我們也應考慮,現(xiàn)行土地法律制度是否需要修改,如何修改,以解決法律與現(xiàn)實之間的矛盾。
D922.3;D920.5
A
2095-4379-(2017)33-0113-02
趙穎莉(1974-),女,漢族,阜新市太平區(qū)人民檢察院,檢委會專職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