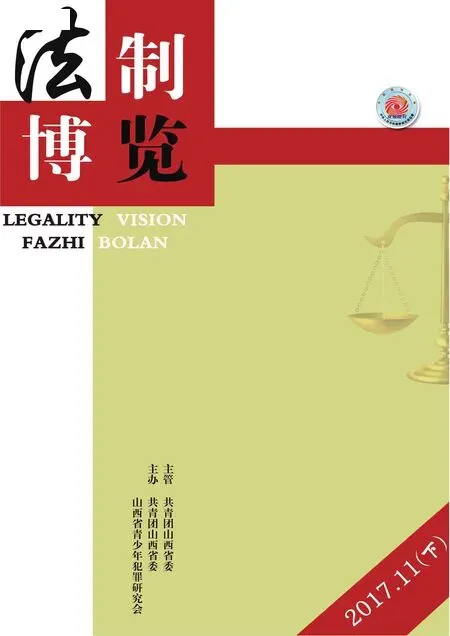淺析涉罪未成年人權益保護
吳 丹
湖北省鄂州市華容區人民檢察院,湖北 鄂州 436000
淺析涉罪未成年人權益保護
吳 丹
湖北省鄂州市華容區人民檢察院,湖北 鄂州 436000
通過對舊未成年人刑事訴訟制度存在的不足,指出新未成年人刑事訴訟制度的完善和突破。
不足;完善和突破;具體適用
一、原先未成年人刑事訴訟制度存在的不足
未成年人刑事訴訟制度是指向國家司法機關在辦理未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所適用的一系列訴訟制度。全國人大常委會相繼于1991年和1999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分別以法律的形式對違法犯罪未成年人進行司法保護并進一步加強預防未成年人犯罪行為,其中《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三十八條確立了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第四十二條確立了涉罪未成年人隱私保護原則。我國于1997年1月1日施行的舊《刑事訴訟法》中對于未成年人的刑事訴訟制度,能夠體現對涉罪未成年人權益特殊保護的條文僅有三處,即第十四條、第三十四條、第一百五十二條,均是作為一般性規定的例外補充而分散規定于有關章節。但我國對于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的處理在立法與司法層面仍缺乏系統性、完整性,沒有形成一套完備的訴訟制度體系來指導刑事訴訟涉罪未成年人的權益保護。由此導致的后果是,在具體的司法實踐過程中,涉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充分的保護。例如,我舊《刑事訴訟法》中沒有對涉罪未成年人的審前羈押出明確規定,僅《未成年人保護法》在第四十一條作出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對審前羈押的未成年人,應當與羈押的成年人分別看管。”但在實際監管,部分看守所并沒有對涉罪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實行區羈押,有的甚至將涉罪未成年人與成年人羈押在一個監室中。這種做法既無法切實維護涉罪未成年人的合法訴訟權益,容易對其身心健康造成巨大影響,不利于防止“交叉感染”,無法保障涉罪未成年人不遭成年犯罪的不良影響,甚至使未成年人向慣犯和累轉變。舊未成年人訴訟制度存在的不足將導致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中國家公權力過于強勢,易造成涉罪未成年人的訴訟權利被國家公權力所侵害,控訴方的力量和訴訟地位遠勝于抗辯一方,即便有審判方居中裁判,但仍無法有利保證司法公正。
二、現行未成年人刑事訴訟制度的完善和突破
(一)完善了涉罪未成年人特有的刑事訴訟權利
1.涉罪未成年人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
法律援助作為社會公益事業,是為了保障社會弱勢群體合法權益,能更好地維護涉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舊《刑事訴訟法》規定指定辯護的機關是人民法院,象僅限于未成年被告人,由人民法院直接指定律師未成年被告人提供辯護,且僅限于審判階段。這不利處在于,首先作為審辯雙方之間缺少中間機構作為中介,由法院直接指定會導致辯護一方喪失獨立性,進而影響司法公正性;其次辯護人律師介入涉罪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的時間較晚,特別是在當時“以偵查為中心”訴訟制度背景下,未能介入偵查、起訴階段,無疑對涉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十分不利,最終可能影響司法公正。新《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規定:“未成年涉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提供辯護”。將獲得法律援助的對象延伸到了未成年涉罪嫌疑人,相應地增加了檢察機關、公安機關作為指定辯護的義務主體,辯護方介入涉罪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的時間提前到了偵查階段,確保未成年人及時獲得法律幫助,并且在中間設置法律援助機構,保證了辯護方的獨立性,更好地保障涉罪未成年人的合法訴訟權,加強了辯護一方的力量和訴訟地位。
2.對涉罪未成年人逮捕措施的嚴格限制適用
逮捕是刑事訴訟中最為嚴苛的一種強制措施,在一定時間內剝奪涉罪未成年人人身自由使其與社會隔,容易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巨大傷害,不利于其正常成長。間接地導致一部分涉世未深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獲取了向著慣犯和累犯身份方向進行轉變的心理基礎。此舉亦加強了辯護一方的力量和訴訟地位。
3.分案處理和不公開審理原則
新《刑事訴訟法》在嚴格限制適用逮捕措施的基礎上,規定了對被拘留、逮捕和執行刑罰的未成年人與成年人應當分別關押、分別管理、分別教育。并根據其生理和心理特點在生活和學習方面給予照顧。分案處理原則的目的,就是為了使進入訴訟階段的未成年人免受來自成年犯罪人的不良影響。筆者于今年6月曾隨行前往武漢市公安局監管支隊調研全市看守所未成年在押人員羈押情況,絕大多數看守所內均設有未成年監室,單獨羈押涉罪未成年人,并定期組織未成年人進行文娛活動。新《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四條明確規定:“審判的時候被告人不滿十八周歲的案件,不公開審理。”該條將舊《刑事訴訟法》中對于“十六歲以上不滿十八歲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也不公開審理”的規定予以變更,限制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不公開審理能更好的保護涉罪未成年人的名譽和隱私,有利于涉罪未成年人進行教育和挽救。
(二)突破性的確立涉罪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程序的四種特殊制度
1.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
新《刑事訴訟法》第兩百六十八條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該條專款規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社會調查的主體是公檢法三機關,并可委托有關組織和機構進行,實踐中多為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社工組織和公益法律服務組織。例如,武漢等地實行特邀調查員制度,有利于檢察機關在對涉罪未成年人嚴格限制適用逮捕措施以及對涉罪未成年人不起訴、附條件不起訴時,通過對未成年人在家庭、學校、社區或村委會的表現情況和相關了解,為其作出是否批準逮捕及是否提起公訴提供依據,最終是為實現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根本目的。
2.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適成年人”制度
合適成年人是為未成年人在接受公安、司法機關審訊時提供幫助的、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擬制代理人。新《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條規定中,涉罪未成年人因其自身的特殊性,在單獨面對公安司法人員時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沒有加好維護自身合法訴訟權益的能力,新《刑事訴訟法》規定在訊問和審判涉罪未成年人是應當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場,在法定代理人無法到場時通過通知合適成年人到場來最低限度的保障涉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有助于緩解涉罪未成年人的緊張、對立情緒,符合“教育、感化、挽救”的方法。司法實踐中已有地區建立了由青少年辦公室、共青團組織等未成年人保護組織與公益法律服務組織成的長效聯動機制,共同挑選和指派具有專業法律素養的志愿者擔任涉罪未成年人的“合適成年人”。
3.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附條件不起訴及其考察幫教制度
新《刑事訴訟法》在第二百七十一、二百七十二、二百七十條分別規定了涉罪未成年人附條件不起訴的適用條監督考察和法律后果。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設立賦予檢察機關對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更為自由的裁量,此制度與社會調查制度相結合通過綜合考慮涉罪未成年人的現實表現來據此決定是否提起公訴,有助降低訴訟壓力,提高訴訟效率,在案件源頭上抓大放將起訴法定主義和起訴便宜主義結合起來,在對未成年人犯罪問題上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4.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
新《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五條規定,體現了對未成年人的特殊寬大政策訴訟法學界的權威學者陳衛東教授曾言:“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都在發育過程之中,未成年人的犯罪帶有大的或然性。對他們的犯罪記錄封存后,使得他們在人生的成長中,不會因為這樣的記錄耽誤上學、招工、影響前程。”而犯罪記錄封存并非將犯罪前科消滅,故可以將犯罪記錄封存看作一種“相對消滅”,只要涉罪未成年人悔過自新、再無新罪,就基本實現了“前科消滅”的類似效果。
[1]劉雅清.檢察機關在未成年人司法保護中的作用[N].檢察日報,2009-05-30.
D922.183
A
2095-4379-(2017)33-0173-02
吳丹,男,湖北省鄂州市華容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