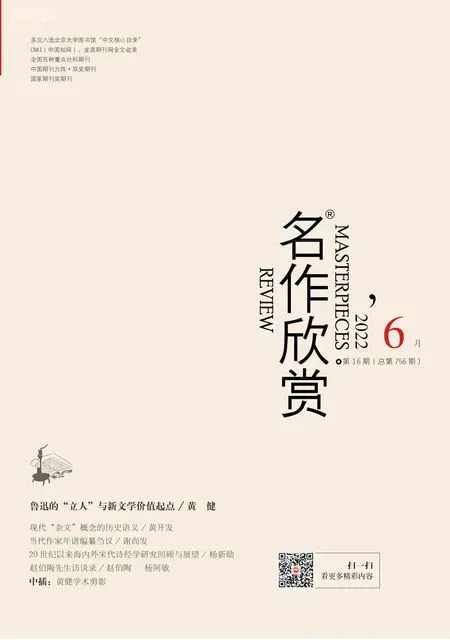《再別康橋》的優(yōu)柔和嚴(yán)肅
北京 李林榮
《再別康橋》的優(yōu)柔和嚴(yán)肅
北京 李林榮
《再別康橋》是徐志摩詩(shī)歌中的名篇,長(zhǎng)期以來(lái)它被解讀成明快、優(yōu)美甚至滿含甜蜜和歡欣的清淺之作。事實(shí)上這只是它的一層表象。細(xì)考全詩(shī)意象細(xì)節(jié)與整體意境的關(guān)聯(lián)脈絡(luò),并參證徐志摩創(chuàng)作當(dāng)時(shí)的生活處境,可以發(fā)現(xiàn)《再別康橋》具有表里沖突、明暗相間的張力結(jié)構(gòu),對(duì)迷茫、優(yōu)柔、凝重的“過(guò)程之美”的詠嘆,才是它真正的底色。
《再別康橋》 徐志摩 細(xì)讀分析 過(guò)程美學(xué)
一
徐志摩生于1897年,逝于1931年,活了不足三十五周歲,生命非常短暫,而且跨越了新舊兩個(gè)時(shí)代,過(guò)渡在古代的黃昏和現(xiàn)代的黎明之間。古代生活的典雅精致,在他面前,已經(jīng)破碎風(fēng)化;現(xiàn)代文明的豐富多彩,在他面前,還沒有充分展開。從這個(gè)意義上看,他所處的時(shí)代和社會(huì),既是一片廢墟,又是一片開墾地。
在這個(gè)大背景、大環(huán)境中,他不算個(gè)一等一的強(qiáng)者,他沒有大踏步地超越,更沒有強(qiáng)有力地支配和影響自己的生活際遇,但也沒有像文化上的浪子和精神里的孤兒那樣,眼前無(wú)路,腳底無(wú)根,迤邐歪斜,被時(shí)代和社會(huì)的潮流所裹挾、淹沒。他本身就是自己生活背景和生活環(huán)境的一部分,但他更像浮雕那樣,在某些角度、某些局部和某些側(cè)面上,從自己的背景和環(huán)境凸顯了出來(lái),表現(xiàn)了一種既存在于其中而又不完全屬于其中的奇異質(zhì)地和嶙峋骨感。
從徐志摩有據(jù)可查的生平材料看,他人生道路不長(zhǎng),愛情里程更短,但迎來(lái)送往的女友絡(luò)繹不絕,有時(shí)候還好幾位一起穿梭左右,應(yīng)接不暇,的確很有資格被人們視作情圣。不過(guò)他的愛情生活并不美滿、成功,相反,倒是貫穿著一系列的失落、迷茫。如果誰(shuí)要到徐志摩這里求取戀愛制勝和婚姻幸福的葵花寶典,那他肯定會(huì)失望。因?yàn)樾熘灸@里沒有愛情、婚姻的成功學(xué),只有愛情失敗學(xué)和婚姻受難學(xué)。如果換個(gè)角度,想看看不一定成功和圓滿,或者不以最終一個(gè)環(huán)節(jié)的成敗計(jì)得失的那種愛情和婚姻,具體是怎樣的況味和景致,尤其是一個(gè)人在始料未及遭遇到這種預(yù)卜不到前景的愛情時(shí),如何用力承受、用心擔(dān)當(dāng),那么,到徐志摩這里來(lái),可找對(duì)了地方。
這不僅是因?yàn)樾熘灸υ谶@方面經(jīng)歷得多,更因?yàn)樗€有一個(gè)特點(diǎn),就是不太會(huì)掩飾或遮蓋自己所親歷的各種難堪和幽暗,而且還經(jīng)常好像是不由自主又像是有點(diǎn)著意而為,會(huì)把自己的難堪和幽暗翻騰出來(lái),渲染、放大、鋪排,寫進(jìn)自己的作品。這類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數(shù)詩(shī),詩(shī)中最有名的,就是《再別康橋》。
二
1928年8月,三十二歲的徐志摩來(lái)到英國(guó),重游六年前自己求學(xué)、生活過(guò)的劍橋大學(xué)國(guó)王學(xué)院。這年冬天,他結(jié)束自己這趟耗時(shí)半年之久,暢游日美英,最后輾轉(zhuǎn)印度的漫長(zhǎng)游歷,乘船回國(guó)。11月6日,船到中國(guó)海上,他回想三個(gè)月前的劍橋之行,寫下了他一生作品中最有名的一首詩(shī)——《再別康橋》。一個(gè)月后,這首詩(shī)發(fā)表在他和一幫朋友共同編創(chuàng)的雜志《新月》月刊第一卷第十號(hào)上,自此往后,廣為傳誦,至今不絕。
現(xiàn)在很多讀者心目中,《再別康橋》這首詩(shī),已經(jīng)不僅僅是徐志摩的一篇名作,而且?guī)缀醭闪诵熘灸φ麄€(gè)人的代號(hào)和象征。每讀這首詩(shī),我們眼前和心里,就很容易閃現(xiàn)出一個(gè)深情而又溫和、優(yōu)雅而又略帶些落寞的身影或面容。我們大多數(shù)人、大多數(shù)時(shí)候,都樂于把這當(dāng)成情感和精神上的一幅美景或者一道甜品來(lái)欣賞、品味。
但實(shí)際上,不論細(xì)察作品本身,還是追究創(chuàng)作背景,都可以發(fā)現(xiàn),《再別康橋》的一派優(yōu)美、敞亮,是遍布著深深的褶皺的,褶皺里滿含的,都是憂愁郁悶和艱難苦恨。
我們一般注意不到這一層,是因?yàn)檫@里有一個(gè)時(shí)空隔閡的問題,也可以說(shuō)是審美代溝的問題。在文學(xué)和生活現(xiàn)實(shí)如何匹配、如何對(duì)應(yīng),或者說(shuō)拿什么樣的文學(xué)形式來(lái)表現(xiàn)什么樣的生活內(nèi)容的做法上,《再別康橋》問世的那個(gè)時(shí)代,和我們當(dāng)前,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是文學(xué)上的,更是精神風(fēng)度和人情世態(tài)上的。而且這種差異,本身的情況也是很豐富、復(fù)雜的,在徐志摩和他的《再別康橋》這里,體現(xiàn)的只是這種差異的一個(gè)小小的局部,在其他人、其他作品那里,還有和徐志摩、和《再別康橋》都不盡一致的表現(xiàn)。
時(shí)下傳說(shuō)的“民國(guó)范兒”如果真的存在過(guò)的話,那么,徐志摩保留在《再別康橋》這里的這種給幽暗以明麗、賦痛苦以優(yōu)雅的做派,或許就該是其中特別的一例。
三
就作品本身看,至少有三個(gè)方面可以顯示出《再別康橋》明麗背后的幽暗、優(yōu)雅背后的痛苦:1.意象的張力,2.韻致的纖弱,3.情思的曲折。
詩(shī)是用意象說(shuō)話的。意象是有特定審美蘊(yùn)含的形象。意象是為了傳達(dá)強(qiáng)烈、豐富的意義而被人自覺創(chuàng)造出來(lái)的,一旦造成,再提起的時(shí)候,就有以一當(dāng)十、以簡(jiǎn)馭繁的效果,像三明治、肉夾饃、夾心餅干一樣,一口下去眾味紛呈,比一樣一樣分吃單嚼,感覺要醇厚得多。一個(gè)特別好的意象存在久了、用得多了,沖擊力和表現(xiàn)力必然衰減,漸漸淪為陳詞濫調(diào)。用玫瑰花來(lái)表示愛情,當(dāng)初肯定也曾跟密電碼似的神奇過(guò)、新穎過(guò)一陣,可濫用之后,就退化成一個(gè)扁平透明的大白話字眼,跟直接提“愛情”這個(gè)詞沒有兩樣。
不論古今中外哪家哪派,凡屬好的詩(shī)和好的詩(shī)人,都給自己所在的那個(gè)時(shí)代和社會(huì)鑄造和奉獻(xiàn)過(guò)精彩、傳神、新穎的意象。等而下之的,也得對(duì)一些舊的意象多少做出增刪、修整。連這都做不到,可能就算不上是詩(shī)。之所以詩(shī)在各國(guó)各時(shí)代都被推崇到藝術(shù)之塔的尖端,根本上就是因?yàn)樵?shī)有這么一種文體稟性,它就是為了證明語(yǔ)言在形式和表現(xiàn)上的更新潛力和更新可能而存在的。
讀詩(shī)首先就是讀意象。《再別康橋》的意象不止一個(gè),全詩(shī)七節(jié),基本每一節(jié)突出一個(gè)或一組意象,但這些意象清一色都屬于張力型而不是松弛型的,都是把在日常生活經(jīng)驗(yàn)里打著架、犯著沖的意跟象,硬綁在一起,形成一種類似一張弓被拉到十分滿,自己跟自己較著很大勁的緊繃狀態(tài)。以下從頭到尾,邊數(shù)邊看: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lái);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云彩。
(《再別康橋》第一節(jié))
這里的意象,是一個(gè)人——“我”相對(duì)于康橋來(lái)而復(fù)去的姿態(tài),而且一來(lái)一走的姿態(tài)都重合,都是“輕輕的”。“輕輕的”姿態(tài),也可以貫通到心態(tài),來(lái)時(shí)“輕輕”,是因?yàn)閼抑模峙滤鶎げ挥觯姴恢胍姷摹W邥r(shí)也“輕輕”,是因?yàn)閬?lái)一趟什么也沒得到,空空如也,沒比來(lái)的時(shí)候增添什么,所以同樣是“輕輕”。“招手”本來(lái)是手上下?lián)u動(dòng),自古及今都是喚人趨近的意思,這里卻反其意而用,拿來(lái)“作別”,而且詩(shī)題明明顯示,“別”的對(duì)象是康橋,來(lái)這趟尋訪的對(duì)象當(dāng)然也是康橋,可這里的“招手”,卻又舍康橋而不顧,直向“西天的云彩”。合起來(lái)看,這個(gè)來(lái)而復(fù)去的“我”,顯然在糾結(jié)中,他的姿態(tài)和心態(tài)都映襯出一時(shí)莫名的巨大失落。
據(jù)有些傳記作者考證,志摩這詩(shī)里寫的這次康橋之行,是偶然得空,臨時(shí)即興安排,所以很可能碰上了乘興而來(lái)卻訪友不遇的尷尬:老熟人沒見著,新朋友也沒結(jié)識(shí),白溜達(dá)一趟。難怪只好俯看流水深潭,遠(yuǎn)望樹草斜陽(yáng),臨走也只能把辭行的表情和手勢(shì)送給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陽(yáng)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艷影,
在我的心頭蕩漾。
(《再別康橋》第二節(jié))
這節(jié)出現(xiàn)了復(fù)合意象,一是河畔的“金柳”,二是夕照下的“新娘”,三是波光里的“艷影”,這“艷影”既是“金柳”的水中投影,同時(shí)也是夕照下的“新娘”的水中投影。三者復(fù)合為一,從字面上看,靠的是修辭和物象上的關(guān)聯(lián),內(nèi)里卻是詩(shī)人逐漸清晰明確起來(lái)的一股情感和思緒在起推動(dòng)和黏合作用。三者之中,實(shí)景只居其一,就是河畔的柳樹,因?yàn)橛鄷熣遥耘私鹕瑑叭弧敖鹆保渌撸捌G影”和“新娘”,都是作者聯(lián)想到的心理虛像。
依常情常理,“金柳”這個(gè)形象,其觀感和意味都該是偏于鮮亮明快的。但詩(shī)人給它的比喻卻是“夕陽(yáng)中的新娘”。“夕陽(yáng)無(wú)限好,只是近黃昏”的夕陽(yáng),歡欣、喜悅、甜蜜、興奮的新娘,被聯(lián)想為一體,這正顯露出一種從亮中見暗、從喜中見憂的幽暗心結(jié)。緊接著的“波光里的艷影,/在我的心頭蕩漾”,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了這種幽暗心結(jié),并且把它直接歸結(jié)給了“我”。波光里的艷影之“艷”,既然來(lái)自“我”將“金柳”當(dāng)成“新娘”的聯(lián)想,那這“艷影”的蕩漾,其實(shí)也就是“我”自己的意識(shí)在起伏波動(dòng),自己也有點(diǎn)拿不準(zhǔn)自己似的。
軟泥上(《新月》初刊時(shí)“上”作“生”,似更恰切)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搖;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再別康橋》第三節(jié))
這里的“軟泥”“青荇”“油油的”“招搖”“柔波”“水草”,或名或狀或動(dòng),都集中強(qiáng)化同樣一點(diǎn)——柔軟,一種從外在的形狀、姿態(tài),到內(nèi)在的感受和品質(zhì),都是貫通一氣的柔軟。而“我”,對(duì)這種柔軟,不但不嫌棄,反而恨不能化身其間,跟著一塊兒去柔軟——“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條水草!”“水草”纏綿無(wú)骨,不夠陽(yáng)剛,但它跟“波光里的艷影”靠得最近。“甘心做一條水草”,就是寧可柔軟到底,也要豁出去爭(zhēng)取跟“波光里的艷影”耳鬢廝磨,依偎在一起。可“波光里的艷影”,本是水中月、鏡中花一路的虛影,并非實(shí)物,縱然變得成綿綿“水草”,又哪能勾得住這“艷影”的絲毫?
以上這兩節(jié),差不多是在濃縮呈現(xiàn)徐志摩從1920年初到康橋至1928年重訪和再別康橋這前后八九年間的真實(shí)情感體驗(yàn)。“艷影”“新娘”的意象,疊合著他對(duì)往昔的情人林徽因的回想和對(duì)暫別的妻子陸小曼的牽念。這回想和牽念,凄美而幽怨,細(xì)膩而糾結(jié)。
四
那榆蔭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間,
沉淀著彩虹似的夢(mèng)。
(《再別康橋》第四節(jié))
詩(shī)到第四節(jié),發(fā)生了轉(zhuǎn)折,取景視野從“河”轉(zhuǎn)向了“潭”,意態(tài)也隨之從“有我”變?yōu)椤盁o(wú)我”。虹映潭中,浮藻亂之,這一景象,與“天上虹”降臨地上之后遭遇夢(mèng)碎這一意蘊(yùn),結(jié)合了起來(lái)。很明顯,這是在形容隱退景外的“我”的總體心境。什么是“彩虹似的夢(mèng)”?那句從《紅樓夢(mèng)》中晴雯判詞里附會(huì)出來(lái)的俗話,“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大概可作為最簡(jiǎn)潔的說(shuō)明。在《再別康橋》這里,彩虹映潭本無(wú)所謂對(duì)錯(cuò),遭揉碎、被沉淀,皆因不巧落在遍布浮藻之處,換句話說(shuō),夢(mèng)之所出,在于天然,實(shí)在無(wú)可厚非,只是現(xiàn)實(shí)太殘酷,才使夢(mèng)碎。而“潭”較之“河”,即靜水之于流水,夢(mèng)碎于靜水,也沉入靜水,更見這夢(mèng)的執(zhí)著難舍。
于是,第五節(jié)展現(xiàn)“尋夢(mèng)”意象:
尋夢(mèng)?撐一支長(zhǎng)篙,
向青草更青處漫溯,
滿載一船星輝,
在星輝斑斕里放歌。
(《再別康橋》第五節(jié))
“尋夢(mèng)”的行為是撐篙行船,但不是順流而下,卻是逆流而上,“漫溯”,“漫”為縱意隨性,與“尋”無(wú)定向的常理相符,“溯”為逆流而上,卻暗示“尋”的方向只在“逝者如斯”的流水上游,也即舊時(shí)光中。整個(gè)看來(lái),這樣的“尋夢(mèng)”,實(shí)際也只能是對(duì)過(guò)往舊事的一番無(wú)謂的緬懷和追思。最后所得的,無(wú)非一些恰似星輝般縹緲、零散、寥落的記憶碎片。“放歌”,即為憶舊引起的重重慨嘆,喻指寫詩(shī)本身。第五節(jié)這段描述,實(shí)際上是在定格寫詩(shī)當(dāng)時(shí)的心思:想到的很多,也很想把所想到的這些,都說(shuō)清道明、抒寫盡興。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別離的笙簫;
夏蟲也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橋!
(《再別康橋》第六節(jié))
第六節(jié)與前一節(jié)同樣,是詩(shī)人當(dāng)時(shí)創(chuàng)作心思的一段寫照,不過(guò)完全收斂和按捺了上一節(jié)里展開的那種想跟往事干杯的興頭,調(diào)換出了一種欲說(shuō)還休、干脆不說(shuō)的婉約含蓄的情調(diào)。但言雖盡,意難平,何況之前畢竟已經(jīng)“說(shuō)”了不少,所以,“悄悄是別離的笙簫”中,“悄悄”在外,“笙簫”在內(nèi),歌聲是沒了,心聲可正轟響。至于“夏蟲”的沉默,一為渲染內(nèi)心“笙簫”的音效之強(qiáng),一也摹擬出了離別康橋時(shí)漸行漸遠(yuǎn)聽得河畔蟲鳴聲慢慢低落終至于無(wú)的實(shí)感。今晚沉默的康橋,就是乍離別之際感覺中悵然若失的那座康橋,隨著再次離別,它頓時(shí)又從可以親聞其聲、近睹其物的清晰狀態(tài),重歸于一片靜默的記憶。循之生活常情,我們不難理解這種瞬間一別、物非人是的恍惚感和失落感。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lái);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云彩。
(《再別康橋》第七節(jié))
第七節(jié)是對(duì)第一節(jié)的回應(yīng)和反復(fù)。“悄悄的”和“輕輕的”同有指言收斂、不事張揚(yáng)的意思,而“悄悄的”更強(qiáng)調(diào)不聲不響、無(wú)語(yǔ)凝咽的情狀,“輕輕的”則偏重指動(dòng)作上不著力,心情上不著意。以“輕輕的”開篇,暗中引領(lǐng)全詩(shī),落下基調(diào):抒懷喻事、感物起興都將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出于真實(shí)經(jīng)驗(yàn)而止于審美尺度。以“悄悄的”收尾,則是對(duì)這一基調(diào)的復(fù)沓和響應(yīng)。“揮一揮衣袖”,既是“不帶走一片云彩”的動(dòng)作,更是把一片心事拂落在此的動(dòng)作。末句中這片不帶走的“云彩”,當(dāng)然不是第一節(jié)中“我”招手作別的那片“西天的云彩”,因?yàn)椤拔魈斓脑撇省北緛?lái)也不為此地專有,跟“我”本也無(wú)關(guān),帶不走也無(wú)須帶走,更何況,依著第五、六兩節(jié)里所示的“星輝”和“今晚”,第七節(jié)詩(shī)境已入黑夜,不是仰看流云的時(shí)候。因而,這時(shí)所提到的跟“我”有關(guān),并且容“我”選擇帶不帶走的“云彩”,其實(shí)只能是從第四節(jié)中飄散出的那片彩虹和沉淀進(jìn)潭水的彩虹似的夢(mèng)。揮別它們,在漫天星輝的夜幕下退場(chǎng),這落寞的身影,把全詩(shī)各節(jié)的意象收束為了屏氣凝神、聲息皆無(wú)的一個(gè)表達(dá)的終點(diǎn)。
五
通觀全詩(shī),意與象、詞與義兩層面之間的緊張持續(xù)存在,但這種緊張始終都約束在了意象內(nèi)部,最后也隨著整個(gè)詩(shī)境構(gòu)造的完工,被及時(shí)地摒棄在了詩(shī)境內(nèi)部。這使得整首詩(shī)沒有在任何一個(gè)細(xì)節(jié)上流露出指向詩(shī)中的“我”和“我”的世界之外的強(qiáng)硬或尖銳姿態(tài)。
從某種強(qiáng)調(diào)“我”與“非我”、人與環(huán)境等對(duì)立二元此消彼長(zhǎng)規(guī)律的斗爭(zhēng)哲學(xué)和斗爭(zhēng)美學(xué)的立場(chǎng)來(lái)看,《再別康橋》這種張力內(nèi)斂的韻致,無(wú)疑是纖弱甚至消極的。它缺乏了些縱使明知電光石火也不惜做玉石俱焚之爭(zhēng)的剛勇氣概,少了些中流擊水、拼出血路的壯美。但不可否認(rèn),它仍然是一種美,一種確有可能和確有價(jià)值的美。
對(duì)此,徐志摩本人充滿缺憾的真實(shí)生活經(jīng)歷傳布到今天仍能給人以美感這一事實(shí),就正是一個(gè)鮮活印證。而展現(xiàn)在《再別康橋》整首詩(shī)中的那條徐志摩特色的情思脈絡(luò),則是一個(gè)縮聚在文字中的印證。全詩(shī)七節(jié),依次凸顯了七個(gè)主題、七種形態(tài)的情思:第一節(jié),揮別西天云——蒼涼失落;第二節(jié),心頭蕩波影——黯然神傷;第三節(jié),甘心做水草——纏綿依戀;第四節(jié),潭中虹夢(mèng)碎——執(zhí)著迷幻;第五節(jié),尋夢(mèng)載星輝——追索挽回;第六節(jié),別離無(wú)笙簫——再度失落;第七節(jié),揮袖留浮云——擱置放棄。這七種情態(tài)環(huán)繞一圈,把為“波光里的艷影”所吸引、蠱惑的那個(gè)“彩虹似的夢(mèng)”,緊緊合圍,形成焦點(diǎn)。
從奔著這個(gè)焦點(diǎn)而來(lái)的向度和力度講,這七種情態(tài)參差不一、錯(cuò)落有致。第一、二節(jié)由遠(yuǎn)及近、由弱漸強(qiáng),第三、四節(jié)靜態(tài)定向,第五節(jié)動(dòng)態(tài)逼近,第六節(jié)折返后撤,第七節(jié)回歸起點(diǎn)。其中,第五節(jié)既是向夢(mèng)逼近的起點(diǎn),同時(shí)也是尋夢(mèng)無(wú)著的幻滅點(diǎn)。此前四節(jié),是前奏,此后兩節(jié),是尾聲。合起來(lái)看,這純屬一場(chǎng)無(wú)果而終、無(wú)功而返的徒勞。但這一場(chǎng)徒勞的過(guò)程里的每一個(gè)環(huán)節(jié),卻得到了同等細(xì)致而又各具神采的生動(dòng)展示。這樣的展示本身,正是《再別康橋》的哲學(xué)和美學(xué)的重心所在。冒用一個(gè)術(shù)語(yǔ),《再別康橋》的哲學(xué)和美學(xué)不妨稱作“過(guò)程哲學(xué)”和“過(guò)程美學(xué)”。
過(guò)程本身是一種美。過(guò)程中的美,必定是些碎裂的片斷。它們不一定都連接著結(jié)果,甚至很可能根本和最終的結(jié)果沾不上邊,但這毫不減損更不消抹它們的美。因?yàn)樗鼈兘M成了一個(gè)切實(shí)存在的過(guò)程,僅此,已經(jīng)足夠成其為美。結(jié)果的有或無(wú)、好或壞,影響不到它們。終究,那是它們之外的另一回事。從這個(gè)側(cè)面上看,耐心見證過(guò)程之美的《再別康橋》,它的優(yōu)柔里,也滿含著說(shuō)不盡的嚴(yán)肅。
作 者:
李林榮,北京第二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文學(xué)院教授,中國(guó)文藝評(píng)論基地執(zhí)行主任,北京老舍文學(xué)院客座教授。編 輯:
張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