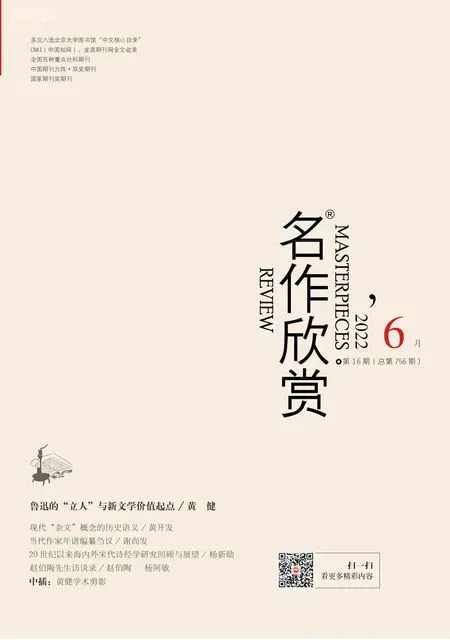王小飛先生的篆刻藝術
北京 王一舸
王小飛先生的篆刻藝術
北京 王一舸
伴隨新中國長大的一代人,也就是我父輩這代人,在藝術創作和藝術主張上有一個特點,那便是于傳統基礎上,力求自己獨特而系統的創新風格。
此話似乎是老生常談,其實內涵特殊。因為,這句話基于兩個方面:
一,他們大都有一定的學養,并不是一味沒有根據地“創新”。在現在這處處流行虛無和解構的時代,沒有根據的“創新”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其結果往往具有破壞性,往往是為了成就“個人”的說法或所謂風格,對整個藝術門類進行敗壞。事實也證明,近視于一時,出發于個人的不成熟“創新”,往往也不具備比作者生命時間更長的藝術生命。當然,如何取舍和融合,如何系統和建構,是由學養與眼界決定的。這也往往是他們這代人最值得驕傲的地方。
二,他們不會株守所謂的中國古典傳統或者西洋傳統,他們汲取營養的源泉也并不只是狹義的繪畫。在他們眼里,縱橫中西古今的經典藝術、民間藝術、裝飾圖案、水彩水粉、石窟壁像、舞蹈聲光、秦磚漢瓦、古董文物……一切美的事物,都能成為自己創作的酵母。如果以文學做比喻,則是經史子集,古今中外,并無高下之別。凡能為創制者,無不“拿來主義”。所以,在此方面,他們也很少有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繼承人”的那套邏輯自居的。那種狹隘的抱殘守缺,他們竊為不取。
上面兩點,構成這代人獨特的氣度和精神氣質。其歷史淵源如果上溯的話,一是他們成長于“五四”運動的土壤,并經過共和國的學院教育,不但不因循故舊,更知道理性取舍。二是他們的老師和他們追慕的人,都是民國時那些學貫中西的人物,這老一輩人往往沉吟傳統,又或留學海外,都是現代中國美術的先驅。他們對于傳統的好和西方的引進,都有自己獨特的認識。三是父親這輩人是“再認識”傳統的一輩人,他們本是從兼容博取的“廣大生活”中來的,又有賢師指點。他們經歷過“文革”,更加珍視自己的藝術生命和一切美的傳統,并以那一代特有的情懷和氣概來繼承和運化。最重要的是,他們珍視“自己創造”的意義,更不愿做外物和成律的附庸。這可能是他們最不同的一點。
王小飛先生便是其中能夠表現出以上特點的代表。他的篆刻創作,便反映了他獨特的精神氣質。他沒有“別人的藝術觀”給自己劃定的界限,篆刻,是他無拘無束、自由延展的表現與印證。可以說,王小飛先生的篆刻已經遠超我們意識上的篆刻的界限。說明這一點,其意義和責任不但是對于他,更是對于整個篆刻藝術和有志于在這一領域有所建樹的人的重要借鑒。
王小飛先生篆刻的藝術意義,首先,體現在篆刻理念上。他的篆刻意識體現著一種純粹的革新性,這種意識上的革新就是他對于篆刻“母本”的選擇。他從意識上,取消了所謂傳統篆刻那種線性發展的“主賓位置”,而是讓篆刻傳統成其創作源泉“之一”。從他的篆刻創作中,我們可以看到有從秦璽到漢印,及至西泠諸家風格的流脈,但這絕不是他印章的主流,也不是他為了彰顯傳統篆刻功力而為之的交卷。同別的風格一樣,這只是他的創作思考之一。在他的世界中,鼎彝瓴瓦,瓷款刻銅,及至各個不同民族的文字,古今中外各類藝術的風格,只要是有優美線條的,他都盡量熔鍛為自己的思考,進行創作。這種達觀的、鯤鵬橫絕的藝術眼量和精神,是他能給世人最重要的財富。他告訴我們,對待藝術應和對待終極的真理一樣,要持著“應無所住”的心,去感受人世間紛紜的美。在他眼中,每一個事物,每一種線條或文字,都是獨特的,都不是可以被抽離成為一個抽象意義,凝固為一種固定范式,形成一個僵化傳統的。這種精神,讓我想到了熊秉明《羅丹的美學》中曾經談到的“這(美的觀念)顯然是兩種不同的傾向:一種是要從特殊事物中發掘出個體的個性的美;一種是要憑借特殊的事物追溯到普遍的典型的美”。而熊秉明引用羅丹“一切都是美的”這句話,來說明羅丹之所以成為偉大的藝術家,就是因為他是前者,即從特殊事物中發掘個體獨特美的藝術家。王小飛先生用自己的一生,用自己的作品實踐了這句話。他也曾對著琳瑯優美的收藏,和我說過類似羅丹的話,即這些存在無論是殘缺還是完整,多么的陳舊古老,是出于民間還是出于泉土,它們都是美的。他這樣善于發現個體美的能力,使其創作變得廣闊,變為能真正創造一個世界一般的廣闊。
在理論上說,這樣的創作是走向無限的。
這正是我們這樣一個有著喜愛給文藝定“九品中正”,喜歡所謂的抽離提取意義,在一種思路或線路上進行“系統化”,喜歡將藝術創作的路越走越窄的國家所缺失和急需的精神。中國從沒有像現在這樣鼓勵和熱愛具有創新精神的人。王小飛先生就是用自己的作品,來彰顯了人類創造精神的力量。
觀念上,他是如此走向無限;具體創作手法上,他也有著能夠啟發后世的獨特之處。那便是,他經常運用一種類似作曲家的創作形式來進行創作,即經常以一個思路為基礎,做許多章法或內容類似,但表現風格各異的作品,就像作曲家在一個主題上生發出各種變奏曲。所以看到他的印稿,給我們的欣賞體驗不再是傳統欣賞篆刻作品那種相對的靜態體驗,而似乎他就活生生存在于你的對面,與你共同討論每一個主題變奏曲,讓你共同參與他的創作過程。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思路、才思,甚至是他的不確定、躊躇和推敲思量。
欣賞這一切的時候,篆刻,這門作為空間存在的美術形式也得到了新的定義,開始走向時間,即思路本身的流動。看他每一種風格、思路的變奏,多么讓人激動,就像我們在期待聽聞“下一個瞬間”的美好音符一樣。他給人體現的是一種活的、時刻變化流動的人類思維。他改變了藝術創作的性質,雖然依然是視覺的、空間的,但是正如音樂的材質是流逝的時間一樣,它也體現了時間藝術的維度。而這種創造者的創造思維活動,不正是最令人激動,又最有學習價值的地方嗎?我想,一個真正有志于創造活動的人,在面對創作的時候,會最深切地體會這種價值的存在。
王小飛先生廣闊的藝術理念和流動的創作手法,結出的是獨特的藝術風格。他的藝術風格,一言以蔽之,就是具有流動性。他的篆刻,已不滿足于傳統二維的、相對靜態的章法關系,他對篆刻這一藝術形式的意識,有了質的發展。
雖然,在傳統的篆刻上,也有對內在氣韻的追求。但是,正如草書之于隸篆,后者的審美基本上還是靜態的、二維的。而對于篆刻發展的探索,尤其對篆刻動態氣象的追求,是構成近現代篆刻發展最重要一個方向。這方面,韓天衡和劉石開分別從自己的維度上進行了探索,韓天衡就曾自言自己篆刻的突破點,得益于觀察舟楫映入水中倒影的運動影像。這無疑是他藝術突破的點,是從“靜”到“動”的轉變。而王小飛在這方面,打開的是另一扇門。那便是從帶有草書意味的花押章或流動線條的鳥蟲篆上,尋找開拓動態的美。這是一扇分隔兩種審美世界的門。王小飛正是在這一傳統的基礎上,推開了這扇門。
正如行草與楷書在造型原則上的基本性質差異一樣,沒有什么比飛動的線條本身對流動變化更具有說服力的了。在這一問題上,他無疑是有了與傳統(篆刻傳統)全然不同的決心,在從更大的傳統,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歷史傳統、文物傳統、鮮活的文字生命傳統中,選擇與自己理念相鏡照的藝術素材。
所以,可以認為王小飛的篆刻,只要符合以下兩點的,他就愿意去創造。一,就是符合他對于動態流動性的風格追求;二,各種不落窠臼的嘗試。前者,可以認為是他篆刻風格化、系統化的表現,雖然他本人不喜歡用所謂風格化、系統化束縛和解讀自己。他以前者的理念追求為基礎,發展出蔚為大觀、萬花筒般多樣的篆刻風格。
古花押章,不但有著傳統草書式優美的線條,而且它還有融合別的文化或文字傳統的可能。王小飛的花押章中非常獨特的地方,便是加上了一些敘利亞文或梵文,甚至八思巴文的線條。這應該是我所知別的篆刻家沒有觸及的地方。他不但系統地運用成為自己風格的一部分,同樣,對于傳統的鳥蟲篆,尤其是古青銅器的金銀錯極富想象力。對飛揚靈動的線條的熱愛,也是我上面所說的,符合于他追求的另一方面。
這些,和他喜愛收藏又有關聯。先生對花押章、鳥蟲文字和瓷器上筆畫飛動的文字與繪畫線條有著朝夕的審視和深入的理解。也正是因此,他才會如此自然系統地將它們融合,有機地組織成為一體。這是一種高層次的融通,一種俯仰隨意的取舍和創生。對于素材的自然運用,構成了王小飛篆刻藝術的另一道獨特的風貌。
在篆刻這一藝術門類中,先生確實是徹徹底底的“打開了自己”。他真正證明了“一個人便是一個世界”這句話。他的藝術走向萬物,走向時間,走向未來,走向無限,走向自己也不確定,還須求索的沉思。但,這才該是藝術的氣質,也應該是藝術家的精神氣質。藝術家不是為主義和理論活著的,也不是為了功名利祿,藝術家應該是最接近上帝的一個職業,因為他們的本質是——創造。之所以不是上帝,是因為藝術家作為人,有太多的未知,有太多的對于世間萬物的個體的體驗、感受,有太多的思索和不解,有太多的在藝術道路上的進行。而藝術家獨特的創造也因此而生。父輩們在藝術上的探索,往往如此。他們有的是達觀取予萬物的精神氣度,有的是對美的修養和追求。無論表現形態如何,從他們的作品中都會讓我們一目了然地感覺到這一切。這也是王小飛先生能夠留給我們的,并且可以流動延續到未知的未來的。
作 者:
王一舸,著名美術評論家、策展人、編劇、昆曲作家。編 輯:
趙際灤 chubanjiluan@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