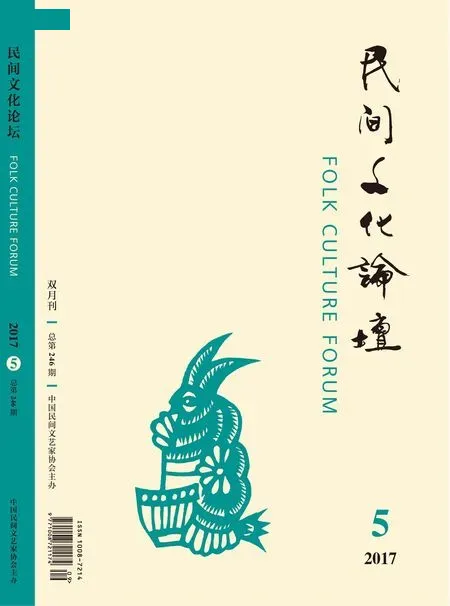神話主義研究的追求及意義
楊利慧
神話主義研究的追求及意義
楊利慧
盡管對神話的改造和挪用自古有之,但“神話主義”概念主要針對的是二十世紀后半葉以來由于現代文化產業和電子媒介技術的廣泛影響而產生的對神話的挪用和重新建構。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與神話的適當區分,有助于為長期被學界排斥在外的相關社會文化現象確立學術合法性。神話與神話主義之間存在密切的互動關系,不可截然分割。神話的神圣性并非絕對的和靜止不變的,而是受到語境和主體的制約,會隨著具體語境以及主體的變化而變化。
神話;神話主義;朝向當下;合法性;神圣性
在“當代中國的神話主義”學術研討會上,每位同人的發言都帶給我很多啟發。大家從不同角度敏銳地看到了本課題力圖探討的一些關鍵維度和問題,比如語境(包括時間和空間)和媒介技術的變遷,特別是指出了“朝向當下”的理論追求產生的學術史背景及其對于神話學以至于民俗學學科的意義。研討中也常常論及神話的神圣性的經典問題,以及是否存在著本質主義視角的神話傳統等等。這些討論都直接觸及了本課題的核心,對于豐富和推進未來的神話主義研究大有裨益。
這里我想針對同人們的意見再簡單補充幾點自己的看法。
第一,關于神話主義研究的動機和意義。毫無疑問,對神話的挪用和再造自古有之,神話學史上有名的案例,可以舉到屈原對于舜與娥皇女英的神話、莊子對混沌神話的文學化和哲學化改編,至于曹雪芹的《紅樓夢》中對于女媧補天神話的挪用和重構,更是婦孺皆知。前蘇聯神話學家葉?莫?梅列金斯基(Yeleazar Meletinsky)眼中的神話主義,主要便是指這一類作家汲取神話傳統而創作文學作品的現象。①[前蘇聯]葉?莫?梅列金斯基著:《神話的詩學》,魏慶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334頁。有關“神話主義”概念發展、演變以及筆者對其進行再闡釋的來龍去脈,可參考拙文《我對“神話主義”的再闡釋:前因與后果》,《長江大學學報》,2015年第5期。不過我重新闡釋的神話主義概念和視角,追求的學術旨趣主要并不在此。我所謂的神話主義,是指“二十世紀后半葉以來,由于現代文化產業和電子媒介技術的廣泛影響而產生的對神話的挪用和重新建構,神話被從其原本生存的社區日常生活的語境移入新的語境中,為不同的觀眾而展現,并被賦予了新的功能和意義。”②楊利慧等:《當代中國的神話主義?總論》,參見楊利慧等著:《當代中國的神話主義——以遺產旅游和電子媒介的考察為中心》,國家社科基金結項成果,未刊稿。這一概念的提出直接承繼并且力圖進一步參與民俗學領域從20世紀60年代肇始并一直延續至今的有關民俗主義、民俗化(folklorization)、民俗的商品化、民俗過程以及“類民俗”(folkloresque)③“類民俗”一詞為美國民俗學者Michael Dylan Foster所創制,來指在流行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對民俗性主題、人物以及形象進行挪用或重新發明的產品。參見Michael Dylan Foster, Jeffrey A. Tolbert,eds. The Folkloresque: Reframing Folklore in a Popular Culture World. Logan: 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6.等的大討論和相關反思,所針對的是20世紀后半葉以來,隨著文化產業、大眾流行文化、媒介技術的迅猛發展所產生的一系列社會巨變。這些新涌現的既熟悉而又陌生的“民俗”現象,與以往的民俗形態有著諸多明顯的差異,卻又相互關聯。在神話學的領域,同樣的巨變也發生著——當代社會中,村寨的薩滿、摩批和老人們口述的神話正漸行漸遠,而遺產旅游以及《仙劍奇俠傳》《王者榮耀》等新興文化產業中重構的神話卻在神話知識的傳播以及大眾神話觀的形塑中具有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顯然,民俗學界和神話學界應當直面這些社會巨變,并用我們的“熱心”和“熱眼”來觀察、記錄和研究這些巨變。這樣的研究取向無疑可以拓寬傳統民俗學和神話學的研究領域,促使具有根深蒂固的“向后看”傳統的民俗學和神話學學科實現“朝向當下”的轉向。
第二,將神話和神話主義進行適當區分的必要性。對于文化產業和大眾流行文化重新改編和建構的民俗,學界一直比較輕視,常常將之貼上“造假”“玷污”以及“腐蝕”“僵化”等標簽,排斥在嚴肅的學術研究之外。這些偏見以“偽民俗”的觀念為代表,在有關民俗主義、民俗化以及“民俗的商品化”的論爭中,也都有鮮明的體現。正因為如此,美國民俗學者邁克爾?福斯特(Michael Dylan Foster)最近新創造了“類民俗”(folkloresque)這一中性的概念,來指涉在流行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對民俗主題、人物以及形象的挪用和重新發明現象,他認為這一概念可以為理解這類現象提供一個理論框架。①The Folkloresque: Reframing Folklore in a Popular Culture World, 封底。我的想法恰和福斯特不謀而合。所謂“有名有實”,有了“名”,“實”才能被看見、被認真對待,無“名”則會被忽視、無視、輕視。“神話主義”的提出,正是要為長期被排斥的、為文化產業、大眾流行文化和媒介技術所挪用和重構的神話,在學術殿堂里安置一個正當的位置,建立其在學術上的合法性。正如施愛東所道出的那樣:“神話主義賦予當代神話的變異性傳承以合法性、正當性,恰恰有助于我們開啟一種新的理解模式,打破‘本真性’的思維局限,從‘真’與‘偽’的僵化思維中跳脫出來,進一步深化我們對于神話作為一種變異性民間文化的認識。”②見本期施愛東文:《“神話主義”的應用與“中國民俗學派”的建設》。有些寬容的學者認為,神話與神話主義都是民俗主體——人——的實踐,因此沒有必要區分二者。我贊成這種開放的態度,但不贊成這樣的做法。理由同上。考慮到前面提及的民俗學史上長期存在、至今依然盛行的對于文化產業和大眾流行文化重新改編和建構的民俗的輕視態度,適當的區分顯然是必要的,無疑有助于學界解放思想,直面現實,接納并重視相關社會現象的研究。籠統地將所有現象一律視為“主體的實踐”,眉毛和胡子一起抓,恐怕無法實現有針對性地推進,有礙學術研究向更加精細、深入的境地發展。
第三,神話和神話主義之間的互動關系。盡管我主張對神話與神話主義的形態進行適當區分,并且借鑒芬蘭民俗學家勞里?杭柯(Lauri Honko)的觀點,將神話主義歸結為神話的“第二次生命”。但是,與杭柯不同,我并不贊成一種直線進化論的民俗生命觀,而主張民俗的生命階段是不斷循環往復的,在神話和神話主義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動關系。應該說,從一開始,我的神話主義觀念就是反對本質主義的。所謂“本質主義”,用王杰文簡明扼要的話來概括就是:“想當然地、固執地認為存在著某個‘本真的’傳統,并把考證、界定與維護這種‘傳統’作為民俗學的學術任務。”③參見本期王杰文的文章:《“朝向當下”意味著什么?——簡評“神話主義”的學術史價值》。在我看來,所謂“第一次生命”和“第二次生命”的劃分不應該截然對立、水火不容,在新語境中被挪用和重構的神話,也可能重新回流進入社區,成為社區內部表達自我認同、重振社區力量的表達性手段。④拙文:《遺產旅游語境中的神話主義——以導游詞底本與導游的敘事表演為中心》,《民俗研究》,2014年第1期;同時,我所謂的神話主義既指涉現象,同時也是一種理論視角:“它含有這樣的意涵和追求:自覺地將相關的神話挪用和重構現象視為神話世界整體的一部分;看到相關現象與神話傳統的關聯性,而不以異質性為由,對之加以排斥。”⑤楊利慧等:《當代中國的神話主義——以遺產旅游和電子媒介的考察為中心?總論》,《當代中國的神話主義——以遺產旅游和電子媒介的考察為中心》,未刊稿,第16頁。
第四,再談神話的神圣性。約十年前,我曾發表過《神話一定是‘神圣的敘事嗎’?——有關神話界定的反思(之一)》一文,主張對神話的界定不一定要固守“神圣性”的僵化限制。⑥《民族文學研究》,2006年第3期。所謂“神話的神圣性”,是指“神話中敘述的遠古事件不僅被認為是真實可信的,而且神話的講述是在莊嚴崇高的氣氛中進行的,其講述場合常與神學和宗教儀式相關聯”。這一表述比較早地被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所提出,對后來在人類學家和民俗學家中形成“神話具有神圣性”的廣泛認識具有至關重要的引導作用。①[美]Hansen, William."Meanings and Boundaries: Reflections on Thompson's 'Myth and Folktales.'" In Myth: A New Symposium, ed. Gregory Schrempp, William Hanse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28.另見[英]G?S?柯克:《論神話的界說》,《西方神話學論文選》第76頁,朝戈金等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而我認為在現實當中,神話的存在形態以及人們的神話觀均具有多樣性,可能具有神圣性,也可能不一定具有神圣性,因此神話研究不應該固守神圣性的教條。這一主張與諸多人類學、民俗學、神話學以及古典學等的學者包括馬林諾夫斯基、克萊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斯蒂斯?湯普森(Stith Thompson)、威廉?巴斯科姆(William Bascom)、阿蘭?鄧迪斯(Alan Dundes)、G.S?柯克(G.S. Kirk)、威廉?漢森(William Hansen)等人的神話觀具有內在的一致性。②相關梳理可參見拙文:《神話一定是‘神圣的敘事嗎’?——有關神話界定的反思(之一)》,《民族文學研究》,2006年第3期。我堅持認為:沒有一個絕對的、抽象的、靜止不變的神圣性懸掛在所有神話的頭上。美國民俗學家理查德?鮑曼(Richard Bauman)曾經指出:文類并不是僵化固定的,而是一個“動態的表達資源(dynamic expressive resource),那些標志著文類的風格特征的慣常期待和聯想,能夠被進一步地組合和重新組合,以生產多樣化的形式和意義”③Richard Bauman, “Contextualization, tradition, and the dialogue of genres: Icelandic legends of the Kraftaskald”, in Rethinking Context: Language as an interactive phenomenon,ed. Alessandro Duranti, and Charles Goodwin. 127.。我們對“神話”這一文類的界定,也應該具備這種反省和“自覺”意識,看到其神圣性會受到語境和主體的制約,會隨著具體的語境以及主體的變化而變化。呂微認為在神話的界定上我是“內容優先論”,我不敢完全茍同,我倒認可自己是“多元論者”——嘗試運用“綜合研究法”,看到神話的內容、形式、功能與意義等多元維度的互動關系及其變化。在這一點上,陳泳超所指出的我是從“偏于文類的角度立論的”,也可謂知人之論。④參見本期陳泳超文:《神話的當代性》。在我看來,呂微從“神話是人的本原的存在”的命題出發,并沒能解決神話作為文類的界定問題,用他的標準,“本原神話、本真神話(道德神話),大概只有《尚書?堯典》和《圣經?創世紀》講述的堯舜禹和上帝的少數故事庶幾可許”⑤參見本期呂微文:《神話作為方法——再談“神話是人的本原的存在”》。,那么,作為民俗學和神話學者,我們該如何處理其他大量的、不符合這一理想標準的“神話”?又如何看待豐富的信仰傳說(belief legend)以及創世史詩與神話的區別?這一抽象的、理想的觀念顯然無法解決民俗學和神話學中的諸多實際問題。因此,盡管我由衷欽佩呂微等人的深入哲學思辨,也從中獲得了很多啟迪,但是正如我在以前和呂微的對話中所指出的:
我更愿意回到靈動鮮活的生活現場,返回到處在時間洪流之中的那些活生生的社會生活語境,觀察在不同地域的社會文化政治背景中、在實際的人際交流與互動過程中,各種不同神話觀的具體呈現;傾聽那些具體可感的、有血有肉的神話傳承者的聲音,以此貼近對于“神話”以及“神話觀”的理解和認識。我們由此看到的神話世界,不再是宏大抽象的概念和界定,而是充滿著多樣性、異質性、語境性以及個體性;神話的內容、形式、功能和意義都展現出十分豐富而復雜的色彩和意蘊。這樣的研究,屬于呂兄常謂的“經驗性研究”,既為大多數神話學者所踐行,而且,在我看來,這也正是神話學學科的生機和活力之所在。⑥楊利慧等:《現代口承神話的民族志研究——以四個漢族社區為個案?后記》,參見楊利慧、張霞等合著:《現代口承神話的民族志研究——以四個漢族社區為個案》,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29頁。
總之,神話主義的探討目前還處在初步階段,我們力圖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個案,先將事實描述出來,并對其類型、特點以及本質屬性等進行歸納和總結。無疑,更多的深入探討還有待未來的繼續拓展。
K890
A
1008-7214(2017)05-0029-03
楊利慧,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馮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