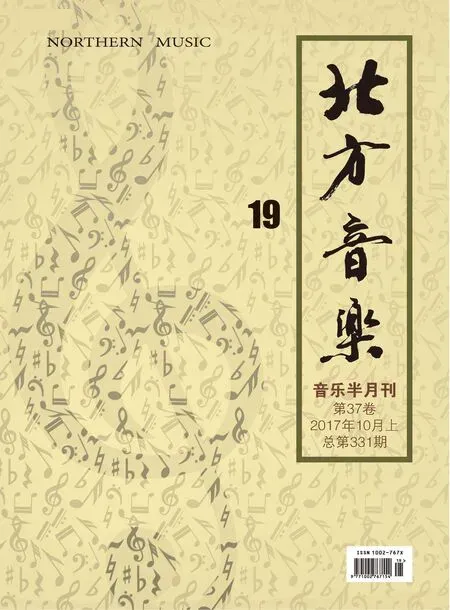對勃拉姆斯《四首鋼琴小品》作品119的探究
楊皓云
(常州工學(xué)院教育與人文學(xué)院,江蘇 常州 213000)
對勃拉姆斯《四首鋼琴小品》作品119的探究
楊皓云
(常州工學(xué)院教育與人文學(xué)院,江蘇 常州 213000)
《四首鋼琴小品》作品119是勃拉姆斯晚期的鋼琴代表作品,樂曲中反映出其深刻的人生哲理思想。在樂曲創(chuàng)作上,勃拉姆斯雖采用簡潔的曲式結(jié)構(gòu),但卻將各種音樂元素,如和聲、節(jié)奏、旋律及動機處理等作了豐富的變化,塑造了其獨一無二的音樂語言。本文將就四首鋼琴小品的創(chuàng)作特點進(jìn)行分析,希望對演奏者在樂曲詮釋上能有所幫助。
勃拉姆斯;四首鋼琴小品;創(chuàng)作特點;分析
一、關(guān)于勃拉姆斯《四首鋼琴小品》作品119
1892至1893年間,勃拉姆斯在巴德?伊雪爾(Bad Ischl),這座位于薩爾茲堡附近的小城,陸續(xù)完成了四套鋼琴小品-作品116至119。作品119正是勃拉姆斯在晚年孤獨悲傷之余,為克拉拉所寫的作品,更是他音樂創(chuàng)作生涯中的最后一首鋼琴作品。
二、《四首鋼琴小品》作品119創(chuàng)作特點分析
(一)第一首,b小調(diào)《間奏曲》,慢板
1.大膽的和聲手法
在樂曲開頭前四小節(jié),勃拉姆斯運用三度音程向下堆疊構(gòu)成縱向的和聲背景。此四小節(jié)在和聲進(jìn)行上藉由二度下行的模進(jìn)手法及循環(huán)五度的方式將開頭的主和弦進(jìn)行至屬和弦。勃拉姆斯刻意安排不協(xié)和音的堆疊以制造出帶有憂郁氛圍的和聲色彩。在彈奏時除了要留意縱向不協(xié)和音的和聲色彩之外,同時也要強調(diào)上聲部的橫向旋律行進(jìn)。因此,以觸鍵上來說,需將主旋律及和聲堆疊音作清楚的音色層次區(qū)別,而主旋律聲部的手指應(yīng)稍微加深觸鍵。
2.特殊節(jié)奏的運用
勃拉姆斯對于某些節(jié)奏型的偏好,在作品119中也隨處可見,其中最具代表的便是赫米歐拉(Hemiola)節(jié)奏的使用。作曲家喜愛在樂曲高潮之前安排節(jié)奏上的切換,像是節(jié)奏的增減值、交錯節(jié)奏、三連音節(jié)奏、切分音及赫米歐拉節(jié)奏等的運用,借此增強樂句的張力及緊湊感,此為勃拉姆斯創(chuàng)作手法的一大特點。如第21至24小節(jié),勃拉姆斯運用了赫米歐拉節(jié)奏型及減值的手法,來加速樂句進(jìn)行的緊湊感,并達(dá)到本曲的第一次高潮。
3.復(fù)音手法
勃拉姆斯相當(dāng)喜愛巴赫的作品,其作曲手法也受到巴赫的影響,因此在勃拉姆斯的作品中處處可見多聲部的織體,呈現(xiàn)出復(fù)音音樂手法,如對位、卡農(nóng)、模進(jìn)等寫作技法,此為其創(chuàng)作鋼琴音樂的顯著特點。在演奏勃拉姆斯晚期鋼琴小品時,要特別留意多聲部的處理。此外,勃拉姆斯特別喜愛中間音域的溫暖音色,因此,時常可見在中間聲部隱約含著旋律線來跟高聲部主旋律作呼應(yīng),演奏者需留意到此細(xì)微的聲部處理,才能確實傳達(dá)出細(xì)膩的音響變化。
(二)第二首,e小調(diào)《間奏曲》,稍微激動的小行板
1.主題變形手法(Thematic transformation)
彈奏此曲要特別留意作曲家的創(chuàng)作技法-主題變形手法(Thematic transformation),也就是勃拉姆斯運用不同的節(jié)奏、音符時值、調(diào)性、樂句及表情記號等安排,使得A、B兩段雖是運用相同的旋律素材,卻展現(xiàn)出不同的性格面貌。這種素材相同,只因作曲手法的改變,而將A段急切的、略帶陰郁的,且躊躇不定的性格轉(zhuǎn)變?yōu)锽段優(yōu)雅如歌似的圓舞曲,即為主題變形手法的運用。
2.復(fù)音手法
在此曲中也可發(fā)現(xiàn)勃拉姆斯使用了對位及卡農(nóng)等復(fù)音手法,使得左右手旋律產(chǎn)生對唱、呼應(yīng)的效果。如第53至55小節(jié),右手卡農(nóng)的手法,將左手的旋律完全模仿,使得左右手產(chǎn)生如同二重唱般的效果,而此作曲手法也傳達(dá)出勃拉姆斯內(nèi)心深處的濃烈情感。
3.和聲手法
此曲的和聲手法除了浪漫樂派常見的平行大小調(diào)轉(zhuǎn)換及屬七和弦不解決之外,比較特別的是在第60至61小節(jié),勃拉姆斯在B段(c-d-c’)的再現(xiàn)c’段運用了旋律先再現(xiàn)后,和聲才確立的作曲手法,使得旋律先配以E大調(diào)ii級的副屬和弦,與B段開頭主題相呼應(yīng),直至第64小節(jié)后才明確導(dǎo)回E大調(diào)和聲。此和聲手法使得第60小節(jié)雖是重復(fù)B段主題,但和聲上卻是帶有升f小調(diào)色彩,在演奏時需留意此細(xì)微的和聲色彩轉(zhuǎn)變,以傳達(dá)出作曲家內(nèi)心情感的變化。
(三)第三首,C大調(diào)《間奏曲》,優(yōu)雅且游戲般地
1.動機發(fā)展手法
此曲中最主要的作曲手法便是以單一主題動機作發(fā)展以貫穿全曲。關(guān)于本曲的曲式,有學(xué)者認(rèn)為勃拉姆斯省去對比樂段,以貫穿式(through-composed)的方式連貫全曲,也就是說此曲在動機上呈現(xiàn)明顯的一致性,以單一的素材多次出現(xiàn)在各段落中,并藉由動機發(fā)展貫穿全曲。另外,也有學(xué)者支持此曲為三段體曲式,因為在第25至35小節(jié)中,此段落以連續(xù)性的轉(zhuǎn)調(diào)和模進(jìn)手法,力度記號也較A段運用頻繁,并且借由調(diào)性上的迅速轉(zhuǎn)變以及表情記號出現(xiàn)的次數(shù)增加使得段落之間在音樂情緒上有明顯的差異,因而形成三段體結(jié)構(gòu)。但不管是一段體還是三段體的論點,樂曲的發(fā)展都是依靠單一主題動機來進(jìn)行,只是作曲家在此動機基礎(chǔ)上更改其它元素,而使得主題有了不同的音樂性格。
此首間奏曲,承接了第二首間奏曲的動機,在中音(E)、屬音(G)及下中音(A)這三個音上作動機發(fā)展。有趣的是,此曲中勃拉姆斯將主旋律放置于內(nèi)聲部,特別展現(xiàn)出中音域溫暖且樸實的音色。在彈奏時,應(yīng)強調(diào)右手內(nèi)聲部主旋律,可將重心多擺在右手的大拇指及食指,以增加觸鍵的力度,同時保持手腕是具有彈性的,這樣音樂的層次感就會很鮮明。
(四)第四首,降E大調(diào)《狂想曲》,堅決的快板
1.動機處理手法
此曲的曲式結(jié)構(gòu)為A-B-C-B’-A’加Coda的拱形曲式。二度音程的三音動機(C-D-降E)是本曲中最主要的核心動機,此三音動機最明顯的地方是在第61至64小節(jié),其功能是扮演銜接B段的過門,帶有鮮明的預(yù)告作用,而B段旋律也是奠基在此三音動機上。之后,此三音動機更是被充分運用,除了在B段結(jié)尾的過門樂段再次使用三音動機之外,C段的樂曲氛圍雖然從B段的緊張不安轉(zhuǎn)為優(yōu)雅愉快般的,但主要旋律仍是采用此三音動機來發(fā)展。接著,此三音動機在C段也不斷出現(xiàn),像是第109至114小節(jié)便是以三音動機作三次的模進(jìn)。特別有趣的是,在C段結(jié)束要銜接B’段前的過門,勃拉姆斯卻是選擇使用反向的三音動機,此作曲手法的巧妙安排也使得B段與C段的樂曲轉(zhuǎn)折是自然且符合邏輯的。這三音動機扮演著多重的角色,除了扮演銜接樂段的過門及作為旋律動機之外,在A段的內(nèi)聲部也可以發(fā)現(xiàn)此隱含的三音動機。在彈奏時,應(yīng)該要留意到此三音動機的運用及發(fā)展,才能確實掌握住整首樂曲的核心架構(gòu)。
三、結(jié)語
勃拉姆斯可說是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的重要代表之一。就樂曲結(jié)構(gòu)及織度上來說,勃拉姆斯繼承了巴洛克與古典時期慣用的作曲手法,像是在織度上,他常以對位的技法呈現(xiàn)復(fù)音音樂,且旋律的移動多以三度、六度為基礎(chǔ)。再者,勃拉姆斯秉持著古典音樂中所強調(diào)的形式主義,以理性、均衡、節(jié)制的方式呈現(xiàn)完美的結(jié)構(gòu)。就旋律及和聲上來說,勃拉姆斯的創(chuàng)作技法則偏向浪漫樂派元素,如就旋律創(chuàng)作來說,勃拉姆斯運用了浪漫時期作曲家喜愛使用的主題變形手法;就和聲上來說,勃拉姆斯相當(dāng)前衛(wèi)地運用了主十三和弦來擴(kuò)張三度音程的結(jié)構(gòu),使其作品展現(xiàn)出浪漫音樂豐富的聲響與色彩效果。顯而見之,勃拉姆斯將古典主義的創(chuàng)作原則與浪漫主義的精神相互融合,因此,在彈奏作品119時,要特別留意作品中所含括的理性層面-巴洛克及古典時期技法,以及感性層面-浪漫時期技法,才能確實將勃拉姆斯晚期鋼琴小品的樂曲精髓完美呈現(xiàn)出來。
[1] Paul Holmes,王婉容.偉大作曲家群像:布拉姆斯[M].臺北:智庫文化,1995.
[2]人民音樂出版社編輯部.論曲式與音樂作品分析[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3.
J658
A
楊皓云(1984—),常州工學(xué)院教育與人文學(xué)院講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鋼琴演奏與教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