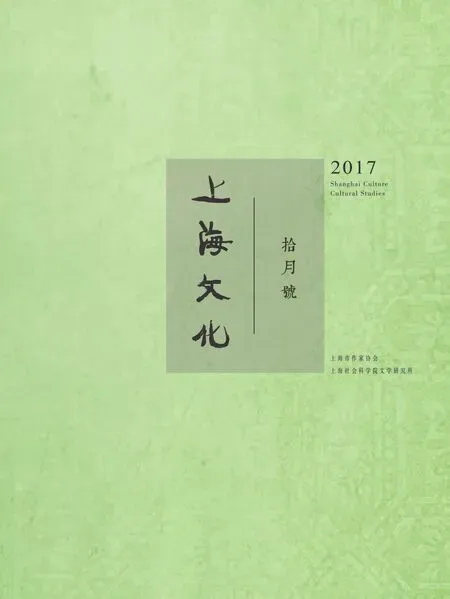中西文化的別樣理解
——以《學衡》為中心的考察
盛丹艷
中西文化的別樣理解
——以《學衡》為中心的考察
盛丹艷*
《學衡》是民國期刊史上一份獨具特色的文化刊物,其所刊載的文章,傳達出對于中西方文化的獨特理解。《學衡》具有中正穩健的文化態度,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它既反對一味復古、守舊,也不同意全盤否定,而是主張昌明國粹,發揚精華;對于西方文明,主張立足于全面和深入的學術研究,形成精確的判斷,擇其精華。《學衡》基于新人文主義的立場,認為中西方古典文明是相契合的,應融會中西方文明的精華,建設中國的新文化。《學衡》堅持學術本位,其新文化觀超越了中西體用之爭,擁有一種別樣的視角。
《學衡》 新人文主義 中西文化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爭便一直未曾停歇,也一直未有定論。不同的知識群體對于中國文化的發展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觀點和方案。其中《學衡》的獨特文化理念值得我們重視。它既不主張一味守舊復古,也不同意否定傳統全盤西化,而是留下了對時代問題和文化發展道路的富有個性的思考。筆者將基于《學衡》所刊載的文章,梳理其所表達的中西方文化觀,以及對于中國新文化建設的相關思考,揭示其獨特立場和文化意義。
一 、昌明國粹:《學衡》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
創辦于1922年的《學衡》以“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為辦刊宗旨,自創刊始,便聚集了一批擁有共同文化理念的學術大家,如梅光迪、吳宓、劉伯明、柳詒徵、胡先骕、繆鳳林、湯用彤、張蔭麟等。在對中西文化的理解上,《學衡》諸君持有相對一致的態度,而雜志所刊載的文章,也傳達出《學衡》獨立的立場和獨特的文化理念。
《學衡》的創刊宗旨具有明確的現實指向,即試圖糾新文化運動之偏,以學術為本,強調持中穩健的學術批評和研究。也因此,《學衡》關于中西文化的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從其對新文化派的批評中體現出來。就中國傳統文化而言,《學衡》與新文化派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白話文運動和對孔子的評價問題上。
關于文學改良和文字革命的主張,在《學衡》創刊之前,即1917年,梅光迪與胡適在美國留學時便展開過爭論。《學衡》創刊之后,這一問題也成為梅光迪、吳宓、胡先骕等批評新文化派的一個重要方面。對于文言與白話之爭,《學衡》的觀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第一,文言和古文并非是死文字和死文學,而是有著深厚的歷史積淀與文化內涵。吳宓指出,文言文乃是“吾國文章之最簡潔、最明顯、最精妙者”,文學的創造自有歷史的沿革,文學的發展也是基于歷史之淵源,“由是增廣拓展,發揮光大,推陳以出新,得尺以進程。雖每一作者自有貢獻,然必有所憑藉,有所取資”。①吳宓:《論今日文學創造之正法》,《學衡》第15期,1923年。其次,正是源于這種歷史性,取消文言,也即是斬斷這種歷史傳承,會帶來嚴重的后果:“文學之源流根株,立為斬斷。舊文學中所有之材料之原理,其中之詞藻之神理,此新文學中皆固無之。而因文字之斷絕隔閡,又不能移為我用。勢必從新作始,仍歷舊程。此其損失之巨,何可言喻”,“即不言保存國粹、發揚國光、鞏固國基諸遠大之關系,但為文學創造者之便利之成功計,亦不宜破滅文言”。②吳宓:《論今日文學創造之正法》,《學衡》第15期,1923年。再次,從中國傳統文學的文字和體裁的變遷來看,在文言與白話兩者的關系上,兩者是可以共存的。從漢魏六朝的駢體,到唐宋的古文,再到宋元以來的白話體之小說戲曲,“古文白話之遞興,乃文學體裁之增加,實非完全變遷,尤非革命也”,古文與白話,“蓋文學體裁不同,而各有所長,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獨立并存之價值”。③吳宓提出:“小說戲劇等有當用白話者,即用簡練修潔之白話。外此,文體之精粗淺深,宜酌照所適,隨時變化。而皆須用文言。”④吳宓:《論今日文學創造之正法》,《學衡》第15期,1923年。最后,對待中國傳統文字也應一分為二地看待,應區分文言和八股,認為“古文之價值,不惟在其形式,抑且在其材料。唐宋人之倡古文,以破選體之詞章。明清人之倡古文,以矯制藝之八股”,新文化運動不應該“以古文與八股并為一物而攻擊者”。⑤吳宓:《論今日文學創造之正法》,《學衡》第15期,1923年。
《學衡》諸君不認同新文化運動把中國文化的問題歸責為語言文字上的優劣的觀點,而是認為,文字無所謂優劣,只看其是否適宜文學創造。文章格律只是一種形式,重要的其實是新的材料和作者的才華和運用。也因此,舊體詩為世人所批評,這并非格律的問題,而是“作者不能以今時今地之聞見、事物、思想、感情,寫入其詩,而但以久經前人道過之語意,陳陳相因,反覆塞,宜乎令人生厭”。⑥吳宓:《論今日文學創造之正法》,《學衡》第15期,1923年。因此,文學創造家之責任,應是融合新材料與舊格律,而不是一味否定舊體詩的價值。也正是基于這樣一種理解,《學衡》始終堅持刊載文言文作品和舊體詩作。
除此之外,為孔子正名是《學衡》維護傳統文化的另一個重要努力。新文化運動對孔子和儒家觀念的抨擊是猛烈的,“打倒孔家店”是當時一個響亮的口號。但《學衡》諸君認為,對于孔子的評價須要商榷。《學衡》諸君對于孔子的評價甚高,“夫孔子之學說,為全世界以往文化中最精粹之一部也”。⑦把中國近代問題都歸咎于孔子,他們認為是不恰當的。如柳詒徵便說:“中國最大之病根非奉行孔子之教,實在不行孔子之教。孔子教人以
③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學衡》第1期,1922年。仁,而今中國大多數之人皆不仁。”①柳詒徵:《論中國近世之病源》,《學衡》第3期,1922年。《學衡》對于孔子和儒家學說的維護與肯定,顯然與當時的主流思潮大相徑庭。
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學衡》既反對極端保守,也不主張極端鄙棄,而是主張明辨、慎思,持中正之態度,發平情之議論。他們尤其提出,無論是批評還是肯定,都應首先“精確估定舊文化之真正價值”,“取適中之義以衡量一切”,②李思純:《論文化》,《學衡》第22期,1923年。以一種精深的學術判斷來完成對傳統文化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
《學衡》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抱有信心,認為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必有可發揚光大,久遠不可磨滅者在”,③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學衡》第1期,1922年。應立足于精深的學術研究,重新認識和評估傳統文化的精粹,將其傳承與發揚光大。“古今之學術、德教、文藝、典章,皆當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發揮而光大之……若謂材料廣博,時力人才有限,則當分別本末輕重,小大精粗,擇其尤者而先為之。”④吳宓:《論新文化運動》,《學衡》第4期,1922年。那么,如何才能對傳統文化作出精確的估定,也即如何完成這種學術上的重估?《學衡》提出:“凡治一學,必須有徹底研究,于其發達之歷史,各派之比較得失,皆當悉其原委,以極上下古今融會貫通之功,而后能不依傍他人,自具心得,為獨立之鑒別批評。”⑤梅光迪:《論今日吾國學術界之需要》,《學衡》第4期,1922年。《學衡》對于這一研究和重估工作是極為重視的,正如梅光迪后來曾談到的:“《學衡》的作者們并非對自身民族傳統中的問題熟視無睹,而是堅信目前更為緊迫的任務是要對已取得的成就加以重新審視,為現代中國重塑平穩、鎮定的心態。在他們看來,這不僅對真正的文化復興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批判性接受西方文化中有益且可吸收的東西必不可少的條件。”⑥《梅光迪文錄》,羅崗、陳春艷編,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3-224頁。
自中國傳統文化遭遇西方文化沖擊以來,如何對待傳統便一直是知識界所要面對的問題。李澤厚認為:“真正的傳統是已經積淀在人們的行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態度中的文化心理結構,儒家孔學的重要性在于它已不僅僅是一種學說、理論、思想,而是溶化浸透在人們生活和心理中了,成了這一民族心理國民性格的重要因素”,“傳統既然是活的現實存在,而不只是某種表層的思想衣裳,它便不是你想扔掉就能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⑦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第46、48頁。他從唯物史觀的角度出發,認為傳統文化所依賴的經濟基礎在現代已經發生了變革,傳統文化需要適應這種變革,作出創造性的轉換。他同時提出,這種轉換需要以對傳統文化中的一切“作進一步具體的分析、細致的研究和理論的建設”。⑧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第46、48頁。雖然分析的視角有所不同,但是這與《學衡》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在某種程度上有共通之處。《學衡》同樣是試圖通過對傳統文化的精細研究和發揚國粹,來為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作準備。在救亡壓倒啟蒙的時代潮流中,《學衡》試圖有所糾偏,對傳統文化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并發揚其精華部分。其所提出的問題是文化層面的一些重要問題,值得認真對待和充分探討。就如文言和白話的問題,并不單純是語言文字問題,而是有著深刻和復雜的牽涉。當時并不存在那樣一種社會心態去包容傳統文化轉型和新文化建設所需要的學術上的充分準備。但不管怎樣,《學衡》所提出的理念,確實代表了當時中國的一部分知識精英對傳統文化的別樣理解。
二、融化新知——《學衡》的西方文化觀
自西學東漸以來,如何對待西方文化,便一直存在爭議,出現了不同的方式和態度。既有抵制抗拒者,也有主張全盤西化者。而在各種取舍中,《學衡》代表了一種穩健溫和的路向,并提出了對于西方文化的獨特理解。
《學衡》諸君既具有深厚的國學素養,也深受歐美文化的熏陶,大多是學貫中西的學者,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對于西學的涌入,他們抱有積極與樂觀的態度,認為這對于中國文化而言是一次難得的機遇,為中國文化實現創新、轉型提供了思想資源。他們認為,東西方文化的接觸和交流,為中國文化提供了學習和吸收的機會,通過觀摩比較,“凡人之長,皆足用以補我之短”。①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學衡》第1期,1922年。西方幾千年來的“典章文物,政術學藝,其人之思想、感情、經驗,以及窮研深幾之科學哲理”,可以“供我研究享受,資用取及”,“吾國舊有之學術文物,得與比較參證,而有新發明、新理解”。②吳宓:《論今日文學創造之正法》,《學衡》第15期,1923年。
在對待西方文化的問題上,《學衡》諸君既不保守,也不激進,而是守持中道。他們主張平等、客觀地對待中西文化,對于當時崇拜歐化的現象,持反對態度,不希望在引進西學的同時,失去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和獨立性。“吾國近年以來,崇拜歐化,智識精神上,已惟歐西之馬首是瞻,甘處于被征服地位”,并進而提出,對于西學應以“至精審之眼光,為最持平之取舍”。③梅光迪:《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學衡》第2期,1922年。
總的來說,《學衡》所傳達出的西方文化觀,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特點:首先,《學衡》認為應當在全面和深入研究西方思想文化的基礎上,注重對西方文化的選擇。《學衡》對于當時被大力引介入中國的西方近代思潮是持反對態度的,認為新文化派對于西方文化未有總體上的把握以及辨析,而以西方近代思潮為西方文化之代表,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在他們眼中,近代盛行的西方思想具有較強的自然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特點,往往忽視了人本身道德性的完善,這一類型的文化并不能作為西方文明之精華。那么,何種思想學說可以作為西方文化的代表,值得被引介?梅光迪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選擇標準:所介紹的西學,一是“須其本體有正當之價值”,二是“以適用于吾國為斷”。對于一種思想的本體價值的判斷,是“取決于少數賢哲,不當以眾人之好尚為歸”,也即應由知識精英來判斷。而所謂適用者,“或以其與吾國固有文化之精神,不相背馳,取之足收培養擴大之功”,“或以其為吾國向所缺乏,可截長以補短也;或以其能救吾國之弊,而為革新改進之助也”。①梅光迪:《現今西洋人文主義》,《學衡》第8期,1922年。其所需求的西方思想,在于“能超越東西界限,而含有普遍永久之性質者”。②梅光迪:《現今西洋人文主義》,《學衡》第8期,1922年。總之,對于西方思想的引介,須持有審慎的態度,不能不加以辨析。
其次,《學衡》立足于新人文主義的立場,判斷與擇取西方文化精華。新人文主義是當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白璧德的學說,深為《學衡》諸君所認同。《學衡》的創刊者梅光迪、吳宓等均是白璧德的學生。《學衡》刊載了不少譯介新人文主義的作品,如《安諾德之文化論》、《白璧德論歐亞兩洲文化》、《穆爾論自然主義與人文主義之文學》、《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談》等,可以說是新人文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主要陣地。
白璧德的學說反對西方自培根以來的自然主義和自盧梭以來的浪漫主義思潮,反對重物質而輕道德的思想傾向,憂心于功利主義的盛行和道德的淪喪,“實際是對科學和民主潮流的一種反撥”。③樂黛云:《世界文化語境中的〈學衡〉派》,《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他主張對個性道德的約束,“節制個人主義及感性,而復歸于適當之中庸”。④吳宓譯:《白璧德之人文主義》,《學衡》第19期,1923年,孫尚揚、郭蘭芳編:《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第7頁。白璧德希望回歸西方古典的人文和宗教傳統,推崇亞里士多德和耶穌,認為近代以來的精神危機正是源于古典人文精神的失落。他對東方文化也極為關注,尤其推崇孔子和釋迦牟尼,將孔子與亞里士多德相提并論,認為“西方之人文大師,以亞里士多德為最重要,孔子與亞里士多德立說在不謀而合”,⑤吳宓譯:《白璧德論歐亞兩洲文化》,《學衡》1925年2月第38期,孫尚揚、郭蘭芳編:《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第54頁。中西古典文化“均主人文,不謀而有合,可總稱為邃古以來所積累之智慧也”。⑥胡先骕譯:《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說》,《學衡》第3期,1922年,孫尚揚、郭蘭芳編:《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第48頁。
新人文主義對于中西古典文化共通之處的強調,以及對于中國文化的洞見,契合了《學衡》諸君尋求中國文化困境解決之道的需要。梅光迪就談到,新人文主義學說“以綜合西方自希臘以來賢哲及東方孔佛之說而成,雖多取材往古,然實獨具創見,自為一家之言。而于近世各種時尚之偏激主張,多所否認”,“其言東方文化,尤具批評眼光”,可以補救“吾國固有文化中之缺點流弊”。⑦梅光迪:《現今西洋人文主義》,《學衡》第8期,1922年。梅光迪認為,新人文主義學說為《學衡》諸君在“形形色色的文化價值觀和文化主張中指明了正確的道路”,使其“在看待本國的文化背景時有了新的視角和方法”。⑧《梅光迪文錄》,第220頁。新人文主義學說所具有的世界性眼光,以及對中西文化的融合追求,得到《學衡》諸君的深切認同,他們試圖通過譯介和傳播新人文主義學說,為中國文化的創新提供一個有效路徑。《學衡》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試圖在中國推動一場“人文主義運動”(梅光迪語)。
白璧德對于當時中國的新舊文化之爭深為關注,他一方面指出,“中國必須有組織、有能力,中國必須具歐西之機械,庶免為日本與列強所侵略”,同時也特別提出警告:中國在力求進步時,“萬不宜效歐西之將盆中小兒隨浴水而傾棄之。簡言之,雖可力攻形式主義之非,同時必須審慎,保存其偉大之舊文明之精魂也”。①胡先骕譯:《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說》,《學衡》第3期,1922年,孫尚揚、郭蘭芳編:《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第42、48頁。中國文化的革新,對于舊式教育“盡可淘汰其浮表之繁文縟節”,同時,要保存固有文化的精髓,即道德精神和人文內涵,“決不可忽略道德,不可盲從今日歐西流行之說,而提倡偽道德。若信功利主義過深,則中國所得于西方者,止不過打字機、電話、汽車等機器……勿冒進步之虛名,而忘卻固有之文化”。②胡先骕譯:《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說》,《學衡》第3期,1922年,孫尚揚、郭蘭芳編:《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第42、48頁。這些判斷與提醒得到《學衡》的呼應。他們以新人文主義的視角,批評新文化運動中對西方近代思潮不加批判的引介,以及對于固有文化傳統的摒棄,憂心于由此可能帶來的道德和文化危機。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方面,在肯定新文化運動具有的思想解放和啟蒙作用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學衡》或許正是從另一側面提示了其可能存在的不足。
《學衡》對于西方文化的理解有自己特定的立場,也持有自己的選擇標準,他們對于西方文化的引介是積極而慎重的,反對一種“不加選擇的世界主義”,強調在全面、深入的學術研究基礎上進行審慎的判斷和選擇,認為若無廣博精粹之研究,將“所知既淺,所取尤謬”。他們尤其提醒要保持學術上的獨立判斷,防止“于其一學之名著及各派之實在價值,皆未之深究,即為枝枝節節偏隘不全之介紹,甚成道聽途說,毫無主張”,“在學術上不敢自信,徒居被動地位,為他人之應聲蟲之宣言也”。③梅光迪:《論今日吾國學術界之需要》,《學衡》第4期,1922年。這些批評和提示在如今依然具有現實意義。
三、融會中西的新文化觀
對于中西文化的關系,《學衡》更為強調兩者間互補、互融的方面。柳詒徵曾在《中國文化西被之商榷》中提出中國文化對外之發展的問題,也尖銳地發問:中國文化的要點何在,可以傳播于歐美?他的觀點是,中國文化的價值即在人倫道德,“吾國文化唯有人倫道德,其他皆此中心之附屬物”,“西方立國以宗教,震旦立國以人倫”,“其于道德,最重義利之辨”,“吾國之學,不講超人之境,而所懸以為人之標準者,最平易亦最艱難”。④柳詒徵:《中國文化西被之商榷》,《學衡》第27期,1924年。而西方文明經歷了從古希臘到羅馬,再到近代歐美各國的思想文化之變遷。在《學衡》看來,近代以來盛行的西洋文化,乃“造作工具之文化”,絲毫不能增進于人之善。而重在人倫的中國文化,“乃進善人性之文化也”,擁有“極中和之道德,極高尚之文學”,正是可以作為西洋文化的一劑藥石。兩種文化實際具有相互補偏糾弊之作用,“東西洋文化咸適其用,不相為害而相為益”。⑤太虛:《東洋文化與西洋文化》,《學衡》第32期,1924年。
《學衡》明確提出要建設中國的新文化,這種新文化“當兼取中西文明之精華而熔鑄之、貫通之”。⑥梅光迪:《論今日吾國學術界之需要》,《學衡》第4期,1922年。因此,盡管《學衡》諸君對新文化派的觀點多有批評,但在建設新文化的必要性上,雙方是一致的,都試圖尋求中國文化的轉型和創新之道,如梅光迪就說:“夫建設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①梅光迪:《論今日吾國學術界之需要》,《學衡》第4期,1922年。但在對于新文化的理解以及具體實現路徑方面,雙方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學衡》所要追求的新文化,是一種兼容了中西文明之精華的世界性的新文化。這一文化對于已有的中西方文明都有所揚棄,所凝聚的兩種文明的精華來自各自的古典文化,所想著力發揚的,亦是這兩種古典文明所具有的人文性、道德性的思想內涵。可以看到,這種觀點具有鮮明的新人文主義學說的特點。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學說強調的便是中西文明在根源處的共通與契合,即中西方古典文化中都蘊含了人文道德的重要智慧,乃是人類文化的精華。而具有了這樣一種古典人文主義精神的新文化,亦是一種世界性的新文化。
在建設新文化的具體思路方面,《學衡》諸君認為,要融會中西,首要的便是對中西文化的精粹作出準確的判斷,而這依然需要以全面和精深的學術研究為依據。他們認為,新文化的建設重在“通知舊有之文化”。而這種所謂的“通知”,則應是“對于中外歷史文化社會風俗政治宗教,有適當之研究,而對于中國古籍,如六經、諸子史、漢魏晉唐宋元明清諸大家著作。西籍如希臘、拉丁、英、德、法、意諸大家之文學及批評,亦皆加以充分之研究”。②胡先骕:《論批評家之責任》,《學衡》第3期,1922年。吳宓則是基于對中西方文化的一種判斷,即“中國之文化,以孔教為中樞,以佛教為輔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臘羅馬之文章哲理與耶教融合孕育而成”,提出首先應著重研究“孔教、佛教、希臘、羅馬之文章哲學及耶教之真義”。③吳宓:《論新文化運動》,《學衡》第4期,1922年。梅光迪也提出了自己對于新文化建設的構想:“改造固有文化,與吸取他人文化,皆須先有徹底研究,加以至明確之評判,副以至精當之手績,合千百融貫中西之通儒大師,宣導國人,蔚為風氣,則四五十年后成效必有可睹也。”④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學衡》第1期,1922年。也就是說,《學衡》諸君認為,要形成融會中西的新文化,一是需要以對中西方文化的徹底研究為基礎,尤其是對中西古典思想的研究,形成明確的評判;二是造就融貫中西的學術大師,培育良好的學術風氣,以促進新文化的培養和建設。
從近代張之洞提出“中體西用”以來,中西文化的關系問題就一直是中國文化建設所必須面對的重要時代問題。《學衡》的新文化觀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中西體用的關系,具有一種世界性。他們認為,中西文化在根源處是相契合的,中西古典文化中關于道德的、人文的精神是一致相通的,近代西方文化遠離了這種精神,而中國的新文化則應立足于發揚傳統中的這種人文主義精神,同時吸取西方古典文化的精華,如此貫通起來的新文化是超越中西之爭的。“向西方文明之古典源頭追溯的傳統主義學術取向一方面使《學衡》在歐化問題上與新潮分道揚鑣,同時也使《學衡》突破了傳統的‘體用’模式”,因為這種新文化是“超越東西界限而含有普遍永恒價值”的。⑤孫尚揚:《在啟蒙與學術之間:重估〈學衡〉》,《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序言,第13頁。這種人文主義的方案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轉型與創新問題提出了一種獨特的解答。
與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大眾的路線相比,《學衡》集中在學術層面的探討,側重于學術領域對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學衡》試圖走的是一種精英主義的路徑,認為文化層面的創新需要由知識精英來完成。正如其宗旨所闡明的,《學衡》“論究學術,闡明真理”,以學術立言,無論是批評還是研究學問,都能秉持慎思明辨、平情立言的學術精神。他們與現實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但并非沒有現實關懷,而是把現實關懷升華為一種學術的觀照。在他們看來,“學術者,又萬世之業也”,知識分子有責任傳承文化并為新文化的建設奠定堅實的學術根基。這種堅持學術本位,致力于學術積累和傳承的辦刊實踐,擁有一種文化上的純粹性。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學衡》諸君在各個學術領域的巨大貢獻證明了其絕非魯迅所說的“假道學所發的假毫光”,而是“中國現代學術的中堅力量之一,更代表著一種不可偏離的學術路向”。①孫尚揚:《在啟蒙與學術之間:重估〈學衡〉》,《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序言,第15頁。而其所傳達出的中正、穩健、審慎、理性的文化態度,超越了復古和激進的兩端,具有中道精神,在文化的古今中西之爭問題上,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別樣的視角。《學衡》所提出的問題和作出的探索,直到今天依然具有現實意義和啟示性。
A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Based on Xue Heng
Sheng Danyan
Xue Hengis a unique cultural journal in the journal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 its essays having a special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its style being moderate and steady. The journal suggests an attitude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neither being blindly conservative and reverting to old ways nor being totally negative. Instead, it advocates to promote the quintess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s for western culture, the journal suggests to make accurate judgement and utilize its essence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academic study. On the basis of new humanism,Xue Hengdeems that the classic civilization of China corresponds to that of the West, so that we should combine the essence of these two civilizations to develop a new culture of China. Adhering to academic position, the cultural thoughts inXue Hengtranscend the dispute 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and the West, thus demonstrating a quite different style from other journals in the same period.
*盛丹艷,女,1981生,江蘇張家港人。《學術月刊》雜志社編輯。主要研究方向為文化理論。
責任編輯:沈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