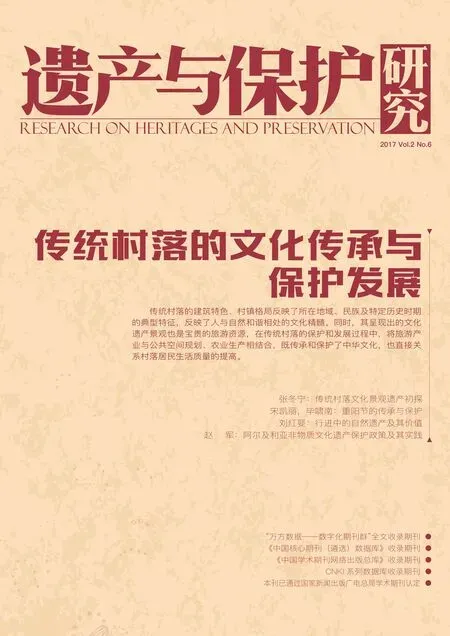文化旅游產業影響下的鄉村公共空間規劃研究
閆 晨,黃艷萍
(福建農林大學園林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2)
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曾存在過許多公共空間,如村口、集市、碼頭、茶館、村肆、祠堂、廟宇等,這些公共空間正是鄉村文化、宗族文化、民俗文化和農業生產文化的載體[1]。然而隨著城市化的影響,傳統的鄉村公共空間逐漸被新建的基礎設施所取代,其獨有的文化遺產也逐漸被弱化和淡忘。隨著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推進和鄉村文化旅游的發展,人們意識到:傳統的鄉村文化不僅僅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還能夠為文化旅游產業帶來經濟效益,而鄉村公共空間的合理規劃便是保護鄉村文化遺產和帶動文化旅游產業的重要環節[2]。因此,鄉村公共空間的規劃是旅游規劃的一項戰略性工作,對今后鄉村資源的有效配置、合理開發、文化旅游的健康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3]。
規劃是在尊重自然環境、了解當地人文環境、順應客觀經濟發展的前提下進行。本文以閩西客家古村落培田村為例,探討其存在的問題和解決方案,以期為鄉村公共空間的規劃提供參考。
1 試驗地概況
試驗地培田村位于福建省龍巖市連城縣,總面積約為18.12 hm2,所轄14個村民小組,擁有389戶1 400余人。該村屬于中亞熱帶山地氣候,具有常年氣候溫暖濕潤、年溫差較小、春雨繁多、夏熱多雨、秋高氣爽、冬少嚴寒的氣候特點。試驗地為峽谷平原地勢,其東臨環抱古村的河源溪,西為松毛嶺,北倚武夷山脈,具有良好的風水資源。
該地塊對外交通可達性強,周邊擁有公路、鐵路和航空立體交通運輸體系,距連城縣僅40 km。村內有幾處被列為國家4A級景區的建筑古跡和傳統宅院,并與相距僅35 km的國家風景名勝區冠豸山聯動,成為連城縣重點旅游線路的一部分。
祖先文化和農耕文化是培田村最重要的文化特征,自古以來,在村內都流傳著“求神不如祭祖”的說法,且傳統耕作被村民視為是崇敬自然和勞動的一種行為[4]。除此之外,閩西地區的傳統技藝還包括有剪紙、打糍粑、墨畫、豆腐制作、竹編等。
2 現存問題與解決策略
2.1 現存問題
(1)建筑風貌不統一。除了作為旅游景點的幾座古祠堂和宅院之外,多為缺乏修繕的古民居、自建自改的現代民房或簡陋的棚戶,其中部分民居廢棄。
(2)基礎設施不完善。村內交通系統缺少必要的組織和引導性標識。廢棄地多,現有公共空間和綠地利用率低且景觀效果差。
(3)青壯年人口外流。村內多為留守老人、婦女和兒童,一部分村民陸續遷往河源溪北岸的新村,鄉村社群空心化。
(4)產業結構單一。多數居民以農耕為主要經濟來源,收入不穩定。部分居民以旅游業的相關產業為生,如土特產、手工藝品、餐飲、民宿等,但由于基礎設施和配套設施不完善,且產品缺乏包裝和特色,游客滿意度較低,導致收益甚微。
(5)商業活動分散。村內現存一條以鄉村傳統商業活動為主的“千米古街”、一個依附于荷花池的集市、數個分散在村內的餐館和民宿,其間缺乏良好的聯動性。
(6)傳統文化被忽視。傳統的民間技藝及民俗文化并沒有得到良好的傳承,除了特定的節日之外,游客無法親身體驗和參與傳統鄉村文化活動。
2.2 解決策略
(1)將建筑按風貌進行分類,對傳統院落和散布在村內的古跡進行保護和必要的修復,對具有較好風貌的傳統民居進行保留和必要的修繕,對廢棄的民居進行改造或拆除,對影響整體風貌的新建建筑進行立面改造和垂直綠化。
(2)延長千米古街,對路面、建筑立面和排水系統進行修繕,增強傳統商業街的可識別性;通過垂直農場、綠色建筑以及地面的生態營造,增強新興商業區域的辨識度和道路的導向性[5]。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古村的生態環境,降低能源消耗,延長建筑壽命,給村民帶來農產增收,給游客帶來舒適的景觀體驗。
(3)結合村內旅游的線路和古跡的分布,對現有荒廢地進行充分利用,并回收鄉村傳統的建設材料以及廢棄材料進行加工和循環利用。對原有公共綠地的景觀性和生態性進行重新塑造,并結合生產和商業活動,賦予公共空間更加多樣化的功能,同時利用空間與人的活動展示傳統文化[6]。
(4)整合零碎分散的商業活動,結合建筑改造、道路廣場修繕和公共綠地重塑,將其相互關聯起來,并融入文化創意和特色活動的開展,形成較為完整的文化旅游廊道。
(5)借用現代科技和媒體,改變傳統的生產模式,利用生態農業、創意集市、特色民宿和多樣的文化旅游活動,豐富當地的產業結構,吸引人口回流和人才引進[7]。
(6)加強游客對傳統文化和技藝的體驗,增強其開放性,依照不同的節氣和假日定期規劃主題活動,并展示宣傳培田村的歷史、民俗和民謠故事等,讓游客與村民共同感受和創造豐富的文化氛圍,有助于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3 總體規劃概念
“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意寓“田間的阡陌風光甚好,可以慢慢游賞,慢慢歸去”[8]。在快節奏的城市生活中,疲憊的人群需要在某一時刻、某個地點放慢腳步,感受足下的土地,留心身邊的田野。本規劃的愿景是希望通過公共空間的重塑、文化旅游產業的重組和鄉村環境的生態改造,豐富游客的旅游體驗,同時改善居民的居住條件、古村的生態環境,并帶來農產增收和文化旅游的高收益,使培田村重新煥發活力。
4 規劃成果
根據現狀的用地情況以及旅游資源,將零散的公共綠地、商業空間、可利用的廢棄地和民居等串聯起來,分別形成兩條各具特色的帶狀公共空間和4個景觀節點。
4.1 帶狀公共空間
(1)歷史文化公共空間是在原有千米古街的基礎上進行延長,對現存風貌較好古建筑群進行保留和修繕,將廢棄的古民居進行建筑改造,融入文化創意產業、特色民宿和餐飲,開放傳統民俗技藝體驗,使傳統商業活動多樣化、特色化。
(2)綠色生態公共空間是在培田村主街的基礎上進行提升,充分利用廢棄地和現有的公共綠地,結合創意集市和濱水區域,建立可流動的人流集散點和商業活動空間。同時,將新建建筑改造成綠色建筑,并結合垂直農場增加生態和生產效益。
4.2 景觀節點
(1)村口。該節點位于培田村南口,利用村口現存的古老水車,結合當地的鄉野植物,營造出古樸寧靜、自然野趣的氛圍。同時,結合地形,設置了攀登步道、趣味的跌水空間以及具有標識性的觀景塔。在觀景塔中,可以將古村對面的筆架山以及環抱古村的河源溪收入視野,鳥瞰古村的整體格局和風光,引導游客進一步探尋古村的文化風貌。
(2)創意集市。該節點結合濱水空間,規劃了商業活動場地和設施,整合了原有布局散亂的農貿市場,使之成為規范且具獨特風貌的創意商業空間,滿足臨時商業活動以及集散、觀賞和休憩的需求。該節點所增設的多功能攤位,不僅可以滿足基本的產品交易,還提供了休憩、交流的設施,是一個面向周圍鄰里和游客的互動窗口[9]。除此之外,該節點還結合構筑物、建筑物的立面,設置了蔬菜的垂直生產空間,充分利用了自然的雨水、陽光資源,提高農業產量。從微觀經濟的角度看,該節點以及周邊的輻射區域,形成了一個從生產到消費的產業生態鏈,促進了居民的農產收入[10]。這樣的公共空間不僅重現了鄉村集市的特色,豐富了游客的體驗,還為當地居民創造了更多創造商業價值的可能,促進了該區域的經濟發展。
(3)口袋公園。在以住宿、餐飲服務為主的建筑群之間,該節點將打造為一個供游客和村民放松身心、休閑交流的公共空間,營造熱情、友好、悠閑的氛圍。在口袋公園里,開闊的陽光草坪、起伏變化的微地形以及充滿鄉村野趣的植物群落,將為周邊的居民和游客提供自由的活動空間、交往空間、趣味空間以及私密空間,改善該區域的生態環境,并創造美好的景觀視覺享受。此外,該公園還將作為周邊建筑的延伸空間,為室外休閑餐飲和兒童游戲體驗等活動提供潛在的場所。
(4)濱水文化廊。該節點位于培田古村最北端,緊鄰河源溪,是古村和新村之間的過渡區域,同時作為古村的另一個入口。濱水文化廊中,利用傳統民居材料和一些廢棄的農耕器具設計了小型的構筑物、雕塑和壁畫,展示了當地的祖先文化和農耕文化,述說祖先的故事和當地居民的傳統習俗。同時,駁岸空間栽植了觀賞草和半濕生植物,并結合當地的卵石進行駁岸軟化,采用較為輕盈的棧道和透水瀝青對濱水步道進行適度的改造和景觀提升[11]。
4.3 局部設計
(1)多功能攤位。該小型構筑物與親水設施相結合,布置于荷花池邊的創意集市,材料部分取自于當地的石材、木材和建筑廢料。攤位頂部的廊架構造采用了長廊的構架形式,為爬藤植物提供生長空間,能夠為販賣者以及消費者提供良好的遮蔭效果[12]。同時,該構筑物還安裝了太陽能面板和風車,利用太陽能和風能實現創意集市區域的能量循環。
(2)蔬菜墻。蔬菜墻結合建筑立面,對建筑外立面進行一定生態改造的同時,對建筑本身內部的空間小氣候也有一定的改善能力[13]。蔬菜墻以簡單的板塊框架結構,利用自然的雨水進行層層灌溉式的無土栽培,同時,蔬菜板能夠根據太陽的方位進行旋轉,對太陽能進行全面的接收利用,實現陽光最大限度地輻射,延長日照時間。
5 結束語
鄉村公共空間是鄉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近年來,由于旅游經濟強勢植入、城市文化霸權、主體偏向和公共性缺失等,鄉村公共空間發生了巨大變化[14]。文化旅游產業的興起,為鄉村文化的回歸和人們對于鄉村保護的反思提供了良好的契機,而鄉村公共空間就是最能夠彰顯特色文化的載體。
在文化旅游產業影響下,許多農村都會結合鄉村旅游的空間布局思維來對鄉村進行建設,滿足游客休閑所需的同時,將宣傳、公益、體驗、學習等活動聚集于鄉村公共空間當中[15]。因此,筆者以培田村為例,結合實地考察,探討通過鄉村公共空間規劃和生產方式多樣化,形成可持續的文化旅游產業鏈和生態農業生產模式,在優化居民生活環境和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時,吸引人口回流、激活鄉村活力和創造力。期望此文可以為鄉村公共空間規劃的研究提供參考價值,同時為我國的“美麗鄉村”建設作出貢獻。
[1]李郇,鄭佳芬.文化創意植入下的村莊空間改造:以東莞下壩坊為例[J].規劃師,2016,32(8):76- 80.
[2]傅英斌.聚水而樂:基于生態示范的鄉村公共空間修復:廣州蓮麻村生態雨水花園設計[J].建筑學報,2016(8):101-103.
[3]王麗潔,聶蕊,王舒揚.基于地域性的鄉村景觀保護與發展策略研究[J].中國園林,2016,32(10):65-67.
[4]陳芳芳.海西民俗文化的建設與鄉村公共空間構筑[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S1):204-205.
[5]王東,王勇,李廣斌.功能與形式視角下的鄉村公共空間演變及其特征研究[J].國際城市規劃,2013,28(2):57-63.
[6]劉坤.我國鄉村公共開放空間研究[D].北京:清華大學,2012.
[7]袁瑾.傳統廟會與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建構:以紹興舜王廟會為個案的討論[J].遺產與保護研究,2016(2):89-94.
[8]高巍,李海兵,柳澤.基于特色景觀營造的長江三角洲典型村落的公共空間改造:以德清縣三合鄉二都村為例[J].華中建筑,2017(3):85- 89.
[9]張娟,王茂軍.鄉村紳士化進程中旅游型村落生活空間重塑特征研究:以北京爨底下村為例[J].人文地理,2017(2):137-144.
[10]王鵬.社區營造視野下的鄉村公共空間設計研究[D].重慶:重慶大學,2016.
[11]胡全柱.文化自覺視角下鄉村公共空間探析[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56(1):62-69.
[12]張琳,劉濱誼,宋秋宜.現代鄉村社區公共文化空間規劃研究:以江蘇句容市于家邊村為例[J].中國城市林業,2016,14(3):12-16.
[13]王春程,孔燕,李廣斌.鄉村公共空間演變特征及驅動機制研究[J].現代城市研究,2014(4):4-9.
[14]程軻崢.城鄉統籌下鄉村旅游中的村鎮公共空間研究[D].重慶:重慶大學,2013.
[15]張健.傳統村落公共空間的更新與重構:以番禺大嶺村為例[J].華中建筑,2012(7):144-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