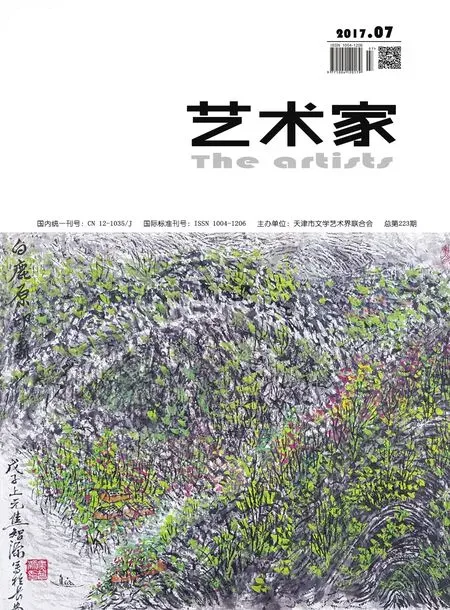就繪畫存在探究藝術(shù)多元之變的主體外因
□楊珍梅 朔州師范高等專科學(xué)校
藝術(shù)當(dāng)隨時(shí)代、藝術(shù)品的產(chǎn)生受到諸多條件的限制,也來自諸多因素的催發(fā)。唯物辯證法認(rèn)為事物的內(nèi)因是事物自身運(yùn)動(dòng)的源泉和動(dòng)力,是事物發(fā)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發(fā)展、變化的第二位原因。內(nèi)因是變化的根據(jù),外因是變化的條件。但是,藝術(shù)品的作者作為社會形態(tài)的人,其成長和形成必定受到外部因素的作用,究其根底,繪畫形態(tài)的存在,不僅反射出主觀因素的精神形態(tài)和存在形態(tài),其深層反射的是外部因素對主體的塑造[1]。
中國繪畫藝術(shù)博大精深,繪畫形式和內(nèi)容隨著時(shí)代的更替不斷更新,究竟是什么樣的外部因素塑造了當(dāng)時(shí)代的作者的性格和作品風(fēng)格?歸根結(jié)底是受到政治制度、社會經(jīng)濟(jì)、科學(xué)與文化方面的制約或引領(lǐng)。今天,就這個(gè)觀點(diǎn)試著探討一下中國繪畫藝術(shù)的發(fā)展脈絡(luò),不充分的地方敬請各位指正。
一、工整細(xì)致的繪畫與繁榮穩(wěn)定的農(nóng)耕文化
唐代的繪畫尤以人物突出,杰出代表有閻立本《步輦圖》、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周昉《簪花仕女圖》、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作為圖像記錄,為現(xiàn)實(shí)生活做出了很大貢獻(xiàn)。此外還有吳道之的道神人物,王維、張?jiān)琛⒗钏加?xùn)的山水。唐代社會穩(wěn)定,生活富裕的側(cè)面寫照,正是這種民族自信和開放包容的社會性格成就了唐代明朗絢麗的藝術(shù)風(fēng)格。
歷史學(xué)家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年之演變,造極于趙宋之世。”有研究者曰:“吾國畫法,至宋而始全。”宋代,政治上處于弱勢,但藝術(shù)比肩唐代,一是繼承了唐代的偉大成就,朝代的更替從本質(zhì)上沒有改變,文化的弦沒有斷也沒有變,宋得以繼續(xù)并發(fā)揚(yáng)光大。二是宋朝的皇帝,大多熱愛文藝,建立畫院,贍養(yǎng)畫師,所謂“上有所好,下必其焉”,形成了全民熱愛藝術(shù)的繁榮場面。宋代小品畫極受后人推崇,細(xì)膩嫻靜,詩詞意蘊(yùn)極濃。但到了南宋的馬遠(yuǎn)、夏圭,將山水畫以邊角的形式呈現(xiàn),這也是宋后期國力不支、民族性格孱弱的體現(xiàn)[2]。
不論唐宋還是追溯以前的五代或魏晉,都處于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相對穩(wěn)定的狀態(tài)。繪畫作品的表現(xiàn)手段和存在形式大致相同,一脈相承,統(tǒng)一具有精致、細(xì)膩的精英式審美價(jià)值。
二、墨戲時(shí)代的開啟與動(dòng)蕩不安的游牧文化
文人畫是士大夫階層抒情表性的一種繪畫方式,它的特點(diǎn)一是娛樂性,是文人以消遣為目的的繪畫;二是精神性,畫中蘊(yùn)含了文人的各種情環(huán);三是不強(qiáng)調(diào)形似,只重視神韻;四是強(qiáng)調(diào)用筆,追求筆墨趣味。此畫種的產(chǎn)生以大文豪蘇軾為代表。文人畫一方面抒發(fā)詩情畫意,另一方面表達(dá)對現(xiàn)世的另類看法。
明清時(shí)期,吏治殘酷,排除異己,朝代更迭的劇烈沖突更是前所未有。在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下,繪畫藝術(shù)失去原有的穩(wěn)定生態(tài),畫家采取明哲保身的態(tài)度,依靠書畫市場換取生存資本,所以作品大多雅俗共賞,內(nèi)容多表現(xiàn)閑情逸致或仙人侍女,代表有吳門畫派、青藤白陽、陳洪綬等。
董其昌與南北宗論。明代后期,官至禮部尚書的董其昌,是繼元趙孟頫之后又一大官僚文人畫家。他的理論,其一輕視吳門畫派,推崇元四家,極力鼓吹文人畫,認(rèn)為繪畫水平取決書法。其二獨(dú)創(chuàng)南北宗論,否定李思訓(xùn),認(rèn)為“漸識”;推崇王維,認(rèn)為“頓悟”。對于中國畫的發(fā)展,這是一次大洗禮。
不能不承認(rèn)當(dāng)時(shí)劇烈的民族沖突、尖銳的社會矛盾、新鮮的異族文化成為激發(fā)作者主觀創(chuàng)造的動(dòng)力和源泉,為明清繪畫形式的轉(zhuǎn)變,提供了主動(dòng)和被動(dòng)的主要因素。
三、藝術(shù)裂變與工業(yè)革命
近代,繪畫兼具了各類藝術(shù)門派的特點(diǎn),從唐宋的詩文入畫始,到明代的書法入畫,直到清末民初,金石味成為寫意畫的又一種審美取向。從吳昌碩開啟融入金石味始,到齊白石衰年變法,到黃賓虹時(shí)期的畫家群,寫意畫的這種風(fēng)格提到相當(dāng)成熟的高度。此時(shí),所謂的南宗完全打敗北宗,以技術(shù)手段為主的繪畫基本不值一提,寫意畫那種多元的欣賞標(biāo)準(zhǔn)為中國水墨畫提供了多種可能,即使不會繪畫的人提起筆來也可以畫出所謂的寫意畫,但修為成一個(gè)令人佩服的畫家又需要終身的琢磨與研習(xí),這是寫意畫因其本身特點(diǎn)為受眾提供的最大的彈性空間[3]。
機(jī)器時(shí)代的到來,是人類的一次飛躍,它不僅直接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也間接改變著人的思維。19世紀(jì)的西方,各種派別異軍突起,比如立體派、野獸派、現(xiàn)實(shí)主義派等等,作者在機(jī)器時(shí)代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行為和思想的突變,一種試圖打破自身精神局限的沖動(dòng)引發(fā)繪畫形態(tài)的多種呈現(xiàn)。比如李可染、林風(fēng)眠、徐悲鴻、蔣兆和等,從廣義的角度審視繪畫的作用和價(jià)值,從實(shí)踐傳承和理論體系上擴(kuò)大了繪畫的概念,建立起以繪畫為主軸的大美術(shù)的概念,為中國美術(shù)立起一座豐碑。
工業(yè)革命給繪畫帶來的影響,主要是觀念上的巨變,如果說以往的繪畫愿意尋祖追蹤,追求和而同,以后的繪畫則追求標(biāo)新立異,追求差而異。因?yàn)闄C(jī)器的復(fù)制給人們帶來不可超越的壓力,人們必將以一種全新的方式確認(rèn)自身的價(jià)值。
四、無厘頭與信息時(shí)代
20世紀(jì)50年代,波普藝術(shù)在英國誕生。波普的意思是:普及的、短暫的、易忘的、低廉的、大量生產(chǎn)的。波普是現(xiàn)代底層藝術(shù)市場的前身,也是大眾文化和商業(yè)社會的文化符號,它的出現(xiàn)不但破壞了藝術(shù)一向遵循的高雅與低俗之分,還使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走向發(fā)生了質(zhì)的變化。
觀念藝術(shù),以20世紀(jì)50年代法國杜尚的《泉》開始揚(yáng)名,也有人認(rèn)為是最為臭名昭著,此后一發(fā)不可收拾。行為藝術(shù)多以性和暴力為表現(xiàn)內(nèi)容,認(rèn)為揭示人的本質(zhì)屬性。裝置藝術(shù)以重置為手段,展示莫名其妙的深刻。在信息化社會環(huán)境的包裹下,作為宇宙的孤獨(dú)存在者,人,無所適從。
信息時(shí)代,很多藝術(shù)實(shí)際上與藝術(shù)本身沒有關(guān)系,只是套用一個(gè)名頭,就像“文革”時(shí)代任何行動(dòng)都要套上語錄,藝術(shù)本身的價(jià)值沒有多少普通人去關(guān)注,普通意義上人們只在乎藝術(shù)本身兩個(gè)字的標(biāo)志作用,以此來區(qū)別與手工勞動(dòng)、機(jī)械生產(chǎn)、科學(xué)研究等社會分工的不同,大概只有少部分人中的一部分會在意藝術(shù)的嚴(yán)肅性和它的原有意義。
五、藝術(shù)的未來在哪里
今天看來,繪畫已是相當(dāng)狹窄的渠道,它包含在美術(shù)中,美術(shù)又包含在藝術(shù)中。繪畫作為基礎(chǔ)的視覺藝術(shù),雖然依舊保持著精神層面的愉悅屬性,但是在廣闊的藝術(shù)領(lǐng)域中,繪畫正逐漸被分解。以繪畫為主的視覺藝術(shù)其美學(xué)功能也逐漸轉(zhuǎn)移到物質(zhì)層面,比如工業(yè)設(shè)計(jì)、廣告設(shè)計(jì)、建筑設(shè)計(jì)、裝潢、園林等,美術(shù)以眾多的方式參與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純粹的藝術(shù)將逐漸被消解,人們隨處可以遇到藝術(shù),但又摸不到藝術(shù)在哪里[4]。
結(jié) 語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科技和自然是相互抵觸的,機(jī)器和人類是相互消解的,當(dāng)外部因素較簡單的時(shí)候,內(nèi)心是寧靜的豐富的,藝術(shù)作品接近高尚;當(dāng)外部因素復(fù)雜的時(shí)候,內(nèi)心是焦慮的簡陋的,藝術(shù)作品異化為無常。兩者此生彼長,永遠(yuǎn)按反比例發(fā)展。人們試圖通過外部彌補(bǔ)自己的不足,反過來,外部的補(bǔ)給再加深內(nèi)部的空缺,就藝術(shù)來講,這是個(gè)永遠(yuǎn)難解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