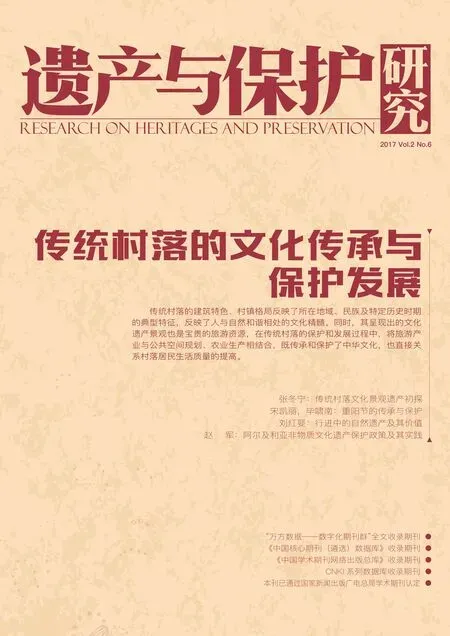文化遺產保護視角下的普孝與普法并舉
陳朝暉
(湖北工程學院中華孝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孝感 432000)
“孝”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文化遺產,“孝入法”可追溯至我國古代以“孝”為倫理核心的宗法禮制。隨著依法治國的理念深入人心和傳統孝文化的回歸,司法界常借用孝道來考量涉孝糾紛案件。學界對此予以回應,在“孝入法”的紛爭中達成共識,既體現了“普孝”與“普法”并舉的社會治理理念,又體現出對傳統孝文化遺產 的保護與利用。
1 近20年的“孝入法”研究
“孝入法”研究有兩層含義:一是法律制度規定孝的權利與義務;二是在法治建設中融入孝治理念。通過CNKI檢索發現,最早研究“孝入法”的論文,見于1998年發表的《孝與漢代法制》。梳理近20年“孝入法”研究,僅有25篇論文。從發文總量上看,這不是一個熱門的研究;但從年度發文趨勢上看,卻是一個充滿活力的話題。2010年和2015年是這一研究的兩個高峰期,從總體走勢來看,發文量呈逐年增長趨勢,這表明:在當今法治背景下,學者開始關注“孝入法”研究,試圖從孝與法的關聯中找到一條適合現代社會發展的治理路徑。
2 紛爭:孝治與法治的沖突
“自漢代,采用司法手段嚴懲不孝犯罪,是孝治施政的重要方面;由于孝治與法治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施政手段,儒家孝治原則付諸歷代封建王朝的司法實踐,程度不同地出現孝與法的矛盾沖突,結果通常是法屈于孝,封建法律原則或司法理性被儒家孝道倫理扭曲,從而形成中國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常見現象”[1]。
“孝”對于法的消極影響,主要有兩點:①孝內涵中幼對長、民對官的絕對服從,漠視了民眾的平等權利;②古代的孝親復仇案、存留養親制度等是孝治影響法治的沖突體現。以現代農村法治為例,“孝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農民法律意識的培養和提高;孝文化阻礙了農村基層民主政治的實現;孝文化容易導致農民獨立人格和法治理念的缺失”[2]。孝的消極影響已危及法律精神。“孝治是傳統中國家國同構和圣賢政治的產物,隨著中國社會從圣賢政治到民主政治、從家國同構到家國兩分、從‘家庭人’到‘社會人’的轉變,傳統的孝治也將逐漸被法治取代”[3]。因此,學界開始思考“孝治”與“法治”沖突的化解之道。“雖然孝依然被現代中國人所秉承和接受,但畢竟它根生于傳統農業社會,曾為專制主義服務,并且是‘人治’的一部分;如今重提孝道,它能否與當今的法治模式和人權主題相契合,不免讓人有些疑惑和擔憂;如果兩者不能契合,孝要么可能淪為某種功利主義做法的標簽,要么可能重新成為人治主義的工具,這一難題不解決,孝的積極意義便很難發揮”[4]。
3 共識:孝治與法治的融合
盡管孝對現代法制建設有其消極性,但在“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同樣重要的今天,非此即彼的思維顯然不妥,應看到傳統“孝治”存在的合法、合理與合情性,解決孝治與法治的沖突最好方式不是對立也不是妥協而是融合。如,涉孝糾紛案件中,法律可用強制手段解決“物質贍養”問題,卻無法解決“精神贍養”問題,但通過借用傳統孝道,可解決當事人的“心病”,正是孝治與法治的融合之道。
關于孝治與法治融合的基礎,許多學者從古代社會治理的經驗出發探討了孝治存在的合理性。夏桂霞認為,“自西周以來,強調宗法孝治的宗族親親、尊尊的倫理制度,要求人們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倫理秩序,規范了人立足于社會的行為準則”[5]。李靜平認為,“夏朝始孝就入律,貫穿封建社會的國家意志,又是儒家的倫理法內容之一,其合理性是老有所養”[6]。王濤認為,“漢代‘以孝治天下’,貫穿于社會各方面,尤其體現于家族法中,使一種道德規范上升為國家法律”[7]。曾少武認為,“古代法律強調遵循禮教、維護綱紀倫常、確定人們血緣關系親疏尊卑和社會等級,親親、尊尊等孝的內容具體體現在法律中,以孝治國的理念成為指導中國歷代王朝立法、司法的基本原則和理論依據”[8]。
正是由于孝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現代法治可借以參考。李俊穎認為,“存留養親制度是中國古代孝與法沖突與融合的產物,是孝文化植根于封建法制的結晶,早已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基礎,但這一制度所體現的人性化特點,對今天的司法實踐具有啟示作用”[9]。孝治對于現代法治的借鑒價值何在?侯欣一認為,“孝滲透中國古代法制的各方面,研究孝與中國古代法制的關系,有助于揭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真正內涵和價值取向”[10]。王學文就“孝”文化是否應入法談到,“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把‘看望、問候’納入到子女贍養父母的法律義務之中,為推廣孝道而立法,可以發揮法律倡導、勸善的功能,令社會老有所依,減少社會對老年人的福利負擔,并有助于將傳統美德保留和發揚”[11]。
4 結論
反思“孝入法”的紛爭與共識,可以發現“孝文化背后具有深層次的法治意蘊:孝文化為現代法治提供了合理的道德價值根基,孝文化體現了中華法系宗法倫理的和諧價值,孝文化是國家法文化的重要補充,要努力實現傳統孝文化在現代法治背景下的創造性轉化”。從文化遺產保護利用與社會治理的視角來看,現代法治同樣強調對傳統孝文化的尊重,我們主張普孝與普法并舉。
[1]黃修明.論儒家“孝治”司法實踐中“孝”與“法”的矛盾沖突[J].江西社會科學,2010(6):56.
[2]易國鋒.傳統孝文化對農村法治建設的影響[J].江漢論壇,2009(5):139-143.
[3]喻中.孝治的終結與法治的興起:從《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17條切入[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2):20.
[4]李擁軍.“孝”的法治難題及其理論破解[J].學習與探索,2013(10):66-67.
[5]夏桂霞.《紅樓夢》再現封建宗法制“孝”“悌”文化[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6):126.
[6]李靜平.論中國古代“孝”的法制文化利與弊[J].滄桑,2010(12):141.
[7]王濤.管窺漢代家族法中的孝[J].法制與社會,2010(24):288.
[8]曾少武.古代納孝入法的歷史本源及法律表現[J].沙洋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0(2):86-88.
[9]李俊穎.孝與法的沖突:淺析清朝存留養親制度的新發展[J].牡丹江大學學報,2014(9):72-74.
[10]侯欣一.孝與漢代法制[J].法學研究,1998(4):134.
[11]王學文.“孝”文化是否應入法[J].山東審判,2012(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