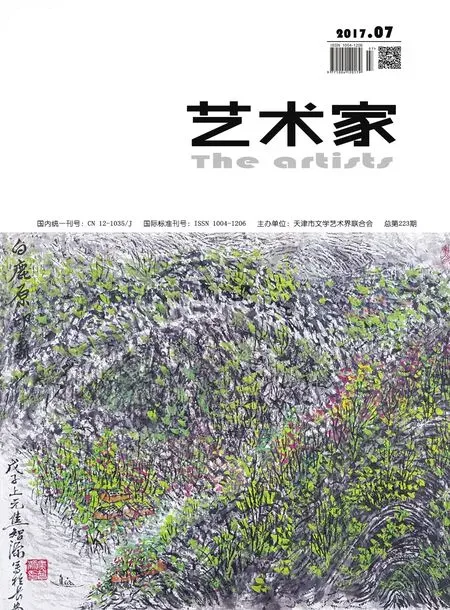淺析中國傳統書法與繪畫間的關系
□譚蕊馨 山東大學(威海)
隨著歷史的發展和演變,中國書法與繪畫在歷史發展上有著緊密的關系。兩者使用相同的工具,在技法和審美情趣上也出現了融合和發展。關于書法與繪畫的關系,唐代張彥遠在其《歷代名畫記》中做出了闡述,在此基礎上,人們發展出了“書畫同體”“書畫同源”“書畫同法”等觀點,且二者的關系也是眾多繪畫論著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見其重要性。本文將從中國書法與繪畫的歷史發展、表現技法、審美鑒賞等方面進行論述思考。
一、書法與繪畫的歷史發展
書法的起源離不開文字的產生。文字經由遠古的“圖畫文字”、甲骨文、金文的象形,發展至東漢、魏晉開始走向自覺,變為一種脫離現實、供欣賞的藝術對象,形成篆書、隸書、楷書、行書、草書等。尤其是后期草書的發展,筆畫更加具有抽象性、符號化的特點,使得書法可以更多地擺脫客觀世界,表現作者本人的內心世界。它來源于具象,脫離于實用。
中國繪畫也起源于象形,由原始的“圖形”發展為“畫”,相較于書法,它保留了物象的形態和氣質。謝赫六法中的“應物象形”,指出繪畫在對物象描繪的基礎上,進行了概括提煉、想象與夸張。漢代是一個藝術大發展的時代,也是我們討論書法和繪畫關系的分水嶺[1]。隨著漢代鴻都門學的建立,書法與功名利祿結合,人們開始重視書法教育并將其上升為藝術,但此時繪畫還停留在教化功能,并未完全脫離實用。至唐代,山水畫的發展才使繪畫進入藝術層面,因此書法的成熟早于繪畫,為繪畫用筆等技法的形成提供了借鑒。也是在漢代,尤其唐代之后,開始了對“書法”和“繪畫”真正意義上的討論。
二、書法與繪畫的表現技法
中國書法與繪畫使用相同的工具——毛筆,就意味著二者在工具使用、技法等方面可以融會貫通,可見畫法與書法相通。
書法比繪畫的成熟時間較早,用筆等方面也為繪畫提供了發展基礎。東晉顧愷之的線條受到篆書的影響,流暢有力;唐代受到行書、草書的影響,吳道子用筆注重提按、用筆方折、重視節奏的快慢變化。中國繪畫講究用筆,其用筆與書法相通,“以書入畫”。書法中書寫的快慢疾馳、停頓轉折等都為繪畫所用,融入“寫意”的意味,將書法的抽象寫意與繪畫的造型相結合,脫離了書法用筆的繪畫,不能夠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繪畫。
中國傳統書法“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是符號化之后的產物,不像繪畫一樣再現客觀世界,而是致力于表現主體的內心世界。書與畫都是“外師造化,中得心源”,但書法擺脫了客觀世界,也更多地展現出作者的宇宙意識、生命意識與時代意識。
中國繪畫與書法在用墨方面也有相通之處,強調“墨分五色”,追求墨色在作品中的變化。除了追求墨色外,繪畫也有色彩的運用。除此之外,都強調畫面的整體布局。中國畫強調“虛實相濟,疏能走馬,密不透風”,與書法強調知白守黑、疏密虛實、干濕方圓等,有異曲同工之妙。
宋代趙希鵠在《洞天清祿·古畫辯》中指出:“善書必能善畫,善畫必能書,書畫其實一事爾。”
三、書法與繪畫的審美鑒賞
中國書法與繪畫有同樣的發源地,受到相同歷史文化環境、中國傳統哲學的影響,在審美情趣上有著共同的追求,除對專業技法的評判之外,更加追求精神思想、哲學層面的意義,以及真善美的追求。
就書法而言,畫家所做的書法,文人學者所做的書法與書家所做的書法,是不同的。畫家相較于書家,其作品筆畫融入了更多的繪畫意味,將書法看作一種形態來對待,追求筆畫的造型、結構;文人學者的書法作品,則更多的是內在文化的傳達,文人氣息更加濃厚。
唐代朱景玄在《唐代名畫錄》中提出了四品“神、妙、能、逸”的品評標準,以“逸”為最高的品評標準,而“逸”離不開畫面和作者的“境界”“氣韻”。人們在初學書法繪畫時,最先掌握的是傳統的技法,掌握技法之后深入探究,并嘗試表達不同的觀念和精神,開始追求畫面的構成。但有許多人在習得技法之后,盲目追求技法,使畫面過于浮躁甚至走向媚俗,其作品并不能得到歷史的認可,甚至被拋棄。中國繪畫與書法的學習,更多的是作者本人自身的修養提升,是對哲學“形而上”的追求,是自我甚至整個社會的修煉。單純地掌握精絕的技巧,不能使藝術家在這一領域中長久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