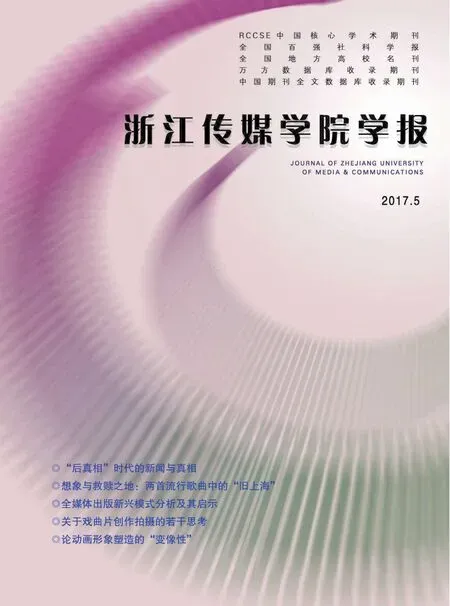“后真相”時代的新聞與真相
陳海峰
“后真相”時代的新聞與真相
陳海峰
2016年“后真相”被牛津詞典官方認定為年度詞,用來解釋這一年發生的諸如英國“脫歐”、美國大選等富于爭議的事件。“后真相”意指情緒超過事實成為影響公共輿論乃至政治社會的因素,真相本身變得不再重要。在大眾傳媒時代,追求真相在新聞業不斷發展過程中逐漸內化為職業理想——即使無法全面實現也要不斷逼近真相。以互聯網傳播技術為基礎的社交媒體時代,新聞業迎來了傳播范式革命,這是社交媒體平臺上“后真相”現象頻頻出現的根本原因。在后真相時代,政治權力和商業力量利用社交媒體制造真相并實現自身利益。
后真相;新聞;真相;范式革命
2016年,“Post-truth”(后真相)一詞由于使用頻次暴增20倍而被牛津詞典官方認定為年度詞——在語言方面反映過去一年熱點的一項指標。牛津詞典總裁卡斯帕·格拉斯沃爾認為2016年“被極具爭議性的政治和社會爭論主導”,“后真相”成為年度詞也在預料之中。“后真相”本意是指“情緒的影響力超過了事實”,在學界被視為政治學概念。[1]2016年的英國“脫歐”、美國大選等一系列充滿爭議的政治事件成為“后真相”的典型注解,世界正在邁入“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時代。
新聞業是一項關于事實和真相的事業,同時與政治密不可分,甚至作為政治本身的一部分而被稱為“第四權力”。當我們將“后真相”和“新聞”放在一起的時候,發現這二者是如此的糾纏和曖昧——“事實”、“真相”、“真實”、“政治”、“輿論”等一大堆與之相關聯的詞語將“后真相”和“新聞”層層包裹起來。那么,“后真相”一詞的誕生對于視真實為生命的新聞業意味著什么呢?本文將就此話題展開探討,嘗試厘清兩者的復雜關系。
一、后真相時代的來臨
(一)“后真相”的基本內涵及產生背景
“后真相”被賦予“情緒的影響力超過事實”的意思,最早是出現在1992年美國《國家》雜志的一篇關于海灣戰爭的文章里。[1]2004年,拉爾夫·凱斯(Ralph Keyes)在其著作《后真相時代:當代生活中的不誠實與欺騙》(《The Post-Truth Era:Dishonesty and Deception in Contemporary Life》)中正式將“后真相”提了出來,用來描述美國政治生活中的新變化:個人信念和情感遠大于真相對民意的影響。[2]凱斯指出,不誠實比性愛和排泄誘發的“繞彎子”都多,欺騙成為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在真實和謊言之間產生了第三類陳詞。[3]
凱斯提出的“后真相”概念并沒有馬上為世人所關注,而是十余年之后牛津詞典官方將“后真相”一詞認定為年度詞的2016年才真正走向大眾。在社會背景方面,“后真相”一詞走紅則被認為與英國“脫歐”和美國大選有直接關系。英國民眾在一些政黨和團體的“忽悠”下以微弱的投票優勢實現了“脫歐”,結果很多英國人很快就后悔“脫歐”了。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特朗普擊敗希拉里當選為新一屆美國總統,然而在隨后的事實核查中被發現有71%的事實表述是完全或大部分錯誤,[4]上任33天平均每天撒謊4次。[5]
從信息傳播的角度來看,從2004年到2016年,“后真相”一詞的社會背景其實發生了不小的變化——社交媒體取代大眾傳媒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凱斯眼中的“后真相”基本上是基于大眾傳媒社會環境而提出的,他批判的對象就包含了說謊的媒體記者Jayson Blair、大學教授Joseph Ellis以及大量的政客、公司經理等。而2016年的“后真相”則與社交媒體不可分割:英國“脫歐”支持者中包含了大量活躍在社交媒體上的年輕人,特朗普則被認為是“推特治國”的總統。所以,社交媒體的興起是推動“后真相”時代來臨的一個重要因素。
根據筆者以上的梳理,發現人們在使用“后真相”一詞時經歷了一個大致的變化:從政治領域到社會領域,從專指到泛指。一開始,“后真相”是指真相變得不再重要,情緒和觀點的傳播裹挾著輿論影響政治決策,這主要發生在歐美國家政治領域。到后來,“后真相”的使用擴展到其他社會領域,泛指那些引發公眾廣泛關注的假新聞,與謠言、“新聞反轉”現象相關聯。而這兩種情況又都默認與社交媒體有密切的關系。
(二)國內外“后真相”研究狀況
國內外關于“后真相”的研究大約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探討“后真相”與新聞(學)、社交媒體、輿論、政治傳播等相關的話題,是按“后真相”概念自身邏輯延伸的研究內容;二是將“后真相”作為一種時代背景來探討另外一些領域的話題。[6]第二類研究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程度較低,因此不再贅述。我們將著重梳理第一類研究成果,相關研究大致分為以下幾類。
一是對于“后真相”政治社會特征的描述,如Jayson Harsin[7]區分了“ROT”(regimes of truth)與“ROPT”(regimes of post-truth)的特點:“ROT”對應的是科學話語、事實(仲裁者)主導的規訓社會(Disciplinary Society),媒體、政治和教育機構緊密結合;“ROPT”對應的是權力利用新“自由”進行“參與/生產/表達”(“消費/擴散/評估”)的“控制社會”(societies of control)。Ari Rabin-Havt等則揭示了一個有組織的、秘密隱藏但不斷成長的“誤傳”行業,行業內的“謊言公司”專門制造并傳播謊言來服務于政治議程。[8]
二是“后真相”時代的新聞事實查驗(fact-checking)問題,例如周睿鳴、劉于思[9]認為,“后真相”語境中的事實查驗失靈現象體現了新聞職業控制與公眾參與之間的矛盾和張力。周煒樂、方師師[10]認為,在“后真相”時代事實核查新聞面臨著從“核查客觀事實”到“協助理解現實”的轉變。
三是中國的一些研究者將“后真相”與新聞傳播學中具體問題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比如:易艷剛以“羅一笑事件”為例探討了“后真相時代”新聞價值標準的變化;[11]董晨宇、孔慶超將“后真相”從國外宏大政治敘事轉移到了中國網民在使用社交媒體時的心理特征上,同時指出這種心理往往被互聯網營銷者利用;[12]開薪悅、孫龍飛將“新聞反轉”現象置于“后真相”視野中進行考察,指出了新聞反轉的常態化可能意味著新聞真實內涵的變化。[13]
國外還有一些暢銷書也論及了“后真相”相關的一些問題。例如,Daniel J.Levitin探討的是在“后真相時代”里如何用科學的方法來鑒定那些“撒謊”的數字和文字。[14]其他暢銷書[15]還有《Post-Truth:The New War on Truth and How to Fight Back》《Post-Truth:How Bullshit Conquered the World》《Trump and a Post-Truth World》等,在此我們不再一一介紹。
縱觀以上研究成果發現,“后真相”本質上反映了大眾傳媒或社交媒體營造的情緒取代了事實和真相,成為公眾決策乃至政府決策的主要參考因素。無論是學者還是大眾,對此都感到十分恐慌。如果進一步區分的話,社交媒體對“后真相”的建構比大眾傳媒要可怕得多。畢竟,大眾傳媒行業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比較完善的職業倫理規范,而社交媒體常常在商業邏輯的左右下不斷沖擊社會底線。從學術研究角度來講,“后真相”對傳統的新聞傳播學中的新聞真實、輿論、政治傳播等問題都形成了挑戰,本文將就此問題做進一步的探討。
二、從真相到“后真相”:“新聞”在悄悄起變化
(一)新聞、事實、真實與真相
我們常說“真實是新聞的生命”、新聞要“用事實說話”,所以新聞與真實、真相、事實這些詞匯有天然的密切關系。那么,新聞就必然是真實的或必然是呈現了真相的嗎?在此,我們對新聞與真實、真相和事實的關系稍作辨析。需要提前說明的是,真實、真相和事實首先是哲學概念。當這些概念與來自新聞傳播學學科的新聞學概念相遇時,我們必須考慮不同學科之間同一名稱概念內涵的差異性。
由陸定一提出的“新聞是新近事實的報道”的新聞定義在新中國新聞理論中具有奠基的意義,我們就從此定義說起。新聞本質上是一種特殊的事實,即新聞事實。新聞學意義的事實是“實際發生的和實際存在的狀態或狀況”。真相是“真實地表現了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真相和本質是一致的。真相一定是事實,但事實不一定就是真相,因為有的事實是假象。真實是認識論意義的概念,是主體對客體的評價。新聞學意義的真實是新聞真實,指的是新聞與真相的符合程度——新聞真實就是新聞事實性真實。事實與新聞的本源有關,而真實與新聞的傳播狀態有關。[16]在理解了新聞與事實、真實和真相的抽象關系后再考察新聞在不同傳播語境中的內涵就會有更加清晰的認知。
(二)大眾傳媒時代的新聞:面向真相而行
新聞向來都不是真相的代名詞。在抽象層面,新聞往往都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真相。在新聞實踐層面,新聞通往真相的道路更加曲折艱難。從新聞把關的角度來講,帕梅拉·休梅克(Pamela J.Shoemaker)將新聞把關分為個人、媒介日常工作、媒體組織、媒體之外社會團體、社會系統等五個層次。[17]也就是說,真相或事實只要歷經五個層次的甄別挑選、扭曲變形才“有資格”成為新聞。這五個層次的把關是新聞生產中客觀存在的,如果再加上政治權力、商業組織或利益集團故意造假的話,真相則無任何可能抵達新聞。
然而,新聞業并沒有因為真相之路困難重重而放棄追求真相。以美國新聞業為例,美國新聞從業者對新聞真實的理解上的變化,就能夠反映整個新聞業對真相的不懈追求:在美國的政黨報刊時期,報刊依附于政黨相互攻訐,意見成為主流的傳播內容,黨派利益和個人見解左右下的報刊只能呈現出非常片面的真實,甚至是謊話連篇;19世紀30年代便士報誕生,獨立報紙走上歷史舞臺,事實性的信息傳播開始取代意見傳播,包括社會底層在內更廣闊范圍的事實得到了呈現。隨后,《紐約時報》等報紙在對抗黃色新聞中塑造了以真實、客觀、公正為特征的新聞風格,將事實視為新聞賴以存在的基礎。[18]
在20世紀初興起的“扒糞運動”中,“扒糞記者”通過深入細致的調查來呈現一種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真實。二戰前后,隨著宣傳、公關等活動的崛起以及傳媒產業進入壟斷化階段,新一代的新聞從業者對調查性報道能否呈現真相產生了懷疑,于是解釋性報道作為一種新的追求真相的新聞報道技術逐漸興盛起來。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完成對越戰和“水門事件”的報道之后,美國新聞業的影響力達到了歷史巔峰。[19]縱觀美國新聞史,是一部隨著“新聞真實”觀念不斷變化而不停追求真相的歷史。
一些重要的新聞理念的誕生,也隱含了追求真相的意蘊。作為歐美新聞業意識形態的客觀性以及新聞專業主義,亦是明知無法真正實現卻努力奔向目標的一種新聞“迷思”。[20]客觀性理念篤信事實可以與價值剝離開來,并通過一套具體的操作技術呈現給受眾。[21]20世紀中期誕生的“社會責任論”,也是在原有呈現真相方式遭遇挑戰后提出的一種追求真相的新理念:報道事實已經不夠了,要報道事實的真相……報刊要描繪社會各集團的典型圖畫。[22]從報道事實到報道真相,新聞業已經自覺追求真相了。
(三)社交媒體時代:制造“真相”的生意
作為一種傳播技術,互聯網激發了人們無限的美好想象,“人人都有麥克風”、“互聯網民主”、“網絡政治參與”、“網絡輿論監督”、“網絡反腐”等一系列話題被不斷提及。當然,我們無法否認互聯網技術賦權的現實和可能性,但同時也必須考慮互聯網傳播模式所帶來的負面沖擊。就有關真實和真相的問題而言,以互聯網技術為基礎的社交媒體對傳統的新聞生產機制和真相呈現程序形成了根本性的沖擊。新浪微博曾因謠言和假新聞而廣受爭議,于是出現了微博“自凈化”的觀點,認為“微博可以通過用戶生產內容的互相補充、糾錯、印證和延伸的結構性關系,自發地接近事實真相”[23]。然而現實是,通過用戶自發呈現真相的案例只能說是偶然現象,社交媒體上謠言仍是滿天飛。后來,國家有關部門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微博謠言整治活動——終究靠的是他律而非所謂的“自凈化”機制。
可以說,社交媒體讓我們走上了一條“去真相化”的道路——進入“后真相”時代。在社交媒體成為信息傳播的主流通道之后,新聞呈現假象而非真相的頻次越來越多了。甚至,每當社交媒體傳出一個熱點事件之后,網友已經習慣于等待“新聞反轉”了。[24]在筆者看來,社交媒體大量催生“后真相”事件是因為受到了兩種邏輯力量支配——政治權力邏輯和商業利潤邏輯。
政治權力邏輯與“后真相”概念的初始內涵有關,即政治權力以自由的名義通過社交媒體制造轟動性的“真相”,從而影響選民投票。典型事件就是英國“脫歐”、2016年美國大選中的政客不斷散布不實信息和煽動性言論,在社交媒體影響輿論走向,進而實現政治目的。Jayson Harsin分析了這種現象,認為“ROPT”(regimes of post-truth)就是控制型社會,政治權力以一種新“自由”的方式來實現參與、生產和表達,具體可以通過大數據分析來實現。[25]商業利潤邏輯是指部分自媒體企業故意制造并傳播一些聳人聽聞、能夠引起網絡亂戰的話題,從而為其自媒體平臺贏得大量流量并實現獲利的情況。微信公眾號閱讀量“10萬+”就是自媒體成功的最重要指標。諸如“咪蒙”之類的微信公眾號賬號深諳此道,幾乎每次發文都能達到“10萬+”的閱讀量。
政治權力邏輯和商業利潤邏輯所對應的現實有很大的差異性,前者存在于宏觀政治場景中,而后者反映在網民微觀的心理層面。[12]不過,兩者都是利用社交媒體操控輿論,都是在做“制造真相”的生意。
三、后真相時代的新聞業
(一)社交媒體傳播范式革命
社交媒體時代“后真相”現象層出不窮,意味著舊的新聞傳播范式正在遭遇危機,新聞傳播乃至信息傳播領域即將發生或正在發生一場范式革命。[26]我們可以就作為解釋框架的新聞定義稍作分析。如果要對“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中所缺失的主體進行補充的話,那么應該是:新聞是記者/報刊/媒體……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但是當我們以此來觀察社交媒體時就陷入困惑:在社交媒體平臺大量傳播的并不是專業的記者和傳媒組織,但又無法否定社交媒體正在生產和傳播大量新聞的現實。舊理論框架遭遇解釋力上的危機,正是范式革命到來的征兆。所以說,“后真相”種種現象只是結果和表象,其本質是新聞的傳播范式的革命。
在筆者看來,大眾傳媒時代與互聯網時代最大的區別在于:前者是專業媒體組織壟斷新聞的生產和傳播,后者是大眾通過各種互聯網應用生產和傳播信息并從中獲得新聞。這種區別同時意味著傳播范式的革命性轉變:大眾取代專業傳媒組織成為信息生產和傳播的主體,大眾傳媒原有功能和定位被架空從而遭遇身份危機:人們不必再通過大眾媒體這個“信息中介”進行表達和交流,各種社交媒體平臺唾手可得,即所謂的“人人都有麥克風”。從大眾傳媒到社交媒體,其把關的基本邏輯也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對于大眾傳媒而言,原始信息材料經過重重把關選擇才有資格成為新聞;而社交媒體大量出現的都是帶有原始信息材料性質的內容,只有那些觸碰宣傳和法律底線的信息才會被“把關”而遭到禁止。[27]這些都是新聞傳播范式革命的具體體現。
(二)社交媒體時代的新聞和真相
大眾傳媒時代或許會被互聯網終結,新聞卻會一直存在。但是,新聞的生產和傳播模式的變化,深深改變著新聞自身的內涵和功能。
普通大眾與大眾傳媒一起成為新聞的生產者和傳播者,新聞的內涵開始變得豐富和復雜起來。新聞的生產和傳播不再奉行新聞專業主義關于事實和價值分開的原則,而是將事實(新聞)和價值(評論)雜糅在一起進行傳播。人們不再從專業媒體組織那里獲取新聞信息,而是習慣于在社交過程中獲得新聞信息——微信朋友圈已經成為很多人獲取新聞的重要途徑。于是,情感交流、情緒表達與獲取新聞的過程融為一體。所以,“后真相”種種現象才得以出現:情緒取代事實成為判斷和決策的依據,真相變得可有可無。
社交媒體范式革命使新聞與真相的關系變得更加曖昧。社交媒體所帶來的傳播范式革命給傳統的新聞業帶來了巨大的沖擊,首當其沖的就是與大眾傳媒傳播范式所匹配的新聞倫理道德和職業規范。在原有狀態下,新聞記者受到新聞倫理道德和職業規范的約束而自覺將新聞真實作為天職。然而到了社交媒體平臺上,大眾取代專業記者成為信息傳播主體,不存在一套倫理規范來約束其信息生產和傳播的行為。所以,社交媒體謠言橫行也很容易理解了——真相,離我們越來越遠。從社交媒體的把關機制看,似乎是更多原始信息材料得到傳播,因此應該更加逼近真相——與社交媒體“自凈化”功能的理念相似。然而在現實中,社交媒體變成了一個獵奇事件的競技場,只有那些煽情的、挑戰底線的話題和事件才能占領輿論高地。再加上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的左右,社交媒體與真相已經無甚關系了。
(三)新聞的民主迷思與互聯網的封建化
研究社交媒體時代的新聞及“后真相”種種現象,自然會考慮新聞與政治民主的關系,很容易就會回到20世紀20年代李普曼和杜威關于民主的論爭上來。這是一個關于大眾、新聞與政治民主關系的迷思。簡而言之,杜威秉承一種傳統的民主思想,相信只有大眾的廣泛參與才能實現民主。而李普曼則對大眾和媒體在民主政治過程中的作用持懷疑態度,他提倡民主政治應該由一批政治精英和專家來運營,大眾作為容易受到偏見左右的群體最好什么都不做。[28]這樣的論爭似乎最終也無法達成共識,而話題延續到了社交媒體時代。
互聯網賦權讓很多人歡欣鼓舞,互聯網技術為政治上的民主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然而,現實卻不是那么樂觀。社交媒體的興盛似乎讓我們看到了另外的一面,即李普曼憂慮的那種情況出現了,受虛假信息蠱惑的大眾瞬間成了烏合之眾。更可怕的是政客、商家利用社交媒體興風作浪,在扇動大眾情緒中獲取利益。如果可以將互聯網空間與哈貝馬斯提出的“公共空間”進行類比的話,原本被寄予厚望的互聯網在不斷走向“封建化”。*哈貝馬斯提出過公共空間的“再封建化”問題,中國學者探討過中國大眾傳媒及互聯網的“封建化”。參閱:展江.警惕傳媒的雙重“封建化”[J].青年記者,2005(3):7-9;史安斌,王沛楠.傳播權利的轉移與互聯網公共領域的“再封建化”——臉譜網進軍新聞業的思考[J].新聞記者,2017(1):20-27;張維.微博公共空間的“再封建化”[J].青年記者,2013(11下):22-23.從傳播的角度看,人們似乎還沒能夠比較合理地使用互聯網這個傳播渠道,常常在“失語”和“失控”之間搖擺,或者“失語”和“失控”兩種狀態同時存在。同時,商業邏輯的控制又急又重,在一定程度上傷害了這個表達工具。在筆者看來,要更大地發揮社交媒體的價值需要在兩個方向上努力:一是自媒體個人和組織應該建立行業自律機制,以自律換自由;二是整體提升大眾的媒介素養和政治素養,培育公眾理性,減少盲從和群體極化現象。
四、結 語
《紐約時報》在2017年初做了一期只有文字的廣告《The Truth Is hard》,其內容是不斷變化以“The Truth Is……”開頭的句子。其中前面的句子主要反映的是美國大選期間包括特朗普在內的政客們對新聞媒體的攻擊性言論以及此前美國盛傳的煽動性言論。最后的四個句子分別是“真相很難”(The Truth Is hard)、“真相難尋”(The Truth Is hard to find)、“真相難知”(The Truth Is hard to know)、“真相比以往都更重要”(The Truth Is important than ever)。這條廣告非常直接地反映了社交媒體時代大眾傳媒的狀態和感受,以及不放棄追尋真相的態度和精神。《紐約時報》的這條廣告也表達了本研究的心聲,社交媒體時代新聞傳播范式革命的趨勢已無法阻擋,但新聞作為追求真相的一項事業應得到繼承。
[1]夏文輝.“后真相”:牛津詞典2016年度詞為啥是它?[EB/OL].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11/18/c_129368227.htm,2016-11-18.
[2]劉學軍.后真相時代社交媒體對美式民主的考驗與挑戰[J].新聞戰線,2017(3):110-112.
[3]Ralph Keye.ThePost-TruthEra:DishonestyandDeceptioninContemporaryLife[M].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04.
[4]陸振華.事實核查真能約束特朗普嗎?[N].21世紀經濟報道,2016-10-24(5).
[5]Chris Cillizza.Donald Trump's unbroken streak of falsehoods now stands at 33 days[N].TheWashingtonPost,2017-2-21.
[6]任隴嬋.“后真相時代”的收視率亂相[J].南方電視學刊,2017(1):87-90.
[7]Jayson Harsin.Regimes of Posttruth,Postpolitics,and Attention Economies[J].CommunicationCulture&Critique,2015,8(2):327-333.
[8]Ari Rabin-Havt,Media Matters for America.Lies,Incorporated:TheWorldofPost-TruthPolitics[M].New York:Anchor books,2016.
[9]周睿鳴,劉于思.客觀事實已經無效了嗎?——“后真相”語境下事實查驗的發展、效果與未來[J].新聞記者,2017(1):36-44.
[10]周煒樂,方師師.從新聞核查到核查新聞——事實核查的美國傳統及在歐洲的嬗變[J].新聞記者,2017(4):33-42.
[11]易艷剛.“后真相時代”新聞價值的標準之變——以“羅爾事件”為例[J].青年記者,2017(2上):17-19.
[12]董晨宇,孔慶超.“后真相時代”——當公眾重歸幻影[J].公關世界,2016(23):90-93.
[13]開薪悅,孫龍飛.“后真相”時代里的新聞“反轉劇”——對新媒體環境下輿論的再思考[J].上饒師范學院學報,2017(1):84-90.
[14]Daniel J.Levitin.WeaponizedLies:HowtoThinkCriticallyinthePost-TruthEra[M].New York:Dutton,2017.
[15]Matthew d'Ancona.Post-Truth:TheNewWaronTruthandHowtoFightBack[M].Ebury Digital(ebook),2017;James Ball.Post-Truth:HowBullshitConqueredtheWorld[M].London:Biteback Publishing,2017;Ken Wilber.TrumpandaPost-TruthWorld[M].Shambhala,2007.
[16]楊保軍.事實·真相·真實——對新聞真實論中三個關鍵概念及其相互關系的理解[J].新聞記者,2008(6):61-65.
[17][美]帕梅拉·休梅克.大眾傳媒把關[M].張詠華譯.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
[18]鄭保衛,李玉潔.真實,一個被追求與被操縱的新聞觀念[J].國際新聞界,2013(5):84-93.
[19][美]達洛爾·M.韋斯特.美國傳媒體制的興衰[M].董立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20]吳飛.迷思與堅守——反思新聞客觀性[J].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5):25-32.
[21]陳力丹,王亦高.深刻理解“新聞客觀性”——讀《維系民主?西方政治與新聞客觀性》一書[J].新聞大學,2006(1):8-16.
[22][美]威爾伯·施拉姆等.報刊的四種理論[M].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103,107.
[23]劉云霄.微博自凈功能的局限性及影響因素——以新浪微博為例[J].新聞世界,2013(3):93-94.
[24]別等反轉啦!地鐵打人案,論法治我只服平安北京[EB/OL].中青在線,http://article.cyol.com/news/content/2017-03/08/content_15720982.htm,2017-3-8.
[25]Jayson Harsin.Regimes of Posttruth,Postpolitics,and Attention Economies[J].CommunicationCulture&Critique,2015,8(2):327-333.
[26][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M].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27]陳海峰.從自媒體把關模式看輿論管理[J].新聞前哨,2014(8):77-79.
[28]胡翼青.調和“李杜之爭”:一種社交化媒體時代的新聞觀——從學術史角度看《新聞的十大原則》[J].新聞記者,2014(4):64-68;單波.新聞傳媒如何扮演民主參與的角色?——評杜威和李普曼在新聞與民主關系問題上的分歧[J].國外社會科學,2003(3):36-42.
[責任編輯:趙曉蘭]
陳海峰,男,講師,新聞學博士。(河南財經政法大學 文化傳播學院,河南 鄭州,450046)
G210
A
1008-6552(2017)05-00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