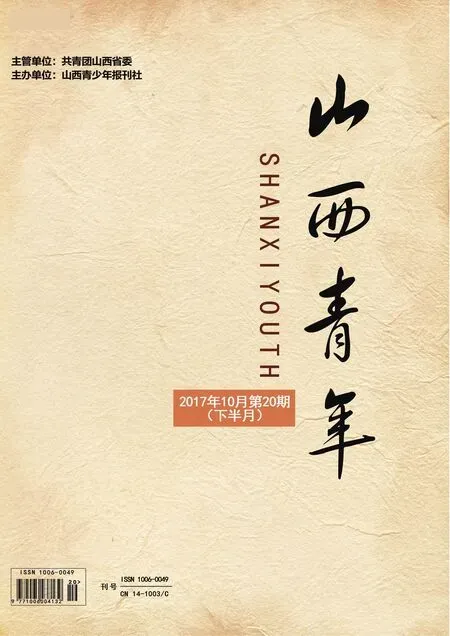歷史不是簡(jiǎn)單的因果關(guān)系*
——讀胡素珊《中國(guó)的內(nèi)戰(zhàn)(1945-1949年的政治斗爭(zhēng))》
孟 艷
外交學(xué)院基礎(chǔ)部,北京 100037
歷史不是簡(jiǎn)單的因果關(guān)系*
——讀胡素珊《中國(guó)的內(nèi)戰(zhàn)(1945-1949年的政治斗爭(zhēng))》
孟 艷*
外交學(xué)院基礎(chǔ)部,北京 100037
美國(guó)學(xué)者胡素珊的《中國(guó)的內(nèi)戰(zhàn)(1945-1949年的政治斗爭(zhēng))》緊緊圍繞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為什么能夠勝出這樣一個(gè)核心問題,以大政治為視角,從城市、農(nóng)村管理和土地改革兩大方面對(duì)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和國(guó)民黨的執(zhí)政能力進(jìn)行了對(duì)比。通過大量期刊文獻(xiàn)的運(yùn)用與分析,作者表明在國(guó)民黨漸漸失去民心與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爭(zhēng)取民心之間不存在簡(jiǎn)單的因果關(guān)系。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之所以能夠取得最后的勝利有兩個(gè)關(guān)鍵性因素,一是自身建設(shè),二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guó)化。充分了解這一點(diǎn),而不是簡(jiǎn)單地認(rèn)為國(guó)民黨的失敗就是共產(chǎn)黨的勝利,才能夠更深刻的認(rèn)識(shí)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所做出的各種努力和嘗試,以及中國(guó)人民選擇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和社會(huì)主義的歷史原因。
中國(guó)的內(nèi)戰(zhàn);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政治原因
歷史不是簡(jiǎn)單的因果關(guān)系,這似乎是每一個(gè)學(xué)習(xí)歷史的人都知曉的簡(jiǎn)單的常識(shí)。然而,我們又必須承認(rèn)在對(duì)一些歷史問題的認(rèn)識(shí)上,往往存在著簡(jiǎn)單的因果式的機(jī)械理解。這種機(jī)械的理解,有時(shí)不僅是方法論上的錯(cuò)誤,最重要的是對(duì)一些歷史事實(shí)的忽略,從而導(dǎo)致對(duì)問題本身的認(rèn)識(shí)發(fā)生根本性的轉(zhuǎn)變。美國(guó)學(xué)者胡素珊的《中國(guó)的內(nèi)戰(zhàn)(1945-1949年的政治斗爭(zhēng))》(以下簡(jiǎn)稱《中國(guó)的內(nèi)戰(zhàn)》)通過對(duì)中國(guó)解放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國(guó)共兩黨政權(quán)易手的原因分析,向我們表明,歷史從來不是簡(jiǎn)單地由一到二的因果關(guān)系。
一、《中國(guó)內(nèi)戰(zhàn)》的“靈感源泉”
《中國(guó)內(nèi)戰(zhàn)》的研究寫作歷時(shí)十年,最終于1978年出版發(fā)行。中文版于1997年由中國(guó)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2014年當(dāng)代人民出版社再版發(fā)行。1997年版本由中國(guó)著名黨史專家張靜如先生作序,2014年版本得到了中國(guó)近代史專家雷頤的推薦。
1945-1949年中國(guó)內(nèi)戰(zhàn)是胡素珊教授政治學(xué)博士論文的一部分,除了本人的興趣外,也與上世紀(jì)60年代末70年代中期美國(guó)的政治環(huán)境密切相關(guān)。上世紀(jì)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是美國(guó)對(duì)共產(chǎn)主義和中國(guó)態(tài)度的轉(zhuǎn)型時(shí)期。《中國(guó)內(nèi)戰(zhàn)》就是“轉(zhuǎn)型時(shí)期的產(chǎn)物”。1969年,尼克松出任美國(guó)第37任總統(tǒng),也就是在這一年胡素珊開始了中國(guó)內(nèi)戰(zhàn)的研究。尼克松上臺(tái)后,1972年訪問了中國(guó),并同蘇聯(lián)簽訂了反彈道導(dǎo)彈條約,自上世紀(jì)50年代以來美國(guó)與共產(chǎn)主義勢(shì)不兩立的強(qiáng)硬作風(fēng)開始緩和。長(zhǎng)達(dá)20年的越南戰(zhàn)爭(zhēng),美國(guó)對(duì)歐洲和蘇聯(lián)的關(guān)注最終轉(zhuǎn)到了亞洲,轉(zhuǎn)到了中國(guó)。由此引發(fā)了該領(lǐng)域?qū)W術(shù)研究主題從“美國(guó)的失敗和蘇聯(lián)的干預(yù)這樣的外部因素占主導(dǎo)地位,演變?yōu)榧杏谥袊?guó)內(nèi)部的原因和規(guī)律”。此外,按照作者自己的說法,這本書的寫作有三個(gè)“靈感源泉”。
第一個(gè)源泉,來自作者的導(dǎo)師查默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1962年,約翰遜教師的博士論文《農(nóng)民民族主義和共產(chǎn)黨政權(quán):革命中國(guó)的開始(1937——1945)》(以下簡(jiǎn)稱《農(nóng)民民族主義》)出版。作者在2014年版的前言中花了比1997年版本更大的篇幅來闡述這部著作對(duì)西方歷史學(xué)界和對(duì)其自身的影響。應(yīng)當(dāng)說,這與約翰遜著作的影響是相當(dāng)?shù)摹T凇掇r(nóng)民民族主義》中,約翰遜提出了一個(gè)與以往同類研究不同的觀點(diǎn),即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人通過領(lǐng)導(dǎo)華北和華東地區(qū)的抗日活動(dòng),贏得了人民廣泛的支持,這才是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最終取得勝利的原因。有評(píng)論指出,《農(nóng)民民族主義》從三個(gè)方面對(duì)共產(chǎn)主義在中國(guó)的勝利做出了創(chuàng)新:(1)大量使用了有價(jià)值的、從未使用過的新材料;(2)緊扣他所認(rèn)為的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取得勝利的關(guān)鍵問題;(3)作者使用了一系列特殊概念,特別引入民族主義的概念進(jìn)行分析,這與以往研究相比更為學(xué)術(shù)化。但是受當(dāng)時(shí)美國(guó)政治環(huán)境的影響,約翰遜的觀點(diǎn)遭到了美國(guó)左翼學(xué)者的批評(píng),并引發(fā)了持久激烈的討論,這場(chǎng)爭(zhēng)論至少持續(xù)到了上世紀(jì)90年代中期。作者表示,正是這場(chǎng)爭(zhēng)論從反面提供了靈感和動(dòng)力,促使她從中國(guó)社會(huì)本身探索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勝利的原因。
第二個(gè)靈感源泉來自約翰·S·謝偉思。1944-1945年,謝偉思隨美國(guó)觀察組前往延安。通過在延安的實(shí)地調(diào)研,觀察組的“中國(guó)通們”最早認(rèn)識(shí)到一旦發(fā)生內(nèi)戰(zhàn),中共而不是國(guó)民黨將會(huì)成為最終的贏家。包括謝偉思、戴維斯這些美國(guó)外交界的中國(guó)通一致認(rèn)為:“為當(dāng)前抗日和戰(zhàn)后遏制蘇聯(lián)這兩個(gè)美國(guó)的實(shí)際利益著想,中共軍事力量應(yīng)該成為美國(guó)政府盡可能與中共保持良好關(guān)系的原因。”當(dāng)上世紀(jì)50年代麥卡錫主義流行后,這些中國(guó)通被指控為美國(guó)“失去”中國(guó)的罪魁禍?zhǔn)住km然經(jīng)過不屈不撓的抗?fàn)帲麄兿此⒘恕安恢艺\(chéng)”的罪名,但是,謝偉思,還有像戴維斯這樣的一些年輕外交官卻因此斷送了政治前程。1962年9月,謝偉思進(jìn)入加利福尼亞大學(xué)伯克利分校學(xué)習(xí),攻讀政治學(xué)碩士學(xué)位,成為了查默斯·約翰遜的學(xué)生。兩年后,54歲的謝偉思以全A的成績(jī)畢業(yè),并留在伯
克利中國(guó)研究中心,直到1973年退休。1972年9月,謝偉思夫婦再次來到中國(guó),并在中國(guó)恢復(fù)聯(lián)合國(guó)合法席位后得到了周總理的接見。謝偉思始終堅(jiān)持其在上世紀(jì)40年代的關(guān)于“共產(chǎn)黨強(qiáng)而國(guó)民黨弱”的觀點(diǎn),他本人則成為中國(guó)研究中心研究生重新發(fā)現(xiàn)歷史的“活紐帶”。還有像謝偉思同時(shí)期的鮑大可一樣的學(xué)者,為致力于“共產(chǎn)主義為什么在中國(guó)取得勝利”研究的研究生們提拱了榜樣,他們關(guān)于中國(guó)的研究成果也成為研究的重要基礎(chǔ)。此外,謝偉思為中心“做了很多善事,其中一件就是把共產(chǎn)主義中國(guó)研究資料圖書館辦成了世界上最好的資料室。”
第三個(gè)靈感源泉,來自于居住在伯克利,對(duì)中國(guó)問題有所了解和有親身經(jīng)歷的一些人。其中有國(guó)民黨軍隊(duì)的軍官和他們的后人,他們的回憶以及對(duì)那段歷史的親歷與感受更加激發(fā)了作者研究的興趣。特別是一位受訪者提到的《觀察》雜志,對(duì)《中國(guó)的內(nèi)戰(zhàn)》的寫作提供了重要幫助,作者自己形容為“十分幸運(yùn)”。書中大量引用了《觀察》雜志中的文章,特別是《觀察》雜志主編儲(chǔ)安平的觀點(diǎn)主張。這個(gè)源泉也解決了筆者在閱讀中的一個(gè)困惑,為什么作者會(huì)如此多地使用報(bào)刊的文獻(xiàn)資料。
二、在國(guó)民黨失民心與共產(chǎn)黨得民心之間
在這本51萬字的著作中,作者緊緊圍繞一個(gè)核心問題,即“在內(nèi)戰(zhàn)時(shí)期,共產(chǎn)黨勝出的原因是什么?”。書中引用了大量的報(bào)刊資料、共產(chǎn)黨文件匯編、調(diào)查報(bào)告和西方學(xué)者的研究成果,闡明了國(guó)共兩黨的城市和農(nóng)村的經(jīng)濟(jì)與社會(huì)政策,以及這些政策措施對(duì)學(xué)生、工人、農(nóng)民和知識(shí)分子產(chǎn)生的影響。僅參考文獻(xiàn)作者就列出了58頁(yè)(全書共480頁(yè)),不得不讓人驚嘆作者對(duì)如此龐雜材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提煉付出了多少心血及其體現(xiàn)出來的研究能力和嚴(yán)謹(jǐn)?shù)难芯繎B(tài)度。
作者將政治權(quán)力的爭(zhēng)奪戰(zhàn)看作各種資源的交換以及導(dǎo)致這種交換的條件,那么一個(gè)關(guān)鍵因素就是如何從現(xiàn)有政權(quán)手中收回資源。如果現(xiàn)政權(quán)存在可以利用的弱點(diǎn),如和各社會(huì)群體之間的脆弱關(guān)系,奪取權(quán)力的目標(biāo)就會(huì)更容易。基于這樣的研究思路,全書分兩大部分展開:“國(guó)民黨統(tǒng)治的最后歲月”和“共產(chǎn)黨的勝利”。在第一部分,作者重點(diǎn)探討了國(guó)民黨在接管日占區(qū)的經(jīng)濟(jì)管理、社會(huì)政策及其對(duì)學(xué)生、工人、知識(shí)分子和農(nóng)民的影響。這些政策以及在這些政策實(shí)行過程中國(guó)民黨表現(xiàn)出來的腐敗與能力不足使得國(guó)民黨與以上四類社會(huì)群體之間的關(guān)系變得更加脆弱。與此同時(shí),共產(chǎn)黨在取得最后勝利的社會(huì)基礎(chǔ)方面也沒有太多的優(yōu)勢(shì)。
從學(xué)生來看。在“反饑餓、反迫害、反內(nèi)戰(zhàn)”的學(xué)生運(yùn)動(dòng)中,國(guó)民黨步步緊逼,迫害學(xué)生運(yùn)動(dòng),甚至使用了國(guó)際法明令禁止的達(dá)姆彈來對(duì)付學(xué)生。“任何想要用暴力對(duì)待青年的人都不大懂得他們的心理,同樣他也不懂得什么是教育。將所有的青年學(xué)生都看作是(共產(chǎn)黨)匪徒將迫使他們加入對(duì)立的陣營(yíng)。”即便如此,我們也很難估算學(xué)生在多大程度上完全站到了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這一邊。《觀察》雜志在1948年轉(zhuǎn)載了對(duì)學(xué)生的問卷調(diào)查說明了這一點(diǎn),支持共產(chǎn)黨一黨專政的學(xué)生比例只有2.7%。
從城市工人階級(jí)看。國(guó)民黨在接管日統(tǒng)區(qū)后,面臨非常嚴(yán)峻的經(jīng)濟(jì)形勢(shì)。雖然國(guó)民黨政府嘗試一些整頓、管理辦法,但始終沒能恢復(fù)城市正常的生產(chǎn)生活,逐漸失去了城市勞工對(duì)國(guó)民黨的信心。國(guó)民黨又一次把失去工人的支持歸咎于共產(chǎn)黨的活動(dòng),然而真正的問題在于:1、日本人的占領(lǐng)有效地切斷了國(guó)民黨對(duì)勞工的控制;2、抗戰(zhàn)結(jié)束時(shí),工人們普遍期望勝利能為他們帶來經(jīng)濟(jì)上的好處;3、猖獗的通貨膨脹和工商業(yè)減產(chǎn)破壞了戰(zhàn)后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因此,工人的騷動(dòng)根本無需共產(chǎn)黨來“制造”,同時(shí),投機(jī)的商人、富人不僅沒有受到任何影響,甚至還發(fā)了戰(zhàn)爭(zhēng)財(cái)。受壓迫最深的勞工隨著自身經(jīng)濟(jì)狀況的惡化,已幾近淪為無產(chǎn)階級(jí),對(duì)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主張的社會(huì)主義的恐懼感下降了。盡管如此,當(dāng)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接管了北平、天津、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后,仍然困難重重。如何穩(wěn)定經(jīng)濟(jì)秩序,控制通貨膨脹?如何發(fā)展生產(chǎn)?如何培養(yǎng)城市勞工的階級(jí)意識(shí)?如何解決干部的短缺問題?土地改革的經(jīng)驗(yàn)、共產(chǎn)黨在管理城市方面的經(jīng)驗(yàn)以及蘇聯(lián)的經(jīng)驗(yàn)顯然非常有限,現(xiàn)實(shí)問題更為復(fù)雜,更不用說來自理論上的挑戰(zhàn)。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在最初和后來的城市管理中同樣犯了很多錯(cuò)誤,如過多強(qiáng)調(diào)了平均主義,過分關(guān)注工人的要求,由此引起的工商界的恐慌,以及不切實(shí)際的工資發(fā)放辦法等。但是,“共產(chǎn)黨都積極地——假如不總是完全成功地——避免國(guó)民黨政府在1945年犯下的錯(cuò)誤。然而就像他們所做的所有其他事情一樣,這個(gè)成就得來并不輕松。”作者在第八章和第九章,用近90頁(yè)的篇幅來說明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在接管城市后進(jìn)行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從知識(shí)分子來看。必須承認(rèn)自由知識(shí)分子對(duì)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和社會(huì)主義的評(píng)價(jià)更多的是負(fù)面的,即使在他們已經(jīng)不再支持和忠于國(guó)民黨的時(shí)候。負(fù)面評(píng)價(jià)集中于對(duì)“內(nèi)戰(zhàn)”和“蘇聯(lián)”的消極認(rèn)識(shí)上。基于“一切困難都出在內(nèi)戰(zhàn)”的判斷,很多人認(rèn)為共產(chǎn)黨對(duì)戰(zhàn)爭(zhēng)負(fù)有相同的責(zé)任。“兩個(gè)黨派以整個(gè)國(guó)家為代價(jià),追求他們自己的自私目的”,還有人指出,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只關(guān)心世界革命,而不顧及自己的國(guó)家。同時(shí),受到蘇聯(lián)的牽連,中國(guó)共產(chǎn)黨被當(dāng)作是法西斯,兩者都想通過嚴(yán)格的組織來控制民眾的意愿。雖然知識(shí)分子承認(rèn)共產(chǎn)黨在國(guó)民黨做的糟糕的地方獲得了成功,但是他們對(duì)共產(chǎn)黨的“一黨專政”缺乏熱情,更希望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可以加入聯(lián)合政府。
從農(nóng)民來看。說中共對(duì)知識(shí)分子和學(xué)生抱有一種較為復(fù)雜的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是由這兩個(gè)群體的階層性質(zhì)以及他們對(duì)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的態(tài)度造成的。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對(duì)待農(nóng)民的態(tài)度則是由農(nóng)民階級(jí)內(nèi)部的復(fù)雜性決定。這種內(nèi)部的復(fù)雜性又是由中國(guó)國(guó)情的復(fù)雜性和國(guó)內(nèi)軍事形勢(shì)變化造成的。因此,作者對(duì)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的農(nóng)村政策,特別是土改政策做了大篇幅的解讀(近90頁(yè))。其中,作者對(duì)“土地改革里的非土地改革因素”、土地改革與土地革命的關(guān)系進(jìn)行了初步探索,特別是突破了長(zhǎng)期以來對(duì)土地改革的傳統(tǒng)理解。這要比國(guó)內(nèi)的研究早了近20年。雖然國(guó)內(nèi)研究受到時(shí)代因素等影響,但考慮到作者在美國(guó)60、70年代能夠進(jìn)行這樣的探索與分析,實(shí)屬不易。
三、小結(jié)
就是在這樣的基礎(chǔ)上,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一點(diǎn)點(diǎn)地爭(zhēng)取民心。在對(duì)待后抗戰(zhàn)時(shí)期的農(nóng)村問題和城市問題上,共產(chǎn)黨沒有任何現(xiàn)成的理論政策和現(xiàn)成的經(jīng)驗(yàn)可供借鑒,卻解決了在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一切棘手、迫切的問題,顯示出了極強(qiáng)的生存能力與適應(yīng)能力。這種能力不是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有了先進(jìn)的指導(dǎo)思想,自然就可以獲得的能力,在這一過程中,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歷盡曲折,經(jīng)過了試驗(yàn)、錯(cuò)誤,付出了巨大代價(jià)。另外,我們必須要看到:“共產(chǎn)黨并非恰好在對(duì)的時(shí)間來到了對(duì)的地方,從國(guó)民黨的崩潰中獲利。1949年,并不是所有民眾都支持在中國(guó)大陸建立共產(chǎn)黨一黨專政。但是共產(chǎn)黨的成績(jī)可圈可點(diǎn),為大眾轉(zhuǎn)而擁護(hù)它們領(lǐng)導(dǎo)的新政府提供了基礎(chǔ)。”
在書的最后一章,作者對(duì)全書的內(nèi)容做出了同樣出色的總結(jié),提醒讀者中國(guó)共產(chǎn)黨能夠取得勝利付出的巨大代價(jià)。不僅如此,作者對(duì)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取得勝利的內(nèi)因——“共產(chǎn)黨的靈活與耐心,一步一步地,一個(gè)指示一個(gè)指示地,將其奪取政權(quán)的斗爭(zhēng)調(diào)整到與環(huán)境相適應(yīng)”。作者極其簡(jiǎn)要地回顧了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在其歷史上的重要時(shí)刻,如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的轉(zhuǎn)型,1934年后在華北發(fā)動(dòng)土地革命等。作者將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這種敏于應(yīng)變的能力,沒有僅僅歸結(jié)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dǎo),而是試圖在1942-1944年的整風(fēng)運(yùn)動(dòng)中尋找答案。然而,作者的論述戛然而止,沒能對(duì)這個(gè)問題繼續(xù)深入下去,但是我們可以體會(huì)到其中蘊(yùn)含的巨大的現(xiàn)實(shí)意義。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之所以能夠迅速地適應(yīng)環(huán)境,做得比許多國(guó)家的共產(chǎn)黨都要出色,是因?yàn)椋伯a(chǎn)黨不僅掌握了馬克思主義提供的分析工具和組織模型,而且更善于通過黨的建設(shè)包括思想、組織紀(jì)律和行動(dòng),來解決中國(guó)實(shí)際的問題。“用這樣的辦法,共產(chǎn)黨將自己的利益與中國(guó)絕大部分人口的利益緊密聯(lián)系起來,從而獲得了群眾的擁護(hù)。堅(jiān)實(shí)的群眾基礎(chǔ)滿足了它對(duì)糧食和人力的需要,使它與國(guó)民黨做斗爭(zhēng)時(shí)有充分的供給。”
此外,作者還提到毛澤東對(duì)馬克思主義的態(tài)度。毛澤東認(rèn)為,馬列主義不是現(xiàn)成的靈丹妙藥的教條主義,而是一個(gè)理論工具,只有在實(shí)地考察了中國(guó)社會(huì)各階級(jí)的實(shí)際生活狀況后,它的有效性才能被證實(shí)。馬克思主義作為全黨指導(dǎo)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在于此。馬克思主義是科學(xué)的理論體系,是科學(xué)的分析工具,是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的政治標(biāo)識(shí)。同時(shí),馬克思主義必須同具體實(shí)踐、具體問題相結(jié)合,才能發(fā)揮其本來的效能。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通過黨的建設(shè)推動(dòng)馬克思主義的中國(guó)化,反過來馬克思主義中國(guó)化及其不斷深化也對(duì)黨的建設(shè)起到了推動(dòng)作用,同時(shí),也對(duì)黨的建設(shè)提出新的要求。將黨的建設(shè)與馬克思主義中國(guó)化聯(lián)系起來看做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取得政權(quán)的原因,說明作者抓住了問題的根本,抓住了“因”—國(guó)民黨失去民心和“果”共產(chǎn)黨贏得民心、取得政權(quán)之間的“秘密”。這也是這本著作在今天讀來仍饒有趣味,具有重要現(xiàn)實(shí)意義的根本。
[1][美]胡素珊.中國(guó)的內(nèi)戰(zhàn)(1945-1949年的政治斗爭(zhēng)).王海良,等譯.中國(guó)青年出版社,1997.
[2][美]胡素珊.中國(guó)的內(nèi)戰(zhàn)(1945-1949年的政治斗爭(zhēng)).啟蒙編譯所,譯.當(dāng)代中國(guó)出版社,2014.
[3][美]琳·喬伊納.為中國(guó)蒙難——美國(guó)外交官謝偉思傳.張大川,譯.當(dāng)代中國(guó)出版社,2014.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yè)務(wù)費(fèi)專項(xiàng)資金項(xiàng)目:青年教師科研啟動(dòng)基金項(xiàng)目重點(diǎn)項(xiàng)目(3162017ZYQA03)。
孟艷(1979-),女,漢族,河北靈壽人,博士研究生,外交學(xué)院基礎(chǔ)部,講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guó)化。
K
A
1006-0049-(2017)20-00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