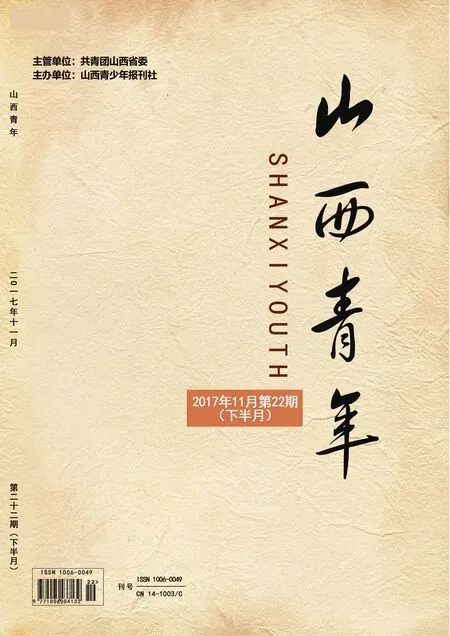對清朝時期天山南路漢回信仰需求的思考
柯 榕
對清朝時期天山南路漢回信仰需求的思考
柯 榕*
新疆醫科大學,新疆 烏魯木齊 830000
清朝平準叛亂之后,大量的漢回進入新疆且行走于不同的路線,天山北路的漢回主要以屯民和士兵為主,天山南路則多是商人群體與綠營士兵,不同的身份使得天山南北漢回在信教需求上各有不同。本文試圖通過分析那彥成奏折提到回民(漢回)“充當阿渾”一事分析天山南路漢回信仰需求,以及清朝管理者可能存在的問題。
阿訇;漢回;天山南路
一、移民天山南北的漢回不同身份特征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平定準噶爾部叛亂之后,在新疆實行了一系列獨具特色的行政、軍事、經濟和社會文化管理機制,這些制度的建立為穩定當時的新疆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本文試圖研究的人群漢回在當時的新疆人口比例中所占很少,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學者將這一人群稱為回民[1]。平準事件之后有大量的內地移民遷入新疆,其中占重要人口的是回民,也就是清朝官員口中的漢回(本文涉及的回民僅指漢回)。雖然漢回與新疆回子同樣信仰伊斯蘭教,但地域差異使其各俱特色,“在全世界的伊斯蘭社會中,將禮拜寺的最高宗教者稱為阿訇的,(除了喀什噶利亞有若干例子之外)只有中國回民伊斯蘭。”[2]由于移民天山北路和南路的漢回來源不一,身份不同,進入新疆為了適應當地的生活環境和人文習俗,信仰習慣也經歷了本土化的過程,新疆回族群體并沒有完全進入原有少數民族伊斯蘭教的體系,而是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信仰習慣,這些現象可以從清朝初期漢回的大規模移民找到歷史根源。
(一)天山北路漢回主要由屯民和士兵構成
元朝以來,漢回以其活躍的商業活動為依托,定居或流走于中國的各個地區。“居住在關內各地的回民族,其歷史大約有一千三百五十多年,回民進入新疆地區的時間最晚.....到今天為止不過是三百多年,”[3]雖然沒有史料明確記載回民進入新疆的具體時間,但根據學者的推斷,“天山北路的回民,可能是在18世紀30年代清朝將準噶爾勢力驅逐到吐魯番盆地以西之后,自1760年開始逐漸從內地移居過來的。”[4]早期的移民者主要來自陜西、甘肅這兩處毗鄰新疆的區域。甘肅肅州回民較多,乾隆年間為了分散該地區人口壓力,遷肅州回民往新疆地區,“《甘肅通志稿》說‘(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移肅州回民分駐哈密’。”[5]“乾隆三十五年從甘肅等省遷往吉木薩爾,阜康的回族屯戶就有1150戶。三十六年,清政府又以‘屯墾實邊’為名,將陜、甘、青回民集體遷徙新疆。據當時戶口統計,僅由甘肅遷居迪化的便有2萬人以上,在達坂城居住的也有500戶。”[6]有學者認為:“新疆回族史始于元朝,而于清朝有較為明顯的變化。”[7]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天山以北一些重要的地區已經有相當規模的漢回遷徙入住,以屯墾戍邊為主要職責。
(二)天山南路商人群體已有一定規模
在天山南路,回子居住較為密集,清政府采取漢、回隔離政策,限制內地的漢人隨意進入回疆地區。所以行走于天山南路的回民可能主要是個人或三五成群的商人團體,并且前往南路經商的漢回人數不斷擴大。《回疆則例》規定:“內地漢民,前往回疆各城覓食傭工者,如無原籍、年貌、職業、印票及人票不符,即行遞解回籍,”此處史料主要是針對內地漢人經商人員,在經濟上嚴格控制入疆商人來源。而在1829年,欽差大臣那彥成在限制漢回移居新疆的對策中提到:“嗣后內地漢回赴回疆貿易、傭工者,均令在原籍請票出關,注明年、貌、執業、照驗,”[8]從那彥成特別強調漢回這一點可以看出,這一時期赴天山南路經商的漢回人數較多,可能已經形成一定的規模從而引起管理者的特別重視。
除了經商的漢回群體外,士兵也是天山南路漢回人口的主要來源。天山南路一些重要的城市實行換防兵制,從換防時間上由最初的二、三年改為后來的五年更換,并且不能攜帶家眷。這些處于天山南路的漢回群體,就不像多數居于北路的漢回一樣,有較為固定的生活地點和生活方式,天山南路漢回部分是士兵,在軍隊編制管理下活動,另一部分是商人,人數分散流動性強。清政府在宗教管理上是否對這個群體給予足夠的注意和關照。佐口透學者在其著作《新疆民族史》新疆的回民一節中提到“關于19世紀50年代喀什利亞的回民,瓦里汗諾夫曾做過考察。他說東干,漢語稱回回,是來自陜西、甘肅、四川的中國回教徒,他們自稱東干。他們有哈乃斐派和沙斐儀派。東干人著漢服,有漢人的相貌,說漢語,在自己的禮拜寺中念著阿拉伯語的祈禱文。”從瓦里汗諾夫的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東干人也就是清初的漢回,在喀什利亞有一定的人口,他們擁有自己的禮拜寺,并不是在當地人的清真寺中進行宗教活動,并且念阿拉伯語的祈禱文。
二、漢回“充當阿渾”行為的另一種思考
喀什噶爾參贊大臣那彥成在道光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一份奏折中稱:“漢回盤踞各城,誆騙回子財務,教誘犯法,久為回疆之害,......張逆滋事以前,竟有漢回剃去發辮,充當阿渾之事。”從那彥成奏折的這段說明中可以看出兩個問題。其一,1828年天山南路主要的城市漢回商人已有一定數量,漢回在當地經商,取回婦為妻由來已久。其二,有部分漢回剃去發辮,充當阿渾。
阿訇(阿渾),伊斯蘭教中職業宗教者的通稱。據《西域圖志》記載:“回子通經典者曰阿渾。為人誦經,以禳災迎福。每遇大年、小年(兩大節日),阿渾誦阿伊特瑪納斯經,為眾祈佑。”阿訇作為職業宗教者,致力于經典研究和教學,通過經文學校向學生教授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以解經誦讀為目的培養后繼的職業宗教者。諸多學者對清朝時期清政府對新疆阿訇及伊斯蘭教的管理政策做過研究,普遍認為清政府對伊斯蘭教采用“恩威并用”[8]、剿撫并存的方式。
清政府官員很早就意識到阿訇在信教群眾中的影響力。“回俗阿渾為掌教之人,凡回子家務及口角爭訟事件,全憑阿渾一言剖斷,回子無不尊依。”[9]所以,“慎選充當回子阿渾”[10]是清政府對下級管理官員反復傳達的信息,什么樣的人員能夠充當阿訇,選取阿訇的具體過程如何,史料上并沒有明確的記載,但是在《欽定回疆則例》中可以看到這樣的內容:“回教阿渾為掌教之人,回子素所信奉,遇有阿渾缺出,由各莊伯克回子查明通達經典、誠實公正之人,公保具繕,準阿奇木伯克稟明,該管大臣點充”。“如有不知經典,化導無方,或人不可靠及剝削回戶者,即行懲革”,并對“原保之阿奇木伯克一并參辦”。
從史料中可以看出,清政府要求阿訇的任用必須通過各莊伯克推舉賢能人士,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過去阿訇地位高于伯克的狀況,伯克掌握任命阿訇的實際權力,但是為了防止阿訇和伯克互相勾結,欺騙地方官員,清政府的行政官員亦可作為監督者,對不可靠的阿訇嚴格查辦,甚至連推舉伯克也一并參辦。
分析那彥成奏折的這段內容,在“充當阿渾”這件事上顯然有疑問。既然明知清朝政府對遴選阿訇如此重視和嚴格,那么當地漢回為什么要冒險犯法去充當,畢竟以經商為主體的南路漢回看似在政治生活上并無太多訴求,希望通過“充當阿渾”來獲得世俗地位的目的顯然不可能實現。筆者認為這一事件背后顯示出來的問題在于清朝管理者不是真的了解漢回和當地回子在伊斯蘭教信仰上的差異,不了解引發的管理真空可能不僅體現在宗教方面,也許已經輻射到漢回生存的各個方面,從而使得這一群體直接或間接的被反叛分子利用,與清政府的離心力日益明顯。
三、對天山南路漢回的宗教環境思考
(一)清政府對待天山南路漢回態度的轉變
清朝統治者對待移民南路或者經商的漢回態度有明顯的變化,從接受到控制再到防范。隨著南路漢回人數的不斷增多,漢回勢力日漸強大,且天山南路多是商人或者士兵,還有因受內地新教起義事件牽連的逃犯和無業游民,清朝官員認為這些人不務正業,誘騙回子犯法,成為社會治安不穩定因素,于是開始建議朝廷控制人口的流動,加強管理,包括不能和回婦通婚等諸多限制。19世紀中期張格爾叛亂,叛軍利用或者蠱惑這些在新疆四方貿易的漢回,由于商人群體大分散小聚居,沒有能力抵抗叛亂,便任其俘虜割辮,剃去發辮在清朝統治者看來是逆反行為,剃發即站在了清朝政府的對立面,也很可能作為勾結外部勢力或者叛逆分子造反的證據。于是清朝從控制漢回人數開始轉為防范和抓捕逆反人員,即使是被迫剃去發辮者也被發配給官兵為奴或者到云貴地區充軍。這一態度的轉變過程,反映了清朝政府對南路漢回群體認識的缺失和管理的真空。
(二)充當阿訇是部分南路漢回的信教需求
清朝官員認為漢回“充當阿渾”是對當地回子起到了不好的作用,是對回子盤剝誆騙的另一種形式,管理者對阿訇這個宗教職業者的敏感度和影響力認識深刻,認為漢回是希望通過阿渾這個宗教職業者的地位獲取世俗權力。筆者認為“充當阿渾”的行為是漢回進行宗教生活的需求,回民有自己的清真寺,就不得已需要自己的阿訇,個別漢回“充當阿渾”不排除其為投機謀生的手段。佐口透學者在其《新疆民族史研究》一書中寫到新疆的回民一節,舉例陜西渭南縣的回族商人趙均瑞,在阿克蘇和葉爾羌地區經商多年,“據說他(趙均瑞)在葉爾羌、阿克蘇還擔任了鄉約,這說明他被公認為當地寓居回民集團的長老和管理者。”這里的鄉約應該就是回族教胞的代表者鄉老,回民商人趙均瑞在這一地區經商多年,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在當地有較為穩固的人脈資源,是回民集團的代表人和管理者。從上述的材料可以看出,隨著漢回人數的不斷擴大,這個群體的生活處境較為矛盾,雖同樣信仰伊斯蘭,但南路漢回擁有自己的清真寺和阿訇及其教坊管理者,并非和當地回子的信仰習俗完全相同,由于語言的限制,回民未必能真正融入當地的宗教生活中,生活在天山南路的漢回,在選取阿訇等職業的宗教人士方面沒有合理合法的渠道,只能通過民間選取的方式。所以在清朝官吏口中的“充當阿渾”一事,筆者認為可能是部分漢回在天山南路尋求的生存之道,而并非完全出于誆騙和謀逆的心理。
(三)天山南路漢回的教派發展難成系統,易受忽視
天山南路和北路的漢回在伊斯蘭教派發展程度上不盡相同,南路回民難以形成受人矚目的規模,則自身的宗教需求更容易受到忽視。乾隆皇帝平定準噶爾叛亂之后,在天山北路設置了17個墾區,屯墾的士兵將當地的教派門宦制度帶入新疆,“時妥明所傳虎夫耶在烏魯木齊一帶影響較大,該門宦中有一些回族官吏,如迪化綠營參將索煥章就是妥明的弟子,索煥章加入后,虎夫耶在新疆發展很快。”[11]在一些官吏或者有威望的人的推動下,后期虎夫耶和哲合林耶門派在新疆都有了較快的發展。天山北路回民多為兵屯和農民,生活環境較為穩定,在教派發展上沿襲內地的門宦制度,發展基本沒有受到阻力。而天山南路多是流動貿易的商人群體,多數不具有穩定的生活環境,再加上清朝政府的控制和防范,人數較少,沒有明顯門宦制度發展的痕跡,雖未見有史料反應真實狀況,但是由于大部分商人也是陜甘一帶遷徙而來,本身帶有不同教派門宦的區別,組織形式如一盤散沙,管理的真空使得這一群體的宗教生活需求不能得到保障。
總的來講,由于內地漢回移民新疆的身份和路線不同,導致了天山南北的漢回在伊斯蘭教宗教習俗和宗教生活上有很大不同,由于清朝統治者的嚴格管理,南路漢回身份復雜多樣,沒有穩定的生存環境等因素,使其生存條件和信仰需求都較北路更加艱難,“充當阿渾”現象所體現的是漢回尋求宗教自由和信教空間的本質,而當時清朝政府對這一本質的忽視,認識不足以及管理的真空為后來回民起義迅速在新疆引起回響,以及新疆漢回群體努力尋求生存空間和伊斯蘭話語權的行為埋下伏筆。
[1][日]佐口透.1760—1860年新疆回民簡況”.回族研究,1992(2):50.
[2][日]佐口透.新疆穆斯林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210.
[3]馬良駿.考證回教歷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85.
[4][日]佐口透,著,章瑩,譯.新疆民族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69.
[5]穆德全.清代回族的分布.寧夏社會科學,1986,10:60.
[6]馬偉.多元融通的新疆回族宗教文化特征研究.新疆師范大學,2012.
[7]蓋金偉.近二十年新疆回族史若干問題研究述評.西域研究,2007(2).
[8]《那文毅公奏議》卷77,道光九年三月五日奏.
[9]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商務印書館,1936:264.
[10]《欽定回疆則例》卷八.
[11]馬岳勇.新疆回族伊斯蘭教的宗教人類學考察.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10(6):48.
柯榕(1987-),女,新疆人,初級職稱,新疆醫科大學,研究方向:中國史新疆近現代民族史。
G
A
1006-0049-(2017)22-007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