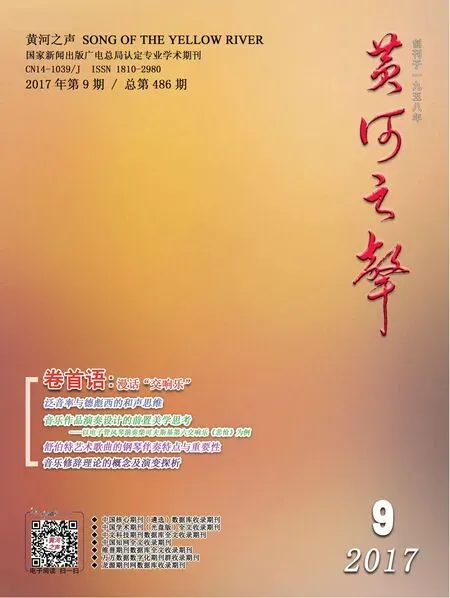“鄭聲”概念的轉變
楊影子
(湖南師范大學音樂學院,湖南 長沙 410006)
“鄭聲”概念的轉變
楊影子
(湖南師范大學音樂學院,湖南 長沙 410006)
本文以筆者在學習中發現的有特殊意義的詞語“鄭聲”為研究對象,通過“鄭聲”這個詞語從周朝以來,經過兩漢時期,到隋唐時期的概念的變化,來闡述這些同類詞語由具象的特指意義,向抽象的美學概念轉變的大趨勢。
“鄭聲”;美學
一、“鄭聲”的最初含義
狹義的“鄭聲”是指的春秋時期的鄭國的民風歌謠。季札在魯國觀樂時說:“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矣,是其先亡乎?季扎發此言論時,是與其他諸侯國民歌相比較時所說,因此,“鄭”是指鄭國,代指鄭國的音樂。東漢許慎《五經異義·魯論》中所說:“鄭國之俗,有溱、洧二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惑,故云鄭聲淫。”這里后世的敘述也證實了“鄭”即鄭國。
“聲”在《樂記·樂本》中有云:“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這里的“聲”即是“聲音”,“音”,則是“音樂”,“樂”即為“雅樂”。“鄭聲”的“聲”也是此意,因為孔子在提出“鄭聲”這一概念之時,已有了“放鄭聲”、重雅樂的態度,是有貶低鄭國音樂的目的的,于是用“聲”而不用“音”,是“鄭聲”而非“鄭音”。只是后人在釋義之時,直接將此詞解釋為鄭國的民風歌謠。且《禮記·樂記》有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僻嬌志,所以是淫也。”此處為“鄭音淫”,則“鄭音”與“鄭聲”,為同意詞匯,鄭聲=鄭音,同為鄭國民風歌謠。
而在《史記·樂書》中有記載:“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彼,何也?”由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兩個“何也”之前的句子為同意排比,則鄭衛之音與新樂為名異實同。則此時的“鄭衛之音”是后世鄭聲內容的擴大,不僅是加入了衛國之音,而且還有泛指一切與古樂相對的新樂的含義。在朱熹的《詩集傳·鄭風》中所云:“世則鄭聲之淫有甚于衛矣。”是以取言之重者,因此鄭衛之音在后世又簡稱鄭聲。是以,鄭衛之音、鄭聲、鄭音互為別稱。
而在孔子的言論中,“鄭聲”這個概念在《論語》中出現了兩次,其一是《論語·衛靈公》中,“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其二是在《論語·陽貨》:“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這兩處言論很清楚的能顯示出孔子對“鄭聲”的態度,“放”和“惡”這兩個字很明顯的體現了孔子的立場,也不難看出孔子是以“為邦”和“鄭聲”本身“淫”的特點出發的。因此,在孔子論“鄭聲”之時,“鄭聲”還是指它的狹義即鄭國的地方音樂,而非它的泛指概念。
二、后世“鄭聲”的含義
(一)先秦時期
子夏曾說,“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s煩志,齊音傲僻嬌志,所以是淫也”。這里可以看出,子夏與孔子一樣,對鄭聲是認為“淫志”的,即是在追求聽覺享受方面失去了節制,而且子夏不僅斥鄭聲,還斥宋音、衛音、齊音,認為這四國的音樂都是于“志”有百害而無一利的。這里的“鄭聲”的含義其實還是鄭國的民風歌謠。
(二)兩漢時期
兩漢時期,雅樂的地位不斷衰微,鄭聲的含義也不斷擴充,已經進化到了涵蓋了一切的通俗音樂的概念了。《漢書·禮樂志》有云:“……秦倡員二十九人,……楚四會員十九人,巴西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六人……或鄭衛之聲,皆可罷。”這是西漢末年漢哀帝“罷樂府”時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所奏。由此可見,漢代此時已經把秦、楚、巴、齊、蔡等地方的樂曲都歸為“鄭聲”。而此時,“鄭聲”與所在的地域已經沒有多少關系了。
《漢書·藝文志》中記載,“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這里說的是當時的雅樂已經徒有其形而無其神,并且失去了雅樂的中心地位,而鄭聲以其超越雅樂的藝術性被人們所喜愛。這從側面能夠看出鄭聲也不是只指鄭國的民間音樂了,而是泛指與雅樂相對立的通俗音樂了,可以稱之為“俗樂”。
(三)隋唐時期
隋唐宮廷燕樂機構的建立與發展更是體現了燕樂的繁榮發展。隋代在開皇初期就以法令形式確立了七部伎的燕樂體制,隋煬帝時,增設兩部,擴充為九部伎。這七部伎與九部伎的內容除了國伎之外,全是民間音樂。
三、結語
鄭聲的概念轉變其實是伴隨著朝代的更替、制度的變化而形成的。從周代禮樂制度的建立,孔子摒棄鄭國地方的音樂,到禮樂制度的衰敗,鄭聲作為一個與雅樂相對立的名詞流傳下來,到漢代泛指與宮廷音樂相對立的一切非雅樂,再到唐代之后,鄭聲更是作為燕樂的一部分。鄭聲的含義與內容經過各個朝代不斷的層累,地域范圍不斷的擴大,從鄭地到鄭衛兩地,再到整個諸侯國;內容不斷地增多,從單單指鄭國的民間音樂,到泛指一切的亡國之音、靡靡之音。鄭聲的概念到了最后,泛指一切與古樂、雅樂相對立的新樂、俗樂。
鄭聲含義其實是一個名詞由具象的代名詞向抽象概念的轉變,是從一種音樂類型向一種美學概念的轉變。隨著周代禮樂制度的消亡,鄭聲這一種特定的音樂實體也消亡了,但是鄭聲這個詞作為概念名詞留下來了。并且后世的文人不斷的豐富鄭聲的內涵、增加鄭聲的內容,直到“鄭聲”成為了一個美學概念,代指一種音樂形象、一種音樂類型。這種概念性的轉變也不只是存在“鄭聲”這一個詞身上,包括在先秦時期與“鄭聲”相對的“雅樂”的概念也是如此,由具象的儀式典禮用樂向抽象的美學方面的概念轉變。■
[1] 徐希茅.喻意志.中國音樂史與名作欣賞普修教程[M].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9.
[2] 何晏,皇侃.論語集解義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5.
[3] 李學勤.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4] 李方元.周代宮廷雅樂與鄭聲[J].音樂研究,19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