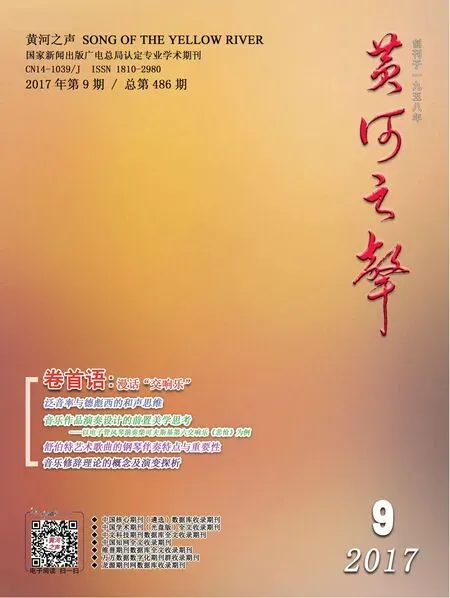羌族二聲部牧歌研究
師立軍 李成秀
(阿壩師范學院,四川 汶川 623002)
羌族二聲部牧歌研究
師立軍 李成秀
(阿壩師范學院,四川 汶川 623002)
論及牧歌,人們會自然聯想到14世紀起源于意大利的牧歌,其抒情的世俗歌曲有別于教堂內的宗教歌曲,又或許聯想到我國北方內蒙古、新疆地區草原游牧民族流傳的長調音樂。然現今聚集于四川西北部阿壩州地區的羌族人民,是幾千年前北方游牧民族的后裔,其文化內涵不僅具有中原農耕文化特征,且游牧民族文化形態共存,本文著眼于羌族勞動歌曲之牧歌形態,研究羌族二聲部牧歌音樂本體特征與其文化內涵和審美特征。
羌族民歌;牧歌;二聲部民歌
中國民間音樂的產生離不開各族人民的生產勞動和社會生活,也非朝夕之間而誕生,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它是人民為了表達思想情感和表現生活面貌而結晶的一種藝術形態。現生活在阿壩州地區的羌族人民,最初是以牧羊為主要生產方式,古書記載“羌,西戎牧羊人也”,早期的羌族人,居無定所,依隨水草,地少五谷,以牧羊為業。隨后逐漸遷途至岷江上游的古羌人民,開始學習農耕技術,在高山上開墾土地,開始了定居的農牧生活,長期以來的這種生產生活方式,留存下了大量的具有特色的羌族勞動歌曲和山歌。
伴隨勞動而產生的歌曲,羌語稱“直布勒惹木”,勞動內容大致涵蓋了耕田、積肥、背肥、打麥、撕玉米、鋤草、上山撈樹葉等,二聲部勞動歌曲集中在阿壩州北部地區,主要有“哦若勒”、“沙蒙”、“納登恰”三種。山歌在羌語中稱為“喔都惹木”,意指山間田野所唱歌曲,按照不同地域、不同的勞作內容和表達情感的差異等諸多因素劃分,“喔都惹木”又被細分為“納拉”、“古納”、“尕羅”、“婁”等幾種類型。其中“納拉”全稱為“納吉納拉”或稱為“拉索”,是羌民在田間地頭勞作時演唱的歌曲;“古納”又稱“哈依哈納”通常是上山或行走時演唱的歌曲;“尕羅”的演唱場合適用于多種勞動場景,是限于二人演唱的多聲音樂;“婁”為婦女們牧羊或行走時演唱的二聲部歌曲,人數不限。這兩類歌曲除音樂本體形態特征存在差別以外,其表達的思想情感和描繪的生活場景幾近相同,而羌族牧羊歌曲是兼具兩種風格特征的一種勞動山歌形態而存在。
一、羌族牧歌的音樂本體分析
羌族牧歌是牧羊時候演唱的歌,疊溪以下的岷江、黑水河及雜谷腦一帶的茂縣、汶川、理縣等地的牧歌以單聲為主,多聲為輔。岷江上游的疊溪以上牧歌形態主要以二聲部為主。其詞義表達的內容多為抒發情感、熱愛生活、熱愛家鄉的為最多。如流傳于茂縣地區的牧歌《這支歌來自何方》歌詞大意是“這一支歌,來自哪方?不唱不行,唱起來吧!……”,再如流傳于松潘縣鎮坪鄉新民村額《牧羊歌》,其歌詞大意為:“天晴放羊,下雨關羊,風兒吹,草兒動,羊兒歡,心兒爽……”該歌曲的譜例如下①:

此曲是由“Do、Re、Mi、Sol”四個音構成的五聲調式,旋律音調以“Re”為起音,從中音區跳進至高音“DO”,以Re-Sol-Do-Re的旋律形態為動機,不斷發展變化,數拍之后高音聲部從高音區進入,一開始于下聲部形成一個三度音程,緊接著進入到純五度音程,隨后純四度、大二度、純一度音程依次進行,整首歌曲旋律情深意濃,節奏多由前緊后松的節奏型貫穿使用,上下兩個旋律節奏無鮮明對比,相同節奏型同步的應用居多,旋律中使用獨特的顫音演唱方法,上下游移不定的微分音是旋律別具一格,余音繞梁、回味無窮。
通過對松潘、茂縣、汶川等地的40余首牧歌比對分析,結果表明:羌族多聲部牧歌音樂多為五聲調式音階,也有六聲、七聲調式應用的情況,徵調式最多,其次為宮、羽調式,而角調式應用最少。旋法上多以三度、五度、八度的跳進為主,二度級進次之,二聲部縱向結合的音調常構成三度、四度、五度、六度和二度的音程關系,樂句或樂段末尾多以八度或同度結束。旋律核心音調多以“Re-Sol-La-Do”、“Sol-La-Do-Re”無半音的四聲音階進行為主,與河湟、洮岷地區流程的花兒音調極其相似。旋律中出現的“Fa”常微升,“Si”則微降,多出現的“Fa”音易構成旋律下方五度的轉調現象。節奏常用前長后短的非方整節奏型構成,兩個聲部一前一后交錯出現,類似號子一樣“一領眾合”,但節奏變化較小,多同節奏進行。音樂結構有單句變化體、兩句式樂段、三、四、五句式樂段,或有歌頭、歌尾構成的擴充式樂句結構。
二、牧歌的功能與特征
音樂要素的有機結合,構成了音響運動的客觀過程和主觀的審美風格,歷經千年的羌族人民長期生長在農牧業社會自給自足的經濟基礎上,不同階層或社會需求的音樂,不同類型或內容的音樂都體現著各自鮮明的特征。
音樂是文化的象征,符號的應用象征集體的智慧,對一個族群的思想意識、心理情緒、行為活動等各方面起著巨大的作用。“牧歌”一詞可以作為特定的符號來認知,讓人直接與山區、草場、羊群對接,它成了放牧生活的符號,這種特符號并無特別的意義,然而把它回歸于幾千年前的游牧民族的特定歷史背景中,它就富有了真正的含義。
演唱牧歌的羌民們以女性居多,她們置身于自己熟悉的生活環境,演唱場合在山林地頭,面對群體亦為自己本群體的局內人,不會給“歌手”的演唱帶來心理壓力,演唱形式是無樂隊伴奏的清唱,可以更自由的即興發揮,即便是多人合作,也顯得流暢自如,演唱方法具有開放性,沒有對歌者作統一的聲音要求,天然生成,不加刻意修飾,聲音風格豐富多樣。
(一)牧歌的審美功能。一首牧歌的演唱,給予對家鄉的眷戀,二聲部和聲的創造,表達了多人的對話,從動機的發展、旋律的走向、音程的連接、織體的變化、音色的對比、節奏的律動各方面無不顯現其音樂意境。
(二)牧歌的娛樂功能。無論中西方民族音樂,大都具有著娛樂性質,一個主要的形式就是游戲。在枯燥的牧羊過程中,人們互相游戲、對歌、交流,是對時間的一種消磨,很大程度上與人們的行為關聯,是這種特定的勞作情形下的娛樂手段。
(三)交流表達功能。通過高低起伏的音符、形態各異的旋律、輕重緩急的速度、不加修飾的音聲等種種方面的傳遞,在特定的民族、特定的空間、特定的文化圈內用作與人、與羊、與自然交流的媒介,它能釋放一種用語言無法表達的思想情感。
(四)文化象征功能。二聲部牧歌音樂被寓意象征羌族文化的符號,其過程是自覺性的。大多數民族文化,尤其以宗教信仰儀式與音樂活動結合的現象最為突出,缺失了音樂的參加,其文化象征就失去了價值,音樂是體現人們精神世界與內心世界的表象,起著很重要的文化象征作用。雖然羌族現在已無文字,但牧歌的演唱依然用羌族語言來演唱,無論是旋法、音調、節奏、演唱方式無不代表著羌族文化特征。
三、結語
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現代科技的迅速發展,羌族傳統式的牧羊生活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其牧歌音樂也逐漸發生了衍變,不斷的被其它音樂文化所替代,牧歌音樂作品的數量不斷縮減,羌族牧歌的前景令人堪憂,如何很好的傳承與發展還需我們投入大量的精力來探究。■
注釋:
① 曲譜引自金藝風,汪代明.中國羌族二聲部民歌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06:99.
[1] 耿少將.羌族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04.
[2] 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四川卷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四川卷[M].北京:中國ISBN中心出版社,1997,12.
[3] 金藝風,汪代明.中國羌族二聲部民歌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0,06.
[4] 金藝風,崔善子.中國羌族民歌旋律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3,08.
[5] 喬建中,韓鍾恩,洛秦.中國傳統音樂[M].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9,03.
[6] 董維松.中國傳統音樂文集·對根的求索[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4,09.
[7] 樹楓.西部民族風情千解[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01.
[8] 金藝風.羌族民歌“勞動歌”的分類研究——以音樂方面為中心[J].武漢:黃鐘(武漢音樂學院學報),2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