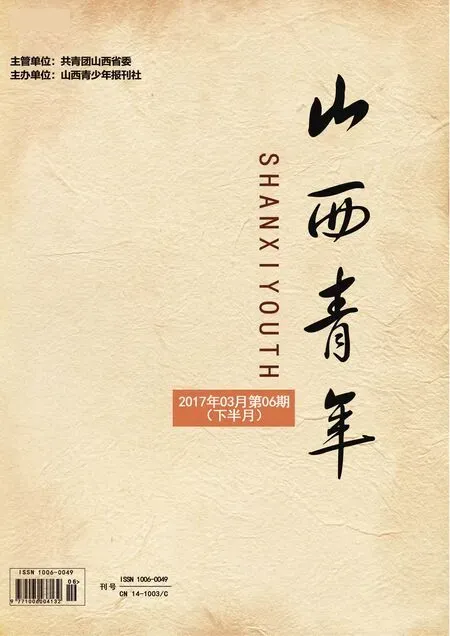淺析民國時期民眾教育館對基層社會的影響
張瑞芳
河北大學歷史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淺析民國時期民眾教育館對基層社會的影響
張瑞芳*
河北大學歷史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民眾教育館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由政府建立并主導的一種社會教育機構,它是中國特有的一種教育制度,同時也是民國時期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同于傳統的學校教育,其主要以提高社會文化水平、改進社會生活為目的,對當時基層政權建設、民眾生活和教育出版業等方面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民國時期;民眾教育館;影響;局限性
民眾教育館是民國時期頗具特色和影響的社會教育機構。它起源于民初的通俗教育館和通俗教育會,產生于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后,是當時政府推行并在城鄉廣泛設立的社會教育“綜合機關”和“中心機關”。它發端于城市,推廣至鄉村;始于江蘇,遍及全國。它主要的職責就是教育民眾,其開展的活動,從識字教育到生計指導再到公民觀念的塑造,涉及當時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匯集了博物館、圖書館和體育場等各種社會教育事業。其主要采用民眾喜聞樂見的施教方式,演講、出版刊物和閱讀是其主要形式。另外其教育的對象與普通的學校也有所不同,除了失學成人之外,還涉及廣大民眾的社會生活,有移風易俗之效。1935年著名的教育家俞慶棠曾說過:“民眾教育館在近年發展之情形,無論在館之數量上,經費上,職員上,其進展之速,均足驚人。在近年中國蓬勃發展的民眾教育運動中,吾人不能不說以民眾教育館(有僅稱教育館,亦有稱農民教育館)的推廣最為有力。”民眾教育館已經成為了開展民眾教育的中心機關。
民國初期,由于軍閥混戰,戰爭不斷,導致民眾教育館的發展缺乏強有力的政府支持和穩定的外部發展環境,處于緩慢發展階段。20世紀二三十年代,民眾教育館處于迅猛發展的時期。經過七八年的發展,已經遍布全國大部分地區,根據民國二十年的數據統計,全國共有公、私立民眾教育館900余所,發展規模不斷壯大。當時大多數人士對民眾教育館報有樂觀的態度,并進一步認為民眾生活可隨之而改變,社會生活亦可隨之而推進,民眾教育館不僅在形式上是各種民教事業的中心,在精神上應使之成為民眾生活的中心,社會文化的中心。
民眾教育館是民國時期推行時間最長的一種官方社會教育機構,它在改良民眾文化、改善民眾生計、塑造公民意識觀念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我們從幾個方面進行分析闡述:
一、民眾教育館與基層政權建設
1928年國民黨政權實施訓政后,在地方建立黨政分治的制衡體制。然而縣黨部在與縣政府的權利博弈較量中,黨權日趨弱化,黨部組織松懈,無力履行相關職責。正是這樣一個大環境,以教化民眾,喚醒民眾為目的民眾教育館應運而生,在基層政權建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民眾教育館主要以“教育”的手段介入到基層政權建設方面,主要表現在協助選舉基層領袖,推動基層權利重組和協調各種社會關系,協助政府重構基層社會秩序等方面。
民眾教育館對選舉之事十分重視,選舉過程也得到了各級政權組織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基層政權的重組。國民政府建立后,面對民初以來社會政局失范的情形,建立中央集權、重構基層統治秩序成為政府的當務之急。在重構基層統治秩序中,政府需要借助民教館這樣的社會教育機構,在行政的監控下,協助選舉“素孚鄉望”、“熱心任事”的基層領袖,推動基層權利的重組”。可見民眾教育館在協助選舉基層領袖,推動基層權利重組方面所起的作用之大。另外民眾教育館在協調各種社會關系方面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指導區務會議及鄉鎮會議、調節民間糾紛等都是其協調社會關系的重要方式。
作為教育機構的民教館,之所以能參與基層政權建設,朱煜在其論文《民眾教育館與基層政權建設—以1928-1937年江蘇省為中心》曾有明確的闡述:“主要是九一八事變后“內憂外患”的危局,激發了民教館知識分子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而國民政府“官辦自治”成效甚微,也欲借助民教館兼具官方和民間色彩的有力條件使之助一臂之力;加之中國社會尊師重道的傳統,故而民教館在協調與基層民眾以及地方政府關系時多能如魚得水。”
二、民眾教育館與私塾改良
民眾教育館主要目的是教化民眾,而私塾又是知識傳播的一種重要的途徑,因此民眾教育館要達到其目的,對私塾進行優化改良就顯得格外重要。
民眾教育館與私塾改良主要以江蘇省為例,以小見大,看待整個民國時期兩者之間的關系。江蘇民眾教育館協助政府改良私塾的活動發端于20世紀30年代初,江蘇省作為率先成立民眾教育館的省份,因此在這方面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在私塾改良方面,江蘇省主要通過建立改良過的私塾研究會、私塾管委會、塾師研究會、私塾改良會、私塾改進會等組織,依靠這些組織,研究私塾改良的方法,以此來推動私塾改良的順利進行。江蘇省改良私塾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主要包括:建立特約改良私塾、進行私塾成績展覽、舉辦塾師訓練班、舉行競賽,展示及集合訓練,參與改良私塾宣傳周等等。
通過以上方式,加上各級政府組織的支持,雖然過程比較曲折,但民眾教育館在改良私塾方面還是取得了一些成績。民眾教育館通過對私塾進行改良,規范了教學秩序、改進了教學方法,豐富了教學內容,一定程度上推進了教育事業的發展。
三、民眾教育館與民眾生活
20世紀初,新式知識分子群體開始將目光轉向下層普通民眾,提倡并從事受眾更為廣泛的社會教育事業。以啟蒙民眾、改造民眾、培養具有愛國心、公共心、獨立性、自治力的一代“新民”。他們在大中城市創辦白話報、閱報社、宣講所、演說會等機構。民眾教育機構為民眾教育館的出現提供了先期條件。再者,當時美國教育學家杜威的“實用主義”、“民本主義”、“生活即教育”“社會改良主義”等思想相繼傳入中國,進而在倡導教育變革的先進知識分子的推動下發展成一種社會教育改革思潮。民國建立之后,這種思潮得以具體的實施,成立了民眾教育機構—民眾教育館。民眾教育館對提高民眾素質,傳播先進文化,推動民眾的現代化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民眾教育館的受眾對象主要是普通居民,其前期的任務是從識字教育再到生計教育,它不同于傳統的學校教育,主要以提高社會文化水平、改進社會生活為目的,其最終的目的是塑造現代化意義上的民眾。
不可否認,民眾教育館在知識傳播方面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其開辦數量的持續增加也能說明這一點。經過民國幾十年的發展,民眾教育館到1936年時達到頂峰,館數由1929年的386所增至1612所,工作人員也由1929年1857人增至7054人。
但是民國政府的大力支持,沒有使民眾教育館達到理想的效果,倡導教育變革的美好愿望也并沒有真正的實現。另外,民眾教育館受眾范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其大多數受教育者都不是普通民眾,“而是來自本來就有意讓子女受教育的人家,目不識丁的壯漢,通常對‘學習做合格公民’不敢興趣,以干活忙和年齡大為借口。”可見其推行的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基層民眾接受任何一個新式教育模式都需要長時期的接受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民眾教育館的普及過程也是如此。
四、民眾教育館與出版業
民眾教育館的主要任務是宣傳和教育民眾,其主要的宣傳媒介即是報刊出版。1932年2月公布的《教育部公布民眾教育館暫行規程》中明文規定各省市及縣市立民眾教育館均得設立出版部,以展開日刊、周刊、畫報、小冊及其他關于社會教育刊物的編輯出版工作。
民眾教育館的出版事業也應運而生。
民眾教育館出版事業分為定期出版的民眾教育刊物和不定期出版物兩種基本的形式。首先介紹定期出版的民眾教育刊物,縣市以上的各級民眾教育館幾乎都有自己獨立發行的民眾教育刊物,通常是月刊,條件好的省立大館會發行周刊或是同時出版多種刊物,人手不夠的縣市立小館則大多發行雙月刊或者季刊。其次是不定期出版物,民眾教育館的各項活動都要圍繞民眾教育展開,其下屬的編輯出版事業也不例外。除了印刷活動所需的各種標語傳單外,主要工作便是編輯出版各種與民眾教育有關的叢書,對于這類書籍,一般都采取不定期發行的形式。
除了上述兩種主要的出版形式之外,民眾教育館還會發行出版一些紀念性的刊物,如江蘇省立徐州民眾教育館于1933年出版的《江蘇省立徐州民眾教育館周年紀念特刊》、浙江省立杭州民眾教育館出版的《浙江省立杭州民眾教育館概況》以及萬縣民眾教育館出版的《萬縣縣立民眾教育總館第一周年紀念特刊》等等。這些刊物基本內容都是圍繞當地教育館發展狀況,為以后民眾教育館事業的開展也起到了很好的借鑒作用。
民眾教育館的出版事業具有顯著的特點,首先它是民眾教育館下設的專門機構,是專門為民眾教育館服務的,其出版的刊物也主要是圍繞著民眾教育館開展工作。其次民眾教育館所辦的出版事業是屬于非營利性質的,它與傳統出版業以盈利性為目的不同,其主要是為民眾教育館服務,其經費大部分來自于政府撥款。另外,其出版的刊物大部分屬于非賣品,這是與其他出版業的最大不同之處。
民眾教育館下設出版事業最直接的影響是推動了民眾教育事業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民眾教育館的影響,提高了民眾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質。另外其在抗日救國方面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九一八事變以后,各地民眾教育館都展開各種抗日宣傳活動,民眾教育館的出版內容里也相應增加了宣傳抗日救國的內容,如江蘇省立南京民眾教育館在1931年的出版物中就有《抗日救國小叢書》一書。
民眾教育館的出版事業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其出版刊物發行的范圍是十分有限的,僅以《民眾教育周報》1932年第1期所載之江蘇省立南京民眾教育館的圖書閱眾成分統計為例,其閱眾學界占50%,商界占18%,軍界占12%,政界占10%,婦女占7%,工人只占3%,農民則沒有。可見廣大勞動人民是很少有機會接觸這些讀物,其受眾范圍是十分有限,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傳播的速度與范圍。
五、結語
作為民國時期社會教育中心機構的民眾教育館,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民眾教育時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推動了社會基礎教育事業的發展,提高了民眾素質,改善了教育環境,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政府與基層民眾的矛盾。民眾教育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民國時期政府管理基層民眾的一種教育手段。
對民國時期民眾教育館整個發展過程及其影響的闡釋,我們不難發現,政府的參與與指導、知識分子的推動、時事的變遷都影響著民眾教育館的運行。當然其本身也存在很多的問題,比如地域分布不均、資源分布不平衡、政府的過度參與(使其缺乏主觀能動性)等等問題,都限制著民眾教育館的長期發展,其與民國政府教化民眾的初衷也出現背離。民國時期廣泛設置的民眾教育館,雖有其歷史局限性,但其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對當今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與改革也有很大的借鑒意義。在簡單梳理民眾教育館影響的同時,我們也要思考以下幾個問題:民眾教育館對當今教育的借鑒意義?其在當時沒有徹底推行的深層次原因?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探究的。
[1]林宗禮.民眾教育實施法.商務印書館,1936.
[2]顧良杰.民教專家會議之經過及其結果.教育與民眾,4(6).
[3]俞慶棠.民眾教育.正中書局,1935.
[4]李蒸.民眾教育館概論.教育與民眾,2(8).
[5]朱煜.民眾教育館與基層政權建設—以1928-1937年江蘇省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4(3).
[6]毛文君.民國時期民眾教育館的發展及活動述論.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4).
[7]教育部社會教育司.民眾教育館.正中書局,1941.
[8][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的現代化.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9]《教育部公布民眾教育館暫行規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10]伍卓瓊.淺論民國時期民眾教育館的出版事業.黑龍江史志,2009(23).
[11]江蘇省立南京民眾教育館發行.民眾教育周報,1932(1).
張瑞芳(1991-),女,漢族,河南周口人,河北大學歷史學院,中國史專業碩士研究生在讀。
G
A
1006-0049-(2017)06-01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