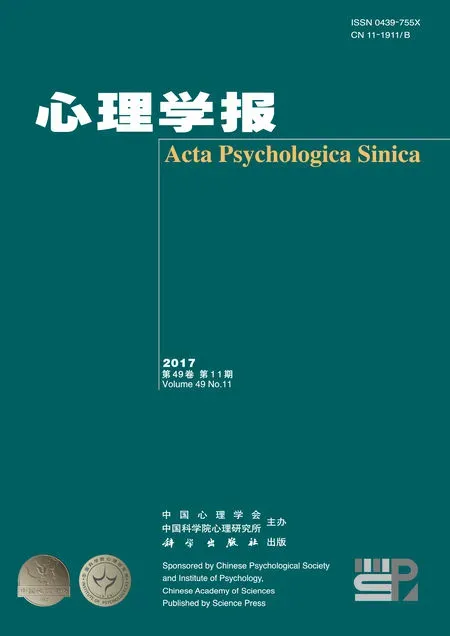聾生“是……的”句的句法意識*
張 帆 李德高
(1浙江特殊教育職業學院, 杭州 310023) (2曲阜師范大學翻譯學院, 山東 日照 276826)
1 引言
聾人在認知上比較多地依賴視覺, 因此發展了手語。若有足夠的語言輸入和實踐, 則其手語表達能力會不亞于健聽人的口語表達能力(Lederberg,Schick, & Spencer, 2013)。然而, 95%的聾兒生長在健聽人家庭, 在手語言語輸入和輸出上, 他們都存在嚴重不足。事實上, 在與健聽人有限的言語交流和與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觸中, 他們只能發展自然手語, 一種基于物象和動作模仿的、表達力有限的語言(Zaidman-Zait & Dromi, 2007)。當然, 聾童一旦入學并融入與其他聾生的日常生活, 那么, 其手語能力就會迅速提高。而且, 他們還會掌握學校所在地的地方手語——社會聾人基于自然手語發展起來的手語方言。
聾生須學習書面語, 并以書面語為媒介來學習文化知識, 但是, 其書面語實踐似乎局限于課程學習。在其他活動中, 他們主要使用手語。手語是他們最自然的語言。因此在教學中, 為幫助聾生理解課堂上將要講解的科學概念, 需引導他們首先用手語就相關話題進行討論(Roald, 2002); 對聾人手語無法表達的數學概念, 老師也往往因為難度太大而放棄講解(Pagliaro & Kritzer, 2005)。對大部分聾生來說, 手語是第一語言, 書面語是第二語言(Mayer,2009)。
聾生往往是入學之后才開始學習使用書面語的, 所以他們與健聽人晚期雙語者情況有些相似。所謂晚期雙語者是指熟練掌握第一語言之后才開始學習使用第二語言的雙語者, 他們學習第二語言時會受到其第一語言經驗的幫助, 也會受到其第一語言經驗的制約(Saito, 2015)。然而, 因為模式上差異(Goldin-Meadow & Mylander, 1998), 聾生學習書面語所遇到的困難可能遠大于健聽生學習第二語言所遇到的困難。而且, 由于以下兩方面原因, 聾生在書面語語法學習中的困難尤其難以克服。
第一, 在其第二語言技能發展早期, 晚期雙語者往往要依賴第一語言語法規則來學習第二語言(Schwartz & Sprouse, 1996)。但因為模式不同, 聾生的手語語言技能難以遷移到其書面語實踐(Goldin-Meadow & Mylander, 1998)。第二, 人在語言活動中會自發地啟用語法技能(Ardila, 2011), 然而, 因為其第二語言技能比較弱, 所以晚期雙語者在第二語言閱讀活動中往往會回避語法信息而更多地倚重語義信息等(Clahsen & Felser, 2006)。同樣, 聾生在書面語活動中也可能會策略性地回避語法信息加工。
因此, 語法技能較低是聾生書面語活動中尤為突出的現象(Lederberg et al., 2013; Wolbers, Dostal,& Bowers, 2012)。例如, 對被動句和帶有定語從句、不定式或動名詞結構的句子等, 聾生理解起來特別困難(Friedmann & Szterman, 2006)。聾生寫出的句子不僅短而且在語法上往往是支離破碎的(Wolbers et al., 2012)。
其實, 自上世紀70年代起, 人們便開始關注聾生的書面語語法問題(Arfé & Boscolo, 2006;Lederberg et al., 2013; van Beijsterveldt & van Hel,2009; Wolbers et al., 2012), 但是, 關于聾生書面語語法意識的研究還有待深入開展(Traxler, Corina,Morford, Hafer, & Hoversten, 2014)。比如說在中國,雖然有學者就聾生書面語語法困難現象進行了一些思考分析(許保生, 傅敏, 2015), 但是, 通過心理學實驗來回答下列問題的研究尚且比較缺乏:聾生在書面語中對哪些句式遇到較大的學習困難?其學習困難在認知上又有怎樣的表現?對這樣的問題做出回答, 不僅會為聾人語文教學提供借鑒, 而且, 對揭示聾生書面語語法技能發展困難的認知本質, 對推動語言認知普遍理論發展都有重要意義。
現代漢語中, “是……的”句是一種常見句式,也是句法最為復雜的句式之一(熊仲儒, 2007)。在“是……的”句中, 處于句尾的助詞“的”與前面的助詞“是”構成語法框架, 使框架內的信息內容得到強調。例如, “她是愛護書籍的”這句話除了表達“她愛護書籍”的意思之外, 還強調, “愛護書籍”是“她”的一種習慣, 或者, 是“她”的一種品質。
然而, 該句式不僅外國留學生學習起來特別困難(謝福, 2010), 而且聾生學習起來也困難。比如說,聾生作文中經常出現把“她是愛護書籍的”寫成“她是愛護書籍”或“她愛護書籍的”的現象。聾生所犯這樣的錯誤說明, 一方面他們對“是……的”句可能發展了一定的語法意識, 另一方面他們關于助詞“是”和“的”的語法框架意識還有所欠缺。聾生的讀寫技能是并行發展的(Albertini, Marschark, &Kincheloe, 2016), 他們在“是……的”句閱讀過程中也應該會有異常表現。本文擬對聾人大學生“是……的”句的句法意識進行實驗研究。
句子閱讀包括語義信息和句法信息兩個并行的信息加工過程(Hofmeister, 2011)。每個詞的信息加工也可分解為詞信息的提取、與之前詞信息的整合和對之后詞信息的預期(Luka & van Petten,2014)。若當前詞是句尾詞, 則讀者往往還要耗費額外的認知資源, 出現所謂的“收尾效應” (wrap-up effect; Hirotani, Frazier, & Rayner 2006)。即, 處于對之前詞進行信息整合的需要, 讀者對(主句和從句)句尾詞的閱讀速度慢于他們對之前詞的閱讀速度(Kennison, Sieck, & Briesch, 2003)。因此和句法技能較強的讀者相比, 就“是……的”句而言, 句法技能較弱的讀者在句尾助詞“的”上的“收尾效應”會比較大。
若兩類讀者A和B在語義知識方面沒有顯著性差異, 但在“是……的”句閱讀中表現出不同大小的“收尾效應”, 則可推斷, A和B對“是……的”句可能發展了不同強度的句法意識。我們將使用移動窗口式自步速逐詞句子閱讀任務來驗證這一研究假設。
聾人學校中, 一個班里的學生大致可分為(聽力損失高于70 dB的)重度聾生和(聽力損失不高于70 dB的)中輕度聾生。和重度聾生不同, 中輕度聾生不但熟練使用手語, 而且, 因經常佩戴助聽器,能夠與健聽人進行口語交流。第二語言實踐有助于雙語者發展目標語語法技能(De Carli et al., 2015)。中輕度聾生因為有口語實踐經歷的緣故, 所以比重度聾生有更為豐富的漢語語言實踐經驗, 因此, 他們可能發展了更強的書面語語法意識。
葉盼云和吳中偉(2008)把外國留學生容易發生錯誤的“是……的”句歸納為3種類型:助詞“是”和“的”之間是形容詞(如“平坦”)、動賓結構(如“愛護書籍”)和帶時間狀語或地點狀語的動詞結構(如“在船上工作”)。對應這 3種“是……的”句, 聾生在作文中均有缺少助詞“是”的錯誤現象(見表 1)。本研究擬針對這3種類型的“是……的”句進行3項實驗研究, 來驗證上述假設。如果3個實驗取得一致結果,那么上述研究假設將會得到強有力的支持。

表1 材料舉例
每個實驗中, 被試需閱讀完整的“是……的”句(簡稱完整句)和助詞“是”省略的“是……的”句(簡稱省略句)。在逐詞句子閱讀任務中, 讀者對每個詞可能都會進行語法和語義上的信息提取、整合和預期(Luka & van Petten, 2014)。當讀到句尾助詞“的”的時候, 他們在省略句中遇到句法信息整合上的困難會大于他們在完整句中遇到的困難。
2 方法
移動窗口式自步速逐詞句子閱讀任務適合考察聾人句子閱讀的認知過程(Traxler et al., 2014)。在這樣的任務中, 讀者若對某詞的信息加工發生困難, 則他/她對該詞的閱讀時間會比較長。和完整句相比, 被試對省略句句尾助詞“的”會出現更大的“收尾效應”。若重度聾生(實驗組)對“是……的”句的語法意識較中輕度聾生(控制組)弱, 則和控制組相比, 實驗組對句尾助詞“的”的加工會出現更大的“收尾效應”。因此, 每個實驗中采用2(被試:實驗組或控制組)×2(句型:完整句或省略句)兩因素混合測量設計。被試是被試間變量, 句型是被試內變量。因變量是被試對句尾助詞“的”的閱讀時間, 即, 反應時。
2.1 被試
來自浙江特殊教育職業學院的實驗組和控制組被試參加了《瑞文標準推理測量》、閱讀能力測驗和背景信息問卷調查。耳聾會影響聾童的語言發展, 并進而影響其智力發展(Shojaei, Jafari, &Gholami, 2016), 因此, 以聾人為對象的研究往往需要平衡其智力水平。關于閱讀能力測量, 我們借用了《聾人大學生漢語課程的開發》(張會文, 呂會華, 吳鈴, 2009)附錄中語文能力測試題的閱讀理解部分, 并假設在其他方面沒有差異的條件下, 若重度聾生的測試分數和中輕度聾生的測量分數沒有顯著性差異, 則兩類被試具備相同的詞匯語義知識。
研究表明, 聾童耳聾發生年齡越早, 其口語能力發展受到制約的程度就越高; 他們接受學前語言訓練效果越好, 入學后其書面語學習效率就可能越高(Shojaei et al., 2016)。如果聾童的父母親懂手語,那么, 他們的手語能力就可能會得到較好發展, 而聾童的手語水平又會影響其書面語學習(鄭璇,2004)。因此, 背景信息問卷調查不僅包括性別還包括耳聾發生年齡、語訓效果和父母親是否使用手語等內容。
如表 2所示, 每個實驗中, 兩種被試在聽力損失方面有顯著性差異, 但在年齡、閱讀測量分數和智力測量分數等方面, 他們之間沒有顯著性差異。
2.2 材料
實驗1、2和3的關鍵材料分別是18、17和18句完整句和相應省略句。參照 Li, Zhang和 Zeng(2016)的做法, 我們請20位不參加實驗的聾生對句子中的詞進行熟悉性評定(1 = 認識; 0 = 不認識),評定分數為0.99 ± 0.06 (M
±SD
)。請20位健聽大學生用 7點量表評定句子的可讀性(7 = 非常容易理解, 1 = 非常難以理解)。在實驗1 [t
(17)= 10.567,p
< 0.001, Cohen'sd
= 5.13]、實驗2 [t
(16)= 7.428,p
< 0.001, Cohen'sd
= 3.71]和實驗3 [t
(17)= 11.457,p
< 0.001, Cohen'sd
= 5.56]中, 完整句的可讀性分數(6.52 ± 0.27; 6.41 ± 0.64; 6.48 ± 0.56)均顯著高于省略句的可讀性分數(4.23 ± 0.36; 5.13 ± 0.53; 5.02 ±0.58)。每個實驗中, 完整句隨機分為兩組, 省略句也相應分成兩組。然后, 這4組材料交叉組合形成兩個關鍵材料組。實驗1和實驗3中, 各組關鍵材料均由半數完整句和半數省略句組成; 實驗 2中, 一組關鍵材料由9個完整句和8個省略句組成, 另一組關鍵材料由8個完整句和9個省略句組成。每個句子被試只閱讀一次:或者其完整句形式, 或者其省略句形式。為避免被試對句型結構特點有所意識或啟用閱讀策略等(Rüschemeyer, Zysset, & Friederici,2006), 實驗中的填充句數量是相應關鍵句的3倍。填充句均為”是……的”句以外的句式, 并在句長和詞匯難度等方面和關鍵句相似。對每個被試, 關鍵材料和填充材料均進行隨機混合。

表2 被試信息
2.3 過程
使用 E-prime 2.0呈現刺激和記錄被試的按鍵反應。每個句子開始時, 在顯示器中央呈現一個矩形框, 框邊的顏色為黑色, 線寬為 0.25磅, 矩形框在長度和寬度上和相應句子所占空間相同。文字在白色背景下以 28號(黑色)宋體呈現。被試按“F”或“J”鍵時, 在左端出現第一個詞(包括助詞“是”和“的”, 實驗 1、2和 3中完整句的句長分別是 4、5和 5個詞), 同時, 矩形框消失; 之后, 被試每按一次“F”或“J”鍵, 下一個詞出現, 之前的詞消失; 最后一次按鍵出現的是句號。每個詞從出現到消失之間的時間間隔記錄為它的反應時。所有句子閱讀之后都有一個閱讀理解題, 被試需根據對相應句子的閱讀理解做出肯定或否定應答。
在被試所在學校的電腦教室內, 對被試分小組進行集體測量, 每個小組最多由5人組成。教室內光線明亮, 被試端坐電腦前, 眼睛與顯示器(型號:LXB-L17C; 分辨率:1280 × 1024 像素; 刷新頻率:75 Hz)中央的水平距離約為60 cm。兩個人之間左右間隔兩個座位, 前后間隔一排座位。實驗開始之前, 由來自該校的(其本人也是聾人的)老師用手語向被試講解操作要求。被試需又快又準確地讀懂每個句子, 并且, 對句子之后出現的閱讀理解題, 按“D”或“K”鍵做出應答。實驗開始時有12個練習句子, 之后是正式實驗句。實驗持續25 min。實驗結束時, 被試每人領取一份價值 10元左右的小禮物,離開教室。
3 結果
實驗組(83.8% ± 5.7%)和控制組(84.3% ± 5.2%)對句子理解題目應答的準確率無顯著性差異,t
(115)= 0.806,p
> 0.10。參照以往研究(Hopp, 2015;Nakamura & Arai, 2012), 關鍵句中詞的反應時如果短于80 ms或長于1200 ms, 數據被刪除。實驗1、2和3中數據刪除比例分別是1.9%、2.5%和2.2%。對被試在句尾助詞“的”的反應時數據進行 2(被試)× 2(句型)兩因素混合測量方差分析(包括被試分析和項目分析)。出于篇幅考慮, 我們主要報告顯著性效應結果。3.1 實驗1


圖1 實驗1結果
3.2 實驗2

圖2 實驗2結果
實驗結果如圖2所示, 在句尾助詞“的”的反應時上, 被試主效應顯著[F
(1, 16)= 8.22,p
< 0.005,η= 0.339], 被試和句型兩因素交互作用顯著[F
(1, 35)= 11.09,p
< 0.005, η= 0.241]。簡單效應分析表明, 實驗組在完整句中對“的”的反應時顯著長于他們在省略句中對“的”的反應時[t
(15) = 5.17,p
<0.001, Cohen'sd
= 2.67], 然而, 控制組對“的”反應時在完整句和省略句之間沒有顯著性差異[t
(20)= 1.47,p
> 0.10]。3.3 實驗3
實驗結果如圖 3所示, 在句尾助詞“的”的反應時上, 被試主效應顯著[F
(1, 17) = 11.93,p
< 0.01,η= 0.412], 被試和句型兩因素交互作用顯著[F
(1, 41) = 6.41,p
< 0.05, η= 0.135;F
(1, 17) =4.82,p
< 0.05, η= 0.198]。簡單效應分析表明, 實驗組在完整句和省略句中對“的”的反應時沒有顯著性差異[t
(19) = 2.06,p
> 0.05;t
(17) = 1.33,p
> 0.10], 然而, 控制組在完整句中對“的”的反應時顯著短于他們在省略句中對“的”的反應時[t
(22) = 2.91,p
< 0.05, Cohen'sd
= 1.24]; 實驗組對完整句中“的”的反應時顯著長于控制組對完整句中“的”的反應時[t
(17) = 3.05,p
< 0.01, Cohen'sd
=1.48], 然而對省略句中“的”的反應時, 實驗組和控制組之間沒有顯著性差異[t
(41) = 0.83,p
> 0.10;t
(17) = 0.800,p
> 0.10]。
圖3 實驗3結果
4 討論
本文以完整的(完整句)和省略助詞“是”的(省略句)“是……的”句為材料, 以主要使用手語的重度聾生(實驗組)和既懂手語又懂口語的中輕度聾生(控制組)為對象, 進行了 3項移動窗口式自步速逐詞句子閱讀實驗測量。實驗1、2和3的完整句中兩個助詞“是”和“的”之間分別是形容詞(如“平坦”)、動賓結構(如“愛護書籍”)和帶時間狀語或地點狀語的動詞結構(如“在船上工作”)。每句讀完之后, 被試需回答一個閱讀理解題目。
結果發現, 實驗組與控制組對句子理解題目應答的準確率均高于80%, 說明他們認真參與實驗并且讀懂了句子。對被試在句尾助詞“的”的反應時分數進行方差分析表明:(1)實驗1和實驗3的結果相似:實驗組對句尾助詞“的”的反應時在完整句和省略句之間沒有顯著性差異, 然而, 控制組在完整句中對句尾助詞“的”的反應時顯著短于他們在省略句中對句尾助詞“的”的反應時; 在完整句中, 實驗組對句尾助詞“的”的反應時顯著長于控制組對句尾助詞“的”的反應時, 然而, 在省略句句尾助詞“的”的反應時上, 實驗組和控制組之間沒有顯著性差異。(2)實驗2中, 控制組對句尾助詞“的”的反應時在完整句和省略句之間沒有顯著性差異, 然而,實驗組在完整句中對句尾助詞“的”的反應時顯著長于他們在省略句中對句尾助詞“的”的反應時。
句子閱讀包括語義信息和句法信息兩個并行的信息加工過程(Hofmeister, 2011)。對每個詞的信息加工可分解為信息提取、整合和預期(Luka & van Petten, 2014), 然而對句尾詞的信息加工往往會出現“收尾效應” (Hirotani et al., 2006)。本研究中3個實驗的結果一致表明, 實驗組似乎和控制組一樣,能夠迅速提取句首詞的語義信息。這與表2所示其閱讀能力測試分數沒有顯著性差異的結果一致。兩類被試畢竟來自同樣的班級, 有相似的受教育經歷,因而也可能發展相似的語義知識網絡。
和語法技能相比, 聾生在語義知識發展方面的困難要小的多(Lederberg et al., 2013)。然而, 僅靠語義信息加工是難以確保流暢性閱讀的(Cain, Oakhill,& Lemmon, 2004)。也許因為實驗組相應心理表征欠缺的緣故, 他們在句法信息加工方面效率較低,所以在閱讀中出現比控制組更大的“收尾效應”。
4.1 重度聾生“是……的”句句法意識薄弱
在實驗1和實驗3中, 控制組對省略句所表現出的“收尾效應”顯著大于他們對完整句所表現出的“收尾效應”。這符合實驗預期, 說明他們在省略句句尾助詞“的”的語法信息加工上遇到更大困難。重要的是, 和控制組相比, 實驗組在完整句和省略句中均有比較長的反應時, 這一結果值得深入討論。
完整句中, 實驗組讀到助詞“是”時能夠提取其表示肯定性判斷含義的心理表征。但可能缺乏該詞在“是……的”句中作為助詞的語法信息表征, 對“是……的”結構框架缺乏足夠的句法意識, 因此讀到句尾助詞“的”時不能在句法上與前面的助詞“是”形成句法結構框架。對“是……的”句句尾助詞“的”的理解難以與之前詞進行信息整合, 從而出現較大的“收尾效應”。
漢語中, 句法主要不是通過形態變化來體現的,而是通過詞的多義性來體現的。這一點似乎與聾生的語言認知特點相左。比如說, 可能與聾生難以對同一事物做出多項選擇判斷現象(Marschark, Lang,& Albertini, 2002)相關, 聾生難以掌握書面語詞的第二個含義(Paul, 1987)。對重度聾生來說, “的”字不論出現在句中還是出現在句尾, 它可能只有一個意思, 那就是它的第一個和使用頻率最高的那個意思, 即, 表示所屬關系的語義(如, “父親的背影”中的“的”)。這恐怕是實驗組對“是……的”語法意識較控制組薄弱的主要原因之一。
實驗組對省略句句尾助詞“的”反應時較長的結果可做同樣解釋。嚴格意義上講, 因為“是”的省略, 省略句在句法上是不完整的, 句尾助詞“的”的出現在句法上是有些突兀的, 因此其可讀性較完整句低。而且控制組對省略句句尾助詞“的”的反應時顯著長于他們對完整句尾助詞“的”的反應時。
關于重度聾生在“是……的”句閱讀中的這些證據, 直接支持了人們在觀察研究中關于聾生書面語句法意識發展有所異常的推斷(Arfé & Boscolo,2006; Friedmann & Szterman, 2006; Lederberg et al.,2013; van Beijsterveldt & van Hel, 2009; Wolbers et al., 2012)。我們相信, 如果采用同樣的設計進行ERP實驗, 那么, 對實驗組在完整句和省略句句尾助詞“的”的信息加工會主要測量到 N400, 對控制組在省略句句尾助詞“的”的信息加工會主要測量到P600。
實驗2中, 雖然控制組對省略句和完整句句尾助詞“的”的反應時差異沒有達到顯著性水平, 但如圖2所示, 他們對省略句的“收尾效應”似乎也有大于他們對完整句“收尾效應”的趨勢。與此相反, 不同于其他兩個實驗的是, 實驗組在完整句中表現出的“收尾效應”反而大于他們在省略句中表現出的“收尾效應”。
重度聾生對省略句中句尾助詞“的”的信息加工和他們在其他兩個實驗中的情況相似, 主要因為語義信息整合困難而出現“收尾效應”; 但是, 在完整句中, 他們所以表現出更大的“收尾效應”一方面因為他們在語義信息整合上遇到困難, 另一方面還因為他們可能已經發展了某種程度上的句法意識:對這種結構有進行語法信息加工的趨勢, 但是, 其加工效率還比較低。
4.2 啟示
本研究中兩種被試之間的主要不同是, 中輕度聾生因為懂口語可能發展了較強的書面語句法意識; 相反, 重度聾生因為主要使用手語, 不大可能普遍發展口語能力(梅芙生, 1999), 因此難以像中輕度聾生那樣發展明確的書面語語法意識。實驗1和實驗3似乎很好地證實了這一推斷, 但是, 實驗2的結果表明, 重度聾生對“是……的”句式在某種程度上也發展有一定的句法意識。這些發現給我們帶來一些重要啟示。
一方面, 雙語者在第一二語言語法方面的差異大小決定其第二語言學習難度(Foucart & Frenck-Mestre, 2011)。手語是視覺語言, 在模式上和口語有差異。在書面語活動中, 不論是自覺不自覺地依賴其第一語言語法技能—手語語法技能(Schwartz& Sprouse, 1996), 還是有意識地回避書面語語法信息(Clahsen & Felser, 2006), 這都不利于聾生發展書面語語法意識。因此, 聾生必須在書面語語法學習實踐中摸索語法規律和發展語法意識。確實,在多年語文學習過程中, 他們也許對某些結構發展了某種程度的語法意識。
如圖1、2和3所示, 控制組對省略句句尾助詞的反應時分別比他們對完整句句尾助詞的反應時長47 ms、7 ms和30 ms。即, 和其他兩種類型的“是……的”句相比, 實驗 2完整句(如“他是愛護書籍的”)中的“是……的”語法框架在心理表征上可能是最為松散的, 畢竟在口語中“他愛護書籍的”這樣的句子聽起來似乎也不是那么拗口, 而且和其他兩個實驗相比, 實驗2中完整句和省略句的可讀性分數之差是最小的, 只有 1.28。因此, 至少在移動窗口式自步速逐詞句子閱讀任務中, 實驗2省略句中的句法錯誤似乎不容易在中輕度聾生身上測量出來。相反, 閱讀這種所謂“心理語法結構最為松散”的“是……的”句時, 重度聾生已經發展起來的某種“是……的”句句法意識反而能夠得以體現。因此,進行句式強化訓練將有助于促進聾生的句法意識發展。
另一方面, 自然手語也是一種語言, 有其獨特的語法系統(Goldin-Meadow & Mylander, 1998)。自上世紀 70年代起, 發達國家聾人似乎主要使用規約手語—主要基于口語創造的官方手語。然而, 由于種種原因, 我國聾人傾向于主要使用自然手語或手語方言, 但迄今為止, 人們對自然手語語法規律知之甚少。不過, 關于重度聾生對“是……的”句似乎發展有一定語法意識的現象, 作者做以下推論。
手語語法和漢語語法之間在某些方面可能有所相似。例如, 有學者認為, 有些自然手語語句中手勢詞之間的先后順序與甲骨文字中成分的位置順序有相似性(游順釗, 1991), 與古漢字中成分的位置順序有相似性(高宇翔, 2017)。因此, 重度聾生所以在書面語活動表現出的某種程度上的語法意識可能是其手語語法技能的正遷移所致。而且, 漢語書面語是視覺信息極其豐富的語言形式, 這種豐富性似乎符合聾人基于視覺的認知習慣。例如, 和美國聾人記憶英文數字情況相比, 日本聾人對漢字數字的記憶成績更高(Flaherty & Moran, 2007); 在青少年聾生具體事物間分類學聯系和主題關聯聯系相對強度意識比較研究中, 韓國青少年聾生對圖片和文字兩種形式的刺激有不同的反應模式, 而中國青少年聾生對圖片和文字兩種形式的刺激卻有相同的反應模式(Yi et al., 2011)。因此, 對漢語中有些書面語形式所蘊涵的語法規律, 聾生也許能夠自然而然地在某種程度上有所駕馭。不過, 對這其中的奧妙尚且需要深入探究。
總之, 重度聾生因為主要是用手語, 所以和中輕度聾生相比, 他們在書面語語法意識發展上處于劣勢, 但是, 他們不是沒有發展書面語語法意識的可能。未來研究需要對聾人手語和聾生的書面語活動進行觀察研究, 并結合心理學實驗, 以各種句式為研究內容, 對聽力損失程度不同聾生的書面語語法認知活動進行考察, 對重度聾生在哪些句式上難以發展明確的語法意識, 在哪些句式上能夠發展一定程度語法意識形成系統認識。相關研究發現不僅為有的放矢地指導聾生進行書面語語法技能訓練提供理論幫助, 而且還會在句式上反襯手語和書面語之間的差異和相似之處, 為指導聾人手語研究和推動聾人語言認知研究發展做出貢獻, 為書面語認知研究本身提供理論指導, 為推動語言認知普遍理論發展做出貢獻。
5 結論
聾生在書面語語法意識發展上有顯著性個體差異:和中輕度聾生相比, 重度聾生對“是……的”句的語法意識比較弱。本研究帶來的啟示是, 需要進行大量這樣的實驗研究, 確定他們在這些句式上的認知特點, 為對聾生進行有的放矢的教學訓練提供借鑒。
Albertini, J. A., Marschark, M., & Kincheloe, P. J. (2016).Deaf students’ reading and writing in college: Fluency,coherence, and comprehension.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21
, 303–309.Ardila, A. (2011).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language systems in the brain.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 1
,23–36.Arfé, B., & Boscolo, P. (2006). Causal coherence in deaf and hearing students’ written narratives.Discourse Processes,42
, 271–300.Cain, K., Oakhill, J., & Lemmon, K. (2004).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inference of word meanings from context:The influence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knowledge, and memory capacity.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6
, 671–681.Clahsen, H., & Felser, C. (2006). Grammatical processing in language learner.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27
, 3–42.De Carli, F., Dessi, B., Mariani, M., Girtler, N., Greco, A.,Rodriguez, G., ... Morelli, M. (2015). Language use affects proficiency in Italian-Spanish bilinguals irrespective of age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8
, 324–339.Flaherty, M. & Moran, A. P. (2007).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troop effect among deaf signers in English and Japanese:Automatic Processing or memory retrieval?American Annals of the Deaf,
152, 283–290.Foucart, A., & Frenck-Mestre, C. (2011). Grammatical gender processing in L2: Electrophysiological evidence of the effect of L1-L2 syntactic similarity.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4
, 379–399.Friedmann, N., & Szterman, R. (2006). Syntactic movement in orally trained children with hearing impairment.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11
, 56–75.Gao, Y. X. (2017). Similarities between natural sign language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haracters.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 37
(1), 28–30.[高宇翔. (2017). 試論中國手勢語和古漢字的相似性.綏化學院學報, 37
(1), 28–30.]Goldin-Meadow, S., & Mylander, C. (1998). Spontaneous sign systems created by deaf children in two cultures.Nature,391
, 279–281.Hirotani, M., Frazier, L., & Rayner, K. (2006). Punctuation and intonation effects on clause and sentence wrap-up:Evidence from eye movements.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54
, 425–443.Hofmeister, P. (2011). Representational complexity and memory retrieval in language comprehension.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26
, 376–405.Hopp, H. (2015).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second language processing of object-subject ambiguities.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36
, 129–173.Kennison, S. M., Sieck, J. P., & Briesch, K. A. (2003).Evidence for a late-occurring effect of phoneme repetition during silent reading.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32
, 297–312.Lederberg, A. R., Schick, B., & Spencer, P. E. (2013).Language and literacy development of deaf and hard-of-hearing children: Successes and challenges.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9
, 15–30.Li, D., Zhang, F., & Zeng, X. H. (2016). Similarities between deaf or hard of hearing and hearing students' awareness of affective words' valence in written language.American Annals of the Deaf, 161
, 303–313.Luka, B. J., & van Petten, C. (2014). Prospective and retrospective semantic processing: Prediction, time, and relationship strength in event-related potentials.Brain and Language, 135
, 115–129.Marschark, M., Lang, H. G., & Albertini, J. A. (2002).Educating deaf students: From research to practice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Mayer, C. (2009). Issues in second language literacy education with learners who are deaf.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12
, 325–334.Mei, F. S. (1999). On methodology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Education Science,
(3), 44–47.[梅芙生. (1999). 對我國聾人語言教學法的沉思.教育科學,
(3), 44–47.]Nakamura, C., & Arai, M. (2012). Preservation of the initial analysis in absence of pragmatic inference with Japanese relative clause sentences. InProceedings of the 34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
(pp.791–796). Hokkaido, Japan.Pagliaro, C. M., & Kritzer, K. L. (2005). Discrete mathematics in deaf education: A survey of teachers' knowledge and uses.American Annals of the Deaf, 150
, 251–259.Paul, P. V. (1987, October). Deaf children’s comprehension of multimeaning words: Research and implic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Indiana Association for Children and Adul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Indianapolis, IN.
Roald, I. (2002). Norwegian deaf teachers’ reflections on their science education: Implications for instruction.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7
, 57–73.Rüschemeyer, S. A., Zysset, S., & Friederici, A. D. (2006).Native and non-native reading of sentences: An fMRI experiment.NeuroImage, 31
, 354–365.Saito, K. (2015). Experience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late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oral proficiency.Language Learning, 65
, 563–595.Schwartz, B. D., & Sprouse, R. A. (1996). L2 cognitive states and the Full Transfer/Full Access model.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12
, 40–72.Shojaei, E., Jafari, Z., & Gholami, M. (2016). Effect of early intervention on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Iranian Journal of Otorhinolaryngology, 28
,13–21.Traxler, M. J., Corina, D. P., Morford, J. P., Hafer, S., &Hoversten, L. J. (2014). Deaf readers’ response to syntactic complexity: Evidence from self-paced reading.Memory &Cognition, 42
, 97–111.van Beijsterveldt, L. M., & van Hel, J. G. (2009). Structural priming of adjective-noun structures in hearing and deaf childre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04
,179–196.Wolbers, K. A., Dostal, H. M., & Bowers, L. M. (2012). “I was born full deaf.” Written language outcomes after 1 year of strategic and interactive writing instruction.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17
, 19–38.Xie, F. (2010). A corpus-based study on the acquisition of"shì……de" (是……的) sentence.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2), 17–24.[謝福. (2010). 基于語料庫的留學生“是……的”句習得研究.語言教學與研究,
(2), 17–24.]Xiong, Z. R. (2007).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hi…de” construction.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4), 321–330.[熊仲儒. (2007). “是……的”的構件分析.中國語文,
(4),321–330.]Xu, B. S., & Fu, M. (2015). Ellipsis of sign language under the deaf culture and its linguistics analysis.Disability Research,15
(1), 31–34.[許保生, 傅敏. (2015). 聾人文化視角下手語的省略現象及其語言學分析.殘疾人研究, 15
(1), 31–34.]Ye, P. Y., & Wu, Z. W. (2008).Explanations of difficult points in Chinese learning as a foreign language
.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葉盼云, 吳中偉. (2008).外國人學漢語難點釋疑
. 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Yi, K., Li, D. G., Park, W. S., Park, K. H., Shim, T. T., Kwern,O., & Kim, J. Y. (2011). Korean deaf adolescents’awareness of thematic and taxonomic relations among ordinary concepts represented by pictures and written words.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16
,375–391.You, X. Z. (1991).Visual linguistics
(Z. M. Xu, Trans.). Taipei:Da’an Press.[游順釗. (1991).視覺語言學
(徐志民譯). 臺北: 大安出版社.]Zaidman-Zait, A., & Dromi, E. (2007). Analogous and distinctive patterns of pre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in toddlers with and without hearing loss.Journal of Speech,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50
, 1166–1180.Zhang, H. W., Lv, H. H., & Wu, L. (2009).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rriculum for deaf college students
. Beijing:Huaxia Press.[張會文, 呂會華, 吳鈴. (2009).聾人大學生漢語課程的開發
. 北京: 華夏出版社.]Zheng, X. (2004). Effect of sign language on deaf children's study of Chinese.Chinese Scientific Journal of Hearing and Speech Rehabilitation,
(1), 51–53.[鄭璇. (2004). 淺論手語對聾兒主流語言學習的影響.中國聽力語言康復科學雜志,
(1), 5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