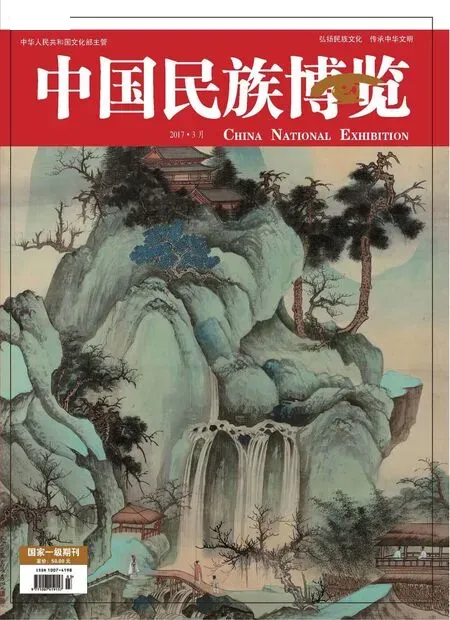用理性還原事實真相
——《十二公民》中的公民意識
褚婉婷
(遼寧師范大學影視藝術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1)
用理性還原事實真相
——《十二公民》中的公民意識
褚婉婷
(遼寧師范大學影視藝術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1)
電影《十二公民》自上映以來深受好評,該影片一舉奪得第9屆羅馬國際電影節(jié)、第18屆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等多項獎項。定名為《十二公民》不僅是為了強調(diào),更有一種諷刺意味摻雜其中。電影通過講述十二個陪審員對案件的不同看法以及探究過程來反映當今社會的真實情況,以及人們對于認識、思考、理解和處理問題的一種真實反映,給觀眾以反思。
電影《十二公民》;理性;事實真相
一、公民意識與社會現(xiàn)實
“公民”一詞是指具有某國國籍,并根據(jù)該國法律規(guī)定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而公民意識是指國家民眾對社會和國家治理的參與意識。電影《十二公民》中的十二個公民,每一個角色都是社會上一類人的綜合體,扮演著不同角色,看待不同事物有著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因此對于電影中案件的分析也說辭不一,最重要的是還摻雜了些許的個人情感因素在其中。其中包含了當?shù)厝藢ν獾厝说钠缫暎恍∩特湆Ω辉kA層的仇視;普通階層的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因遇到不公平待遇而產(chǎn)生消極心態(tài);曾遭受過委屈的經(jīng)歷等。這也使得影片一開始的事件分析根本無法進行,而為什么不同階層的人在一開始對一個有疑點的案件最后竟然有一致的看法,這不禁引發(fā)觀眾的思考。縱觀影片全局不難發(fā)現(xiàn),正是由于八號陪審員對于公民意識的重視與強調(diào),一再堅持自己的看法,理性分析問題,不斷說服其他陪審員,才能夠支撐著故事一步步走向事情的真相。
《十二公民》最大的特點就是緊緊圍繞當今社會發(fā)展環(huán)境,對存在的問題提出質(zhì)疑。電影的主題是圍繞一個“富二代殺死親生父親”的辯題展開,乍一看這個題目指向性極強,大多數(shù)人們都會覺得錯誤應該在富二代身上,人們習慣對這件事情進行價值判斷,而不是真正從事實出發(fā),真正拋開主觀意識去判斷事件的真實性。當今社會,信息爆炸帶來的信息不對稱,帶有攻擊性的言語、網(wǎng)絡標語、輿論導向等,使得人們大都從自身遭遇出發(fā)去判斷事情,忽略了理性地去分析問題,沒有人愿意真正弄清楚事情的真?zhèn)巍T撾娪白畲笠饬x就在于能夠將觀眾對事件的認知從主觀考慮自然轉移到事情本身上,拋棄外界干擾與雜念,通過已有的事實證據(jù)來判斷,而不是以情緒、價值觀、社會信息的導向來判斷。
二、核心人物性格特點分析
電影中的核心人物八號檢察官,他的出現(xiàn)讓案件分析首先出現(xiàn)分歧和矛盾點,讓事件分析不得不重新梳理。開始大家并不知其身份,但他對于公正審判的堅持不僅是他檢察官的身份,還有其自身強烈的公民意識,這也正是其他十一位陪審員以及社會廣大公民所缺少的。在座的十二位公民有權利,但忽略了權利與義務的同在。公民在行使權力的同時更要對自己的言行負責任。或許是因對正義的渴望或對真相的追求,一步步牽動大家從開始的不認真討論得出敷衍的結果,到最后激烈爭執(zhí)從而得出一致的答案。電影中八號的一句“憑什么你的一句話決定這個孩子的生死?”道出了社會對于審判案件態(tài)度上的不認真。小小的討論桌匯聚了十二個不同的公民,代表著十二種對案件不同的態(tài)度,從而映射出整個社會的一種風氣。唯有八號人物的出現(xiàn),真正從理性出發(fā)從真相入手,才一步步征服大家去除偏見,影響社會走向公平正義。這種理性既是司法人員也是社會大眾都非常必要的一種素質(zhì),更是當今社會所欠缺的,現(xiàn)實生活中很少有人能夠為了事不關己的實踐而據(jù)理力爭還原事情真相,還“富二代”和社會一個真相。
相比較于八號的理性存在,性情相反的三號對于強調(diào)自己的權利多一些,其無視對其他人的冒犯。三號和八號間是最大矛盾沖突點,在思想上和言語上形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對角線。三號身上有老北京人與生俱來的優(yōu)越感和交織著妻離子散的沒落感,可恨之處尤顯可憐。他與兒子的矛盾導致的嚴重心理陰影都通過所謂孝道報復性傳遞出來。對于案件分析過多摻雜個人情感,態(tài)度極其不認真,盲目去否認他人觀點。甚至大家都在討論問題時他拿著筆和紙和對面的人玩起了游戲,而在八號搶過紙筆之后卻勃然大怒遷怒于別人,這種行為也在現(xiàn)實中常見,人們常常只顧維護自己的權利與義務而忽略尊重別人,以自我為中心認為錯都在別人而不道歉。這樣的情緒一直發(fā)展到他是最后一個轉變意見的人,思維固化。但他也是最令人為之動容的一個陪審員,在一次次的勸解中他的思維開始發(fā)生轉變,對案件的分析也逐步透徹,大家也能真正理性地分析其難處。無論是對他還是他對案件,理性的對待最終都會走向事情真相。
同樣的十號陪審員,將北京本土人對于“外地人”的歧視,對于“蹲過牢”人的歧視,對于“孩子沒法升學只能做民工”的哭訴等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這些都是只重自身權利而忽略他人存在的表現(xiàn)。認為自己永遠是對的,即便別人反對也要為了面子死撐,面子如同利益一般。正是所謂面子讓整個陪審團從一開始就漫不經(jīng)心,一口咬定富二代有罪,都認為自己判斷得對,從而丑化那些標簽,并沒有真正考慮即使是富二代有罪那也是一條人命,也是有尊嚴的,也應該被尊重。整個陪審團就仿佛代表整個司法程序,對于一個生命的抉擇是生是死,不能夠輕易判斷,必須要有足夠證據(jù)證明有罪或無罪。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抉擇中的一份子,都有義務理性認真地分析得出正確判斷,還原真相,給社會還以公正的審判。正因有了三號八號這樣的對立觀點,才有了大家對充滿道德感事件的審視,二者凝聚了太多人的特征,這一社會特質(zhì)讓這部電影更具本土靈魂,引發(fā)本土觀眾的思考與共鳴。
三、尋找偏見背后的原因與共識
八號在討論中道出“大家只關心結果,并不關心過程”,這也是這個社會所獨有的一種特色,而恰恰本部電影中陪審團的存在就是在強調(diào)這個過程的意義所在。只有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才能對已有證據(jù)和證詞進行質(zhì)疑和透徹剖析,尋找破綻還原事件真相。如今大家看到新聞都會盲目分析判斷,缺乏這樣真正的討論。現(xiàn)實生活中人們往往事不關己,而這部電影卻以小見大,將看似簡單簡陋的事情予以充分的思考和合理分析。八號雖是檢察官,有這樣的公民意識和素養(yǎng),但這個社會有多少這樣的檢察官?細節(jié)之處見真章,觀眾觀影后再次遇到類似事件時或許會有不同見解吧。其實道理大家都懂,但情緒容易埋沒清醒,太多事情掩蓋了理性,竭盡克制也難免盲目做出判斷。人們并非沒有偏見,人都會從自身角度看待某一個事情,只是從一開始就保持理性的人很少。
影片中大家基本都在爭吵中進行案件分析,很少有人平心靜氣地說話,那么為什么大家不能好好說話呢?很多時候人們臉上和藹善良,心里卻早已風起云涌,很多時候不是沒有觀點不了解,只是不想開口,無論對人還是對事都會產(chǎn)生先入為主的執(zhí)念,這也許就是偏見。其實這恰恰是人們心理最真實的想法,這時一旦與人形成相反意見,認真溝通已很難實現(xiàn)。片中人物來自各個階層,有的被長期漠視,有的長期存在偏見思想甚至已融入生活,有的甚至失去了原則底線,形形色色的人已經(jīng)被生活磨礪得不知該如何好好說話了,每次發(fā)言不是對案件的合理分析,反倒變成了自己的訴苦渴望被理解。對于案件本身根深蒂固認為富二代有罪,那么又由誰來還原事情真相呢?電影的可貴之處是在此過程中一點點消除人與人之間的成見,人們習慣認為富二代一定飛揚跋扈,河南人一定做壞事,女孩和大款在一起就是為了錢,北京人一定瞧不起外來人口等。雖然這些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一定是存在的,但這絕不是判斷事件本身的絕對標準。電影告訴我們在這個充滿戾氣的社會中太缺少理解他人的心了,我們又何嘗不是他人口中的“外地人”呢?
四、電影的本土化改編
《十二公民》選擇在單一封閉的場景內(nèi)憑借十二位戲劇演員撐起了一場起伏跌宕的戲。電影的改編“模擬”了一場中國“公民”的法庭論辯。正如其宣傳語 “十二個中國人,十二億聲音”一樣,電影以雄心勃勃的姿態(tài)挑戰(zhàn)了一項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本部電影的標簽“仇富”“富二代”,都是一個個敏感字眼,但卻都是具有本土特色的詞語,與原版“貧民窟二代”等意味相同。對每位陪審員的深入刻畫以及賦予中國特色的社會背景都極具特色。人與人之間總會因各種限制而產(chǎn)生偏見,但沒人愿意承認自己存在偏見,正如片中說著地域歧視卻還想著證明自己公正一樣。而其中涉及“河南人”“你們外地人”如何如何,盡管影片為此起了些許爭執(zhí)最終也于事無補。日常生活中這也許是常態(tài),大家都司空見慣了。顯然大家對這些詞語字眼就是帶著偏見去看的,已經(jīng)融入生活很難改變,因此處理案件上很難將理性擺在首位,對于案件的不統(tǒng)一在所難免。他們只是社會中各階層的普通人,無法改變社會,只有改變對社會的看法。這也給觀眾留下了思考,如果每個人都愿意為之努力,把對他人的偏見轉化為理解,少一些偏見的標簽,也許會帶來不一樣的社會風氣。
五、結束語
十二人的陪審團在一起討論案件好像是一次集體療傷,大家就相同的話題共同展開討論,彼此袒露自己內(nèi)心的想法,同時又直面別人產(chǎn)生的問題,在觀察與被觀察、分析與被分析中,情感體驗和人際關系都在發(fā)生微妙變化,也在一次一次的“有罪”“無罪”中發(fā)生著奇妙的反應。大家慢慢放下了內(nèi)心的自我,去直面問題,理性分析問題。每個人在過程中都找到了自我,將自己的小心思整理好歸位。而陪審員的每一次講述也都將人生百態(tài)冷暖自知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出來,一部電影更好像一段人生。
J60
A
褚婉婷(1993-),女,遼寧遼陽,遼寧師范大學戲劇與影視學專業(yè)研究生,研究方向:戲劇與影視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