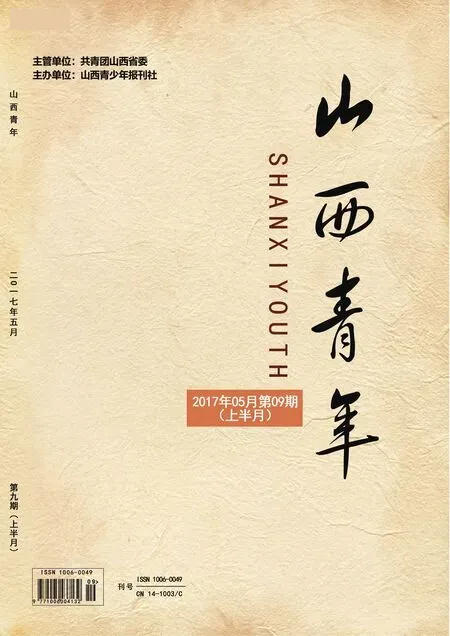迪士尼公主動畫電影中女性形象的演變軌跡*
張海濤 蘇 文
1.西安石油大學人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5;2.西北大學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5
?
迪士尼公主動畫電影中女性形象的演變軌跡*
張海濤1**蘇 文**
1.西安石油大學人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5;2.西北大學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5
迪士尼公主系列動畫中公主形象的演變,隱含著一條女性不斷自我解放的軌跡。這條頗具女性主義色彩的軌跡體現了現代女性的精神生長及其對生存意義、生命價值的探尋與肯定。也從形而上的層面映射出現代社會圍繞在性別上的權力差異。
迪士尼電影;公主動畫;女性主義
迪士尼公主動畫從第一部公主電影《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1937年)的問世到2013年《冰雪奇緣》的熱映,跨越近80年,誕生了12部公主電影。12部影片雖無敘事上的承續,但內隱著一條線索,即:女權主義的發展和女性地位的提升。
一、沉睡中的女性——迪士尼經典公主形象
1937年《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的橫空出世開創了動畫長片的先河。僅在影片首映后的第六天,七個小矮人連同迪士尼先生一起登上了《時代》雜志的封面,當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迪士尼先生獲得了一個特別榮譽獎,除了一個標準尺寸的獎杯,還附贈了七個小獎杯,名利雙收的迪士尼先生就此開始搭建龐大的迪士尼帝國。
然而,白雪公主雖是迪士尼首發公主,但卻是十三位公主中性格特征最不明顯的一位。除了“肌膚如白雪,黑發如檀木,嘴唇如玫瑰”[1]的外貌,再就是靈魂與天性的純潔良善,僅此而已。正如影評家們所言,這部電影塑造白雪公主的童話世界的意義要遠大于塑造白雪公主人物形象的意義。即是說,以白雪公主為核心,通過不同人物對待她的態度,重心在于塑造、七個小矮人、獵人、王子、皇后等童話世界里的諸多人物。
白雪公主在片中沒有表現出任何反抗或獨立精神,在糊里糊涂地吃下皇后準備的毒蘋果后,就只躺在棺木里靜候王子來吻醒。她自始至終都身姿被動。就連她所歌唱的《總有一天我的王子會出現》都充滿著消極等待和盲目樂觀的心態。然而,白雪公主的誕生自有其時代背景。身處美國經濟大蕭條(1937年)余波中的美國人民亟需重拾他們的生活勇氣和信心。白雪公主的童話故事正好迎合了這一心態。
在這一時期的迪士尼公主動畫中,公主形象可以簡單地概括為美麗、單純、善良。她們從小在國王父權光環的保護圈下生活,單純無辜卻總是命途多舛。她們不是在繼母壓迫下卻依舊不失對美好向往的可憐兒,就是心懷美好的愿景和理念來等待著白馬王子的柔弱可人兒,而更為普遍的是被動等待救助或仙人魔法的幫忙的消極樂觀主義者。
二、從沉睡到覺醒——迪士尼公主形象的演變
“20世紀80年代,迪斯尼公司開始改編來自全世界各個地域的原生態故事。”[2]人物內心世界的多樣呈現也成為此際迪士尼卡通的重點著力處。隨著19世紀末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社會女權主義運動的興起和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迪斯尼卡通影片中公主形象的被動性特征逐漸消解,人物開始被賦予較強的女性主義色彩,女性的自主性、獨立性以及勇敢、堅強等品質開始逐漸得以展現,個性明確、內心世界豐富且勇于表達自我意識的現代新女性形象被塑造起來。
《小美人魚》、《美女與野獸》、《風中奇緣》、《冰雪奇緣》等一系列動畫電影先后推出,這些影片依托經典文本,通過改編、重構將具有明顯現代價值觀念的女性形象塑造起來。強調了女性尋找自我及愛情,擺脫束縛和壓抑的覺醒意識,體現了女性的主體意識不同程度的覺醒。
(一)勇氣的覺醒——人魚公主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脫胎于安徒生童話《海的女兒》的《小美人魚》(1989年)。只是這一次在迪士尼的熒幕上,小人魚由純真善良變成了青春洋溢勇敢冒險追愛的紅發女孩。
在《小美人魚》中,人魚公主愛麗兒敢于勇敢沖破國王頒布的禁令,愛上身為人類的男子,心甘情愿地為了愛情放棄動聽的歌喉和上百年的壽命,只想和她的愛人一起走完人類短暫的一生。在這里人魚公主一改往日柔弱的公主形象,轉而依靠女性的堅韌與決絕追尋愛情。首次化被動為主動,把握個人命運的同時也拯救了王子和國家,成為自我命運的主宰者和愛情理想的堅決實踐者,映射出女性主體意識的光芒。
從小美人魚愛麗兒開始,迪士尼的公主們一改之前深閨美婦的形象。從此,迪士尼的公主也終于不再是完全扁平的童話圣女,而是像普通人一樣,有缺點、有毛病。愛麗兒帶著青春期女孩兒特有的叛逆和不顧一切,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戀。她相信自我、勇于冒險,主動地追求自己的真愛。所以,這位人魚公主也當之無愧的被稱為:迪士尼公主中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女權主義者。
(二)智慧的覺醒——貝爾
1991年上映的由女性編劇琳達改編自法國童話的《美女與野獸》具有高度的性別意識。與人魚公主艾麗兒不諳世事相比,法國鄉村女孩貝爾成了“熱愛讀書,不以貌取人,重視文化內涵”的知性女性。她對加斯頓的拒絕意味著對以貌取人的膚淺愛情觀的擯棄,客觀上構成了對男權婚戀視角的反叛。貝爾對野獸的解救甚至可以看做對傳統男女社會角色的重新定義。艾麗兒的自我蛻變呈現為自外而內的過程,貝拉卻讓男性的改觀從內心延宕到外表。其潛臺詞是,男性的涅槃需由女性引領。
女權主義是女性自由個體與制度化父權文化齟齬的產物,在迪士尼早期動畫公主電影中,女性主角的幸福往往來自于男性愛情的滋養,體現著父權制文化語境下女性對男性的依附。1995年的《風中奇緣》卻展示了女性自主權利的增大。以印第安人形象出現女主人公寶康是部落酋長的女兒,她也算是“公主”形象。她比《美女與野獸》中的貝爾具有更豐富的女性主義內涵,她以部族首領的身份解救英國探險家,化解了異族間的沖突。更選擇留守故土,離別愛人,充分展現了判斷的自主性和決策的獨立性。影片多方位呈現了寶康公主豐富多樣的內心生活,她的家園責任意識以及她對自己前途命運的自我把握無不體現出女性獨立的生命意識和個性化的生命價值追求。
(三)權利的覺醒——冰雪公主
2013年的《冰雪奇緣》延續了迪士尼對經典文本的改編傳統,在對安徒生童話進行重新詮釋和解讀的基礎上充分加入了標志性的類型元素。到了這一時期,公主們故事的主線已幾乎與愛情無關。尤需注意的是,片中男性角色的形象也不再是以前的完全正面的英雄形象而逐漸變得越來越反面。迪士尼的公主電影,也被賦予了新時期的意義而越來越成為“女性電影”[3]。《冰雪奇緣》更是完成了前無古人的創舉:王子成了電影中最大的反派。
不同于以往的迪士尼公主動畫片,《冰雪奇緣》第一次在影片中設置了雙女主角,情節的主線也第一次脫離開男女之愛而圍繞姐妹情展開。在迪士尼公主動畫電影中一貫的“落難與拯救”故事模式中,女性的落難通過女性同胞的解救而得以完成。影片一以貫之的姐妹情取代愛情成為影片的情感主色調。尤其影片最后,妹妹安娜婀娜的身姿背離愛情(男性角色克里斯托夫)奔向姐姐。姐姐艾莎在姐妹情的感召下融化冰雪,重獲溫暖。至此,迪士尼公主動畫電影的愛情世界坍塌,親情世界聳立。
與原作相比,安徒生原著中吉爾達和凱伊青梅竹馬的異性戀關系,改編成了電影中的安娜與艾莎的姐妹關系。風雪中吉爾達執著尋找凱伊的情節,也完全被妹妹安娜不顧一切尋找姐姐的電影語言所替代。只有原著中的部分肯定性情感質素得到保留,如:用愛感化對方,化惡為善。
影片開端,艾莎公主的無心之失傷害到了妹妹安娜,艾莎為此深為自責。艾莎的超能力在國王與山精的對話中被說成是與生俱來的先天稟賦,這似乎彰顯著女性本性的某種先驗性。而艾莎被告誡、被誤解時的自我封閉又似乎隱喻了社會對于女性這種先天本性的防范和曲解。艾莎對女性本性的隱藏昭示出女性在父權社會被壓制、被剝奪的從屬地位。
考察起來,迪士尼動畫對父女之情往往持肯定的情感態度。慈祥的父親往往成為成全女兒意志的行動元:《小美人魚》愛麗兒奔向愛情的雙腿要依靠父親的魔力獲得;《風中奇緣》中寶嘉康蒂對父親的勸說促成了約翰·史密斯的被釋放。但在《冰雪奇緣》中,國王父親的形象一反常態,不僅父女之情十分冷淡,甚至個人能力也乏善可陳,他對艾莎僅有幫助,無非就是提供給艾莎一副手套,并告誡她“別去想它,別去施展它”。《冰雪奇緣》對父親形象的有意識淡化意味著,父親的退場、父權的消失對女性的自我覺醒和成長發揮著重要作用。
影片突出強調了女性的自我成長與解放,在影片的高潮,女王艾莎走出城堡,在漫天雪地里盡情宣泄著制造冰雪的魔力。這是艾莎的自我宣泄,同時也是對世俗桎梏的擺脫,更是在王冠丟棄、長發飄灑后對女性軀體的盡情展示。扔手套、脫披風、丟皇冠,這一系列的動作正是她回歸真實自我的宣言。
20世紀女性主義的杰出代表伍爾芙曾大聲疾呼要女性“成為自己”。她指出,在主流話語中缺乏婦女的聲音,大部分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其實都只是說著男性作家要她們說的話,做著男性作家要她們做的事。《冰雪奇緣》的可貴之處即在于它對女性聲音的解放。
三、結語
迪士尼公主系列動畫中公主形象的嬗變,將女性形象進行了充滿時代感的詮釋和轉化,在迪士尼公主們的故事里,女性的主體意識逐漸增強,高大全的男性正面形象遭到了解構。正如有學者所說:“迪士尼公主動畫中的這些女性形象……從單純、善良的公主到有個性、奮起抗爭的時代女性,從而實現了女性由依附于男性到獨立自主的轉變過程,也充分展現了現代女性在心靈和智慧上的日益成長和對生命價值與意義的探尋與肯定,并從精神、意志以及信仰等方面都對男性及男權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4]
[1]安徒生.白雪皇后[M].葉君健,譯.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10.
[2]Butler Judith.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M].New York:Rutledge,1990.
[3]金丹元,曹瓊.女性主義、女性電影抑或是女性意識——重識當下中國電影中涉及的幾個女性話題[J].社會科學,2007.
[4]程瑜瑜.迪士尼卡通電影中女性形象的嬗變[J].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11.7.
* 陜西省教育廳專項科研計劃項目:改革開放以來好萊塢電影中的華人形象嬗變研究(項目號:15JK1590)。
J
A
1006-0049-(2017)09-0027-02
** 作者簡介:張海濤(1982-),男,文學博士,西安石油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副教授,世界美學協會會員,中華美學學會(國家一級學會)會員,主要研究方向:文藝學、美學;蘇文(1991-),女,西北大學文學院,2015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