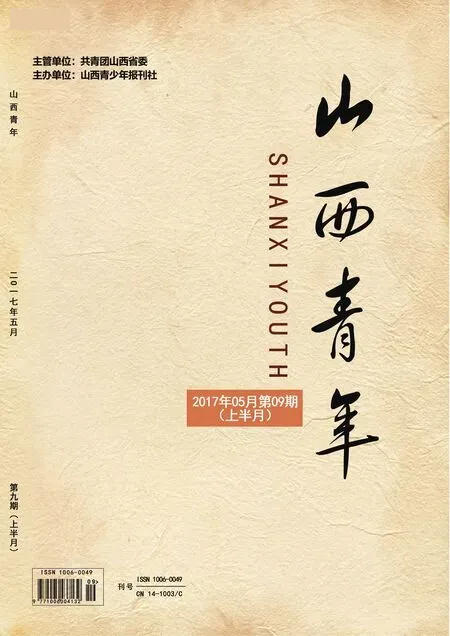《鬧樊樓多情周勝仙》中周勝仙命運悲劇分析
林 杰
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四川 南充 637000
?
《鬧樊樓多情周勝仙》中周勝仙命運悲劇分析
林 杰*
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四川 南充 637000
《醒世恒言》是明末馮夢龍纂輯的一部白話短篇小說集。其題材或來自民間傳說,或來自史傳和唐、宋小說。內容修飾潤色較精,形象鮮明,結構充實完整,描寫細膩,不同程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面貌和市民思想感情。在第十四卷《鬧樊樓多情周勝仙》中刻畫了一個多情、忠貞、矢志不渝的癡女形象,她敢愛敢恨,為求真愛,兩度身死,雖最終與心上人夢中相聚,卻仍逃不出悲劇的輪回桎梏。周勝仙作為反叛者的形象存在于馮夢龍筆下,其對愛情的積極主動與傳統的封建倫理綱常構成了二律背反,是為當世的統治秩序所不容,其悲劇原因與話本小說的創作來源、作者的價值觀念以及文中周勝仙的人物性格特點都有關系。筆者通過文本細讀和史料收集,結合先驗性的閱讀體驗,對周勝仙命運悲劇的深層原因進行突圍分析。
周勝仙;男權;悲劇命運;女性意識;婚戀
湯顯祖在《牡丹亭》題詞里寫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鬧樊樓多情周勝仙》中的周勝仙,也是這樣一位至情至性的女子,可她的一片癡情卻并未使她獲得夢寐以求的愛情,反而將她推入一個又一個的悲劇困境中,乃至失去生命。
自周勝仙在金明池邊與范二郎一見鐘情,并借由賣水的兩人互報家門后,周勝仙的生命悲劇便拉開了序幕。
一、生命悲劇的層次性體征表現
(一)金明池逢范二郎,歸罷已是相思長
周勝仙因在金明池邂逅了范二郎,春心萌動,便對范二郎展開了積極主動的追求。她機智的通過與賣水的爭執,借此自報家門。范二郎也對周勝仙有情,以同樣的方式答復了周勝仙,使得周勝仙“心里好歡喜”。但在封建禮法制度的制約下,男女之間沒有一個可以自由交往的環境,少女心中的異樣情愫無法發泄,使得她相思成疾,由“點心也不吃,飯也不吃,覺得身體不快”到了“若還不肯嫁與他,這小娘子病難醫”的地步。這就是周勝仙的第一層悲劇,相思成疾,甚至危及到了性命。
(二)不教嫁與范二郎,氣絕倒地身冰涼
周勝仙母親為救其性命,央人去范家說親,親事既成,周勝仙的病也不藥而愈,心安意樂等著周父回歸嫁娶。不料,周父堅決反對這門親事,周勝仙在屏風后聽見“一口氣塞上來,氣倒在地”,等周母趕來相救,“卻死了”。就這樣,周父將大量財物細軟放入棺材,將假死狀態的周勝仙幾近于活埋了,并且這些財物也使得周勝仙遭遇了第三層悲劇——失去貞潔。
(三)貞操失了盜墓賊,傷心被囚無自由
盜墓賊朱真看上了隨周勝仙下葬的財物,挖開墳墓,在除女孩兒身上的金銀首飾時看見女孩兒身體,“淫心頓起”,將周勝仙奸了,并把周勝仙騙至家中,囚禁起來,失去了人身自由。
(四)噩夢卻了離朱真,慘死棍棒心上魂
盡管被盜墓賊囚禁,失去自由,但是周勝仙一直在找機會逃走。終于,機會等到了,她逃了出來,找到范二郎,卻在范二郎“滅!滅!”聲中打死了。至此,便是周勝仙最大的悲劇也是最后的悲劇,真正的失去了生命,為情而死。
二、悲劇命運的疊加與原因洞察
周勝仙死了,我們一開始可能會唏噓不已,覺得范二郎太沖動了,否則可以成就一段姻緣,認為周勝仙是死于一場失誤。事實上,周勝仙的悲劇命運早已注定,理學家程穎明確表示“女子之義,從于人也,必待父母之命,兄弟之義,媒妁之言。男先下之,然后從焉”,而周勝仙一開始在心里思量“若是我嫁得一個似這般子弟,可知好哩!”這就與封建倫理綱常背道而馳,周勝仙越是堅持,她的前路便越是荊棘滿地,這是最主要且最本質的原因。除此之外,這與話本小說的創作來源、作者的價值觀念以及文中周勝仙的人物性格特點都有關系。
(一)傳統禮教對交往方式的變態扭曲
從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政治上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不斷強化并即將達到頂峰,而商品經濟在這一時期繁榮發展,使得市民階層不斷壯大,儒家所推崇的“義利觀”受到沖擊,士農工商無不言利。“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2]便是當時的生動寫照,這對封建統治者的統治是極為不利的。由此,在上層士人中刮起一陣振興儒學之風,大力提倡綱常倫理,其中就以宋明理學為最。強調“存天理,滅人欲”,鼓吹“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禁欲主義,具有嚴苛的綱常禮教束縛。雖然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天理”和“人欲”產生了尖銳的對立,并在社會中出現了一股反傳統的“逆流”,比如“異端之尤”李贄就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3],“食色性也”等肯定人的正常欲求的觀點。這些觀點也在社會上有著一定的影響力,但是在封建官吏的迫害之下,這些觀點始終是作為一種“逆流”存在的,對正統思想有一定的沖擊,卻始終被正統思想壓制,沒有造成革命性顛覆性的影響。比如在《鬧樊樓多情周勝仙》中周勝仙與范二郎“四目相視,俱各有情”,但是卻不能直接交談,只能通過與賣水的吵架借機向對方介紹自己。并且,兩人回家之后,由于禮教的束縛,無法相見,兩人紛紛陷入相思之苦。這里就體現了當時男女雖然具有了一定的反叛意識,但仍舊無法掙脫傳統禮教的束縛。
1.文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產物,不可避免的會帶上時代的烙印,且宋元小說話本的對象是廣大的市民階層,迎合市民的趣味是敘事者首要關注的。所以,在當時多種價值觀念的沖擊之下,市民既對婚戀自由這種順從“人欲”的思想感到向往,同時,這些市民生活在封建社會這樣一個大環境下,卻也無法脫離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制約,他們不可能有超越時代的婚戀自由,男女平等的觀念。體現了一種市民真情意識和封建禮教并存的狀態,并且封建禮教占主導。這就是為什么在《鬧樊樓多情周勝仙》中,熱烈積極追求愛情的周勝仙既受到敘事者的同情,卻又在同情中含有譴責,并給她設置了一個悲劇性的結局。
作者在結尾點評道“情郎情女等情癡,只為情奇事亦奇。若把無情有情比,無情翻似得便宜。”這是對周勝仙癡情的直接贊美和同情。但在這贊美和同情中,我們也可發現敘事者對周勝仙的譴責,比如在周勝仙看似對那賣水的道,實則對范二郎的暗示“你敢隨我去?”,范二郎跟著去了,敘事者在點評這一處時,使用的是“惹出一場沒頭腦官司”。表現出了敘事者將周勝仙主動邀約看做是對范二郎的一場災難、一種禍害。所以,在市民階層看來,周勝仙的悲劇結局是必然的,這是對于社會秩序的一種遵從。同時,我們可以從這發現,敘事者是站在男性角度的立場上看待問題的,是一種男權主導下對女性一定范圍內自主意識的認同,如果超出這個范圍,比如周勝仙追求愛情給范二郎帶來了災難,就會受到了譴責。
2.周勝仙的悲劇結局是必然,與當時以男權為主導的社會背景密不可分。首先,周勝仙第一次死去便是由于周父不同意他和范二郎的親事,她受到父權的桎梏,無法反抗,只能是氣倒在地。而從后文來看,周父在其女兒氣絕身亡后,也并未感到后悔,周父作為一個冷漠的封建家長,嚴格按照封建制度那套來要求所有人,甚至是自己的女兒。在他心目中,女兒只是他用以和“大戶人家”聯姻,增長面子的工具,這種思想反映了男權社會下女性生存的真實狀態。
其次,范二郎對周勝仙“欲大于情”,是一種“獵艷”的心理。比如范二郎初次見到周勝仙,想的是“芙蓉帳里作鸞凰,云雨此時何處覓?”直接體現出一種肉欲的追求。并且,在他眼中,周勝仙的容貌是“色色易,迷難拆,隱深閨,藏柳陌。足步金蓮,腰肢一捻,嫩臉映桃紅,香肌暈玉白。嬌姿恨惹狂童,情態愁牽艷客”,帶著一種挑逗妖媚的美,不具年輕女孩兒清純可人的美,充滿情色意味。但話本卻對這種輕薄褻玩女子的行為予以暗許和贊揚,并不認為這樣有何不妥,這種對女性狎昵有余尊重不足的心態就是男權社會下女性無人權的表露。在封建社會,“女子無職業、無知識、無意志、無人格,作為男子的奴隸,一人專有的玩物,摧殘自己以悅媚男子的,原來是男尊女卑的結果;習之既久,謂為固然,又變成為一切行動的原因。乃說女子的人生標準,只是柔順貞靜,無非無儀。[4]”所以,周勝仙這種主動追求愛情的行為完全脫離了當時的社會秩序,為世所不容,所以結局注定是悲劇。
更兼在男權社會下,女子作為男子的附屬品,要求女子從一而終,死心塌地。女子對男子的犧牲奉獻被認做是理所當然的,他們無需付出就能得到女性的癡情眷戀,生死相從,這是男性的愛情理想。所以,在話本中,周勝仙對范二郎生死不渝,熱情主動,兩度死去,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其癡情讓神也為之動容,最后給假三天,讓周勝仙一了心愿。而與之對應的范二郎,從一開始就是被動的,他的所有作為都是在周勝仙的帶動之下,只需做出應承即可,甚至在周勝仙死而復生,好不容易逃了出來尋他時,他一句話不聽,親手將周勝仙打死。可即便是這樣,周勝仙仍對他癡心不改,托夢在獄中與范二郎歡好,為他求情出獄,但是出獄后他竟是歡天喜地回家,最后娶妻生子。那般的無情冷漠,對愛情無所作為,和周勝仙對他付出的感情是完全不對等的,他無法回應周勝仙對愛情的執著,所以周勝仙愛情的悲劇是必然的。
(二)話本故事來源的悲劇性注定
從話本的創作來源看,具有一定的現實依據。《鬧樊樓多情周勝仙》改編自廉布《清尊錄》中的《大桶張氏》。《大桶張氏》講了一個“以財雄長京師”的張家少主路經孫家,看到孫家女兒漂亮,便隨口許下婚約,以玉條為信物。但是后來張家卻娶了別戶,孫氏女“去房內蒙被臥,俄頃即死”,下葬之后被盜墓者發棺而起,再去找張家,“曳其衣且哭且罵”,被張家以為鬼,“推仆地,立死”。并且,這個故事衍生了多個版本,有王明清的《玉條脫》,洪邁的《鄂州南市女》,中間情節或有不同,但都是以女子死亡為結局。小說是源于現實且高于現實的,當時應該是確有女子下葬之后死而復生的事發生,并被人誤認為鬼打死,所以,文人以此取材進行加工。《鬧樊樓多情周勝仙》改編據此,周勝仙的悲劇結尾自然會受到原型中悲劇結尾的影響。
(三)時代局限性的藩籬與突圍
從編者馮夢龍來看,馮夢龍在輯錄這些小說話本時,因為遺漏或是版本不齊,必然會對其進行再加工。馮夢龍是一個具有高度文化修養的文人,他一方面受到李贄“童心說”、湯顯祖“至情說”的影響,強調文學要表達人的真情實感。比如他在《情史》中明確的表露過觀點“天地若有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無情,不能環相生”[5]。另一方面,一個社會的統治思想總是這個社會統治階級的思想,沒有人能完全沖破封建思想禮教的藩籬。所以,馮夢龍既認同正統的儒家觀念,也具有個性解放的思潮,他雖然質疑禮法對人感情的壓制,具有文人的批判精神和自由心態,但是,人的意識是在一定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因此具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所以,馮夢龍雖然表達了對周勝仙大膽主動追求愛情的贊美和同情,具有反傳統的意識,但是仍沒有擺脫男權主義下女性主動追求愛情的命運悲劇。
(四)抗爭禮教過程中的妥協
從周勝仙的性格弱點來看,周勝仙有著對愛情的美好追求和反叛意識,但她不能完全走出家庭的影子和自己理性意志的籠罩。她沒有《碾玉觀音》中璩秀秀的堅決果斷,敢于拋開一切的決心和勇氣。她雖然成功的用機智贏得了范二郎的心,但是卻沒有堅持和守衛它的力量,在對愛情的渴望和懼父心理的雙重矛盾下,她聽到周父不同意她的婚姻,只能氣倒身亡,甚至在她真正的死去后,她了卻心愿的行為,也是在五道將軍的恩準下實現的。所以,她的所有反叛都是在尊重權力的前提下實施的,沒有一種決絕的,魚死網破的態度,這也是她悲劇命運的重要原因。
三、結語:封建悲劇的客觀認證
在商品經濟的驅動下,女子的自我意識有一定的覺醒,她們大膽主動,堅定執著的追求愛情,小說話本對這樣的女性給與了贊美和同情,表達了當時人們渴望沖破封建樊籠的自由平等意識。對此,我們不能一味拔高這種反封建意識,但也不能用現代人的眼光去苛責其中的男權主義、禮教綱常,要正確看待其中的進步性和局限性。
[1]湯顯祖.牡丹亭[M].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
[2][明]張瀚.松窗夢語卷4《商賈紀》[M].中華書局,1985.
[3]李贄.焚書卷1《答鄧石陽》[M].中華書局,2011.
[4]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M].上海書店,1984.18.
[5]馮夢龍.情史﹒龍子猶序[M].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林杰,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在讀,研究方向:古代文學。
I
A
1006-0049-(2017)09-006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