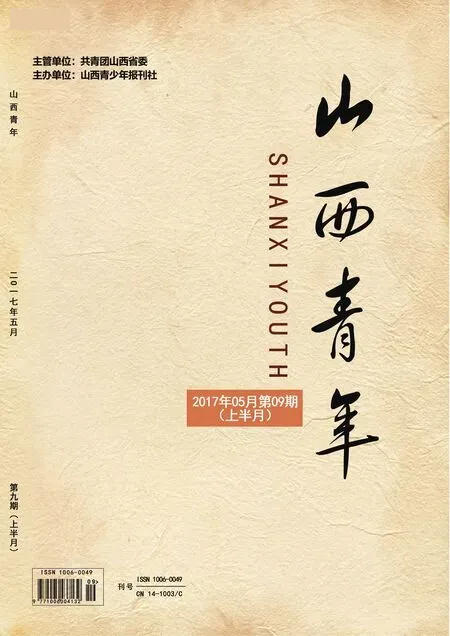基督教法律思想對國家主權認定的影響
李 琴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 200042
?
基督教法律思想對國家主權認定的影響
李 琴*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 200042
對基督教法律,特別是中世紀時期的法律如彭小瑜所說我們“有意識的了解還不多,無意識的誤會卻很深”。基督教是繼羅馬帝國統一后黑暗時代的精神與世俗領袖。完全符合國家的構成要件:領土、人民和主權。筆者從不認為基督教影響了哪些國家,基督教法律思想本就是歐洲各民族國家的精神財富。今試圖對基督教中世紀負有盛名的幾位法學家的觀點進行觀察、剖析、歸納,指出從不承認“國家”到“主權至上”的發展中,基督教發揮了重大作用。
基督教;教父哲學;主權學說
公元1世紀,基督教發源于羅馬的巴勒斯坦省。基督教主要包括天主教、正教、新教三大教派和其他一些較小教派。在中國,因為歷史翻譯的原因,通常把新教稱為基督教,為了說明“基督教”的確切概念。因此基督教一般也被認為是教會法。
關于基督教對西方法制的影響已多有論述[1],更多限于基督教對憲政、刑法、婚姻、訴訟等方面,今試圖從法律思想角度出發,探析基督教法律思想對西方國家形態的影響。法制史不同于法律思想史,法制史是制度的回顧,法律思想史則是思維的累積。法律思想與法制制度的關系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法律思想是人民在認識法律現場的基礎上產生的,法律制度是法律現象的最主要的構成部分。[2]二者更是一與多的關系,同一時期盛行于當時的法律思想可以有多種,但最后凝結為法律制度的只有一種。因此研究法律思想的流變相當必要。今試圖對基督教中世紀對負有盛名的幾位法學家的觀點進行觀察、剖析、歸納,指出從不承認“國家”到“主權至上”的發展中,基督教發揮了重大作用。
雖然在公元392年基督教就已經成為羅馬的國教,但直到中世紀的歐洲才是基督教神學的時代。因此集中于中世紀的法學家,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分崩離析后,封建建制從確立到消亡,各民族意識覺醒,需要一個統治的力量,歐洲長時期的政教二元并立,基督教逐漸占據了精神和世俗領地。
一、《圣經》為源頭的“國家”虛無主義
雖然集中論述中世紀,但《圣經》不可不提。歐洲中世紀的法律思想以《圣經》為源頭。主要集中在《舊約》中的《律法書》和《新約》的《保羅信札》,傳遞出一種對世俗的冷漠,追求靈魂救贖。耶穌就說:“我的國不屬于這世界”。提出了“雙重忠誠”和“上帝選民”的概念。強調雖然世俗諸多不好,但是在神權至上的基礎上仍是要遵守世俗的義務。應該說,這一時期的貢獻有三,首先世俗意義是促使大眾對社會規則包括法律的遵守,這也是為何歐洲失去了羅馬帝國、查理曼帝國的強權統治后仍能正常運轉;深一層意義是將平等的觀念植入大眾的腦海中,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更何況在面對世俗政權和貴族呢?最為重要是種下反抗意識的種子,任何企圖為不平的人或事都可以被推翻的。這對中世紀末期結束千年大幕的民族國家建立,不可說無功。
二、教父哲學——神學自然法
捍衛《圣經》正典地位并對其進行研究的派系為教父哲學。貢獻最大者為圣·安布洛斯、圣·杰羅姆、圣·奧古斯丁,其中以奧古斯丁最甚。奧古斯丁將柏拉圖的法律思想融入基督教中,賦予基督教中的神自然的來源,將自然和神聯系在一起,解決了基督教的信仰問題。
主張“兩國論”,中世紀雖然是羅馬時代的后一階段,但是受蘇格拉底和亞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的影響卻一點兒也不少。奧古斯丁是這種自然法與基督教結合的集大成者。
“神權法”和“世俗法”的劃分。法的分類是古代羅馬法學家的重大貢獻。奧古斯丁吸收了西塞羅的理論,并融合神權思想,將法律劃分為“永恒法”和“世俗法”。“永恒法”,是上帝的旨意,包含了所有善意和正義,將亙古長存;“世俗法”則是“永恒法”的派生,雖然必須符合正義的,但是是對人類惡的一面的規束。“世俗法”的存在是為了不善者。[3]
奧古斯丁是闡述公民社會問題的第一位著作家,將柏拉圖的思想引進拉丁世界。其主要思想是對地國與天國的雙城劃分,并極力主張天國厭惡地國,從他文中一個故事即可看出,亞歷山大大帝抓獲一個海盜并質問他,借海盜之口,奧古斯丁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大帝問“你在海上劫掠,意欲何為?”,海盜回答道:“和你在陸上劫掠的想法是一樣的。只是因為我駕駛小船劫掠,所以我被稱為海盜;你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被稱為皇帝。”[4]
三、阿奎那——神學話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
中世紀隨著人權意識的覺醒,東方文化的沖擊和各地方不平靜的躁動,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廣泛傳播,基督教逐漸發展出將經驗主義哲學、政治學融入基督教神學的經院神學派系。“托馬斯·阿奎那的難題,是如何調和亞里士多德的城邦與奧古斯丁的罪人之城”[5]
亞里士多德主張積極入世的理性觀,阿奎那突破神學局限性,開始承認人的理性,贊同人是社會的動物。為了維護好這一社會需要的秩序。落實到國家形態上,阿奎那將國家分為正義的和非正義的。正義的有君主政治、貴族政治和平民政治,最好是君主政治;不正義的政治有暴君政治、寡頭政治和暴民政治,以暴君政治最壞。阿奎那主張君主政治是因為歷史經驗證明權力最后往往會集中于個人手中,且權力集中于個體手中更易產生和平。這種觀點在美國國父們的《聯邦黨人文集》中也多有體現。從效率角度出發君主政治確實會迅敏些。但是最好與最壞之間取決于君主個人,而對君主進行制約的應該是公共機構。蒙昧狀態下的公共監督意識已經覺醒,權力制衡在萌芽,不再萬事訴諸于上帝。這是偉大的一步。
四、讓·布丹——主權學說
“共同體所有的絕對且永久的權力”,是“凌駕于公民和臣民之上的最高的和絕對的權力”。[6]包括立法權、戰爭和媾和權和吏任免權等權力。不過讓·布丹的主權學說難免走入另一個極端,認為主權至上,這種至上是相對于其權力來源公眾也是如此。其在名著《主權倫》中這樣提到“主權性權威和絕對權力的精義就是不經臣民的同意可以頒布對全體臣民都適用的法律”,這種說法過于激進。布丹自己也認識到,主權者權力的邊界應該限定在上帝的約束范圍內和“自然法”,但這種規制顯得有些無力,畢竟歷史的車輪已經前進到群雄逐鹿中世紀末期。
“主權一詞,非布丹首創,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將這個詞與國家聯系在一起的是讓·布丹,是他賦予了“主權”絕對的最高的意義。從這時起,國家無情地超過宗教、君主等概念了。
基督教對西方法制的影響有很多,但是由于對羅馬法的崇敬之情,往往首屈一指的是教會保留了許多羅馬法的珍貴資料,即使退一步也會想到教會大國的神權與世俗政權并存,再或者是基督教耳提面命式的馴化了大多數為文盲的歐洲中世紀人,使得他們遵守法律,在1000多年里相安無事地生活。但是就筆者而言,我更愿意從那些閃爍著智慧光芒的中世紀教士的書中尋找法律思想的流變,并追尋這些流變對今天社會的影響。
[1]朱曦.基督教對西方法制史的影響.青年與社會,2013(02).
[2]嚴存生主編.西方法律思想史,2016.2.
[3]嚴存生主編.西方法律思想史,2016.69.
[4]奧古斯丁.上帝之城(第4卷,第4章).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147-148.
[5][英]約翰·麥克里蘭.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棟.海南出版社,2003:136.
[6][法]讓·布丹.主權論.李衛海,錢俊文,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1.
李琴(1993-),女,華東政法大學,2016級法律史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國法制史。
B
A
1006-0049-(2017)09-01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