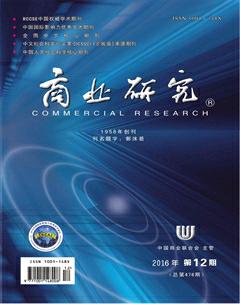交叉持股、內部人控制與經營績效
黃昌富 張晶晶



摘要:本文以我國2010-2014年滬深上市公司為樣本,考察交叉持股、內部人控制與經營績效的關系。實證結果表明,交叉持股與經營績效存在顯著的倒U型關系,交叉持股在一定的范圍內有助于經營績效的改善,但是超過一定的閾值后,經營績效反而會下降;交叉持股與內部人控制之間存在顯著的U型關系,在拐點之前監督效應占優,而超過拐點后侵占效應則更為明顯;內部人控制在交叉持股與經營績效的關系中具有中介傳導作用,交叉持股通過影響內部人控制,進而影響企業的經營績效。
關鍵詞:交叉持股;內部人控制;經營績效;中介效應
中圖分類號:F270.3 文獻標識碼:A
作者簡介:黃昌富(1959-),男,湖北當陽人,三峽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企業戰略管理;張晶晶(1992-),女,湖北當陽人,三峽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企業戰略管理。
一、引言
交叉持股作為一種特殊的股權結構于20世紀中期起源于日本,隨后逐漸興盛,普遍存在于各國的上市公司中。我國的交叉持股制度始于20世紀90年代,股權分置改革和新會計準則的正式實施極大地推動了交叉持股在我國的發展。據不完全統計,2010-2014年五年間我國滬深兩市存在交叉持股的A股上市公司均達到了500例。截止2014年底,雅戈爾、雙錢股份、杭州解百、隧道股份、上海三毛等相當一部分上市公司持有數十家甚至更多上市公司的股份,交叉持股已然成為了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的重要表現形式。由于交叉持股的企業共同形成了龐大的交叉持股網絡,所以存在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會造成上市公司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股市經歷牛市時,存在交叉持股的公司會實現資產增值,獲利豐厚;股市泡沫一旦破滅,上市公司市值大幅縮水,損失慘重,這也正反映出交叉持股所帶來的風險。2015年8月,阿里巴巴與蘇寧云商宣布進行交叉持股,阿里成為蘇寧的第二大股東。雙方強強聯手,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兩家公司將利用天貓的物流體系與蘇寧的實體店鋪實現電商與傳統家電的合作,線上與線下的融合,這一事件使交叉持股再一次成為了熱點話題。
目前,對于交叉持股對經營績效影響的研究尚未統一結論。一方面,有研究指出交叉持股能夠建立合作聯盟,降低交易成本,分散經營風險,其績效較非交叉持股的上市公司高。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Constand(2002)[1]認為交叉持股會架空公司治理機制,引發嚴重的內部人控制問題,發生不公平的關聯交易,績效低于沒有交叉持股的公司。當前對交叉持股與經營績效之間關系研究結論不一致的原因在于缺乏對這兩者內在作用機制的研究,它們之間的關系仍然是一個“黑箱”。交叉持股之所以會影響企業的經營績效,是因為股權結構對企業的治理機制具有積極或消極的影響。
交叉持股會帶來公司治理中的內部人控制問題。根據委托代理理論,管理者對于公司股東權益的危害性與管理者控制力成正相關,即管理者對公司控制力越強,越會誘發自利和不負責行為[2],有損企業的經營績效。因此,內部人控制與交叉持股和經營績效存在密切的聯系,交叉持股可能作用于內部人控制繼而影響企業的經營績效。
鑒于此,本文以2010-2014五年間交叉持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數據作為研究對象,以實證研究的方式分析交叉持股與經營績效的關系,并進一步探討內部人控制對交叉持股與經營績效間關系的影響,檢驗內部人控制在交叉持股與經營績效間的中介傳導機制,以期厘清交叉持股與經營績效的內在機理。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交叉持股與經營績效的研究
對于交叉持股與經營績效的研究,諸多學者如Douthett(2001)[3]等得出了交叉持股與經營績效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的結論。首先,交叉持股會促進企業間的合作聯盟,產生協同效應。一是交叉持股可以維持成員企業在生產、研發、營銷等方面的合作,帶來規模經濟效應[4] 。成員企業間保持著長期穩定的交易關系還可以降低彼此的交易成本,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5];二是交叉持股使各個企業即可以保持自身的獨立性,又可以參與多元化的經營,降低經營風險,享受聯合體帶來的范圍經濟效應。但是,許多上市公司進行低比例的交叉持股大都并非為了提高主營業務的獲利能力,而更多的是為了獲得短期的套利,基于此目的的交叉持股則并不利于企業間形成合作聯盟。其次,交叉持股可以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保證擁有充足的經費用于研發。交叉持股企業間還可以通過互相借鑒好的管理經驗,優化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效率,改善經營績效。然而,也有研究得出了交叉持股對企業經營績效不利的結論。當交叉持股比例過高時,極有可能產生嚴重的內部人控制問題,導致公司治理結構失去制衡,發生關聯交易使業績下滑[6]。此外,交叉持股比例過高可能是因為管理層醉心于交叉持股,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尋找交叉持股的目標而不是企業內部的管理上,經營必然會因此而受影響。所以,交叉持股具有雙刃劍效應,對企業的經營既有正面影響又有負面影響。可能在一定范圍的合適水平內,交叉持股可以改善企業的經營績效,但是超過這一范圍則無助于經營績效的提升反而會降低績效。
因此,本文提出假設1:交叉持股與經營績效存在倒U型關系,相對于擁有適度交叉持股比例,擁有低比例或高比例交叉持股的企業績效較差。
(二)交叉持股與內部人控制的研究
交叉持股對公司的治理會產生兩種相反的效應,即監督效應和侵占效應。監督效應是指大股東會積極監督管理者,防止管理者的自利行為。股東對管理層實施監督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當交叉持股比例較低時,持股單位監督管理層所付出的成本與收益不對等,所以不會積極地參與公司的治理,“搭便車”才是其最佳選擇[7]。但是企業的效益和股東的利益息息相關,隨著交叉持股比例的增加,持股企業會更注重于獲得長期穩定的投資回報。這樣,持股企業往往不會“用腳投票”,相比其他股東會有更多的動機而對公司的管理層施加監督與控制,以防止管理層以犧牲公司利益為代價謀求私利[8-9]。Ghatak和Kali(2001)[10]基于信息經濟學,提出交叉持股為公司提供的監督機制能有效的預防管理層采取機會主義行為,較好的克服內部人控制問題,減少管理層與股東間的代理成本,改善企業的經營績效。
李新春等(2008)[11]提出侵占效應是指大股東有動機并且有能力掏空公司,可能會做出損害公司利益的自利行為。根據經濟人假設,經濟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大股東與中小股東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大股東可能以其他股東的利益為代價通過追求自利目標而不是公司價值目標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隨著交叉持股比例的增加,持股方對于被持股方的控制權逐漸加強,極端的情況是交叉持股關系中持股單位成為了被持股單位的控股股東。此時,交叉持股股東基本能任命公司的董事與監事人選,董事會和監事會會失去應有的獨立性,無法發揮監督公司的作用。董事長也由持股單位所委派或直接由持股方人員擔任,有時還兼任總經理,這為持股方通過不公平關聯交易、隧道挖掘等方式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了機會。另外,存在交叉持股的股權結構形式時,就會出現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的偏離。呂新軍(2015)[12]認為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偏離的程度越大,股東就能以越小的侵占成本獲取自身利益,就越有動機掠奪公司的資產與利潤。關聯交易是股東掠奪公司的慣用手段,而不公平關聯交易的順利進行,必然需要管理層的配合,若交叉持股股東與高管達成合謀就一定會涉及到利益互換,高管為交叉持股股東侵占公司財產提供方便,股東則給予高管更多薪酬或采取更為寬松的態度,這就自然引起嚴重的內部人控制問題[13]。
與此同時,在穩定的高比例交叉持股網絡中,由于公司治理結構中的“董事會中心主義”,企業的經營者往往掌握著其在其他企業所占股份的發言權。對于各企業代理人來說,其最好的行動方式是不干預對方公司的經營活動,以換取其他企業對自己采取同樣的態度,達到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和平衡。這樣一來,交叉持股成員企業的經營者對于各自企業的控制權即內部人控制得到了強化[14]。
綜上所述,交叉持股同時存在監督效應與侵占效應,這兩種效應此消彼長同時發揮著作用,因而交叉持股與內部人控制之間可能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呈U型的二次曲線關系。
因此,本文提出假設2:交叉持股與內部人控制之間存在U型關系,適度的交叉持股有助于降低內部人控制程度。
交叉持股程度適當時,會更多地表現為監督效應。管理層由于受到更多的外部性監督約束,自利行為會較為收斂,支付給自己的薪酬則會相對合理。持股方為了防止管理層的道德風險問題,會更傾向于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分離,減少內部董事的比例,并引入更多的獨立董事。而交叉持股超出一定比例范圍時,侵占效應便會占優。管理層可能與交叉持股股東形成合謀或直接是交叉持股股東的利益代表,無論哪種情況,管理層都會對企業有較強的控制力,因而會盡可能地提高自己薪酬水平,傾向于兩職兼任并減少獨立董事的人數。因此,本文在假設2的基礎上提出四個子假設:
假設2.1:交叉持股與高管薪酬之間存在U型關系。
假設2.2:交叉持股與內部董事比例之間存在U型關系。
假設2.3:交叉持股與獨立董事比例之間呈倒U型關系。
假設2.4:交叉持股與董事長總經理兩職合一之間存在U型關系。
(三)內部人控制在交叉持股與經營績效間的中介效應
根據委托代理理論,企業的經營權與所有權兩權分離時,由于高管負責企業的經營管理活動,擁有部分自主權,而股東幾乎不可能時刻監督他們的行為,相應的監管成本也很高。因此,作為內部人的高管很可能利用自己所擁有的信息優勢和控制權實現個人效用最大化[15],難免把資本用在非經營性項目上,通過提高自己的薪酬水平、在職消費等方式享福作樂,而在企業的經營中往往會為了眼前的利益而采取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加大企業的經營成本,侵蝕企業的利潤[16],甚至不顧企業的長期發展盲目構建自己的企業帝國。管理者對于公司股東權益的危害性與其控制力成正相關,即管理者對公司控制力越強,越會誘發自利和不負責行為[17]。王韜和李梅(2005)[18]通過實證研究也發現,內部人控制度與企業的經營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也就是說,內部人控制問題有損于企業的經營績效,企業的經營績效會隨著內部人控制程度的加深而明顯下降。
如前文所述,交叉持股與內部人控制之間存在內在聯系,而內部人控制與企業績效之間也存在密切的關系,所以交叉持股對企業經營業績的影響勢必通過內部人得到發揮。然而現有的文獻還未曾考慮交叉持股、內部人控制與經營績效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因此,本文將這三者聯系起來,以考察交叉持股是否通過內部人控制進而影響了企業的經營績效。
據此,本文提出假設3:內部人控制在交叉持股與經營績效的倒U型關系具有中介作用,交叉持股通過影響內部人控制,進而影響了績效。
三、變量選取與模型設定
(一)樣本與數據來源
世界各國現存的交叉持股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日德為代表的相互持股模式,強調兩個法人之間相互持有對方的股份,即A企業持有B企業股份的同時B企業也必須持有A企業的股份;另一種是以英美為代表的單項持股模式,這種模式并不要求雙方向持股,只要一方持有另一方的股份即視作交叉持股。如秦俊和朱方明(2009)[19]所說,由于國內理論界受到日本相互持股的影響,存在認為交叉持股就是相互持股的認識偏差,這種偏差與我國的實務不符,也縮小了交叉持股的研究范圍。除了直接交叉持股(如A公司與B公司相互持股)外,企業間接交叉持股也不應該被忽略[20]。因此,考慮我國交叉持股的實際情況,本文所指的交叉持股為廣義的交叉持股,既包括相互持股的情況也包括單項持股的情況。
本文以2010-2014年滬深兩市A股中存在交叉持股的上市公司作為原始樣本,并做了如下篩選:(1)剔除ST和*ST公司;(2)剔除金融類行業的公司;(3)剔除持股單位2010-2014年五年間非連續交叉持股的樣本;(4)由于我國上市公司交叉持股的比例普遍偏小,過半數的交叉持股比例在1%以下,并且大多數都是為了獲取短期的資本利得,幾乎無法影響被持股單位,所以不列為本文的考慮范圍,因此根據被持股企業的前十大股東數據庫剔除交叉持股股東非前十大股東的樣本;(5)剔除數據缺失的樣本。最終,我們得到了64個樣本共計320個觀測值。本文交叉持股比例數據是通過Wind金融數據庫手工收集整理得到,公司基本信息、高管資料及財務數據均來自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研究所使用的數據統計處理軟件為SPSS和Eviews。
(二)變量選取與模型設定
1.經營績效(Perf)。本文采用凈資產收益率(ROE)作為經營績效的評價指標。
2.交叉持股比例(CSH)。本文采用交叉持股比例來衡量交叉持股的程度,交叉持股比例是由持股方所持有的被持股方的股份數量占被持股方全部股份的比例得到。若存在幾個上市公司同時持有一家上市公司股份時,交叉持股比例則為所有上市公司持有股份數之和占其總股數的比例。
3.內部人控制(IC)。本文參考有關內部人控制實證研究方面的文獻后,使用大多數學者認同并采用的內部董事比例(Inboard)、前三名高管薪酬(Income)、獨立董事比例(Indirector)、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Dual)情況這四個指標來衡量內部人控制。其中,內部董事比例(Inboard)由樣本公司高管進入董事會的人數占董事會總人數的比例得到,該比例越大,管理層對董事會的制衡度就越大,董事會對管理層的監督力度就更弱,內部人控制度程度也就越大[21];高管薪酬(Income)則是以上市公司排名在前三位的高管薪酬總額的自然對數來衡量,當高管對企業的控制力越強時就會支付給自己更高的薪水,所以高管薪酬總額越高,內部人控制程度越深;獨立董事比例(Indirector)為公司獨立董事人數與董事會總人數的比值,由于獨立董事能夠對企業的事務做出相對獨立的判斷,所以獨立董事比例提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約束管理層,緩解內部人控制問題;兩職合一(Dual),當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時取值為1,兩職分離時取值為0。馮彩和高波(2004)[22]的研究指出董事長總經理兩職兼任時會有更多的機會濫用職權謀取私利,導致內部人控制更明顯;內部人控制度(Incontrol),為了綜合反映內部人控制,本文借鑒吳世農和文芳(2010)[23]等學者的方法對內部董事比例、前三名高管薪酬、獨立董事比例、是否兩職合一進行主成分分析構造出度量內部人控制的綜合指標內部人控制度(IC)。
4.控制變量。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為企業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
具體變量的定義如表1所示。
本文設置了如下三個模型來檢驗前文所述的理論假設。其中模型1用來檢驗交叉持股與經營績效之間的二次曲線關系,利用模型2來考察交叉持股與內部人控制之間的相關性,模型2.1、2.2、2.3、2.4則是用來分別檢驗交叉持股與衡量內部人控制的四個指標間的關系。最后,由于本文需要檢驗的是交叉持股通過倒U型曲線影響內部人控制,繼而影響企業的經營績效,采用Baron和Kenny(1986)的三步驟中介效應檢驗方法來檢驗曲線形的關系將不再適用。因此本文借鑒董保寶(2014)[24]的做法,參照Edwards和Lambert(2007)[25]的調節路徑分析方法來進行中介效應檢驗,在模型二的基礎上加入內部人控制及內部人控制與交叉持股的交互項,建立模型三來檢驗內部人控制在交叉持股與企業績效關系間的中介作用。
四、實證研究
(一)描述性統計
表2是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由統計結果發現,樣本企業間交叉持股比例的最大值為74.82%,最小的僅為0.17%,交叉持股程度的差距非常大,說明我國上市公司對于交叉持股抱有截然不同的態度,有的企業熱衷于交叉持股,而有的企業對交叉持股則并不看重。獨立董事比例的平均值為37.53%,整體上符合上市公司對于獨立董事不少于1/3的要求。高管薪酬最高的為6 399 600元,是高管最低薪酬467 600元的10倍還多,可見我國不同企業的高管薪酬差異之大。此外,內部董事比例的均值為21.60%,最大為71.43%,最小為0,平均有11.19%的公司存在總經理與董事長兩職合一的情況,說明我國還有一定數量的公司尚未實行兩職分離制度。企業規模的平均值為22.8369,即平均總資產為827 827萬元。資產負債率平均值為53.57%,樣本公司的財務風險略高。
(二)多元回歸分析
交叉持股與內部人控制的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以內部人控制度綜合指標作為因變量時,交叉持股的平方項系數顯著為正,而獨立董事比例越高代表內部人控制程度越低,與獨立董事的回歸中交叉持股的平方項系數顯著為負,說明交叉持股與內部人控制之間存在顯著的U型關系。即在U型關系的拐點之前,交叉持股比例的增加有利于緩和內部人控制,在交叉持股比例達到U型關系的拐點值后,內部人控制會隨著交叉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加強,因而假設2獲得支持。因為在合適的交叉持股范圍內,交叉持股股東的監督效應占優,能有效抑制內部人控制問題,而在穩定的高比例交叉持股情況下,持股單位的侵占效應更為明顯,股東與管理層的合謀引起嚴重的內部人控制問題,交叉持股企業間達成的共識也會使內部人控制得到強化。交叉持股與高管薪酬、內部董事比例、獨立董事比例、兩職兼任的回歸結果顯示交叉持股與高管薪酬、內部董事比例分別存在顯著的U型關系,與董事長總經理兩職合一的U型關系不顯著,而與獨立董事則存在顯著的倒U型關系。交叉持股的監督效應使高管的薪酬相對合理,高管與董事會成員更傾向于兩職分離,獨立董事比例得到提升,而交叉持股的侵占效應所帶來的效果則反之,假設2.1、2.2、2.3分別得到了支持。
交叉持股與企業績效的實證檢驗結果如表4的(6)-(8)列所示,交叉持股的平方項系數顯著為負,說明交叉持股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倒U型關系。即交叉持股比例較低時,企業績效隨著交叉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交叉持股比例達到一定的閾值后,績效則隨著交叉持股比例的增加反而減小,假設1得到了支持。當交叉持股比例處于適當水平時,交叉持股能夠促進企業間形成合作聯盟,產生協同效應,降低交易費用,并能給企業帶來優化管理模式、提高融資能力的好處。而交叉持股比例過高時,則會分散企業經營的中心,還極有可能因為交叉持股股東與管理層的合謀導致治理結構失衡,產生嚴重的內部人控制問題,發生關聯交易,使業績下滑。為了檢驗內部人控制在交叉持股與企業績效關系間的中介作用,在模型中加入了內部人控制度及內部人控制度與交叉持股的交互項后,回歸結果顯示,交叉持股比例的二次項系數顯著為負,再次證明了交叉持股與績效間的倒U型關系,而內部人控制度的系數顯著為正,內部人控制度與交叉持股的交互項系數不顯著,證明了內部人控制在交叉持股與企業績效的倒U型關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也就是說,交叉持股通過內部人控制進而影響了企業的經營績效,適度的交叉持股的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內部人控制問題從而有助于經營績效的改善,交叉持股超過一定的閾值后則反而會導致嚴重的內部人控制問題,引發管理層的自利行為,降低企業的經營績效[26]。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確保上述回歸結果的可靠性,本文做了如下穩健性檢驗:(1)使用資產回報率ROA代替ROE作為經營績效的衡量指標檢驗交叉持股與經營績效的關系及內部人控制的中介作用。回歸結果如表4的(9)-(11)列所示,交叉持股二次項的系數顯著性有所降低,但仍然在5%的水平上顯著,內部人控制的中介作用也得到了驗證,結果并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2)交叉持股對于經營績效及內部人控制的影響可能不會在當年顯現出來,存在一定的滯后性,所以將衡量經營績效的指標滯后一年采用t+1期的凈資產收益率進行回歸;(3)交叉持股比例數據的處理方法可能對實證檢驗的結果存在影響,當幾家公司同時持有一家公司的股份時,將其中的最高持股比例作為交叉持股的比例進行穩健性檢驗;(4)有部分學者采用高管持股比例作為內部人控制度的衡量指標之一,因此在衡量內部人控制的指標中加入高管持股比例這一項,并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內部人控制度的綜合指標,再進行實證檢驗。穩健性檢驗的回歸結果均與前文相差無幾,并未發生改變,所以結論依然成立。
五、結論
交叉持股作為股權結構的一種形式,與公司治理存在密切的內在聯系,不同程度的交叉持股會帶來公司治理的差異,從而影響其對企業經營績效的目標函數。因此,本文使用2010-2014五年間交叉持股的上市公司面板數據作為研究對象,分析了交叉持股與經營績效及內部人控制之間的二次曲線關系,進一步檢驗了內部人控制在交叉持股與經營績效間的中介作用。主要的研究結論是:(1)交叉持股與內部人控制之間存在顯著的U型關系,適度的交叉持股有助于降低內部人控制程度。交叉持股保持在相對較低程度的情況下,持股股東為了獲得長期穩定的收益,會對公司的管理層施加監督與控制,防止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而在穩定的高比例交叉持股中,交叉持股股東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會與高管達成合謀,作為對高管的回報會給予高管更多的控制權,引發嚴重的內部人控制問題。(2)交叉持股與經營績效存在顯著的倒U型關系,交叉持股程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有助于經營績效的改善,但是超過一定的閾值后,反而會導致經營績效不佳。可能的原因在于,適度的交叉持股可以促進成員企業建立聯盟,帶來協同效應,而過度的交叉持股會使企業偏離經營的重心并產生內部人控制問題,從而降低經營績效。(3)內部人控制對交叉持股與經營績效的關系具有中介效應,交叉持股通過影響內部人控制進而影響了企業的經營績效。
參考文獻:
[1] Ang J,Constand R. The portfolio behavior of Japanese corporations stable shareholders[J].Journal of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2002,12(2):89-106.
[2] 劉孟暉,高友才.現金股利的異常派現、代理成本與公司價值——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南開管理評論,2015(1).
[3] Douthett EB,Jung K. Japanese Corporate Grouping(Keiretsu) and the Informativeness of Earning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 Accounting,2001,12(2):133-159.
[4] 儲一昀,王偉志.我國第一起交叉持股案例引發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5).
[5] 冉明東.論企業交叉持股的雙刃劍效應——基于公司治理框架的案例研究[J].會計研究,2011(5).
[6] 胡潔,胡穎.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關系的實證分析[J].管理世界,2006(3).
[7] 張春霖.存在道德風險的委托代理關系:理論分析及其應用中的問題[J].經濟研究,1995(8).
[8] 郭澤光,敖小波,吳秋生.內部治理、內部控制與債務契約治理——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南開管理評論,2015(1).
[9] Chen C,Guo W,Mande V. Corporate value, managerial stockholdings and investments of Japanese firm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2006,17(1):29-51.
[10]Ghatak M,Kali R.Financially interlinked business groups[J].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2001,10(4):591-619.
[11]李新春,楊學儒,姜岳新,等.內部人所有權與企業價值——對中國民營上市公司的研究[J].經濟研究,2008(11).
[12]呂新軍.股權結構、高管激勵與上市公司治理效率——基于異質性隨機邊界模型的研究[J].管理評論,2015(6).
[13]李文洲,冉茂盛.大股東掏空視角下的薪酬激勵與盈余管理[J].管理科學,2014(6).
[14]李曉春.交叉持股公司治理的困境及出路[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版,2013(4).
[15]白俊,連立帥.國企過度投資溯因:政府干預抑或管理層自利[J].會計研究,2014(2).
[16] 孫天法.內部人控制的形式、危害與解決措施[J].中國工業經濟,2003(7).
[17] 徐細雄,劉星.放權改革、薪酬管制與企業高管腐敗[J].管理世界,2013(3).
[18] 王韜,李梅.論股權泛化條件下的內部人控制[J].財貿經濟,2005(2).
[19]秦俊,朱方明.我國上市公司間交叉持股的現狀與特征[J].財經論叢,2009(3).
[20]Dietzenbacher E, Temurshoev U. Ownership relationsin the presence of cross-shareholding[J].Journal ofEconomics,2008,95(3):189-212.
[21]何浚.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1998(5).
[22]馮彩,高波.內部人控制對上市公司績效的影響——以滬市為例進行的研究[J].華東經濟管理,2004(5).
[23]吳世農,文芳.管理層權力、私有收益與薪酬操縱[J].經濟研究,2010(11).
[24]董保寶.風險需要平衡嗎:新企業風險承擔與績效倒U型關系及創業能力的中介作用[J].管理世界,2014(1).
[25]Edwards JR,Lambert LS.Methods for Integrating Moderation and Mediation:A GeneralAnalytical Framework Using Moderated Path Analysis[J].Sychological Methods,2007,12(1):1-22.
[26] 楊瑞龍,鄭志.競爭、內部人控制與經濟績效——許繼集團治理結構及其績效的經濟學解釋[J].中國工業經濟,2001(10).
Abstract:Based on the samples of cross-shareholding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10 to 2014, the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ross-shareholding, insider control and operating performance. The empirical results find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cross shareholding and operating performance is inverse U shape:cross-shareholding can help to improve operating performance within a certain range,however, if the specific threshold is exceeded,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will drop instead; the cross shareholding has an obvious U-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insider control: before the turning point the dominant effect is supervision, and after the turning point, the occupation effect is more obvious; moreover, the insider control acts as a mediator in the invers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ross shareholding and operating performance and by affecting insider control, the cross shareholding can influence operating performance further.
Key words:cross-shareholding; insider control; operating performance; mesomeric effect
(責任編輯:維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