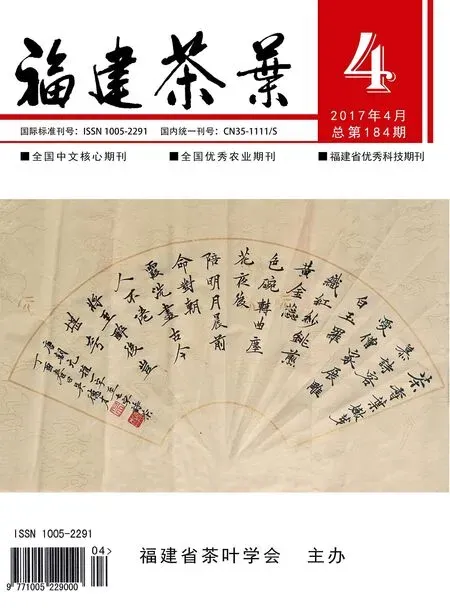中西方茶文化在翻譯中的體現及順應性研究
杜曼麗
(咸陽師范學院,陜西咸陽712000)
中西方茶文化在翻譯中的體現及順應性研究
杜曼麗
(咸陽師范學院,陜西咸陽712000)
茶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內容,對中西方的文學藝術創作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本文以翻譯順應論為基本研究框架,介紹了該理論的形成、發展及構成要素,并從茶名翻譯、茶具翻譯、茶禮翻譯和茶詩翻譯等四個方面舉例分析了中西方茶文化的順應性翻譯策略及其傳達效果,指出譯者在翻譯時應當堅持“忠實性”原則與“順應性”原則,立足于原文的深層文化及審美意義,順應作者的創作意圖,采用為目的語讀者所喜聞樂見的表達方式和邏輯方法,對茶文化進行積極有效的傳達,促進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與融合。
中西;茶文化;翻譯;順應性;忠實性
我國茶文化歷史悠久、博大精深,是傳統民族文化的瑰寶,也是我國勞動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集中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思想意志、價值取向和審美理念。十六世紀,中西方貿易不斷擴大,茶葉作為與絲綢、陶瓷并重的民族特色產品開始遠銷至歐亞各國,茶文化也伴隨著日益升溫的茶葉貿易進入西方,以其優雅的技藝與獨特的功效獲得了各國人民的青睞,并在之后數百年的發展歷程中與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內外環境緊密融合,最終形成了以“英國下午茶”為典型的別具一格的西方茶文化,在世界茶文化的舞臺上綻放異彩。
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茶文化對中西方文學藝術的創作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我國有《茶經》、《續茶經》、《茶錄》、《茶譜》、《大觀茶論》、《本朝茶法》等茶學專著,也有《茶煙》、《陽羨茶》、《煮土茶歌》、《雙井茶》、《月兔茶》、《試院煎茶》、《劍南詩稿》等詠茶詩詞,還有《爾雅》、《詩經》、《牡丹亭》、《紅樓夢》等借茶抒懷的古典著作,更有《茶館》、《春茶》、《茶友》、《茶人三部曲》等以“茶”為題材的現代小說作品。無獨有偶,在西方文學作品中,同樣隨處可見茶文化的綺麗身影。比如,在奧斯汀所著的《傲慢與偏見》中,主人公用餐之后必有茶會,狄更斯的多部作品中都以茶來塑造人物形象、渲染故事場景、抒發內心情感,浪漫主義詩人濟慈和雪萊在詩篇中不吝筆墨描繪人們日常飲茶的場景,劇作家皮內羅則將茶視為作品的靈魂,指出“茶之所在,即是希望之所在”,散文家喬治·吉辛則認為茶是圣潔的象征,茶與散文的結合是優雅、閑適而愜意的,西方文學泰斗塞繆爾·約翰遜更是將自己描述為日夜與茶相伴的“茶鬼”,幾乎每一部作品的搭建都離不開茶文化的幫襯。
正所謂“世間文化一家親”,為了滿足文化交流的需要,這些文化作品就必須要借助翻譯這座橋梁進入異國他鄉供讀者鑒賞。然而,由于中西方語言表達方式不同,思維方式、風俗習慣、價值認知等也有巨大差異,因此,若要成功傳遞這些作品中的茶文化,就要選擇恰當的翻譯策略,在立足于原文基本精神的基礎上,既順應原文的審美深度,又順應讀者的邏輯習慣,實現中西方茶文化的相互理解及縱深發展。
1 翻譯順應論
在翻譯理論界,比較著名的翻譯方法有異化和歸化兩種。其中,異化是指盡可能地保留原文的語言及文化特色,譯者盡量不打擾原作者的安寧,讓讀者去接近作者,目的語讀者一看便知這是對外國作品的翻譯,閱讀過程中可以領略外國文化的獨特魅力,有利于兩種語言和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與融合;歸化則是要盡可能地適應目的語的語言及文化習慣,“盡可能不擾亂讀者的安寧,讓作者去接近讀者”,原文的陌生感和語言的障礙得以淡化乃至消除,通俗易懂,目的語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順暢利落,有時甚至會誤以為這是原汁原味的目的語原創作品。
許多年來,關于異化與歸化的爭論僵持不下,在此過程中,翻譯理論學家發散思維、刻苦鉆研,將翻譯學與語言學結合起來,衍生出一系列更加完善、更為具體的翻譯理論,其中,翻譯順應論就是最為著名的一個。
1999年,語言學家維索爾倫在《語用學新解》中首次系統地提出了順應論的思想,明確指出語言的使用是一個間斷的語言選擇的過程,這種選擇可以是有意識的或者是無意識的,可以是出于語言內部的也可是外部的原因,但究其根本,它是一種順應性的選擇過程,包括從宏觀角度對社會、文化的發展以及人類的認知水平做出判斷,還有從微觀層面上對語言結構的層次及其內涵進行順應性研究。在語言使用上,人們之所以可以做出順應性的選擇,是因為語言本身具有順應性、商討性和變異性的特點,其中又以順應性為核心。后來,翻譯理論界發現順應論對于翻譯有很強的解釋力,便把翻譯活動與順應論相結合,形成了翻譯順應論。該理論認為,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應當做到對原文的順應以及對目的語環境的順應,首先必須深入理解原文,做好對意義的選擇,其次要明確翻譯目的,做好對翻譯對象的選擇,最后則要選擇恰當的翻譯策略和表達方式,把原文的意義以目的語讀者所喜聞樂見的形式予以表達,實現不同語言文化之間的順利溝通。
2 中西方茶文化的順應性翻譯
中國茶文化是世界茶文化的源頭,擁有數千年的輝煌歷史,在形式與內容上都可以說是包羅萬象。如今,在我國民族商品和民族文化“走出去”的戰略環境下,既有深刻內涵又有實體表征且不乏西方對照的茶文化便成為了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的核心依托。下面,筆者將以中國茶文化的英譯為例,探討翻譯順應論在我國茶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首先,茶文化英譯的首要難點在于對茶名的理解和傳達。眾所周知,我國茶類名目繁多、千姿百態,從茶葉的物理屬性上來看,可以分為綠茶、紅茶、白茶、黃茶、青茶、黑茶等幾大類,但若考慮產地、形態、色澤、口感、典故、歷史等因素,則有成千上萬種之多,比如云南普洱茶、六安瓜片茶、西湖龍井茶等等。筆者認為,茶是我國文化的獨特風景,茶名則是我國茶文化的歷史積淀,一言兩語很難說清,所以,對于茶文化的翻譯,應當采取順應原文內涵的策略,以直譯或者音譯的方式,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擴大目的語讀者的文化視野,營造具體的跨文化交際語境。對于“普洱茶”、“女兒茶”、“龍井茶”、“六安茶”等,譯者可以音譯為“Pu’er tea”、“Nu’er tea”、“Longjing tea”、“Lu-an tea”,因為這些茶名在西方已經具備一定的知名度,這種“漢語拼音+ tea”的譯法并不會影響目的語讀者對茶名的理解。
其次,在茶文化中,茶具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茶道藝術中最為關鍵的內容,它可以體現飲茶者的審美水平和內在心境,也可以反映出飲茶者對于飲茶禮儀的重視程度。“茶圣”陸羽曾在《茶經》中明確指出:飲茶有二十四器,含茶杯、茶碗、茶斗等,“二十四器闕一,則茶廢矣”,可見茶具對于茶道的重要意義。在我國的文學作品中,不乏對各類茶具的描寫,有些作者還會以茶具之精良襯托茶品之高貴,以茶具之形態刻繪人物之地位。比如《紅樓夢》中對于薛寶釵所用茶杯的描述:
一個旁邊有一耳,杯上鐫著“頒瓟斝”三個隸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晉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于秘府”一行小字(曹雪芹,2004:279)。
這段文字涉及諸多中華文化的特色內容,特別是“頒瓟斝”這幾個字,若不專門研究,恐怕現今的國內人士都未必能夠參透。其實,“頒瓟”是一種類似葫蘆的植物,“斝”則是古代酒器的名稱,我國素有“頒瓟文化”一說,即在葫蘆生長之時,用斝的模具套在其上,讓葫蘆按照斝的外形長大成型,而后取瓤去籽,風干成為飲茶、飲酒的器具。然而,西方并沒有葫蘆這種植物,有些譯者主張為了順應西方文化,減少文本的陌生感,干脆使用西方人常見的植物來代替,例如將“頒瓟斝”翻譯成為“the pumpkin cup(南瓜杯)”。這種做法看似消除了文化之間的理解障礙,實則改變了原文的內涵性質,使原文的美感與深意皆不復存在,從根本上違背了順應論所一貫遵從的“忠實性原則”,不利于中國文化的傳播。所以,譯者應當尊重作者的文化意圖和審美情懷,“用古器”、“行古道”,運用西方的表達方式和邏輯習慣,傳達中國的古典文化韻味:
One with a handle and the name in unicial characters:Calabash Cup.In smaller characters it bore the inscriptions“Treasured by Wang Kai of the Jin Dynasty”and“In the fourth month of the fifth year of the Yuan Feng period of the Song Dynastry,Su Shi of Meishan saw this cup in the Imperial Secretariat”。(楊憲益,1994:293)
盡管西方讀者可能并不理解晉代、宋代、蘇軾這些名詞的具體意義,但通過后期查閱,可以從中參悟到茶杯是一件歷史悠遠且頗具審美價值的古董,繼而了解到賈府在當時社會中的崇高地位與奢華生活。
再次,茶禮儀是茶道的精髓,也是茶文化的核心要素,是儒家文化的集中展示,也是對道家與佛家理念的藝術化呈現。中華民族擁有悠久的飲茶歷史,各地人民在長期的飲茶活動中逐步養成了獨特的風俗習慣,經過社會文化的洗禮,逐步演變成為一種大家禮數,比如“以茶待客”、“以茶代酒”、“以茶論婚”、“以茶贈友”等。曹雪芹是中國文化的集大成者,對茶禮的研究自然不輸任何一位茶學專家,這一點在《紅樓夢》中就有非常直觀的體現。例如:
豈不聞“一杯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飲牛飲騾了”,你吃這一海便成什么?(曹雪芹,2004:279)
這段文字說明茶乃靈氣之物,應當細細品味,決不可隨意飲用,與陸羽《茶經》中的適度理念不謀而合:“諸第一與第二第三碗,次之第四第五碗,外非渴甚莫之飲”。不過,由于其中并沒有文化性極強的詞匯,譯者能夠很容易把握其中的內涵,因此在翻譯時,譯者可以采取順應目的語行文結構及邏輯思維的策略,擺脫原文的形式束縛,讓目的語讀者在輕松讀懂的情況下了解我國茶文化中趣味盎然的禮儀規范:
You know what they say.One cup for a connoisseur,two for a rustic,and three fro a thirsty mule.What sort of creature does that make you if you drink this bowlful?(Hawkes,1978:769)
最后,茶文化是文學創作的靈感源泉和動力支持,我國茶文化不僅停留在視覺、味覺與聽覺的享受之中,更存在于思想、情感與審美的熏陶之內,借助優美的文字流傳千年、亙古永恒。我國古代文人墨客向來視茶為知己,茶的品節與德性甚至要高于梅、蘭、竹、菊“四君子”,所以他們經常以茶明志,詠茶抒懷,將茶文化融入到詩詞歌賦之中,把飲茶提升到更高的意境,充分展現出飲茶者的精神追求和藝術態度。在《紅樓夢》中我們便能夠找到上述才華橫溢、風流倜儻的人物形象,他們筆墨之下渲染的茶顯得靈動飽滿、蘊意深刻,對于這些詩詞的順應性翻譯同樣耐人尋味。例如:
倦繡佳人幽夢長,金籠鶴鵡喚茶湯。
窗明麝月開宮鏡,寶靄檀云品御香。(曹雪芹,2004:151)
這首詩描繪了大觀園的富家小姐夏日生活的片段:佳人在鸚鵡的陪伴下描鸞刺鳳,品飲上好的茶湯,或是點著御香攬鏡上妝,在水畔亭臺乘涼打趣,疲倦時就慵懶入夢,打發悠閑的午后時光。作者以“金籠”、“宮鏡”、“御香”突出了生活的奢華與安逸,再加上“筆墨點染”的渲染效果,揭開宮鏡后滿室生輝,就如同明月的光輝透過小窗灑滿地板一樣,點上御香后滿室飄香,就仿佛檀云繞梁、美不勝收,點染結合,將貴族家庭的氣派與富貴表現得淋漓盡致。由于詩詞是文化性、地域性、時代性極強的藝術創作形式,在翻譯時應當盡可能地考慮目的語讀者的閱讀體驗,使譯文成為一種再創作,當然這也是以譯者的準確理解為前提的,達到既忠實于原文、又順應于讀者的效果:
Weary of embroidery,the beauty dreams;
In its golden cage the parrot cries,“Brew tea!”
Bright window,moon like musk-scented palace mirror.
Dim the chamber with fumes of sandalwood and incense.(楊憲益,1994:333)
3 結語
茶文化是民族文化與具體飲茶環境相互融合的偉大創造,具有較強的民族性、文化性、歷史性和時代性。對中西方茶文化作品進行翻譯時,譯者應當全面把握原文的內涵意蘊和藝術審美,準確理解目的語環境下的語用習慣、邏輯方式和意識形態,采用恰當的翻譯策略和傳達手段,做到既忠實于原文和作者,又能夠滿足目的語讀者的閱讀需求,順應目的語文化語境的動態變化,最終實現中西方茶文化的相互交流和順利傳播。
[1]楊憲益,戴乃迭.A Dream of Red Mansions[M].外文出版社, 1994.
[2]曹雪芹,高鶚.紅樓夢[M].岳麓書社,2004.
咸陽師范學院專項科研基金重點項目(項目編號:14XSYKO25)。
杜曼麗(1976-),女,陜西咸陽人,碩士,講師,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