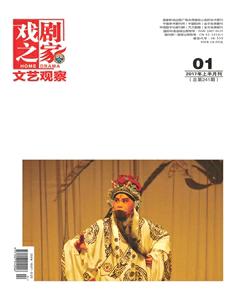欲望的階梯
唐艷玲
【摘 要】由物質文明建構的社會中,人性是一個很難捉摸與固定的復雜構想,影片深入淺出中,向我們做了一個人性的審視。
【關鍵詞】欲望;人性;抉擇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01-0126-02
一部電影可以展示一段奇妙的人生,像《阿甘正傳》里象征希望與幸福的一塊朱古力,讓人回味無窮;它可以是《荒島獵人》中賴以棲息的簡陋林舍,遮蓋庇佑著困境中的心靈與肉體;也可以是《亂世佳人》中濃縮精華的一段魅力人生,讓人心境激蕩。影片向人講述一個法國的天才鋼琴師因為緊張而比賽失敗。生活中萬念俱灰,迫于生計,無意中他成了一個盲人調音師,接觸中他發現人們對于盲人調音師更為友好,小費更高。利欲熏心,他也越來越陷入自己的窺視欲中,不幸卷進一場殺人案中。
剖析解體,一個天才聰慧的鋼琴師,一件無意間的殺人案。本無內在的聯系,可是人的欲望就像一條鐵鏈從這頭一直蔓延增長到另一頭,兩者便有了交集。
故事的構架和節奏敘事,像電影中不斷隨機起伏的音樂,伏筆、開始、過程、高潮即結局的線條敘事,節奏與敘事絲絲入扣。
伏筆中影片開始用7個鏡頭,交代了故事發生的主要人物、事件、場景。一場琴弦的演奏,一個死去的男人,一個裸體的鋼琴家,一個背后的女主。看似混亂的現場,個體之間卻有著無法割裂的聯系,人物的情節排列,暗暗調動了觀眾的觀影興趣和胃口。屬于電影敘事類型中倒敘的手法。
電影中背景音樂是《詩人之戀之十:我聽見有人唱》中g小調,取義于海涅《詩集》,懷念失去愛情的《抒情節奏曲》。曲調哀婉、低沉,調配以男人的獨白,加以突如其來的死亡場景,男主人的生死未卜,種種疑惑,引人心懸一刻,埋下引線。
影片中結尾與開始的巧妙敘事契合,把一半的結尾拿到開頭說,既有心理敘事的鋪墊,也保證了整條線索的完整性和契合性,結構上提升了影片的思想境界。
故事始于一個天才鋼琴師,在自己目標比賽中失敗,這是故事的起因,也是情感的第二個轉折點。影片用七個鏡頭,交代了在空曠的演奏大廳,渺小的主人公。他是享受音樂的,但賽制的嚴苛和殘酷,已經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他無法在眾目睽睽之下展示自己,他的緊張心情猶如影片中緊繃無法舒展的背景音樂。
鋼琴師比賽失敗,生活陷入一片黑暗,迫于生計,他成為了一名盲人調音師。這是故事的中段轉折。
失敗之后的生活,如同影片中鏡頭對于他面前魚缸的刻畫,就像《畢業生》里對于魚與魚缸的刻畫一樣,阿德里安現在的處境如同他面前的被困在魚缸里的那條魚,限制自由,孤獨,無法理解,個人的悲觀情緒被放大化。
迫于生計,他成為一個調音師。為了獲得更多的尊重、理解和關愛,他在一段故事中得到啟發,認為失去比擁有更令人珍惜,于是決定成為一個盲人調音師。決定成為一個調音師,前者屬于迫于生活的無奈,社會壓迫的需求,而后者屬于需求言語化的復雜要求指令,從需求分離出來的,人性的一種貪欲。投機取巧,賺取小便宜的心理。正是由于這種心理的變化,也使他越陷越深。影片中用了兩種對比的手法,一個是來自老板的傲慢無禮的態度,希望吃糖吃死他。而在他成為盲人之后,顧客反而對他照顧有加,勸他少吃糖。這些贊賞,受人尊重,滿足了他的虛榮心。就在得到中,他漸漸變得失去自我的本性,習慣利用自己編織的謊言,去獲得更多的權利和隱私。不斷變本加厲,利用了人們對于弱者同情保護的善良心理,獲得更多的需求。這時一個盲人的身份,使他獲得了比正常人應該享有的更多的特權,他由一個生活的失敗者成了凌駕于人們之上的王者。他享受著這種特權的給予,用他自以為是的聰明欺騙周圍的人,加之實力,不斷獲取更多的利益好處。漸漸的內心的欲望與渴求也不斷地膨脹、扭曲,逐漸產生了窺視欲,由一個生活的弱者變為了社會中叮咬縫隙的食小利者。
影片中,阿德里安渴求來自社會對于他天才能力的肯定,但是他失敗了。這就是為什么影片中他說“他需要這些”,他需要滿足感,需要認可,需要鮮花與掌聲,需要尊重。但比賽失敗,他什么都沒有,他不甘于這種不公正的待遇,迫于生計,加之內心的膽小軟弱,他不得不尋求另一條求生的道路,他的實力,與那么一點聰明,使他成為了一個盲人鋼琴師,他內心急切的渴求和不斷膨脹的欲望,使他的窺視欲望和好奇心不斷增大,這種欲利的驅使,使他越走越遠,最終把他推向絕望的邊緣,無法回頭。
影片中疑點重重,伏筆眾多,又遺留線索。價值體現與意義追尋,讓人深思。結尾中,主人公阿德里安的內心獨白,袒露了隱藏在背后,自己的疏忽和遺漏。即使自己認為表現完美,但是終究逃不出惡人心思縝密的眼睛。女主人四次懷疑男主是不是裝瞎。第一次男主在沒有女主的引導下,自己走向了房間,超出女主的意料。第二次男主坐在鋼琴旁邊,受了驚嚇,呆住了神,女主提醒他。第三次女主摘下男主的眼鏡,檢查男主是否真瞎。第四次女主翻看男主的衣兜,發現真相。影片中鎮定彈琴的阿德里安發現自己的日程本子遺落在口袋,造成了假象的識破。緊跟隨獨白,女主正如阿德里安料想的那樣在檢查翻看他的外衣口袋。隨即,女主沒有拿出干凈的衣服走出來,反而用槍慢慢接近阿德里安的腦袋的時候,同她之前極力撒謊掩蓋她殺人的場景相比,此時她已經識破了來客,得知自己已經暴露,邪惡最終戰勝了那一絲絲憐憫,她撕下了偽裝的面具,想要殺人滅口。
影片處處埋藏著玄機和巧思,不斷讓觀眾發現和解答,故事始終處于懸疑的敘事情境中,觀影思緒被導演左右,并引領到主人公的敘事心理中。影片中,當男主發現正在槍口下時,他企圖用他善良的內心和柔美的鋼琴聲化解女主對于他的敵意,此時鋼琴變為安撫情緒的工具,鋼琴安撫的對象由自己轉到了慘死的先生,再轉到背后危險的女士,主人公自我暗示的情節,變成了導演對于觀眾的一個迷惑誤導。只要鋼琴沒有停下,“彈者”與“殺手”的對峙就不會停下,調音師的生命就沒有結束,造成了影片敘事的結尾,給觀眾帶來不同的觀看體驗和結果。
結局不論是篇首中阿德里安的獨白和彈奏的鋼琴聲戛然而止,還是黑屏傳來的一聲既可以是槍響也可以是男主人公登上臺前的關門的那一刻,更是結局中音樂沒有停止,前者象征著一扇大門把所有的人與事物都關在了門里,封閉起來。后者的結局,更加開放,音樂的延續也象征了人在欲望的道路上無法回頭。
在其他人物設置中,阿德里安的老板抱怨這世界到處都是偷窺狂和暴露狂,在昨天同他聊天兩個小時的女孩就給他發了這樣的照片,每個人身上都有各種欲望和需求,對于美好的追求,偷窺,暴露欲,美與丑,黑與白的對立與交合,都是人們情感心理中共通的地方,它壞的一面,也是人類思想感情進化中未被超越的鴻溝。
欲望的不斷驅使,思想的不斷迷失,一步一步不斷背離正常的生活,人性的階梯把它推向了人生的黑暗處,那里充滿血光、死亡、病態的心理,就連感化人的心靈音樂也無法挽救。
調音師本性是善良的,但人又是善變的,一旦利欲突破了人的心理防線,它可以吞滅一個人的本性,把人引向毀滅的邊緣。這也是自食因果。
參考文獻:
[1]調音的鋼琴師——評微電影《調音師》[J].大眾文藝,2012.
[2]趙偉.拉康的欲望理論新探[J].學術論壇,2011.